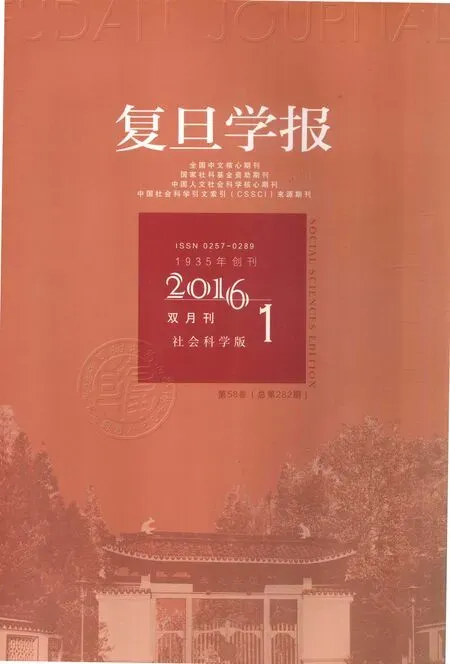中国早期文献稳定性与可信度的矛盾问题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周秦汉唐经典的形成与诠释(笔谈)
中国早期文献稳定性与可信度的矛盾问题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编者按]2015年5月9日,由《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办的“周秦汉唐经典的形成与诠释”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期将与会论文以笔谈形式刊发,以飨读者。本次研讨会还邀请了陈尚君、杨明、汪涌豪、陈引驰、戴燕、马亚中等教授莅临评议,在此谨致谢忱!
众所周知,周秦汉唐是中华文化经典产生的最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籍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钞本时代”。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经典文本的研究,目前似乎处于瓶颈状态,如何前行,令人困惑。可喜的是,国内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同时借鉴海内外学术研究的经验,扬长避短,力辟蹊径,力图从更高的层面上对这一时段的文学进行深入的探索。我想,这种求真务实、转益多师的学术品格,别具重要意义。
孙少华、徐建委两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优秀青年学者。他们以周秦汉唐文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努力科研,积极撰写文章,博观约取,深思熟虑,合作完成了《从文献到文本》一书的撰写,其副标题为: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顾名思义,作者把唐代以前的文本文献作为考察对象,涉及先唐经典、文本文献及钞本传承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如何界定、评价先唐经典,这是见仁见智的老话题,向无定论。中国学问源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所谓“六经”,汉代称为“六艺”。《乐经》不传,古文经学家以为《乐经》实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经学家则认为没有《乐经》,《诗》《礼》之中已包含有乐,只有“五经”。东汉时,“五经”以外,增加《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同《周易》《尚书》《诗经》一起,并为“九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在“九经”基础上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尔雅》三书,称“十二经”,并将十二部经书全部刻石,史称“开成石经”。宋代为抬高《孟子》地位,朱熹作《孟子集注》,并列入经书,于是儒家经典遂有了“十三经”。这是儒家的基本经典,也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典籍。当然,也有以“五经”为基础而扩展增加者。如初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收录汉魏六朝二百余家对《周易》《尚书》《毛诗》等十四部经典的释词、注音等资料。所论“经典”,还包括《尔雅》《老子》《庄子》等。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九)又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现代学者的划分,又有所不同。黄侃认为真正可以称为经典的只有八部,即《毛诗》《周礼》《左传》《史记》《汉书》《文选》《说文解字》《尔雅》。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杭州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姜亮夫先生教导我们要终身研读十二部经典,即:《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老子》《庄子》《楚辞》。这个书目以“五经”为核心,辅之以“三礼”、“三传”。“三礼”中较为难读的《仪礼》没有被列入。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还应当加上《文选》。
从《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的论述范围看,作者心目中的经典,涵义则更为宽泛,还应该包括诸子如《淮南子》《吕氏春秋》一类的典籍,是广义的经典范畴。另外,作者还讨论了先唐的文本文献问题。这与今天所说的文献,不仅包括书面材料,还包括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切载体多有不同,而与《论语》所说“文献不足征也”的“文献”涵义相近,是指记录的各类知识的图书与典章。这类文献数量很多,内容很杂,后来便衍生出一门学问,叫文献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他又说:“我们所提倡的国学,十有九属于这个范围。”在这里,文献与经典便发生了关系。我的理解,孙少华、徐建委两位同志所说的先唐文本文献,大约近于梁启超划定的范围,是狭义文献,并特指先唐文献,也就是早期钞本时代的文本文献。
近年来,“钞本文献”“刻本典籍”“文本演变”等问题,备受海内外古典学界关注。按照后现代理论,钞本时代的经典,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叠加现象。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有的是单一资料来源,也有的是早期多重资料来源,存在大量异文,具有不确定性。今天所看到的众多版本,很难说哪种本子是定本,哪种本子有后人叠加进去的内容。不同性质的文本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这些文本文献,很可能就会出现言人人殊的情况。据此,海外一些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先唐经典的稳定性是不存在的。
但是,问题远不是预设的那样简单。
如果从殷商文字开始算起,传统文献流传至今已有三千多年。汉代以来,佞古思潮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认为现存早期文献都是老祖宗说的,老祖宗写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庄子·天运篇》提到的“六经”就是今天看到的“五经”。宋元以后,人们疑古改经,直至清初,很多经典与史料才重新得到系统的整理。以阎若璩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学者发现,像《尚书》这样的早期文献,其中有很多记载相互矛盾,有必要进行厘清,甚至对文献本身也提出质疑。19世纪末,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出版,2013年圣彼得堡国立孔子学院中俄文对照再版,第330页)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十二种辨伪方法,也将先秦以来流传的很多典籍列为伪托之作。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了学术界近一个世纪。
最近三十多年,地不藏宝。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近百年来出土的甲骨文,更能证明司马迁所见史料具有可靠性。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的品质。
当然,这只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一种形态,其不确定性、可疑性因素依然大量存在。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就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历史文献,更像是历史小说。这也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耳传播,经过世世代代的漫长流传,最后才被写定。在这个流传过程中,口传文献信息不断被累积、删改、演变,最终形成文本文献。如《汉书》中的《哀帝纪》《天文志》《五行志》均记载有流传于汉代的“讹言行诏筹”,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行志》说:“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稾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载体、文字、解读、影响不断变化,说明一个文本文献,从口头传播,到最后定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者、接受者、传播者、阐释者各不相同,所产生的文本内容也就颇多差异。
出现这种情形,至少有主客观两重因素。从客观上说,早期的历史,口耳相传。历史主干为经,较为粗略;后人阐释为传,注重细节。到后来,经传合流,便形成历史。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些经与传,勾画出中国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从主观上说,任何历史都是由人来书写的。有了人,便有了不同的思想。面对同一历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处理。平民历史学家写历史是一种写法,官方历史学家又是另外一种写法。不论是谁,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史料就有不同的取舍,甚至是有意的遮蔽。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文化不高的刘邦、相貌一般的朱元璋,都被历史学家描绘成龙颜“隆准而龙颜”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至于他们的劣迹,则略而不记。秦汉对于历史著述、诸子言论的控制非常严密,像《史记》这样还算比较公允的史书,东汉初年的汉明帝仍诏问班固,批评司马迁“微文刺讥”,东汉末年的王允也视其为“谤书”,禁止其流传。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论衡》中记载了很多六国以来的历史故事,叹为异书。事实上,王充从班彪处看到过一些汉代原始文献,包括《史记》,这里有线索可考,而博学如蔡邕,在进入高层之前则未必有这样的阅读条件。站在今天的立场来推想,从战国末年列国的分分合合,到楚汉八年的血腥纷争,在这样的一段时期里,不知发生过多少动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故事!可惜,只有一部被刘邦认可的《楚汉春秋》(陆贾著)残存于世,其精华部分被《史记》收录,而其他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献则烟消云散,以致后世没有产生一部类似《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小说,来描绘这段跌宕起伏的宏阔历史,真是遗憾!显然,这是统治集团有意控制和选择的结果。魏晋以后,当权者对于民间的掌控已力不从心,所以才会有三国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箭垛式的人物亦越来越丰满,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讲唱文学逐渐成熟,最终推出了《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从此,历史与小说分道扬镳。历史俨然以公正、真实相标榜,但在实际的叙述中,如前所述,由于立场的不同,对于材料的取舍便大不同,结论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在同一叙述者的著作中,也常常会有前后矛盾的记载。历史著述中的这些有意无意的错误,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无意的错误可以理解,由于闻见有限,根据一些主观臆测充实历史文本,很可能会与史实相违背。而有意的错误更是不在少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清代顾千里就主张“不校之校”,认为中国的典籍,毁就毁在历次的校勘整理上,校一次错一次,逐渐失却原貌。
由此看来,中国早期文献的抄撰与流传过程非常复杂。其稳定性与可信度的矛盾无处不在。余嘉锡《古书通例》对此有客观的分析,要言不烦,很有说服力。他告诉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不能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也不能因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问题,凡事都要具体分析。这应当成为我们对待中国早期文献所应持守的基本原则。
孙少华、徐建委二位同志在撰写《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中,努力恪守这一原则。全书紧紧围绕先唐文献的歧异与文本形成等核心问题,从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入手,或宏观考察,或微观分析,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首先,作者充分注意到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的“历史性”与“时代性”问题。作者指出,阅读先唐文献,必须深入考察其产生的文化、历史、思想渊源,同时又要注意其所处时代的学术、社会、政治需要,避免将文本文献研究简单化与程式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文本而忽略其演变的细节。作者认真比对了《淮南子·主术》与《吕氏春秋》两书所引的相同文献,认为编纂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处的地域、时代,以及编纂古书的目的、文本性质等不同,决定了文本文献中的文字表述、文本风格的差异。汉代人的“阅读习惯”“阅读思维”使得他们在整理先秦文献的时候,既有对先秦文献的较多改变,也有可能完整保留,一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指出了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流传过程的复杂性与多系统性。文本文献是多层次、多系统的工程,其经典化也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文选》所收左思《蜀都赋》,李善注引扬雄《蜀都赋》加以充实印证,读者可以接触到正文与注文两种文本,突破了单一选本的阅读限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选本、注文以及二者重新组合而成的新的文本文献,拓展了读者的思考空间,从而有可能改变读者最初局限于选本正文而产生的误读,起到“纠偏”的作用。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选本的原貌与编者的最初设想。这就是早期文本文献选本与注本的特殊作用。这个问题很有趣,值得继续探讨。
最后,为了印证上述两点认识,作者广泛考察了秦汉以来流传的“公共素材”,用以说明这些材料是如何改变历史叙述的。作者选择了两个重要节点展开自己的论述。第一个节点是两汉之际。西汉后期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先秦典籍,编纂《别录》与《七略》,东汉初年的班固在刘向、刘歆父子成果基础上编修而成《汉书·艺文志》。汉代对文献的整理,在客观上将先秦学术文化框架定于一尊,后世很难超越。这是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第一次系统整理的结果。第二个节点是唐宋之际。我曾经在《钞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一文中说过:在中华文化史上,唐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早期经典文献,大多定型于这个时期。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咸通九年印制《金刚经》,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此前,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推进儒家经典化进程,包括编纂“五经正义”、校刻“开成石经”,但是传播终究有限。随着宋代刻书事业的发达,文化经典走进千家万户,经典化工作也相应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文本到文献——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毛诗诂训传》为底本,仔细勘对《毛诗正义》注疏中的三百多条异文,深入考察了宋人是如何将这些异文整齐划一,最终完成经典化的定型工作的。不仅如此,本书作者还以《晋书》为例,重点讨论了这部唐代文本的独特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作用于历代读者的阅读想象之中,形成后来关于魏晋时代的“整体历史形象”。这些,都是让人很感兴趣的话题,很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在以往阅读中固化下来的观念,甚至改变文学史叙事的僵化格局。
其实,中国古代学术还有一个重要节点,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形成的学术传统,它与前两个节点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术的三大传统。周秦汉唐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尝试解决20世纪学术传统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要做到视野广阔,上及先秦两汉,下至唐宋明清,甚至到近现代,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周秦汉唐。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