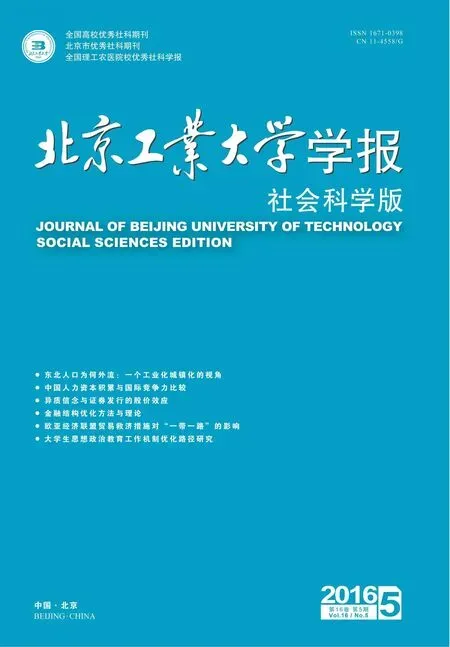社会工作视野下失独家庭问题研究现状与前瞻
陈 锋, 李玉芬
(1.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124;2.北京工业大学 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124)
社会工作视野下失独家庭问题研究现状与前瞻
陈锋1,2, 李玉芬1
(1.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100124;2.北京工业大学 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100124)
失独家庭理论的研究最初以问题视角为主,对全面认识和了解失独家庭相关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但问题视角对失独家庭成员的潜能和资源的挖掘缺乏关注,而优势视角对失独家庭的问题研究则是一个弥补。在实务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实际的干预,探索相关实务介入方法,实现了失独家庭问题研究从“理论”向“实务”的范式转换,但就整体而言实务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失独家庭的社会政策研究中,研究者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2个范畴探讨了现有政策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但是失独家庭的社会政策定位尚不明确,并且相关具体政策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失独家庭的研究可以通过增加行动研究的数量、深化相关实务研究、加强失独家庭的分类研究、明确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定位和细化相关社会政策的研究等方面来拓展失独家庭问题的研究。
失独家庭; 社会工作; 理论研究; 实务研究; 政策研究
引言
“失独家庭”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提出始于2012年5月9日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此后失独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目前关于失独家庭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界定,概念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失独长者年龄的限定和对失独家庭范围界定2个方面。在失独长者年龄方面,王广州等根据计划生育政策将失独家庭界定为:“父母年龄在49岁以上、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的家庭。”[1]但部分学者则不同意49岁的年龄限制,如陈柏涵认为:失独是指一个家庭中的独生子女由于疾病或意外等原因死亡,而父母丧失生育能力并且没有另外收养子女的状况[2]。在失独家庭范围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失独家庭只包括独生子女死亡的家庭[1-2]。有的学者不同意这一界定,如学者穆光宗提出失独家庭还包括如下4类相对失独现象,即因病残而失独,因失踪而失独,因不孝而失独,因空巢而失独[3]。综合以上的概念界定,同时借鉴失独家庭救助政策里提及的限定标准,本文将失独家庭界定为父母双方年龄都在49岁以上,独生子女意外死亡或伤残,并且不再领养及生育子女的家庭。
近几年失独家庭问题的严重性逐渐引起政府和相关学者的关注。从失独家庭数量上看,失独家庭数量大且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至少有100万个这样的“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的速度在递增[4]。据人口学家易富贤推断,不久之后的中国,可能会有1 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5]。从失独家庭呈现的问题看,失独家庭问题复杂且难以介入。宏观层面,失独家庭面临一系列政策制度的缺失,如失独家庭补助定义模糊且标准偏低、补助门槛过高、收养制度和入住养老院签字制度不合理等;微观层面,失独家庭面临养老、经济、心理、家庭关系调试和社会融入等方面的问题。失独家庭问题的大量存在既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不符合广大失独家庭的根本利益。学者陆学艺、景天魁均强调了促进社会公平和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6-7]。因此,有关失独家庭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改善失独家庭自身状况都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工作方法,在介入失独家庭问题方面有自身的优势,因此相关学者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研究失独家庭相关问题。概括来说,既有的研究主要有3种类别:一是关于失独家庭的理论探讨,二是关于失独家庭的实务研究,三是关于失独家庭的政策研究。这3种类别的研究对于失独家庭问题的理解和介入有哪些可借鉴的成果?应当如何进一步推进失独家庭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将通过对既有的3类研究的梳理和反思,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对研究的不足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拓展空间。
一、失独家庭问题的理论研究
目前关于失独家庭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多,其研究侧重对问题的解释和分析,研究者借助相关理论视角,分析和解释失独家庭的相关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性建议。总的来说,目前遵循这一路径的研究有2类,即问题视角取向和优势视角取向。
(一)问题视角下的失独家庭问题研究
这类研究从问题视角出发,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失独家庭存在的问题,探讨“失独”现象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方向性建议。
较多学者采用社会支持理论分析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方曙光最早针对失独家庭生活现状及社会支持网络进行了定量研究,分析了失独家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重建的相关策略[8]。在此基础上,学者王勇[9]和王秋波[10]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状况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关注失独家庭整体的社会支持体系状况,此后一些学者分别就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中某一方面的状况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学者马一、冉文伟、谢勇才和董丽晶等分别从政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现有的失独家庭社会救助体系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了政府建立健全失独家庭救助制度的责任,指出现有的失独家庭救助制度还存在着扶助内容狭窄、保障水平偏低、制度覆盖面不高和责任主体单一等方面的问题[11-14]。这些学者从政策视角出发做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健全失独家庭救助政策提供了依据。另外一些学者从服务的视角切入,分析了目前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的不足。王雪辉分析了失独家庭社会服务体系发展不足,提出构建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个人四位一体的失独家庭社会服务体系[15]。陈盼盼通过对广州市的10位失独老人的访谈和分析,提出了以社区为依托,构建失独老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三角社区照顾模式[16]。陈恩通过实地调查探讨了失独群体自组织在构建失独家庭社会服务支持体系和促进失独家庭社会再融入的作用[17]。这些研究为建立和完善失独家庭的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了参考。
在社会支持理论视角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其他理论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失独家庭在心理、家庭关系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的问题。据调查,心理问题是大部分失独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如陈雯对湖北省307位独生子女死亡的家庭调查显示:76.9%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心理正常状态人群仅占11.4%[18]。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者通过访谈,深入探讨了失独者的心理状况,如徐琦通过对14名失独者的深度访谈,在主体建构的视角下运用叙事解读的研究策略对访谈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发现失独者在回顾经历生命重击的历程中,分别经历了绝望期、迷失期和重塑期,失独者在各个时期的主体认知与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并指出“失独父母”往往难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顺利从痛苦的承受期向缓解期过渡[19]。失独家庭除了在心理上面临困扰之外,家庭关系上也存在相应的问题。 如张必春等从失独家庭的家庭稳定性视角出发,指出失独家庭存在家庭结构失衡和家庭功能紊乱2个方面的困扰[20]。赵仲杰从家庭结构的视角出发,发现独生子女伤残、死亡会导致父母提前离世或者夫妻关系破裂,而独生子女作为“唯一承担者”角色,一旦离世便会使家庭丧失人口再生产、赡养和情感交流功能[21]。在遭遇心理危机以及家庭危机之后,失独家庭还面临着社会融入的困境。如谭磊指出:失独家庭在社会融入方面表现出自我封闭,生活适应障碍以及解决问题能力低下等现象[22]。一些学者指出:失独家庭本身就是风险家庭,面临多重的风险和困境,如杨勇刚等指出了失独老人面临的制度风险、经济风险和自身风险等养老风险[23]。向徳平等从风险——脆弱性视角出发,指出失独家庭面临多重困境,提出要将外部支持体系建设和内部发展能力相结合,以消减失独家庭面临的风险和降低失独家庭的脆弱性[24]。这些研究有助于启发我们多角度思考失独家庭的相关问题。
除了关注失独家庭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失独”这一现象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如侯秀丽等探讨了失独现象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及影响,指出失独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25]。陈伟杰从个体、社会和公共秩序三重视角,分析了失独现象所引发的相关问题,提出构建地方社会工作合作平台,通过平台的运作纾解失独者的个体困境,以削减其不满,实现组织地方化,满足其表达的需要,使失独者实现蜂巢式的集聚,以其所在社区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为基本的诉求对象,从而降低大规模横向联合及其激进化的可能性[26]。这类研究提醒我们在关注失独家庭自身问题的同时,也要关注“失独”现象可能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
(二)优势视角下的失独家庭问题研究
2)当取值范围在[xnmin,xnmax]以内,且第n维信息已失效,则FC取为接近于1的较大值,使试验向量尽可能获得目标向量信息;
问题视角在初步呈现失独家庭的现状、原因解释及其社会影响方面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通常更多在较为宏观层面进行解读,对失独家庭的微观关注相对欠缺,同时对失独家庭如何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则欠缺探讨。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学者从优势视角出发挖掘失独家庭的潜能和资源,为解决失独家庭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谢启文从社会工作的增能视角出发,认为失独家庭作为特殊弱势群体,处于一种消权状态,从个体主动和外部推动2个模式对失独家庭进行增能,可以帮助失独家庭恢复基本权能,提高其生命质量,保证其安度晚年[27]。郭庆等运用家庭抗逆力的理论框架,认为失独家庭结构处于“拔根”状态,提出构建系统的保护性因素支持机制,以社会建设的高度实现失独家庭重新“扎根”[28]。学者肖云等则运用优势视角的基本理念,指出个人、团体、社会应共同帮助他们抚平精神创伤,改变外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使其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优势与其生活环境的整合,以逐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安享晚年[29]。王文静等从优势视角出发,认为对失独家庭的救助策略需要融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专业方法,将现有的注重经济支援的“生存型救助”策略转向关注失独家庭成长的“发展型救助”策略。针对失独家庭个体情绪、家庭发展以及社会再适应等生存困境,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进行介入,帮助失独家庭挖掘自身潜能,恢复家庭功能,最终走出多重困境,实现社会再适应和自我实现的目标[30]。这一研究视角为解决失独家庭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启发我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时候能关注服务对象自身的优势。
目前关于失独家庭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流,本质上是一种侧重解释与分析的研究范式。这一类研究从“问题”与“优势”2个视角出发,运用相关理论分析了失独家庭在社会支持体系、心理、家庭关系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失独”现象可能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借助增能理论、家庭抗逆力理论和优势视角理论分析了失独家庭存在的优势和资源。分别从“问题”和“优势”2个视角提出了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可能性策略。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失独家庭的相关问题,了解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相关策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知识性材料。但是这类研究更多地着眼于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失独家庭的现状和问题,对于失独家庭问题的干预却没有进一步的实务研究,使得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知识层面的讨论,提出的相关对策建议不一定能达到真正的救助目的。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除了理解社会、描述社会现象以及解释社会的运作、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外,更需要在实务层面进一步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和路径。
二、失独家庭问题的实务研究
为了弥补理论视角研究的不足,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对失独家庭成员情绪、心理以及生活方面展开具体的帮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实务反思。
针对失独者出现的情绪问题,如情绪低落与愤怒等,较多的研究者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进行了干预,根据研究者的结案评估,大部分的案主情绪有了较大的缓解,干预效果良好[31-34]。研究者的干预方式主要有2种:一是直接干预。运用个案会谈的技巧,如倾听、鼓励支持和同情心等,协助案主进行情绪宣泄,为案主提供情绪支持。二是间接干预。通过链接案主的亲人和朋友为案主提供情绪支援,链接社区的志愿者为案主提供精神慰籍。既有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工作的相关工作方法和技巧能有效地应对失独家庭成员的情绪问题。
针对失独者在经济和生活上面临的困难,研究者链接相关资源,为失独者提供帮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失独者的困难[32-35]。较多的研究者采用了以下2种干预方式:一是向失独者亲人、朋友或者社区链接相关的物质资源,缓解失独家庭的经济困难。二是链接社区的人力资源,开展志愿者帮扶等活动,为失独家庭提供生活帮扶。这些帮扶行动能让失独者感受到来自外界的支持,不仅有利于失独家庭维持正常的生活,也有助于失独者情绪的恢复。但是这种帮扶多半来自于非正式的渠道,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部分研究者尝试为失独者做心理辅导,希望协助失独者走出哀伤,恢复正常的生活。既有的研究尝试通过同质群体互助的方式,为失独家庭开展心理帮扶。如链接已经恢复的失独者,为服务对象进行心理疏导[34],为服务对象开展互助小组[36]服务。但是由于心理辅导难度较大,需要的时间较长,对帮扶者的专业水平要求也较高,因此,目前的研究者都处于尝试阶段,帮扶过程尚未形成系统,帮扶成效非常有限。
以上是社会工作者对于帮扶失独家庭进行的相关实践,这些实践为失独家庭的实务干预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学者黄耀明进一步将帮扶的实践和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行动研究的方法介入失独家庭的重建,展示了社会工作行动研究方法帮扶失独家庭生活重建及社会工作支持体系建构的实务介入经验。具体呈现了实践探索过程中失独问题泛化、失独问题外化、生命价值重塑、失独者互助、家庭重建等焦点工作策略[37],为失独家庭的实务干预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总的来看,实务研究的核心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取向,研究者通过实际接触研究对象,探索相关实务介入方法,实现了失独家庭问题研究从“理论”向“实务”的范式转换。与前一种研究侧重理论分析相比,这一种研究通过实务的干预,在失独家庭情绪疏导和经济与生活帮扶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干预方法。在失独家庭的心理辅导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尤其是学者黄耀明针对失独家庭开展的行动研究,为失独家庭的帮扶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目前这类研究还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数量少。目前除了学者黄耀明的研究外,期刊网上几乎找不到其他关于失独家庭的实务研究,既有的研究大多是社工专业学生在毕业论文中做的探索性研究,并且研究选取的样本量都非常小,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不足。二是研究深度不够。目前针对失独家庭的实务干预基本上还处于浅层次,主要集中在情绪疏导以及经济与生活的帮扶。对于失独家庭的心理辅导还处于尝试阶段,干预成效有限,未能形成系统的和有效的经验。在失独家庭的家庭关系调试和社会融入方面还几乎未有涉及。三是缺乏分类研究。不同类别(失独原因、失独年限、失独者性别以及失独家庭经济状况)失独家庭的具体问题呈现也会有所不同,目前的研究却没有针对不同的失独家庭做分类的研究,所以相关研究指向性和针对性不强。
三、失独家庭问题的政策研究
健全的社会政策是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保障,因此学者从失独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分析现有的相关政策的不足,进而提出相关的建议。目前遵循这一路径的研究主要有2类:一是社会救助的研究;二是社会保障的研究。
部分学者将失独家庭的现实问题纳入到了整个社会保障的范畴进行探讨[38-43]。一些学者分析了现有的关于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如谢勇才等指出:政府在失独群体社会保障制度中责任的缺失,包括在失独群体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不健全,失独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缺乏顶层设计,中央财政在失独群体社会保障制度中责任缺位以及失独群体社会保障制度责任主体之间关系紧张4个方面。建议政府应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加强法制建设、做好顶层设计、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和协调责任主体之间关系等方面完善失独群体社会保障制度[38]。另一些学者分析了失独父母的社会保障诉求的特征。如谢勇才等在对失独父母的社会保障诉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具有诉求对象指向政府和理想诉求与现实诉求并存的特征。据此提出健全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关建议[43]。
另外一些学者将失独家庭的问题纳入到了社会救助的范畴进行了探讨[11,13,44-52]。部分学者综合分析了现有失独家庭社会救助政策的不足,强调了政府在健全失独家庭社会救助制度中的责任[11,13],并提出了综合性的建议。如谢勇才等指出:现有的扶助制度存在内容狭窄、保障水平偏低、制度覆盖面不高和责任主体单一等诸多问题,并提出政府应当从完善扶助内容、提高保障水平、扩大制度覆盖面和引入多元主体等方面来完善失独家庭扶助制度[13]。马一指出:目前的失独家庭救助制度无法突破法理论和立法的局限,因此建议政府建立全方位的失独家庭救济机制[11]。另外一些学者从某一方面的救助政策出发,具体分析了失独家庭不同方面救助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如谢勇才等分析了失独家庭特殊医疗困境的成因,指出手术签字难等是失独家庭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47]。曾维涛等分析了失独家庭经济救助政策存在的不足,指出当前的失独家庭经济扶助政策存在国家扶助标准偏低、区域差异较大、动态调整机制不成熟、政策服务不完善、扶助方式和渠道单一等诸多问题,建议通过完善的动态调整机制、改善政策服务、改进扶助方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现有的失独家庭经济扶助政策[52]。
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政策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研究。如方曙光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失独老人存在社会政策支持、社会交往和社区融入等方面的缺失。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影响失独老人社会生活重建的包括社会政策,指出了健全失独家庭社会政策的必要性[53]。慈勤英等指出:单向的偏重失独家庭苦难的报道倾向,部分建构了一个“无解”“苦难化”“特殊化”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的“媒介形象”和“独生导致失独”的逻辑暗示。这种媒介关注的“标签化”背后有部分学者研究定位、价值指向和政策建议的支持,这种标签化不利于失独家庭融入社会,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误读和抨击,因此建议去标签化,并将失独特别扶助政策整合于社会救助体系中[54]。
目前这类研究主要是从失独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分析现有社会政策的不足并提出相关的完善政策。既有的研究分别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范畴探讨了现有政策的不足以及完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政府健全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而健全的社会政策乃是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保障。但是目前关于失独家庭社会政策的研究还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失独家庭的相关政策究竟是应当纳入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来考虑,还是仅纳入到社会救助或者社会保险的范畴尚没有统一。其次,关于失独家庭某一方面的具体政策的研究较少,较多的学者从整体上分析了现有保障和救助政策的不足,而对于具体的经济、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缺乏。
四、结论
已有的研究分别从理论、实务和政策层面丰富了失独家庭的相关研究,为解决失独家庭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同时为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但是目前社会工作视角下失独家庭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的不足。
(1)目前关于失独家庭社会工作研究较少,并且既有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侧重对失独家庭相关问题的理论分析,实务研究非常缺乏。社会工作是一门综合的应用性科学,与其他学科研究关注对问题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不同,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失独家庭研究应当更加注重探索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实务介入方法。
(2)实务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深度和广度都不够。目前针对失独家庭的干预,还停留在情绪疏导、经济和生活帮扶等一类问题上,对于深层次的心理问题的干预还处于尝试阶段,未形成系统的和有效的干预方法。有关失独家庭关系调试和社会融入等问题的干预几乎还未涉及。
(3)缺乏分类研究,既有的研究不论是对失独家庭理论方面的研究,还是对失独家庭实务的研究都没有区分不同类别(性别、年龄和失独年限等)的失独家庭。
(4)政策类研究对于失独家庭的社会政策定位尚不明确,关于失独家庭具体政策的研究较少。
根据对现有研究状况的梳理反思,未来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失独家庭问题研究可从4个方面努力。
(1)加大失独家庭问题的行动研究,在关注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实务干预的重视,将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失独家庭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提升理论研究的实践说服力,为解决失独家庭提供更多科学的和具体的专业方法。
(2)深化和扩展失独家庭的实务研究。对失独家庭面临的心理问题做更系统和深入的干预研究,关注失独家庭关系调适及社会融入方面实务干预的研究。
(3)加强分类研究,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以及不同失独年限的失独家庭做专门的分类,提高研究的针对性。
(4)明确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定位,并进一步细化失独家庭相关社会政策的研究。
[1] 王广州, 郭志刚, 郭震威. 对伤残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人数的初步测算[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1): 37-43,95-96.
[2] 陈柏涵. 失独之痛, 何以所依?[J]. 中国社会工作, 2013(2): 16-18.
[3] 穆光宗. 失独父母的自我拯救和社会拯救[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3): 117-12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0.
[5] 杨晓升. 失独中国家庭之痛[M]. 西安: 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 29.
[6] 陆学艺. 加快社会建设: 我国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3(2): 1-6,18.
[7] 景天魁. 社会管理创新与福利社会建设[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2(1): 1-5,20.
[8] 方曙光. 社会断裂与社会支持: 失独老人社会关系的重建[J]. 人口与发展, 2013, 19(5): 89-94,109.
[9] 王勇. 关于构建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的思考[J].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14(5): 24-25.
[10] 王秋波. 我国构建“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研究[J]. 理论学刊, 2015(4): 92-96.
[11] 马一. 当代中国失独家庭救济机制的系统建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42-51.
[12] 冉文伟, 陈玉光. 失独父母的养老困境与社会支持体系构建[J]. 新视野, 2015(3): 106-111.
[13] 谢勇才, 王茂福. 失独家庭扶助制度的问题与出路研究——基于全国22个省《失独家庭扶助制度实施方案》的分析[J]. 江淮论坛, 2015(5): 131-135.
[14] 董丽晶, 杨威. 失独老人社会救助体系建构探究[J]. 理论导刊, 2015(11): 12-14.
[15] 王雪辉. 失独家庭的社会服务体系构建[J]. 人口与社会, 2015, 31(4): 60-68.
[16] 陈盼盼. 失独老人社区照顾的模式[J]. 重庆社会科学, 2015(6): 47-54.
[17] 陈恩. 重建社会支持网: 失独群体自组织形成机制探讨——基于上海的两个案例[J]. 北京社会科学, 2014(11): 55-60.
[18] 陈雯. 从“制度”到“能动性”: 对死亡独生子女家庭扶助机制的思考[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2(2): 114-120.
[19] 徐绮. 绝望·迷失·重塑: 失独者生命意义的主体建构[D].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2014.
[20] 张必春, 陈伟东. 变迁与调适: 失独父母家庭稳定性的维护逻辑——基于家庭动力学视角的思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52(3): 19-26.
[21] 赵仲杰. 城市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给其父母带来的困境及对策——以北京市宣武区调查数据为依据[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25(2): 55-59.
[22] 谭磊. 论社会工作视角下失独父母的社会融入问题[J]. 东疆学刊, 2014, 31(3): 82-86.
[23] 杨勇刚, 胡琳娜, 马刚. 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失独老人养老风险化解机制——基于对河北省保定市的调研[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9(2): 100-106,159-160.
[24] 向德平, 周晶. 失独家庭的多重困境及消减路径研究——基于“风险—脆弱性”的分析框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55(6): 60-67,172.
[25] 侯秀丽, 王保庆. 我国失独现状的分析与思考[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3): 92-102.
[26] 陈伟杰. 地方社会工作合作平台推进下的失独问题化解——基于个体困境、社会问题和公共秩序的三重视角[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52-59,77.
[27] 谢启文. 增能: 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新视角[J]. 人口与发展, 2013, 19(6): 104-109.
[28] 郭庆, 孙建娥. 从拔根到扎根: 家庭抗逆力视角下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及其干预[J]. 社会保障研究, 2015(4): 21-27.
[29] 肖云, 杨光辉. 优势视角下失独老人的养老困境及相应对策[J]. 人口与发展, 2014, 20(1): 107-112.
[30] 王文静, 王蕾蕾, 闫小红. 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社会工作视角下失独家庭的救助策略[J]. 新疆社会科学, 2014(5): 119-123,162.
[31] 方超. 优势视角下的失独家庭个案工作介入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15.
[32] 王文涛. 个案工作介入“失独家庭”的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4.
[33] 王芬. 社会工作介入失独家庭养老服务问题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4.
[34] 王竹韵. 增能理论视角下“失独家庭”心理调适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15.
[35] 王雨婷. 基于增能视角的失独家庭社区工作介入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4.
[36] 赵宗宇. 失独老人社会工作介入的个案研究[D].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2014.
[37] 黄耀明. 失子之殇: 社会工作介入失独家庭重建的本土化探索[J].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2014(1): 128-148.
[38] 谢勇才, 王茂福. 论我国失独群体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J]. 中州学刊, 2015(1): 68-72.
[39] 睢党臣, 彭庆超. 农村计生家庭养老保障的现实境遇[J]. 重庆社会科学, 2015(9): 72-80.
[49] 贾锋. 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权的国家保障[J]. 理论探索, 2014(2): 115-120.
[41] 谢勇才, 王茂福. 我国发达地区失独群体社会保障模式比较与对策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4(11): 107-114.
[42] 王茂福, 谢勇才. 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以北京模式为例[J]. 兰州学刊, 2013(7): 91-96.
[43] 谢勇才, 丁建定. 失独父母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失独父母四份诉求书的分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6): 78-82.
[44] 周伟, 米红. 中国失独家庭规模估计及扶助标准探讨[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5): 2-9,126.
[45] 陆杰华, 卢镱逢. 失独家庭扶助制度的当下问题与改革路径分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6): 33-38.
[46] 曾维涛, 熊小刚, 朱椿荣. 我国失独家庭经济扶助政策分析及其完善对策[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5(3): 42-50.
[47] 谢勇才, 王茂福. 失独父母特殊医疗困境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11): 12-17.
[48] 崔喆, 刘智勇. 多角度入手完善我国失独父母扶助体系[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4(5): 96-97.
[49] 谢勇才, 黄万丁, 王茂福. 失独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探析——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J]. 社会保障研究, 2013(1): 72-79.
[50] 黄建. 失独家庭社会救助问题研究[J]. 理论探索, 2013(6): 62-66.
[51] 刘亚娜. 中国失独者贫困状况及救助体系建构[J]. 社会科学辑刊, 2013(5): 46-50.
[52] 曾维涛, 熊小刚, 朱椿荣. 我国失独家庭经济扶助政策分析及其完善对策[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5(3): 44-50.
[53] 方曙光. 社会政策视阈下失独老人社会生活的重新建构[J]. 社会科学辑刊, 2013(5): 51-56.
[54] 慈勤英, 周冬霞. 失独家庭政策“去特殊化”探讨——基于媒介失独家庭社会形象建构的反思[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2): 34-42,126-127.
(责任编辑刘健)
Presen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CHEN Feng1,2, LI Yu-fen1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Beijing Society-Building & Social Governance,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The theory research on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focu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s at first and it could really help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s ignored the abilities and resources owned by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s was a supplement. The practical intervention research explored the conditions of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and the pract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by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 practices. This type of research shift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n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from “perspective of theory” to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intervention”, while it was still at primary stage as a whole. The social policy research discussed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policies and offere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from two categorie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assistance. While the orientation of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social policy is not clear and the research on specific policies is not sufficient. As a summary, w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ractical intervention research and research classification as well as making an intensive study of the micr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family members, clearing the orientation of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social policy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research on specific policies.
the lost only child family; social work; theory research; practical intervention research; social policy
2016-06-08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科技基金资助
陈锋(1985—),男,福建永泰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博士
C 913.1
A
1671-0398(2016)05-0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