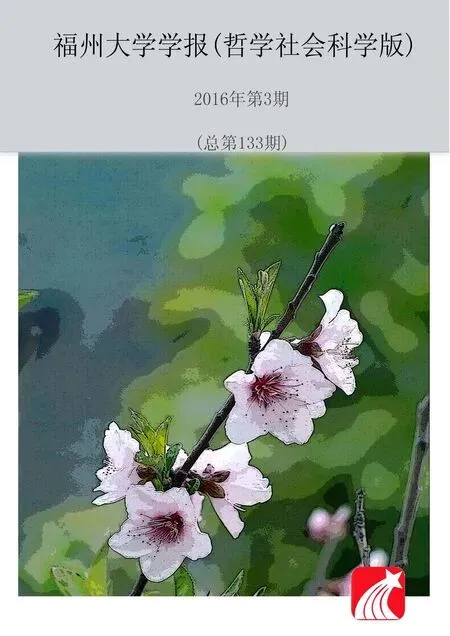唐宋福建海上交通与对外佛教文化交流
谢重光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唐宋福建海上交通与对外佛教文化交流
谢重光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系统梳理汉晋以来福建的海上交通情况,可以看出自唐中叶开始,福建的海上交通迅速发展,至宋代进入海上交通繁荣、海上贸易兴盛时期,其标志是泉州港的崛起与福建执造船业之牛耳。泉州之外,宋代福建其他地区的海上贸易也有较大发展,而以福州为突出。伴随海上贸易而兴的对外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交流为最盛。据此可以重点考述福建与东北亚新罗、日本进行海上贸易与佛教文化交流的情形。
关键词:唐宋; 福建文化; 海上交通; 佛教交流
一、唐宋福建海上交通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得自然条件之便,滨海的闽越人与其北临的吴越人一样,自古就有与大海打交道,在海上讨生活的特长。所谓“以船为车,以楫为马”[1],是古文献对于滨海越人靠海吃海生活的生动写照。但这条资料所反映的主要还是江河运输与近海捕捞,长途的海上交通虽然也有,终归不是很发达。东汉时有一条材料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在今福州附近,说明当时的闽江海口充当了岭南向朝廷贡献物资的海运中转站,但其时这条海路“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代价极大,不久郑弘奏开五岭中的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2]可见一度起用的岭南经东冶往北方的海路运输被陆路运输所取代,也足见当时东冶尚未成为正常的商港。
南朝时也有两条关于福建海上交通的资料,其一是唐初释道宣的《续高僧传》所载,我国佛教翻译史上四大名僧之一天竺拘那罗陀,华名真谛,梁代泛海来中国,至陈永定二年(558)“还返豫章,又上临川、晋安诸郡”。当时的晋安郡辖今福建东部,福州、泉州都在当时晋安郡的范围内。陈文帝时真谛自江表“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3]关于梁安郡的地望,有主张在今泉州南安的,甚至说南安九日山的翻经石,就是真谛在此译经的遗迹。但也有推断是广东惠州的,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根据这条史料,真谛到过福建是事实。但他从豫章经临川至晋安,走的是陆路,不足以说明福建的海上交通情况。只有在梁安郡确是今泉州南安的情况下,才能确证南朝福建的海上交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二是《法苑珠林》的一条材料,说陈太建初(569-),泉州严恭从家乡用船载物到扬州市易[4],足以说明其时福建与江浙确有海上航路及海上贸易往来。陈代的泉州即晋安郡,辖区涵盖今福建东南部,但严恭是泉州长乐人,所以这条材料具体反映的是福州与江南互通海上贸易的情况。
隋代福建海上交通的情况,见于杨素平王国庆之役。“泉州人王国庆,南安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诸亡贼皆归之。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素泛海掩至,国庆惶遽,弃州而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路追捕。”后来王国庆为了输诚于杨素,擒斩了浙江贼帅高智慧,而高智慧曾拥有“船舰千艘”,王国庆能够击败高智慧,其水军实力必定相当雄厚。杨素统率的舟师无疑也是很强大的。[5]是役杨素、高智慧、王国庆的舟师往来于浙江福建之间,说明其时闽浙之间的海路畅通,不过一般只用于军事上,由于海路艰阻,商业往来还比较少。
这种状况,至唐中叶略有改观。唐中宗嗣圣中(684),有胡商康没遮过漳州漳浦县温源溪,“将浴,投十钱,泉为涨溢,浴毕,泉复如故”[6]。这里提到的胡商康没遮,从姓氏判断,或为中亚康国人。中亚商人到漳州,可能自陆路来,也可能由海路来。若其来自海路,说明唐前期福建与海外的商贸往来已较前进步。但迄至唐中叶,福建的对外贸易港口尚不完备,就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来说,海路还很艰阻,海上通商的记载只有零星几条,福建的海外贸易真正趋于繁盛,还应是唐中期之后的事。近来有人任意拔高唐代福州海上交通的地位,甚至说盛唐时福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此说凭空臆造,于史无征,不足据信。
唐中叶后,福建的海上贸易地位提高,主要表现是泉州港逐渐崛起。诗人包何有《送李使君赴泉州》一诗曰: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市井十洲人”说的是泉州居民五方杂处,包括来自海外十洲的各国蕃客入居,“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说的是海外蕃客以朝贡贸易的名义前来泉州经商,从而入居或活动于泉州。包何生卒年不详,约略活动于天宝末年前后,所以此诗反映了唐中叶泉州海外贸易繁荣的情况。
晚唐诗人薛能有一首《送福建李大夫》诗,说福建“船到城添外国人”[7]。诗中李大夫是指乾符二年至三年任福州刺史兼福建都团练观察使的李诲。[8]“船到城添外国人”之城,诗中没有确指是那一座城,可能是福州,也可能是泉州。但结合唐大和八年(834)唐文宗的诏书来看,应该是泉州。文宗诏书令有关节度使、观察使应对“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常加存问”,“接以恩仁”,减轻苛税,“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9]当时福建只有泉州设有专门机构主管“舶脚收市”。那么,其时在福建,像薛能诗谈到的那样,有外国船进进出出,外国人在市井来来往往的城市,自是以泉州的可能性为大。
唐后期泉州港的崛起,为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五代闽国政权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则为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闽国王氏政权在开拓海外贸易方面,是福州、泉州南北一齐着力。在福州,王审知针对此前闽疆税重,百货壅滞的弊病,“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又因“海上黄崎波涛为阻”,派人“凿开为港”,号为甘棠港。[10]由此大大便利了闽国的内外贸易,“赡水陆之产,通南北之商”[11]。他还大力“招徕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12]。其开明、开放的外交、外贸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南洋各国踊跃前来修好和通商,连此前从未与中国交通的佛齐诸国“亦逾沧海,来集鸿胪”[13],海上贸易一时成为热门事业,虽然风险大,仍有很多人趋之若鹜,节度推官黄滔有感于此,有诗云:“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14]
在泉州,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任泉州刺史17年,任内多方招徕外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15]他的对外开放政策非常成功,做到了“吏民安之”,社会稳定,贸易繁荣,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在他的经营下,前来泉州经商和定居的蕃客越来越多,泉州港的通航和商贸条件越来越成熟。及至五代末期陈洪进割据清源军时期,曾一次向宋廷“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后来又一次“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16]反映出海外贸易带给陈氏政权的巨大利益,也反映出贸易经济在其时闽南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乳香、象牙、龙脑香等物及大量硬通货的流通,无疑主要来自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
有宋一代,一方面有官府对于蕃商、胡贾的积极而灵活的管理政策,有条件地允许蕃客在经商地居留,甚至还为蕃客子弟建立蕃学[17];另一方面,泉州便利的港口条件与泉州文化的包容精神对海外各国蕃客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泉州迅速成为世界著名贸易港,来自南洋、东北亚和波斯、大食的蕃客有了较大的规模,他们在城南建立了自己独立的聚居区。[18]南洋、波斯、大食蕃客多为伊斯兰教徒,因而又在东郊开辟了独立的伊斯兰公墓,还修建了进行公开宗教活动的伊斯兰教寺院。[19]
宋代福建的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全面开展,尤以福州为盛。得益于五代闽国时期福州在港口条件、造船技术、经商传统方面的深厚基础。从宋人的有关诗咏中,我们不难感知福州海上商贸繁荣的盛况。例如刘弇诗曰:“南来海舶浮云涛,上有游子千金豪。”[20]鲍祗诗曰:“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秋。”[21]龙昌期诗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22]温益诗曰:“潮回画戟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23]如此繁华景象,都与福州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密不可分。
宋代福建海交、外贸史的资料不胜枚举,其中对南洋、中东的史料人们谈论很多,毋庸赘述,这里仅举几则与东北亚高丽、日本的史料,以见其概。先说宋与高丽之间的交通与贸易:
《宋史》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24]苏轼《论高丽进奉状》称:“高丽数年不至……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25]又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称:“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有客商王应升等,冒认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显见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26]
再看宋与日本之间的交通与贸易:
北宋咸平五年(日本天皇长保三年,1002),“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27]日本天皇万寿三年(1026)秋,宋朝福州商客周文裔回国。日本天皇万寿四年(1027)秋,宋朝福州商客陈文祐再度来到日本。同时,宋朝福州商客陈文祐回国。日本天皇长元元年(1028)九月,宋朝福州商客周文裔又来日本,十二月十五日,致书右大臣藤原实资,并献方物。[28]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日僧成寻入中国求法,乘坐中国商船,船头三人,一为南雄州人,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29]崛和天皇康和四年(1102),宋朝泉州商客李充到达日本。崛和天皇长治元年(1104),宋朝泉州商客李充回国。崛和天皇长治二年(1105),八月,宋朝泉州商客李充等来到大宰府,呈递本国的公文,请求贸易。[30]
以上所列,都是中国海船特别是福建海船往来于中国、高丽、日本之间的事例。到了南宋,日商的船只也加入了中日海上贸易的行列。他们以本国出产的高级木料制成建筑用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31]
总之,宋代福建对外的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都比以前有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港口的建设、航路的开辟、贸易对象国的扩展、贸易的规模、贸易商品的品类、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都是空前的。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宋代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需求的扩大等等方面都有关系,其中福建造船业在全国独领风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早在唐代,福建的造船业在东南沿海一带已取得领先的地位。天宝三载(744),鉴真筹备第四次东渡時,就派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轻货往福州买船”。[32]到了宋代,“海舟以福建为上”[33]成为官民的共识。[34]宋代福建造的海船,实例有前些年泉州发掘的宋船,估计载重为200吨,应是属于3600斛的海船。参照宋人吴自牧《梦梁录》的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中等2000斛至1000斛,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35]则泉州发掘出的这艘海船,只是中等之船,最大的船,要比这大得多。这样的大海船,体大坚固,能载五六百人,装有罗盘针,故能远渡重洋,成为宋代福建海上贸易迅猛发展的坚强保证。
二、唐宋福建对外佛教文化交流
唐宋福建海上交通的内容,与经贸相伴而行的是文化,尤以佛教文化为主。有时甚至是因为佛教文化的交流带动了经贸的开展。这与唐宋中国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相关,也与福建佛教的繁盛相关。因此,这里首先要略述唐宋福建佛教的发展状况。
福建佛教的兴盛,发轫于唐中叶。早在天宝末或稍后,著名禅宗宗师马祖道一曾到福建建阳弘法。后来福州长乐籍禅师怀海在江西得法于马祖,实行丛林改革,制定百丈清规,倡导农禅道路,风靡于天下。怀海传弟子黄檗希运禅师,希运传义玄禅师,创立临济宗。怀海另一弟子沩山灵祐,福建长溪人(今福建霞浦),与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了沩仰宗。临济宗与沩仰宗属于南岳怀让系统。禅宗南宗的另一大系统是青原行思系统。行思五传至雪峰义存,是福建南安人。义存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先后创立了云门宗和法眼宗。而行思四传弟子莆田人曹山本寂,与其师洞山良价创立了曹洞宗。观此,则知晚唐五代禅宗五大家中,创立者或本身是福建人,或是福建禅师的弟子。唐末五代福建禅师在全国影响之深广,由此不难想见。
唐末五代福建本身也成为禅宗重镇,其关键是著名禅师大安与义存于唐末咸通年间回到福建开山传法。其背景是经过唐武宗毁佛的摧残,佛教诸宗消沉,禅宗也受到沉重的打击,活动于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许多著名禅师,如德山宣鉴、临济义玄、天童藏奂、广爱从谏、径山鉴宗等人纷纷谢世[36],而福建局势相对比较安定,王潮、王审知取得福建政权后更大力扶植佛教,度僧、造寺不遗余力,给了禅宗很好的发展空间。回到福建后,大安在福州开创西禅寺,义存开创闽侯雪峰寺,义存弟子玄沙师备开创卧龙山安国院,义存另一弟子神晏开创鼓山涌泉寺,都发挥了深厚的佛学修养和传法特长,法席鼎盛,聚徒常不下数百,上千乃至千余,名闻天下。云门宗、法眼宗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孕育出来的。
唐末五代福州成为禅宗的重镇,泉州也有佛国之称,其余如漳州、莆田等地,也都有名闻天下的寺院与僧人。其趋势延续到宋代,福建仍是全国佛教最盛之区。当时福建寺院之多,僧众之盛,佛教氛围之浓,从诗人的歌咏中可见一斑。以福州为例,宋代谢泌《长乐集总序》诗曰:“湖田播种重收谷,道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37]黄裳诗曰:“万户管弦春卖酒,三山钟鼓晓参禅。”[38]北宋熙宁间任福州知州的程师孟诗曰:“故国楼台千佛寺,新城歌舞万人家。”[39]
在佛教文化方面,唐宋福建佛教最值得称道的,除了前述创宗立派之举,当数五代时泉州招庆寺僧静、筠二禅师编撰出《祖堂集》,乃中国第一部禅宗灯录。宋代福州先后二次刊刻大藏经之举,其一是福州东禅等觉院所雕“崇宁万寿大藏经”(原名东禅大藏经),简称崇宁藏,北宋元丰三年至崇宁二年(1080—1103)雕印。全藏850函、1440部,6108卷;其二是福州开元寺劝募雕印的《开元寺大藏经》,又称毗卢藏,始刻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完成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一部最早的禅宗灯录和两部民间私刻的大藏经,在佛教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为国内所宝爱,也是海外特别是海东诸国努力求购的经典。
唐宋时期福建的对外佛教文化交流,就是在这一时期福建海上交通与佛教文化空前兴盛的背景下展开,兹举其荦荦大者,缕述于下。
先说唐代。首先要提到的是鉴真东渡传法的壮举,有福建僧人参加并作出了贡献。鉴真初发愿东渡時,有僧二十一人“愿同心随和上去”,其中之一昙静,就是泉州超公寺僧。及至天宝十二载,鉴真乘日本遣唐使船向日本东渡成功,“相随弟子”又有泉州超公寺僧昙静等14人。[40]又据《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逸文[41],鉴真多次东渡追随左右的都有星静其人,与另外始终追随鉴真的法进、义静等并列,颇疑“星静”即“昙静”之误写。然则昙静是鉴真东渡最坚定的支持者,作为大和上的侍从,艰难相随十年,终于成行。至日本后,据《类聚三代格》所载,昙静“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又传昙静率弟子、技工辅助鉴真和尚东渡时,随带泉州茶种和禅茶习俗去日本,他对佛教文化及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其次要提到的是日本空海法师到福建一事。空海法师在日本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他于唐贞元二十年(804)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华求法,回国后开创日本密宗真言宗,同时受梵文字母和汉字偏旁的启发,创造了日本字母平假名,以后片假名也在平假名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此外,他在汉诗学和书法艺术方面也有很大贡献。这么一位佛教和文化巨人,在来华途中遭遇飓风,所坐船只漂抵闽东霞浦赤岸海口登陆,在赤岸村居留了四十一天后,全船开往福州,被安置在福州开元寺住了一个多月。他在福建逗留两个多月,对于福建的佛教与文化有所了解,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在福建霞浦赤岸建立了空海法师纪念堂、祭海亭和空海石像,被誉为“空海漂泊受难的圣地”“报恩谢德的圣地”,常有日本学者和真言宗信徒来此瞻仰、朝拜。
继空海之后,日本智证大师园珍,赴唐求法时也因遭风漂流,于宣宗大中年间(847—859)来到福州开元寺。园珍上福州都督府乞求公验文书云:“伏乞公验,以为凭据。谨连元赤,伏听处分。”福州都督府发给园珍一行的公验云:“随身物经书四百五十卷,衣钵、剃刀子等,旅灶一具。”[42]园珍所携经书,或即在福建购得或获赠所得。
关于福建与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当以高丽高僧释元表与福建宁德支提寺的因缘为典型。“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元表初到支提山时,此山不容人居,乃猛兽毒虫窟穴。元表坚忍不拔,涧饮木食,保护经典,刻苦修持。遇到武宗毁佛,“元表将经以花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43]终于躲过这场劫难。后来支提寺发展为东南名刹,天冠菩萨道场,元表应居首功。其与新罗金地藏在九华山开创地藏王菩萨道场,互相辉映,都是中国佛教史及中国与朝鲜韩国佛教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
唐五代也有来自天竺和西域的高僧到福建,进行佛教文化交流。例如唐末来泉州弘法的印度高僧知亮,侨寓开元寺,人称袒缚和尚。后移居德化戴云山,能汉诗,有诗咏戴云山曰:“戴云山顶白云齐,登顶方知世界低。异常奇花人不识,一池分作九条溪。”[44]开元寺有袒缚院,以其曾居而得名。五代时又有西域僧朝悟大师,居泉州开元寺,“数有异徵。既去,寺僧刻木为像奉之,号木头陀,亦号挑灯道者。”[45]
由于中外佛教文化交流频繁,外国僧人的日用器具也在泉州佛寺中使用。例如军持,原来是天竺佛教徒用以贮水饮用和净手的水瓶。据元代释大圭记载,唐末泉州开元寺主持释文偁,“性高洁,澹然自处,至未尝乎泉布。其影不出者三十年,连倍(背)金刚(金刚经),昼夜有讽讽之声,室为之生白。所蓄军持出水,实不涸,盥辄随寒燠宜殆,类天给侍之者。”[46]
再说两宋。这一时期福建的经济文化与海上交通发展都强于唐代,佛教文化的成就也超迈唐代,故对外佛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内容更加丰富。首先要提到的是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天竺僧人罗护那航海到泉州,“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47]。这是外国僧人在泉州建的惟一佛教寺院。
北宋元祐二年(1087),泉州海商徐戬,先受高丽财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等经版2900余片,用海舶载去交纳。[48]二年后,徐戬载高丽僧寿介等来中国杭州,杭州知州苏轼将他们送到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归国”;其后“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于是便通知明州,如果没有“因便舶舡”,便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49]以此与《高丽史》的记载相印证,似乎可以说,当时泉州是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同时也是中国与高丽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
南宋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入宋僧从福建带回佛教经典,首先应该举出的是日僧带回福州版《大藏经》一事。这部《大藏经》是在太祖开宝敕版以后,由福州的东禅和开元二寺刻印的。日本现存的福州版《大藏经》,自宫内厅图书寮的藏本起,以至京都醍醐寺、知恩寺、东寺、东福寺等的藏本,都是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的混合藏。[50]据研究,这部福州版《大藏经》,很可能是由日本近江园城寺僧庆政从泉州或福州带回的,因为庆政入宋后于建保五年(即南宋嘉定十年,1217)来到泉州,而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所藏福州版《大藏经》的《大般涅磐经》卷三十三的版心中有“日本国僧庆政舍”的刊记,在同书卷三十六的版心中有“日本国僧行一舍版十片”的刊记;该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三的版心中,则有“日本国僧庆政舍、周正刀”的刊记,宫内厅图书寮所藏福州版《大藏经·妙法莲华经》卷七版心中则有“日本国比丘明仁舍刊换”题记。又,高山寺旧藏的波斯文书的前言中写有:
此是南蕃文字也,南无释迦如来,南无阿弥陀佛也,两三人到来舶上望书之。
尔时大宋嘉定十年丁丑于泉州记之。
为送遣本朝辨和尚(高辨明惠上人),禅庵令书之,彼和尚殊芳印度之风故也。沙门庆政记之。[51]
由此可知,庆政入宋后,当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时确在泉州。庆政既到泉州,极有可能顺便访问了中途的福州,或许就是他印制《大藏经》带回国来。而行一、明仁当和庆政同时或随从庆政来到福州,且和带回大藏经有关。[52]这部大藏经的输入日本,不但促进了日本佛教的传播,也刺激了日本的刊印事业。
佛教典籍从福建输入高丽方面,五代泉州招庆寺僧静、筠二禅师编撰的《祖堂集》二十卷的输入是重头戏。这部最早的禅宗灯录,自北宋以后即在中国失传,1912年,经日本学者关野贞,小野玄妙等调查得知,此书在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已被收入高丽版大藏经,其版现存于韩国伽耶山海印寺。二次大战以后,日本曾发行过仿制本。近年来,中国也据以重新整理刊印行世。《祖堂集》传入海东,经过七八百年后再传回中国,实乃中韩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佳话。
注释:
[1] 《越绝书》卷八。按:这里说的是吴越人,但闽越人的情况与此相似。
[2] 《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关于东冶的地望,章怀太子注曰:“今泉州闽县是。”闽县即今福州。
[3] 《续高僧传》卷一《拘那陀罗传》。
[4] 《法苑珠林》卷十六《感应缘·陈扬州严恭》。
[5]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6] 《八闽通志》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漳浦县”引漳州《图经》。
[7] 《全唐诗》卷五五九,薛能《送福建李大夫》。
[8] 郁贤皓:《唐刺史考》卷一五一《江南东道·福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9] 《唐大诏令集》卷十《太和三年疾愈德音》,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10][12] 《十国春秋》卷九十《闽一·太祖世家》。
[11] 钱昱《闽忠懿王庙碑》,《十国春秋》卷九十《闽一·太祖世家》引。
[13] 于竞《王审知德政碑》,《十国春秋》卷九十《闽一·太祖世家》引。按:佛齐国两《唐书》、两《五代史》皆未载,《宋史》始载之。可知其国唐時未通职贡,其与中国通,始自五代闽国。
[14] 《黄御史集》卷二《贾客》,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十国春秋》卷九四《王延彬传》。
[16] 《宋史》卷四八三《世家六·漳泉留氏、陈氏》。
[17] 宋徽宗时曾颁布准许蕃客入籍的诏令:“令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其财产依海外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属者,并依户绝法,仍入市舶司拘留。”(《宋会要辑稿》,徽宗政和四年)又据宋人蔡絛的记载:“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8),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番学。”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二,冯惠民、沈锡麟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
[18] 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宋代泉州“胡商航海踵至,其富者资累巨万,列居城南”。
[19] 现存泉州通淮街的清净寺,是全国保留至今的唯一一座宋代伊斯兰教寺院,也是泉州最早创建的伊斯兰教寺院。据该寺元代重修时留下的阿拉伯文修寺碑记,这座寺院原名“圣友寺”,初建于回历400年,即公元1009年。
[20] 〔宋〕刘弇:《龙云集》卷六《送陈师益还建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宋〕鲍祗:《咏长乐县》,《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州》。
[22] 〔宋〕龙昌期:《福州诗》,《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州》。
[23] 〔宋〕温 益:《福州诗》,《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州》。
[24] 《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三·高丽》。
[25] 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七·日本国》。
[28] 〔日〕大日本古記録 :《小右記》,东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东京 :岩波书店,1976年。
[29] 〔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
[30] 〔日〕《朝野群载》。
[31] 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倭国》。
[32][40][41]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本:《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3] [34]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梦梁录》卷十二《江海船舰》。
[36] 参见张云江《法眼文益禅师》第一章第二节的相关论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37][38][39] 《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州》。
[42] 〔日〕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之研究——智证大师园珍篇》,转引自周一良:《入唐僧园珍与唐朝史料》,见《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43] 《宋高僧传》卷三十《唐高丽国元表传》。
[44] 《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二十四《仙释》。
[45] 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仙释》。
[46] 〔元〕释大圭:《紫云开士传》卷一。
[47]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天竺国》。
[48] 《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
[49] 〔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六《乞令髙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50][52]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南宋、元篇第二章第三节《入宋僧带回的宋版<大藏经>和它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51] 〔日〕桥本进吉《庆政上人待考》所引,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责任编辑:余言]
收稿日期:2016-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佛教改革与近代人间佛教研究”(13BZJ011)
作者简介:谢重光, 男, 福建武平人,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16)03-0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