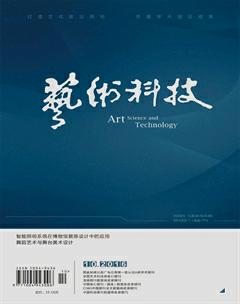王渔洋《秋柳四首》微探
摘 要:提起王渔洋,或者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王士禛”,对文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很自然地将其与“神韵说”联系起来。他所提倡的“典、远、谐、则”直至今日还被许多喜爱诗歌创作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尽管“神韵说”被视为执掌康熙诗坛,被钱谦益视为“接班人”的王士禛一生最大的成就,但是使其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后来构架神韵诗风雏形的作品确是看似“名不见经传”的——《秋柳四首》。本文从诗歌本身出发,通过研究《秋柳四首》语言的运用,主旨的表达以及情感的宣泄,来探寻《秋柳》诗和者众多,进而成为王渔洋诗歌创作里程碑背后的因由。
关键词:王渔洋;秋柳诗;原因
“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首。”[1]此时,这位《莱根堂诗集序》中的主人公还不知道这四首《秋柳》诗会因为化实为虚的委婉笔调,慨叹盛衰无常的巧妙用典奠定了自己成为诗坛盟主的地位。它一出现,便以“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分甘余话》)之势,震动了清初文坛,在短短的时间里,海内“和者不减百家”(《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如此得到诸家青睐的《秋柳四首》不仅在语言的运用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其包含一种“新美”的东西,同时在景物的选取,内容的叙述和情感的表达上都让人对其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喜爱,它的魅力不言而喻。
1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言的运用
鉴赏一篇文学作品,不论它的题材是诗歌、散文、小说抑或是杂文,所有阅读作品的人接触到的最初的东西便是这篇作品的语言。可以说,语言是一个作品的第一要素,是一个作品的原点。任何作品只有在这个原点上进行发挥,进行想象和再创造,才会通过笔墨之中的勾勒传达出笔墨之外的世界。而王渔洋对于语言这一问题曾经借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八字。(《香祖笔记》卷八)王渔洋同样也很重视诗的音律,门生问他何为“平中清浊,仄中抑扬”,他解释说:“清浊如通、同、清、情四字,通、清为清,同、情为浊;仄中如入声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须相间用之,乃有抑扬抗坠之妙,古人所谓一片宫商也。”(《带经堂诗话》卷二)又说:“唐、宋、元、明诸大家,无一字不谐,明何、李、边、徐、王、李辈亦然。”(《带经堂诗话》卷九)可见,王渔洋对于诗歌语言的把握是十分重视的,而在《秋柳四首》这一早期的诗歌作品中,他所喜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便被毫无保留的表现出来:全诗四章,虽写秋柳,而全诗无一“柳”字。取第二首诗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这篇诗歌作品语言的运用。
开头的第一联: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篇首即用叠字“娟娟”,“凉露”二字为双声,第一句最后结尾落在“霜”字上。“娟娟”的本义为“美好、美丽的样子”,可在此处却和阴冷的“凉露”和“霜”相组合,给人一种新鲜感,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而第二句则从数量入手,先用“万缕千条”营造出一个场面,“万”、“千”二字迭韵。同时紧接着“拂”字,这一个拟人的动作将整句话都点亮了,给诗句增添了动感。然后在动作之后,又出以“玉塘”二字,这一静一动,使得第一联便令人感到了语言背后情绪的流动。而这一联最大的亮点便是:未写“秋柳”却已含二字。第一句的霜可谓点名了季节,霜常出现在“秋”冬季的早晨,而第二句的“万缕千条”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柳”。这样一种类似打哑谜似的表达,将标题的意义在开头便暗含其中,让读诗的人从开篇便开始展开想象。
接下来第二联: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第二联连用六个名词,从词性上看可以说较之第一联毫无变化。句中不是将秋柳的姿态进行朴素的写生,也并不是直率地表露对于秋柳的感情,而只是排列与秋柳有某种关系的言语,其中甚至混杂着无论对秋天,还是对柳树都不甚有关的词语。这样突兀出现的第二联,使人自然而然地去寻找词语背后的意义。于是,便很好地引出了所蕴含的典故。这六个名词单纯的排列组合,最后落在了“镜”和“箱”字上。这是两个有后鼻音“ng”的字,鼻音的使用令第二联的整体气氛较之第一联变得低沉。
然后,再谈第三联: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这一联的结构也很整齐,属于动宾结构,“怜”和“见”字前还有“空”和“不”字做状语,组成状中短语。同时“怜”和“见”字迭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从第二联过渡过来的第三联,尽管不再是六个相同词性的词语的排列组合,但这两个诗句都有一个长长的宾语“板渚隋堤水”和“琅琊大道王”同样是蕴含两个典故。但这次在音调的处理上,诗人选择了声调为阳平的“怜”和去声的“见”。这样一高一低,一平一去,似乎令人联想到一位沉吟泽畔的诗人,在抬头长叹和低头哀叹,这一扬一抑中完成了抒怀。
最后,来看第四联: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第四联的结构并非严格的对偶,这一点和第一联一样,似乎有首尾照应的“嫌疑”。而它与第一联相比更特别的地方在于:首联的两句诗可以看作两句话,表达了两个不同的意思,而尾联的最后两句诗却是前后连贯的一句话,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说属于假设复句。尾联所营造的气氛仿佛是在向某人诉说着过去的事情。而此联中的“永丰坊”与前面的“中妇镜”、“女儿箱”、“隋堤水”和“琅琊大道王”一样,包含有典故,但同样是属于僻典。这些不常见的词汇尽管在阅读之初令人“望而却步”,但从反面来说,它的陌生让人产生好奇心,进而对这些虽不常见但具有凝练之美的词汇展开猜想,去体会作品的内涵,最终达到诗人借语言的魅力来传递内心情感的目的。
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说:“此诗的语言没有打破古典的气氛而又有新鲜感。”“此诗大体使用的是作为今体诗古典的唐诗的语言,尽管如此,却带有一种新鲜感。那主要是基于如前所述,使用了‘黄骢曲啦,‘乌夜村啦之类少见的词语。这些词语,是在唐代,甚至唐以前产生的,因而其感觉是古典的。在唐人的诗中,确实可以看到这样的词语。使用它,决不会破坏古典的气氛,但实际上在唐人诗里是看不见这些用语的,至少在一般的唐人的诗中是见不到的。这里就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新鲜感。”[2]这种在用语、抑扬、逻辑关系和音调上的新鲜感,使得读此诗的人便会顺其自然地去寻找诗歌本身的内涵。
2 此时无声胜有声——主旨的表达
对于《秋柳四首》所含主旨的争论一直在继续,与其说这是由于诗中所用僻典的缘故,不如认为是由于诗中存在着与秋柳难以有关的词语,给诗歌本身的主旨蒙上了一层面纱,也为不同寓意的理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看法是认为此诗寄托了对于明亡的哀悼之情。屈复、李兆元、郑鸿等便是这一派的代表。而高丙谋和朱晓村则认为此诗为怜悯一个曾经侍奉过明福王,后又沦落济南,名叫郑妥娘的歌妓而作。同时,认为此诗并无寓意的也不少,如近人江庸《趋庭随笔》第一卷,既引徐嘉《顾亭林诗笺注》于《赋得秋柳》下引黄葆年说,又引王祖源《渔洋山人秋柳诗笺》,然后指出:“虽言之娓娓,要皆揣测之辞,恐阮亭当日不过随题抒写,未必果有用意。”[3]甚至还有惠栋、潜庐老人批评《秋柳四首》为“先生少年英雄欺人之语,人奉为圭臬,则过矣”。[1]总之,这样四首看似普通的《秋柳》诗,却达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不得不说这是诗人巧心安排的结果——主旨的不明确,却使得诗歌的内涵更加的丰富。诗人的“不语”却突出了想要表达的意义,此时无声(未点明)更胜有声(明确点明)。
除了暗含主旨外,刻意隐藏“秋柳”二字,也是诗人另外一种“无声”的表达技巧。在大明湖畔作诗,却不写眼前所见的景物,而是作远距离观照,从“大明湖”转换到了“白下门”,又从“顺治年间的济南”穿越到了“唐代洛阳的永丰坊”,这一空间与时间的转变将读者的目光投向了视觉的极限,放眼到天地之外,随之也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这种似真似幻,既亲切又神秘的诗境,使得对主旨的理解让人们在言外领取。
诗歌的言外之旨,韵外之美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民族特色和艺术传统,清代理论家叶燮把它概括为“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溟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下》)。王渔洋的《秋柳》诗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理论的精髓,把“以获取言外之意来得到诗歌的艺术表现之美,作为产生魅力和动人的所在,掌握了文外之美的要义,深得诗之本旨和艺术创造的真谛”,[4]成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人们欢迎并合乎他们口味的新诗作。
3 醉翁之意不在酒——情感的宣泄
《秋柳》诗之所以能够传遍大江南北,除了语言的巧妙组合,主旨的用心隐含,内在情感的宣泄也是其“和者不减数百家”(《渔洋山人自撰年谱》)的重要原因。时人和《秋柳》而今存和作者计有:徐夜《和阮亭秋柳四首》(存三首)、《再题阮亭秋柳诗卷》(《隐君诗集》卷二),王士禄《秋柳次季弟贻上韵二首》(《十笏草堂诗》),顾炎武《赋得秋柳》(《亭林诗集》卷三),曹溶《秋柳》(《静惕堂诗集》卷三),朱彝尊《同曹侍郎遥和王司李士禛秋柳之作》(《曝书亭集》卷四),冒襄《和阮亭秋柳诗原韵》四首(《巢民诗集》),陈维崧《秋柳四首和王贻上韵》四首(《湖海楼集》),汪懋麟《秋柳和王阮亭先生韵》(《百尺梧桐阁集》)。这些和者均为清初诗坛的名流。诗中朦胧的故国沧桑之思最易为这些遗逸野老、布衣才士所接受,这样的选择自然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
王渔洋所处的时代属于明末清初,社会的动荡,新朝的建立,异族统治的压迫,这些天崩地裂的灾难,既是汉族士大夫易代的“黍离之痛”,亦是外族入主中原的国破家亡之悲。在这样的新旧变革中,一部分人高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组织救亡图存的队伍,大江南北燃起反抗的怒火;另一部分人则以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和人格,或者以死殉国,或者隐居岩穴幽谷,向征服者表示不满与抗议。然而,仍有一部分的文人既不像救亡队伍“抛头颅、洒热血”般的激进,也没有“不问世事”、“以死报国”的悲观,但他们内心隐隐作痛地兴亡之感却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口进行宣泄。而《秋柳》诗所表现的淡淡的兴亡感与清初社会心理的变化合拍,应和鼎革之际士人哀伤的情绪与伤逝怀旧的心态,也与向内心世界逃避的倾向一致。又在统治者日趋严密的进行思想控制的时候,为操觚之士营造一个躲开文字狱的避风港,适宜压抑状态下内敛拘谨的抒情需要,让他们在流连山水中找到自身的心理空间,于使典咏史中发出淡化人生的感喟,由此化解内心的矛盾,释放生存的焦虑。[4]这也是王渔洋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而《秋柳》被奉为诗坛圭臬的重要原因。
从明末清初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来看,不难理解《秋柳》诗含蓄蕴藉的原因,同时,从个人经历这一小的维度来分析,王渔洋的童年是在朝代更替,国仇家恨中度过的,他在其《渔洋文略·五烈节家传》中记载了当时他目睹母亲孙宜人于乱中自缢的经过:“张氏,士和(渔洋从兄)妻,新城人,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自经东阁中,以发覆面。初,先宜人(其母孙宜人)与张对缢,先宜人绳绝不死,时夜中,喉咯咯有声,但言渴甚,士禛方八岁,无所得水,乃以手掬鱼盎冰进之,以书册覆体上,又明日兵退,得无死,视张则久绝矣。”[4]尽管“壬午之难”发生时王渔洋还是一个孩童,他的兴亡之感决不会像顾炎武、屈大均他们那样强烈,但国破家亡之悲还是在诗人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颗国仇家恨的种子慢慢地生根发芽,急需寻找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顺治十四年秋八月的一天,诗人终于等到了这样的一次机会。《渔洋集·秋柳诗四首序》:昔江南王子,感落叶以兴悲;金城司马,攀长条而陨涕。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偶成四什,以示众人,为我和之。顺治丁酉秋日北渚亭书。[1]此时,诗人“醉翁之意不在柳”,内心的感慨与悲叹便借着秋柳这一意象,温润委婉的道出。“得江山之助”的《秋柳四首》便将明朝遗老,布衣士族那种“敢怒不敢言”的心情酣畅淋漓地宣泄了出来。诗中“销魂”、“残照”、“白下”等,难以实指的莫名悲伤,“若过”、“重问”等欲说还休的语言运用,都使人感受到了对人事变迁和往事成尘的嗟伤与哀怨。
综上所述,《秋柳四首》的一鸣惊人,声满天下,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必然如此。《秋柳》诗以它独特的语言魅力、委婉的主旨表达、酣畅的情感抒发以及具有“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美学精神的神韵诗风,为清初的诗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人惊叹。
参考文献:
[1] 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济南:齐鲁书社,2007:30,51,29.
[2] 吉川幸次郎(日).中国诗史[M].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46.
[3] 刘世南.清诗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82.
[4] 张明主.王士禛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240,308,066.
[5] 王士禛(清).王士禛年谱[M].孙言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 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8] 王士禛(清).渔洋精华录集释[M].李毓芙,牟通,李茂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 王士禛(清).渔洋精华录集注[M].惠栋(清),金荣,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
[10] 王士禛(清).渔洋山人感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 孙康宜(美).成为典范:渔洋诗作及诗论微探[J].北京:文学评论,2001(1).
[12]刘利侠.论王士禛《秋柳诗》的文学史意义[J].太原:名作欣赏,2011(29).
[13]吕鑫.王渔洋《秋柳》诗和者甚众的原因探析[J].长沙:文学界,2012(08).
作者简介:万里晴(1993—),女,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