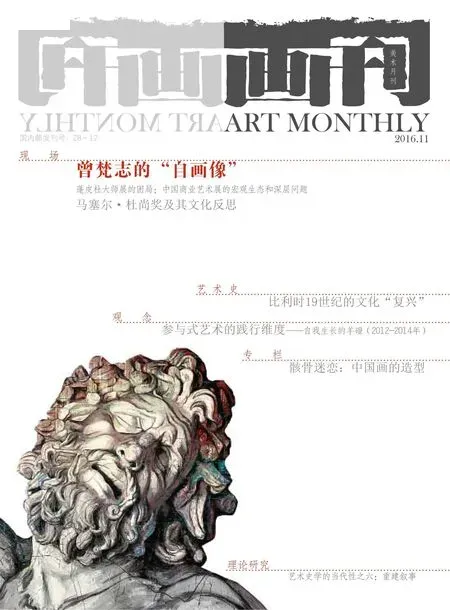曾梵志的“自画像”
王文菲
曾梵志的“自画像”
王文菲
在展览“曾梵志:散步”中,对于不了解这位艺术家的观众,恐怕令其印象最深的作品并非成名作《协和医院》三联画系列,亦非尺幅巨大的《抽象风景》系列,而是作于2009年的《自画像09-8-1》: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大展厅被6面独立的展墙分隔,每一面展墙的左侧打开一扇正方形的大窗,而6扇窗户的尽头,悬挂着曾梵志本人的自画像。自画像中的曾梵志轻握画笔,似乎正凭借画家的“天才”勾勒身后混沌的风景,而其鲜艳的红袍、锐利的眼神与镇定自若的气质则让周围的一切显得黯然失色。

《面具系列1996第6号》 曾梵志 布面油画 360cm×200 cm 1996年 ©曾梵志工作室
展览空间由日本的明星设计师安藤忠雄设计,意图通过整个展厅再现艺术家的“脑部结构图”——对于一次明星级艺术家的回顾性展览,这一设计理念可谓恰如其分:一方面,任何一位观众均可在极具纵深感的“窗口”旁与曾梵志的“化身”合影——他的个人形象如此耀眼,以至于整个展厅中的作品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该形象的某种注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艺术生涯镌刻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以至于若脱离具体的创作语境,我们或许唯有保持缄默,才能称得上审慎。

《蓝》 曾梵志 布面油画 700cm×400 cm 2015年 ©曾梵志工作室
曾梵志的创作生涯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每一位创造者都面临着“影响的焦虑”,但对那些活跃于90年代的艺术家而言,这种“焦虑情绪”显得更为复杂。1989年的“’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后,“八五美术新潮”正式退潮[1]。随着某种政治论争的“悬置”,“八五美术新潮”所蕴含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失去了其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而这一致力于“与传统决裂”的潮流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语汇[2]。在“后八九”的时代,一方面,随着启蒙主义宏大计划的挫败,玩世主义、政治波普成为一时之选,崇高的追求为无聊感所取代[3];另一方面,彼时,西方现代主义的范式早已成为某种“经典”,它既并非源于中国本土,亦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当代艺术相去甚远。展览中,6面独立展墙的一侧按照时间顺序呈现曾梵志的作品,反映其在这种境遇中的探索轨迹。
在早期作品,如作于1990年的《散步》《忧郁的人》《受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不过,西方艺术对曾梵志的影响绝非仅停留在风格的层面。在其成名作《协和医院》系列中,曾梵志戏仿了西方宗教三联画的形式,以经典画作的基本构图描绘协和医院内的场景,将具有崇高感的范式用于摹写中国本土的日常生活。尽管事关生死的医院与“崇高感”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曾梵志漫画式的表现手法却更多地赋予其某种“黑色幽默”的质感——这预示了他的代表作品《面具》系列:呆滞的眼神、比例夸张的双手成为两个系列作品的共同特征。此时,曾梵志或许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将西方的经典艺术“内化”的问题。随后,移居北京的曾梵志对如何经营自己的艺术生涯,做出了更为深思熟虑的规划。在《面具》系列中,他从戏仿、挪用西方经典图式,转为揶揄20世纪90年代充斥中国日常视觉图像中的符号,制作出颇具时代感的漫画式图像——昔日理想主义的空洞、当下消费主义的虚无与未来的迷茫感均以“不痛不痒”的面貌展现在观者面前。这些作品显得既轻松、又沉重;而在其通俗的外观之下,又赋予国内外的评论家们深度阐释的余地。无论如何,这些作品让曾梵志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使其逐渐走向国际艺术界的舞台。
整个20世纪90年代,曾梵志致力于研究如何将“人物”形象置于社会背景中,以戏谑的语调与精准的符号切入时代的脉搏。而当这类题材或样式演化至炉火纯青之时,他明智地选择另辟蹊径。在展厅四周的墙壁上,陈列着曾梵志所熟悉的肖像作品,包括作于2002年的《我们》——此时,曾梵志开始钻研一种属于自己的“技法”,试图突出“线条”本身的表意的作用。对于当代艺术,虽然绘画的“技法”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论题;但对曾梵志来说,这关乎如何发展出一种具有高辨识度的个人语言。如果难以在观念上进行突破,那么回到形式本身,大概是最为稳妥的办法。这一技法上的实验延续至曾梵志的《抽象风景》系列。尽管展墙文字称该系列的笔法源于中国古典园林的“气韵生动”,但许多评论家更愿意称之为“乱笔”。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正如陈列在独立展墙另一侧的巨幅《致敬》系列作品所展现的那样,曾梵志似乎在有意地进行某种“自觉的艺术史”建构。他将西方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如《拉奥孔》、丢勒的《野兔》《祈祷的手》、达·芬奇的《伯林顿府草图》等)中的标志性图像几乎完全移植到自己的画面中,可谓以“乱笔”完成了一次“临摹”。假如所谓的“乱笔”确实具有某种中国传统绘画的古典气质,而曾梵志又以此对西方经典进行了成功的“再塑造”,那么这或许算是另一种“文化输出”,正如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图兰朵》。事实证明,这算是成功的实验:2014年,曾梵志受法国卢浮宫的委托创作了《从1830至今No. 4》,以“乱笔”重构了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该画作与德拉克洛瓦的原作并列悬挂在卢浮宫展出。

《协和三联画之一》 曾梵志 布面油画 460cm×180 cm 1991年 ©曾梵志工作室

左·《散步》 曾梵志 布面油画 20cm×30 cm 1990年 ©曾梵志工作室

右·《肖像》 曾梵志 布面油画 150cm×200 cm 2004年 ©曾梵志工作室
或许,通过研究曾梵志的创作历程,我们已经可以在理解其同代艺术家在创作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处理西方艺术的遗产?这一遗产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未被充分消化。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创作真正具有当代意义的艺术作品?在迅速地完成借鉴、对抗、融合之后,曾梵志选择对西方艺术的文化资源进行“悬置”,尽管这一选择似乎与近年来本土传统文化的复兴趋势不谋而合。在大展厅尽头的独立展区中,近期创作的纸上作品俨然成为本次展览的卖点——曾梵志与新加坡泰勒版画研究院(STPI)展开合作,依据纸张本身的纹理创作了一系列据说深得宋画“真传”的作品。这些作品唯有在暗室中的特殊布光效果之下才能展现出自身的魅力——这个区域的布展是极其成功的,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究竟是绘画作品本身的精妙绝伦,抑或光影效果本身所营造的肃穆感让人赞叹不已。
然而,这20多年来,曾梵志绘画面貌的改变如此频繁,各阶段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这究竟是否可视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体现?或者,我们可以更
大胆地追问:他是否一直处于某种“试错”之中?不容忽视的是,从早年描写市井生活的《协和医院》系列,到如今颇具“士大夫”趣味的纸上作品,曾梵志的创作似乎与社会现实渐行渐远。又或许,他的创作遵从着另外一种秘而不宣而至关重要的逻辑?或反映了同一社会现实的另一面?如果说“艺术”毕竟是具有阶级性的,那么,当“人民”这一字眼显得过于空泛时,我们时代的艺术家究竟为谁而创作?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每一次风格的转变都没有对曾梵志在市场上的成功形成阻碍。或许,这位艺术家曾因拍出天价的作品而备受争议,但资本的选择毕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时代精神。作为审美实践的艺术创作,向来处于同资本的博弈之中。博弈的结果,尚待时日揭晓;历史的判断,终将平息争议。然而,曾梵志,这位于连式的艺术家,其孜孜不倦的野心、审时度势的眼光,恰好鲜活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整体“上升”的社会风貌;其惊人的成功轨迹或许已超越其艺术作品本身,而成为一次伟大的“行为艺术”——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事件更“当代”的,也让此次展览的举办获得充分的理由。
或许,一幅曾梵志作于1994年的《自画像》可以让我们更为直观地理解其曲折的创作生涯。与文章开篇提及的《自画像09-8-1》相对照,我们便可以窥探同一位艺术家在不同阶段对“自我形象”的诠释;这种诠释或许比艺术家精心编造的“宏大叙事”更能真切地反映出其自我认知在时代的变迁中的变化:艺术家目光凝重,紧握右手,俨然一位革命者姿态;他的影子短小,与棕黄色调一并构筑了正午时分令人压抑的怀旧氛围,仿佛逝去的理想主义年代“莫须有”的光芒正凝结在这一刻。而毕竟一去不复返或从来未存在过的事物,才值得被铭记。

左·《哥哥》 曾梵志 布面油画 50cm×70 cm 2004年 ©曾梵志工作室

右·《拉奥孔》 曾梵志 布面油画 400x400cm 2015 ©曾梵志工作室
注释:
[1]参见鲁虹:《90年代中前期的中国当代艺术》,《东方艺术》2013年第3期,第44-57页。
[2]吕澎:《“新绘画”的历史与语言流变》,《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第112-114页。
[3]栗宪庭:《当前中国艺术的“无聊感”——析玩世现实主义潮流》,《21世纪双月刊》,第69-75页。
注:
展览名称:曾梵志:散步
展览时间:2016年9月19日-11月19日
展览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本文图片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