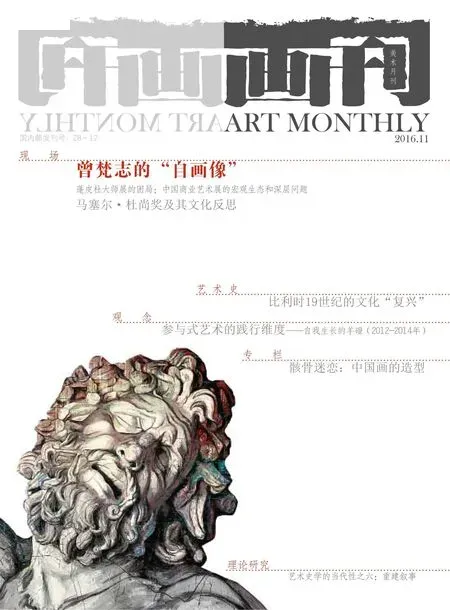沃霍尔和他的影子
王凯梅
沃霍尔和他的影子
王凯梅
在当代艺术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或许没有哪个艺术流派能有像波普艺术这样普世的影响力。当年安迪·沃霍尔预言“每个人都有成名的15分钟”( In the future,everyone will be world-famous for 15 minutes),今天,所有人都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操作自媒体,并且可以随时随地与上万粉丝分享、互动。我们甚至可以想像,如果沃霍尔还活在今天,他会如何欢呼这股来自大众的、网络世界的,对成名、金钱、物质欲永不停息的力量。或许他其实已经在用他的缺席,让今天的网络明星们生活在他的影子里了。
沃霍尔在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所做的一切:开工厂批量生产艺术作品、拍6个小时只有一个镜头的艺术电影、以艺术的名义将纸盒和罐头瓶一类的日常之物推上艺术的神圣殿堂、用“嗑药、性、摇滚乐”搅乱精英文化的虚伪秩序,这都是他的遗产。在他之后的艺术领域,新的美学概念不断在被探索。对应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波普艺术被重新界定,而沃霍尔的影子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艺术的阵营。今年9月份,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开幕的展览“波普之上”,聚焦的正是一群试图界定当代艺术新美学的中外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从波普艺术的传统中走出,眺望着“波普之上”的广阔领域;而就在10月底,安迪·沃霍尔鲜少露面的作品《影子》空降余德耀美术馆。同一空间的两个展览将人们的目光向波普艺术重新聚焦,那么,半个世纪前,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艺术在波普艺术之后已经‘消失’”的判断,在今天的艺术语境中如何解读?在沃霍尔已经离世近30年后的今天,他的影子们和作为作品的《影子》在中国的重现,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反响?当代艺术圈,沃霍尔的威力是否依旧锐利?波普艺术的批判性是否还在继续发酵?

上·《影子》 安迪·沃霍尔

下·谭天作品 2016年
走进“影子”展厅的一瞬间,人立刻被色彩紧紧地包围进去:赤红、深黑、明黄、暗紫……展线长达135米的四面白墙被充斥着各种色彩的画面挤塞得不留一丝间隙。这片完全是色块与色块之间相互咬合的画面,有着相同的尺寸,让人无法分辨出光在哪里,影子又是何物。连绵不断的色彩长廊把观众带入沉浸式的体验。创作于1978年的《影子》起源于一张模糊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光的照片,沃霍尔将其发展成整整102幅,高180厘米、宽120厘米的作品,并且强调所有画面必须通过整体呈现,才构成一件作品。“有人问我它是不是件艺术品,我说不是。你看啊,开幕派对上还有迪斯科,我觉得它就是个装饰品。”1975年《影子》第一次在纽约展览时,沃霍尔如是说,并且不失策略性地强调,只有把所有画面展出,才能体现作品在空间中的重要性。在把波普艺术的机械制造和丝网画面,去除透视的平面处理放大到极致的工艺过程中,一个平庸的原型经过102个隆重的重复,也必将诞生伟大。可以说,沃霍尔掌控到了消费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影子》是他用波普艺术的核心力量,为寻常之物树立起来的最宏大的纪念碑。
相比沃霍尔丝网画中最典型的题材——对消费品的机械制作、对娱乐圈名人的执迷反复,《影子》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波普光环下的另一面,一种暗物质,一种对无名和莫名的反复咏诵,让我们回想到沃霍尔早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车祸场景、行刑室内的电椅和1964年创作的悬挂在惠特尼美术馆入口处的13名死刑犯的照片。死亡与灾难是这些色彩斑斓、不断重复的画面中时刻涌动的真实的恐惧。这种恐惧如果追溯到沃霍尔自身,就要触及到他的童年成长记忆、对自身缺陷的不满,和通过他人的光环覆盖自卑的手段。《影子》在余德耀美术馆的全面呈现,无论102块画面上遍布多少明亮的色彩,黑色依然是作品中直逼视觉的主打色。它们夸张地重复,聚合在一起的宏大体量让空间有了令人可以感受到的悲怆的重量。重复之于沃霍尔不是在建构真实,而是在化解创伤。而创伤在《影子》中的体现,在脱离了梦露的迷人面孔下试图遮掩的悲剧人生后面,走向一种依附于色彩而又超越其上的情感渲染。这里,沃霍尔的作品有了音乐的节奏和电影的动感。我们走过一幅一幅相同又相异的画面,影子在我们的视野中开始活动起来,绘画图像中运动的潜能通过时间成为开启空间的另外一把钥匙。在没有空间透视的画面上,时间衔接着我们在展厅中的行进,每个人各自在脑海中将形成一部由102帧画面编辑成的运动的图像。如罗兰·巴尔特《明室》中对意趣的阐述,那漂游在画面外的更宽更广的想象的画面,构造作品的意趣,这是情感滋生于画面的逻辑。
《庄子·齐物论》中有黑暗与影子的对话,原文说罔兩(影子之外的微阴)问景(影子)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在庄子的世界里,影子虽然是由物质自身的形态决定的,但它真正的属性却又超越物质而成为一种精神之物,所谓“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这之间的神秘性浮游在认识的边缘地带,时而让我们相信身影相随,时而又在影的飘浮中试图捕捉那些虚渺空灵的东西,比如精神、哀伤、爱……庄子对世界真实与虚拟的思考回归到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所为,其根本不就是精神的神秘性和模糊性吗?沃霍尔的画面似乎回应了2000年前的庄子世界中的空灵,飘浮在临界的情感在这里找到了可以依托的非常物质的避难所。
同《影子》压倒性的黑色弥散的悲情氛围相比,“波普之上”的气息无疑是轻松俏皮的,或许这正显露出50岁的沃霍尔面对生命悲剧性的领悟,与一群生活在当下的青年艺术家们正在感受的生命源动力,形成了对比。

《蝴蝶房》 塔博尔·罗巴克 2015年
生命体验成为走入“波普之上”首先相遇的作品,安妮卡·伊(Anicka Yi)的作品收集了众多女艺术家的私人气息,制成散发气味的细菌,在塑料大棚一般的装置中慢慢滋生。细菌、气味、女性……作品带给人的联想是浸入到肌肤之下的私密感。尽管艺术家要探讨的是气味所代表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和行业的生存状态,细菌可以繁衍成疾病,也可以被忽略不计,这是女权主义者在当今社会的处境的隐喻吗?接下来进入的放映厅里卡米耶·昂罗(Camille Henrot)的影象作品《非常累》也非常好看,说唱音乐和诗人的想像把带着童趣看待宇宙的好奇心折射在编写宇宙发展史的野心中,各种流行元素抓住了数码时代思维的跳跃,不知不觉,观者已经被吸引。
随后的展厅出现了中国艺术家谭天和吴笛的作品。谭天的绘画带着自嘲的口吻看待绘画的状态,直接书写在画面上的短句如同连环画的对话栏,可以被看作是同波普艺术传统最近的联系;吴笛带着她对现成品的个人定义,作品肃穆的外表下伪装着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少见的幽默,博物馆的陈列台上庄重摆放着的是一只超有细节的沙皮狗的雕塑,一个乳房喷溅乳汁的女子像镶嵌在华丽的巴洛克式的画框里。这让吴笛的作品成为展览中延展波普艺术对消费社会批判意识中最有关联的地方,尽管它们刺激的首先不是感官的直接反应,而是离奇的场景引发的联想;与吴笛相反,中国艺术家童昆鸟的作品则是扑面而来的喧嚣和热闹,各种大街上回收的旧物汇集成一架蒸汽朋克式的诺亚方舟,混乱粗糙的物件和各种声音的咆哮让人目不暇接。童昆鸟的方舟《从罗马尼亚到洛杉矶》,是一个奔波在机场到机场的“在路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走国际路线的写照,这些被艺术史论家于渺称为生活在“平流层中的艺术家”[1],他们作品的地方性或许只存在于展签里他们名字的拼写中了。反倒是美国艺术家阿列克斯·伊斯雷尔(Alex Isreal)的景观雕塑直击他生活的南加州美学,一只硕大的太阳镜镜片凝聚了美国西海岸的阳光美景和娱乐明星的生活方式。在作品的制作上,伊斯雷尔也是极简精到。如果说艺术在制作上有高级与低级的差别,现成品的鼻祖杜尚就是高级的范例,放置在厨房高椅上的自行车车轮从色彩到做工无不体现着杜尚那貌似随意的处理背后的优雅精良;杰夫·昆斯的充气狗可被看作波普艺术在新时代里质量高级的另外一个范例,暂且不谈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无聊,昆斯的作品总能保持制作的精美无痕,这也是艺术美学范畴内的思考和实践。
“波普之上”是由洛杉矶的策展人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和住在上海的英国策展人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共同策划的。史密斯选择涉足流行文化和使用网络技术的中国艺术家,他们自身的成长并没有直接受到西方波普艺术的直接影响。但同样,他们似乎也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短短30年中,摆脱了他们上一辈艺术家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包袱。如果说波普艺术和中国当代艺术最直接的关联,我们会首先想到“八五新潮”的艺术家,尤其是被称为“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的一代艺术家,而显然,这里参展的以80后艺术家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艺术家们,他们观看世界的眼光朝外面对的是网络和数字的世界,向内观察的是个人内心的感触。中国艺术家aaajiao徐文恺挖掘电脑文件日新月异的更新换代中极速产生的“遗物”,把Windows程序的视窗演变成布满图示的钢铁碑林,提醒我们被消费的信息同记忆的关系;而美国艺术家克丽·特赖布(Kerry Tribe)的作品则将日常之物转化成人造风景,用诗句重建自然与人的思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这两位方法迥异的艺术家共同探讨的都是被消费的人造之物,用艺术填充视觉之外的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当我们能够用这样一种思路去看这个汇集了中外艺术家的展览的时候,平等对话方可成立。

左·《嗨,妈妈》 吴笛 2012年

右·《刀面》 萨马拉·戈尔登 2014年
注释:
[1] 于渺在获得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第五届评委奖的采访中说道:现在的一些年轻艺术家就像进入大气的平流层一样,从纽约飞到威尼斯飞到上海,平稳得很,可以跟下面的气流完全不发生关系,也不影响各自的成功,我把他们叫做“平流层艺术家”。见2016年1月刊《画刊》杂志。
注:
展览地点:余德耀美术馆
展览名称:OVERPOP(波普之上)
展览时间:2016年9月4日-2017年1月15日
展览名称:安迪·沃霍尔:影子
展览时间:2016年10月29日-2017年1月15日
本文图片由余德耀美术馆提供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