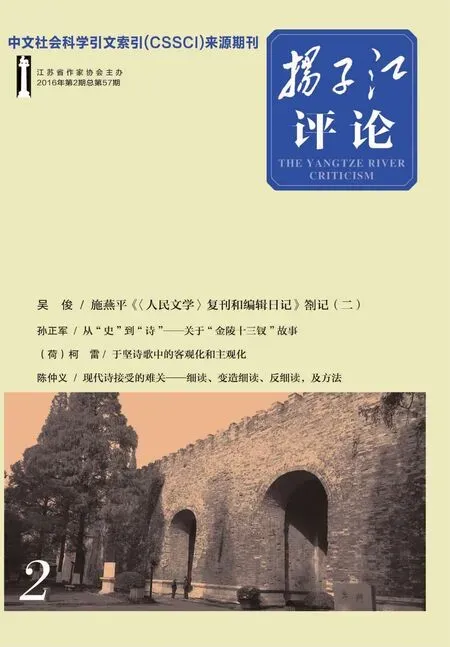一种态度:关于中国文学、翻译及诗——奥地利翻译家、诗人维马丁(Martin Winter)访谈
周维东
一种态度:关于中国文学、翻译及诗——奥地利翻译家、诗人维马丁(Martin Winter)访谈
周维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2AZD086)阶段性成果。
周:马丁您好!您组织翻译的《LEUCHTSPUR》(中文译名《路灯》)在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据说这是《人民文学》的德语版,祝贺您!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杂志吗?
维:这是《人民文学》杂志社组织的翻译。大致在三、四年前,《人民文学》组织了英文翻译,书名叫《PATHLIGHT》,中文的意思就是“路灯”。德语版也用了这个中文译名,我组织翻译。
周:“LEUCHTSPUR”有特别的涵义吗?
维:“LEUCHTSPURE”大概的中文意思是“光脉”,是光划过之后,留下的痕迹。你能明白吗?它和“PATHLIGHT”还有一点不同。“人民文学”的英文翻译是“People Literature”,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P”、“L”,成为“人民文学”在西方特殊的标记,必须保留。你看PATHLIGHT,P、L也是第一个字母。在德语中,找一个合适的词很难找,最后确定为LEUCHTSPUR,也是以P、L为词首,但顺序有点改变,没有办法。
周:与《人民文学》合作LEUCHTSPUR时,你们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里面的内容是您选择的吗?
维:不是的。里面的篇目是《人民文学》提供的,但所有的翻译者都是我找的。
周:您觉得选择这些篇目有怎样的考虑呢?
维:我不太清楚。但封面(封底)上的这首诗,还是让我很诧异,它似乎与我理解的官方的态度并不一致。诗名叫《WIR UND ICH》(《我们和我》),作者是李琦,这是我的翻译。我给你看中文原稿吧!
有许多时候,不同的人
代表了我、包括了我
从少年至今,很多隆重的
看上去盛大或是严肃的场合
庆典中,会议里,报纸上
我,被铿锵有力的代表
我们满怀着——我们信心百倍
我们,就是全体,不由分说
我们幸福,我们斗志昂扬
我们领会或者贯彻,姿态奋勇
我们,我们,我们
从来没有任何人
代替我难过。这是独享的
我所看见,我所听到
我所经历的,一些痛楚
必须独自体验。那种从心脏
到毛细血管辐射的感觉
无法用语言,一一精准地记录
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悲伤袭来
当你把变碎的自己,重新整合
那不再是我们,那真实的
切肤之痛,那是我的感受
是我,我自己的我,我本人的我
她说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都被“我们”代替,只用“痛”是“我”的,是别人不可代替的。这很有意思。
周:我能明白你的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中国官方在选择文学海外传播时的立场和态度——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和文件,还是负责人个人的理解?中国曾经有针对海外传播的文学翻译、出版工作,如《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中国文学》在2001年停刊了,“熊猫丛书”好像后来也没有继续出版,原因据说是上世纪90年代后海外读者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我想《人民文学》在选择这些篇目时,可能也要考虑海外读者——比如德语区读者的兴趣。文学的跨语境传播是个很复杂的事情,纵然有强烈的官方意志,可能也要考虑接受者的情况。
维:我知道“PANDA”。可能有你说的情况,但我不太清楚。
周:我注意到LEUCHTSPUR的出版社是中国外文出版社,这些书能在德语区发行,一般读者能看到吗?
维:我不太清楚能不能在德语区发行,大概需要和这边的出版社合作吧。一般读者很难买到这本书,但它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出过。在北京有法兰克福书展的办公室,会了解中国各方面图书出版的情况。德国大使馆可能也是这些书传播的一个途径。
周:以后会有德语区出版社出版LEUCHTSPUR吗?
维:有这个计划,但要谈。出版社要考虑市场的问题。
周:在德语区,哪些中国当代作家对一般读者(相对研究者)比较有影响力?
维:额——,几乎没有……
周:莫言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维:当然,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德语地区很多人知道他,但那也是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在此之前,也有读者,但并没有达到出版社的预期。2009年的时候,出版社组织了莫言和余华的作品朗诵会,他们也从中国过来了,活动在大学(维也纳大学:访者注)里举行,很多教授和孔子学院工作人员都积极参与、组织,但现场也只来了100多人。出版社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那么那么畅销的作家,在这边的读者竟然不多。廖亦武在德语区知道的人比较多,那是因为他现在就住在柏林。
周: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中国文学不太有趣,还是文化差异、意识形态的原因?
维:跟文学好不好没有关系,也没有其他原因,主要是没有那么多翻译,大家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作品。其实像LEUCHTSPUR,里面很多作品都是很不错的。但中国作家对这边的出版社来说,还是太陌生了。他们不知道出版哪位作家的能赚钱。出版社没有兴趣,也就很难组织翻译了。可能英语出版社要好一点,因为读者更多,可以尝试翻译更多的中国作家作品;德语出版社——特别是奥地利的——都很小,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很难出版中国文学的书。之前,德语出版社出版过沈从文、老舍的书,但现在都没有再版。如果出版社把这些书再版,慢慢培养,可能会有更多人了解、喜欢中国文学。
周:从古代以来,哪些中国作家在德语区比较有影响力?譬如:一般的读者大概都听说过李白、杜甫吗?
维:很难说。但大多数都知道老子、庄子,还有《易经》。我父亲就喜欢《易经》,他在家里经常会读这本书,而且还用铜钱进行占卜。他们真的很相信,认为其中包含了很多玄机。李白、杜甫是不是一般人都知道,真的不好说。
周:那您开始接触中国文学是从谁开始的呢?是怎样的经历?
维:我最早接触中国文学是通过老舍。你可能猜不到我看的是那部作品——是《猫城记》。你刚才问奥地利人不太了解中国文学是不是有其他原因,我可以根据我的经历来说,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对我而言,它(《猫城记》——访者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是它是不是有趣。今天我知道它包含丰富的内涵,但在当时,它对我来说就是一本科幻小说,只是觉得很有趣。我就是在书店翻着翻着看到这本书,并没有注意作者是谁,是哪个国家的。
周:我看到很多汉学家到中国后都非常推崇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鲁迅应该是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吧?
维:鲁迅当然是世界性的作家——这毫无疑问。但他是不是德语区最广为认知的中国现代作家?很难说。我感觉沈从文、老舍似乎更为一般读者欢迎,对一般读者而言,鲁迅太难了,过于严肃,大家更喜欢放松一点的文学。在欧洲,有很多人喜欢鲁迅,但主要集中在专业读者(研究者)当中,或者是所谓的“左派”,他们很喜欢鲁迅。
周:您是奥地利——也是德语地区著名翻译家,您翻译过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呢?
维:我翻译过刘震云的作品,比如他的《温故一九四二》,当时要出版他的一个小说集,我就翻译了。他也来过奥地利朗诵,是2011年。另外我还翻译个很多中国作家单篇的作品。
周:我知道你翻译了不少伊沙的诗。
维:是的!我主要翻译的是诗歌,偶尔也翻译小说和散文,因为我自己也写诗。我很喜欢伊沙和他周围诗人写的“口语诗歌”,《新世纪诗典》我翻译比较多。
周:作为一个翻译家,您选择的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维:更多时候,翻译什么的决定权在出版社,他们要出版中国语言的作品,会来找我翻译。翻译家当然也有自己的兴趣,比如我,更多是翻译诗歌,因为我自己也写诗。我翻译伊沙和《新世纪诗典》的诗,因为他们诗歌的态度与我的态度比较一致。所谓“口语诗”并不一定都是口语,主要是一种态度。
周:您怎样看待伊沙和《新世纪诗典》的“态度”?
维:主要是要求直接写日常生活,表达具体的经验,不要提前考虑某种艺术形式,然后再进行写作。有些诗人会提前想到艺术形式,比如臧棣,他的很多诗都有相同的名字,如“×××入门”、“××丛书”,给人最明显的印象就是艺术形式。生活里的东西,在臧棣的诗里也有,但作为读者,你首先感受到的是艺术形式。伊沙刚刚相反,他的诗好像没有艺术形式,都是生活里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认真感受他的诗,他并没有不要艺术形式,而且有时候是很漂亮,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形式太漂亮了很可怕,比如《9·11心理报告》
第1秒钟目瞪口呆
第2秒钟呆若木鸡
第3秒钟将信将疑
第4秒钟确信无疑
第5秒钟隔岸观火
第6秒钟幸灾乐祸
第7秒钟口称复仇
第8秒钟崇拜歹徒
第9秒钟感叹信仰
第10秒钟猛然记起
这十行,前面都是“第几秒”,后面都是四个字的成语,非常整齐。但他很快打破这些,接下来:
我的胞妹
就住在纽约
急拨电话
要国际长途
未通
扑向电脑
上网
发伊妹儿
敲字
手指发抖
“妹子,妹子
你还活着吗?
老哥快要急死了!
把这些写到诗里面,我没有碰到类似的诗歌。这是我喜欢的一点。伊沙的性格类似于我。我不想评判谁的诗比较好,但我个人比较喜欢伊沙的方式。
周:您的这种看法,在德语地区有代表性吗?
维:有人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比如我认识的一位柏林的女翻译家,她非常喜欢臧棣,也翻译了不少臧棣的诗。她自己也写诗,是很像散文诗的那种,不分行,写在一起,从语调上来看,每一首都相似。我看她翻译臧棣的诗,感觉很不错,但我看了臧棣的中文诗歌,怎么每一首都有一样的名字(是指很多同名诗——访者著),感觉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感情,就有点不耐烦了。对我来说,在诗里面,如果没有具体的经验,就是没有感情。读一首诗,如果首先是形式很好,然后再扑捉到丰富的内容,效果当然很好,但我常常没有这个耐心。
周: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他们的诗重复,是因为内容不够具体?
维:是的。对我来说,只有在具体的事物和经验中,才能捕捉到作者的感情。对于过于注重形式的诗,我偶尔才能读得很深,更多时候,这些诗都不能将我带入其中。但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很注意找到某种形式。我自己的诗,其实非常注意形式。但我不是先找一个形式,这对我来说不可能,我碰到一件事或什么,我心里先有一种东西,要写出来。写出来的过程就会有了一个形式——我不能想象先有一个形式。
周:在翻译所谓“口语诗歌”的时候,因为这些诗人经常会用一些中文的俗语、口语,在翻译的时候这些“口语”的特质会不会减少呢?
维:其实“口语诗”中真正使用的“口语”并不多。在《新世纪诗典》中,也并不全是“口语诗”,伊沙尽量要求选择的范围尽量广泛,他有自己态度,但《新世纪诗典》并不拘泥于一种诗歌——当然伊沙所反对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在《新世纪诗典》里肯定没有。
周:我记得《新世纪诗典》中也选过您的诗,有一首叫《报摊》:晚报/晚报//早有早报/晚有晚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大概也是用中文写的吧?
维:是的。当时我住在北京。这首诗是不能翻译的,我尝试过很多次把它翻译成德语,都没有成功。
周:对于所谓的“口语诗”,因为强调书写具体的经验,也有人质疑破坏了诗歌的美感,也导致诗歌写作口水化,您怎么看?
维:有很多人说口语诗——好诗不多。屁话,都是屁话。不管这样说的人是批评家或者诗人,都是屁话。他们并没有读那么多的诗,很多诗人的诗他们没有认真读,很多诗人写过大量的诗他们也没有读到。然后就说:好诗不多!有很多人喜欢听这种屁话,因为有时候很管用、省事,比如办诗歌节,举办方只请几个诗人,然后对观众说:这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其他人——好诗不多。对于一般的读者,这种说法感觉非常内行、很专业,其实都是屁话。
周:关于伊沙和他提倡的“口语诗”,有人觉得他很有立场,也有人觉得有“游戏”的倾向——就是为了解构崇高,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维:“口语诗”的说法出现很早,大概是于坚和韩东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当时他们倡导“民间”的立场。伊沙与韩东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伊沙自己也承认,他的诗与韩东他们提倡的“民间写作”有一定的联系。但后来,伊沙与于坚之间有了分歧,伊沙认为于坚已经成了官方的人,与他的诗歌态度不一致。伊沙有的诗比较幽默,你可以说有“游戏”的倾向,但很多诗是非常严肃的。他的《结结巴巴》,跟90年代特殊的社会氛围有关。90年代,中国诗人普遍陷入找不到表达方式的困惑,不仅仅是因为担心写出来的诗不能发表,而是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表达形式。《结结巴巴》在不能表达的困惑中,算是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结结巴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那时候他的其他诗,比如《饿死诗人》,我们都知道他十分愤怒,要“饿死诗人”,他真的那么“恨”他的同行吗?他的“狠”是从哪里来的?主要还是跟不能表达有关系,因为不能通畅的表达,所以对于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非常不满、愤怒。这些诗都是非常严肃的。
周:我知道沈浩波也是您非常欣赏的一位诗人,您也邀请他明年(2016年)二月访问奥地利,他的诗您最欣赏哪一点?
维:我很喜欢沈浩波的诗。他有自己的风格,他的诗经常写一个故事,很像一篇小小说、小话剧。
周:是的,他的诗有时候很难让人分辨是诗歌还是小说,我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读《玛丽的爱情》,同学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是诗吗?后来一次诗歌研讨会上,我细读这首诗,也有一位学者直接说这不是诗。到底怎样去定义他的诗呢?
维:判断是不是诗,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朗诵,就能知道是诗歌,还是小说、话剧或散文。朗诵的时候,能够很清晰地区分出来,诗歌有它的节奏。《玛丽的爱情》肯定是诗。
周:对于这首诗,有批评家说他写的很“世故”,就是说他非常清楚大众的兴奋点——或者说底线在哪里,而后直奔这个“点”或者“线”而去,形成某种效应。
维:沈浩波开始受到注意是因为所谓“下半身诗歌”,在这方面他很成功。他就是要让人休克(震撼),让人接受不了;你接受不了来讨伐他,讨伐越激烈,他越高兴,因为你进入了他的圈套,他就越成功。这不仅是一个策略,这也是一种态度。
周:总体来说,沈浩波一般的诗我都能接受,但类似《一把好乳》这样的诗,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诗可以这样直接吗?
维:男人的想法有时候就是这么脏,只是一般人没有说出来。类似《一把好乳》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艺术创作中,一百年前里面就有这种态度。
周:的确,相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像《一把好乳》这样的诗歌,也不算是最挑战的尝试。作为文学中与艺术最接近的文类,“艺术”和“诗”之间可以完全没有界限吗?
维:在性的方面,沈浩波真的是非常极端。这种诗无论在哪里都是挑衅,即使在美国,也会有很多人接受不了。但这是他的一种态度,对于这样的挑衅,有的人会非常反对,但也会有人非常喜欢。你说诗歌可不可以这样,我只能从个人的角度说:可以理解。我喜欢这样的态度。但沈浩波最近的一首诗,叫《我在你家喝啤酒》,不知你有没有看过,恰恰是我比较担心的,他显得很多愁善感。
周:这首诗就发表在我编的微信公众号《西川论坛》上,当时他给了我十首诗,总的名字叫《光芒伸出了他的黄金手掌》,是其中一首诗《光芒》中的一句。
维:那太好了。
周:我看您的很多诗歌,我不知道您的很多中文诗歌是翻译的,还是直接有中文写的?
维:都有。比如前面说过的《报摊》就是中文写的。像《一无所有》、《没啥好说的》是用英文写的,是伊沙翻译的。还有一些诗是用德语写的。
周:您自己写诗的时候,和翻译诗歌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维:我写诗都有一种节奏,每一首诗都有它的节奏。我写的时候,它的节奏就出来了,有了这个节奏就有了一首诗。不可能先有某个节奏,先有节奏再写是翻译。如果有一首诗要翻译,你就得找这首诗的节奏,找到了,翻译才能开始。有时候,我先就是不停的读,再想想,然后再读,然后再就试着翻译,有时候很顺利翻译出来了,有时候还是翻译不出来,就只能放弃了。
周:节奏是不是也是一种形式呢?
维:当然,节奏就是一种形式,但每一首都不同:有的时候有押韵,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是非常传统的形式,有的时候是现代的形式。你看我的这首诗HOPEYOU HAD A HAPPY MOON①,它的一半是英文,一半是德语,非常有意思。这首诗是在中秋节写的,刚好那一天也是9·11年十年,我就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是可以唱的,它的形式是一首传唱很久的德语儿童歌,名字叫Abendlied(夜曲),作者是Matthias Claudius,比歌德还要老。Matthias Claudius写了很多可以唱的诗,有的诗至今还在教堂里面唱,他的诗最明显的特点,是相信神,但不是宗教歌曲,里面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里的东西。这个曲子我经常唱给我的孩子听,心里就有这个形式。这首诗可以说是先有了形式,但里面有9·11、中秋节、跨国公司、政治家等内容,十分有意思。
周:您的诗有很多都与中国有关,比如:《一无所有》、《没什么好说的》、《想象》、《报摊》等,中国在您的诗歌里意味着什么?
维:我曾经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的时间,之前在重庆,后来到北京,我的两个孩子都是中国出生的。在《一无所有》中,你可能看到一个词“我们”(“我们都是平头百姓”),我是在2007年之后才敢用这个词,之前我都是用“他们”。
周:在这些诗中,“没什么好说的”似乎是主导的一种情绪,您能谈谈这些诗吗?
维:我的诗对中国有太多的感情,“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其中一种。相对于中国诗人,我是一个外来人,可以更超然。
周:“没什么好说的”也包含了多种情感。很喜欢《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②这首诗,感觉英语的题目感觉更好,“there is nothing”和诗歌中句子:“there is nothing to describe”;“there is nothing to explain”;“there is nothing to remember”等,更能建立丰富的联系。“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经常想到的是“说”,而没有想到“没什么好说的”的根本是“没有什么”,是“there is nothing”。“没有什么”和“一无所有”似乎也不太一样,“一无所有”让人联想到崔健的歌,勾连起的是“文革”后中国人的感受,这和中国今天的情况并不相符;“没有什么”更符合今天的感受,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仿佛很繁华,但其实是泡沫。There is nothing容易让人联想到西西弗斯神话,也能让人感受到其中个体的无力和无奈:什么都没有,你在忙什么?
维:是的。
周:您关于“西方”的诗,有很多似乎都与宗教有关,其中有个重要的意象“光”,这是神圣崇高的象征,但您经常对它们进行调侃。这种挑战的态度,和关于中国的诗是一致的,但感觉您挑战的对象发生了改变,您似乎很关注宗教问题?
维:有的是与宗教有关系的,比如那些和教堂有关的诗;有的也不仅仅与宗教有关。
周:您的《布拉格:礼拜天的犹太区》③,给我的感觉非常震撼:风琴和唱诗班开唱/房子里的人死了/银行里的人死了/邮局里的人死了/城里的房子旧了/大街和小巷旧了/(礼拜天的犹太区)。它让我想起您的《一无所有》,其中“风琴和唱诗班开场”和“房子盖了又拆”非常相似,这是嘲讽吗?
维:这是一个极端的形式。我写的时候,并不确定能不能这样写,因为是极端的形式,因为差不多每一行都一样。我最开始想到这首诗,是在布拉格的感触。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布拉格,有没有看到在犹太区纪念卡夫卡的雕塑,那个雕塑不是卡夫卡本人,是他故事里面的人,他们通个这个方式是纪念他。卡夫卡是在犹太区长大的,他的故居就在犹太区里面,就在街上那个街上。纪念卡夫卡雕塑的旁边,有个犹太庙,我在里面看到很多德语的痕迹。在东欧,在犹太人当中,很多人是讲德语的,德语文化在这里非常盛行,犹太人做礼拜常常都是用德语,卡夫卡的文学也是用德语创作的。所以在犹太庙里看到德语,并不奇怪。但二战过后,这里的德语文化就被消灭了,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在东欧也杀了很多人,这就把一部分说德语的人消灭了;德国战败后,因为一部分东欧的德语区支持过希特勒,那些说德语的人也被赶走了;还有一部分波兰、乌克兰的纠纷,也把德国人赶走了。这里面有个荒谬的逻辑。希特勒和纳粹一直认为德意志民族、德语文化很优秀,所以他们要屠杀犹太人、斯拉夫人,但在东欧、在犹太人那里,德语文化是非常流行的,那你这样不是自己在扼杀德语文化吗?
周:原来在这些诗背后还有这样的文化逻辑啊!
维:在布拉格,很多犹太人的人被杀了,但犹太庙还保存着,里面的很多文字还是德语,你能看到当时犹太人的文化,他们大多数都是用德语,不是希伯来语。在犹太庙里面,我看到德语的一句经文:“人的灵魂是神的光”,这就是“光”意象的来源。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我的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在这首诗里,我还说到“房子上的人死了”。房子上的人,是犹太庙对面屋顶上的雕塑。这些雕塑的人本来就是死的,住在里面的人都被杀了,雕塑当然也死了。卡夫卡的后代都被杀了。我到犹太区的时候,有一个小教堂,现在还在用,整好是星期天,有唱歌的声音,也有风琴,我就想写一首诗。
周:你这么说了之后,我就更明白你所说的态度了,正如伊沙所说,你的诗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悲悯。
维:他说的是《柏林姑娘》④。那是在柏林车站,她躺在一个椅子上,头掉的很低。那么睡,要不就是喝醉了,要不就是吃了毒药……我们走过之后,是准备到哪里去,我妻子说要不我们再去看看她吧,我也觉得应该去,但时间太紧,没有去成。她长的很漂亮、金色的头发,身材也很好,我不知道她为了什么。
周:感谢您接收我的访问。
维:也谢谢你!
【注释】
① HOPE YOU HAD A HAPPY MOON(希望你和月亮都很高兴)未在中国发表,特附全诗,中文翻译由诗人自己完成:the moon is up in heaven(天上高高的月亮)/they talk of 9/11(很多人说9/11)/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你不知怎么说)/the moon is very bright now(它现在非常明亮)/a peaceful ball of light now(那月球多么和平)/a rather dead one anyway.(它多么安静无生命。)//and everyone remembers(而每个人都记得)/the fire and the embers(那烈火以及灰烬)/a sudden act of war.(那豁然地开战。)/the city of the towers(它攻击整个城市,)/of music and of flowers(那摩天楼和音乐)/and everything a city's for.(那普通人间的生活。)//you think of sarajewo(我想到萨拉热窝)/you think of srebrenica(和斯雷布雷尼察)/of bagdad and belgrade(巴格达和贝尔格莱德)/you think of senseless carnage(那疯狂的大屠杀)/of buildings and of courage(那房屋以及勇气)/and of some pictures people made.(还有所剩下的照片。)//das mondfest ist erst morgen(而明天就是中秋)/heut hat man andre sorgen(今天还相当暖和)/das wetter war recht heiss(也可以说很热。)/und viele gingen baden(人家很多去游泳)/und kamen nicht zu schaden(都没有受到伤害)/die grillen zirpen gar nicht leis.(那蝉声就像八月份。)//zum mondfest isst man kuchen(中秋节就吃月饼)/den braucht man nicht zu suchen(在中国到处都有)/den gibt es ueberall(也几乎跑不掉。)/mit ananas und dotter(那油腻凤梨蛋黄)/fast wie bei harry potter(那当地风俗魔术)/ein fester kalorienschwall.(那很多卡路里大卡。)// man steigt auf eine hoehe(中秋节经常登高)/dass man ihn besser sehe(登高想看见月亮)/man trinkt und singt ein lied(一块喝酒歌唱)/und denkt an seine lieben(也想到很多朋友)/im fernen china drueben(在中国很多亲人)/an alle die man selten sieht.(你很久没见到的脸。)//they have a wall in china(在中国一条长城)/a wall in palestina(在以色列的围墙)/a wall in israel(那以巴隔离墙。)/and many politicians(而到处都有政客)/who work for corporations(为大公司而努力)/and get elected without fail.(很可能赢了大选举。)//the sun is up and shining(现在太阳已升起)/we've had a little whining(孩子们有点抱怨)/though school has started well.(不过顺利开学。)/we've had some cakes with poppy(都吃了罂粟蛋糕)/the house looks pretty sloppy(房间看到很糟糕)/I wish our son could show and tell.(但愿儿子正常说话。)//sept 2011
② 因在文中涉及中英文意义的转变,特附该诗的原文及诗人伊沙的翻译:there is nothing to describe(没啥好说的)/we are ordinary people(我们是平头百姓)/building up and tearing down(对盖了又拆)/there is nothing to describe(没啥好说的)//there is nothing to explain(没啥好解释的)/we are ordinary people(我们是平头百姓)/building up and tearing down(对盖了又拆)/there is nothing to explain(没啥好解释的)//there is nothing to remember(没啥好记住的)/we are ordinary people(我们是平头百姓)/building up and tearing down(对盖了又拆)/there is nothing to remember(没啥好记住的)//there is nothing to expect(没啥好期待的)/ we are ordinary people(我们是平头百姓)/building up and tearing down(对盖了又拆)/there is nothing to expect(没啥好期待的)//there is nothing to regret(没啥好遗憾的)/we are ordinary people(我们是平头百姓)/ building up and tearing down(对盖了又拆)/there is nothing to regret(没啥好遗憾的)//there is nothing to forget(没啥好忘记的)/we are ordinary people(我们是平头百姓)/building up and tearing down(对于盖了又拆)/there is nothing to forget(没啥好忘记的)//August 2007
③ 该诗未在中国公开发表,特附全文,伊沙翻译。风琴和唱诗班开唱/房子里的人死了/银行里的人死了/邮局里的人死了/城里的房子旧了/大街和小巷旧了/风琴和唱诗班开唱/镇上来的孩子死了/镇上来的老人死了/镇上来的女人死了/镇上来的男人死了//风琴和唱诗班开唱/教堂里的天使死了/光明中的使者死了/黑暗中的雕像死了/大街和小巷旧了/城里的房子旧了/风琴和唱诗班开唱//2011.10.布拉格
④ 《柏林姑娘》初发表于《新世纪诗典》,维马丁诗 伊沙译。附全诗:柏林姑娘/柏林漂亮姑娘/柏林漂亮年轻姑娘/柏林漂亮年轻大姑娘/睡觉在地铁/希望她活着(2015/7)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