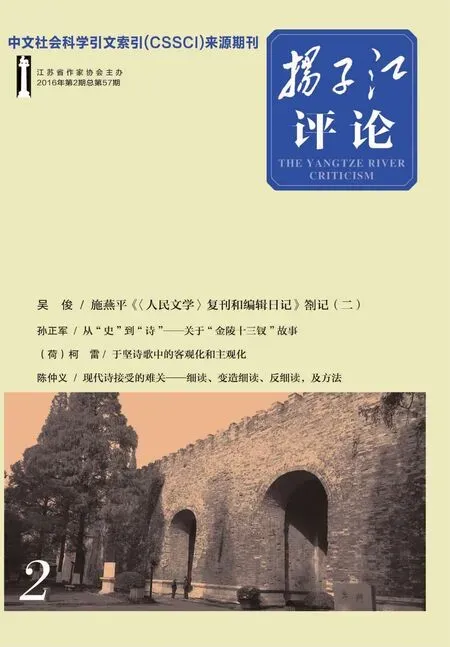打捞历史,直面现实——贾平凹《老生》阅读札记
刘晓飞
打捞历史,直面现实——贾平凹《老生》阅读札记
刘晓飞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一般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有效衔接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5N012)阶段性成果。
民族或者国家的历史积淀,会以不同姿态不同颜色不同角度不断呈现在后人眼前;而当下正在进行中的现实,更会折射出五彩斑斓的炫目光芒。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历史和如何看待现实,这体现了写作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而无论什么作品,其实都是历史遗迹或者现实事件的容器,它所能抵达读者内心的深度,最终取决于写作者的勇气、思想深度以及采用的艺术手段。在我看来,贾平凹的近作《老生》是一个颇有厚度和质感的大网,此间神话与人话交织缠绕,历史与现实交错呼应,是编织者贾平凹以莫大勇气记录惨烈历历过去当下事、经纬纵横探索创作方式的一次尝试。
一、《山海经》与阴歌
阅读这部小说,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穿插其间的古奥的《山海经》造成了不小的阅读障碍,是否有存在必要?有人认为文本中加入《山海经》是写作者在故弄玄虚,生硬勉强。让我们试着从文本出发来对出现在文本中的《山海经》进行必要的观察考量,这里面又涉及到唱师、师生的身份转化以及作品的整体构思。
《老生》以一个游荡民间的唱师为线索人物,串联起了百年中国的历史。而作品一开始唱师已经接近人生的终点,蛰居山洞奄奄一息。作为照顾和陪伴者的学生出现,然后讲授《山海经》的老师随之而来。百年历史中,唱师是经历者和讲述者,这就决定了这段历史是作为唱师回忆录的形式呈现的,这个漫游的唱师让人想起伟大的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但不同于荷马后世整理和传唱者身份的是,唱师是这段历史的在场者和参与者,对他来说,百年历史是曾经在眼前在身边的鲜活现实。类似讲述者的角色在贾平凹小说中并不少见,比如《古炉》中的善人,他们一般是年龄较长,本身就是以往历史的一部分,由他们现身说史,历史就有了很大的可信度。唱师讲述历史过程中,倾听者是学生和老师,对师生来说,他们是通过唱师讲述获得百年历史,原本长长的凝固的静态的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与事。
而且,唱师、师生是互相倾听、互相获得的,在学生学习《山海经》的时候,唱师又变成了倾听者,师生问答的内容是《山海经》,对这三个人来说,远古的山海经时代是谁也不曾经历过的,只能凭借文字和想象才能成型,那些山那些海那些神奇的飞禽走兽对他们来说是完完全全的静态凝固的,但是就像近代百年历史在唱师讲述中活色生香一样,神话时代也完全可以在三人共同的努力解读中奔腾不息。所以,正是有了《山海经》的存在,《老生》中的时间和空间大大拓展,岂止是百年历史,一下子突进到了远古时代,从而把整个人类历史和空间囊括其中。
再仔细看小说中出现的《山海经》内容,每一部分隐隐约约和后面唱师讲述的时代有所呼应。穿插在第一个故事中的两段《山海经》文字,涉及到的是混沌初开中人对世界的初步认识,有食、阴阳、神、五行、声音,而对应这一部分的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游击战争时期,也是红色革命的肇始期。第二个故事,唱师主要讲述的是解放初进行的涉及面广泛的土地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给贫苦老百姓。在土改过程中混混痞子趁机上位,中饱私囊,草菅人命等等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接二连三地出现,而靠勤劳致富行善乡里的地主却被一再剥夺和迫害,控诉无门。在相对应的《山海经》部分,出现了“西山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出现了“见则天下安宁”的“凤皇”,也出现了“其鸣自号……见则天下大旱”的“颙”,鸟兽开始自呼其号,在控诉,发泄,谁说这不是对应那些以革命之名为非作歹的魔鬼,对应那些冤死屈死的魂灵?在这一部分中,老师甚至在解读中直接地毫不客气地点出“人是有病的动物”。第三个故事的时间段是文革前后,于是《山海经》中出现了“见则大兵”的朱厌,出现了“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西王母,教师进一步解读说,兵“是指战争和杀戮,也可以是指专政”。第四个故事是文革之后,小镇畸形发展史和经济腾飞史,以及突如其来的村庄覆灭,于是《山海经》中出现了“人面兽身”的厉鬼和许许多多的怪兽怪鸟怪鱼,癫狂世界中群魔乱舞。作品结尾部分,唱师仙去,而恰好《山海经》讲到的部分,到处是“无草木鸟兽”“无草木”“无石”,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此可见,出现在作品中的《山海经》章节与唱师所讲述的相应年代之间,有着明显的互文性、隐喻性和呼应性,正是通过这样的指涉、转移和联系,文本从静止封闭走向了流动与对话,达到了“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①的效果。
从《山海经》的字里缝间,就能体会到远古时代自身的变迁;而作品中的《山海经》部分与唱师讲述的现代历史部分,有对应,有继承。西方著名历史学家维柯提出了历史循环理论,他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三个螺旋式上升的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②用这个理论来分析《老生》中的历史,《山海经》时代是毋庸置疑的神话时代。而唱师生存的百多年历史,既可以看成是与《山海经》相对的人的时代,也暗含着这三个阶段的小循环:红色革命年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起源与开端,是神的年代;土地革命年代和文革前后,由于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是英雄的时代;而经济大发展的年代,也是人类社会的巅峰,是人的时代,由于人的自私贪婪和不择手段,盛极必衰地从文明高峰摔落下来,社会与人同时毁灭。
从类似角度来看唱师的职业以及他所唱的阴歌,除了民间神秘主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让灵魂安放,打通生与死的边界,与天地万物勾连。唱师的阴歌,没有时代的限制,也没有阶级的划分,男女老幼只要被死亡裹挟而去,悲怆的阴歌就悠悠地升起。唱师和阴歌,似乎游离于残酷现实之外,两者的寿命是如此的漫长;但是实际上,在现实强大的力量之下,这个职业和这样的歌,也会出现命运大幅度的跌宕起伏,或荡然无存或兴旺繁盛,起起落落,“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品中老生“我”所从事的工作和地点一再变化:从红色革命年代正阳镇的唱师,到土改年代县城文工团的后勤杂工,到文革前后秦岭革命斗争史编写组组长,再到经济发展年代回龙湾镇的唱师,辗转反侧,腾挪起落。在第一个故事中,残酷血腥的革命年代,唱师的阴歌不断回响;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故事中,政权稳定下来,阶级斗争兴起,于是唱师消失,阴歌退却;在第四个故事中,由扒火车偷盗开始的的罪恶经济发展年代,唱师又重操旧业,阴歌又开始一再唱响,背后是“活鬼在回龙镇多得能把你绊倒”,人心死亡,肉体死亡,死亡连番猛烈袭击,直至灭村的结局。唱师最后为当归村来回唱反复唱,直唱了三天三夜,这是最后的绝唱,为当归村,为坏了的世态人心。
作者在后记中提出了一个疑问“回望命运,能看到的是我脚下的阴影,不管是现实的路还是无影的路,那都是路,我疑惑的是,路是我走出来的?我是从路上走过来的?”在这里,“我”又不仅仅是我了,是一个大写的“人”,芸芸终生的“人”。千万年来的历史是千千万万的人踏出来的血路,形形色色人物纵横交错的人生轨迹,就是一部中华大历史。通过《山海经》,通过阴歌,通过百年历史,《老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从中透露出了历史的广阔无垠与人类生存的苍茫之感。
二、随意的历史与革命的真相
如果把贾平凹的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排列起来看,会发现与之前作品相比,他倾注在《老生》中的“野心”或者是大胆创新。从写作内容和历史空间来看,从早期的商州系列,到后来的《废都》、再到后来的《秦腔》、《高家庄》、《古炉》、《带灯》,这些作品选取的基本都是一时一地的生活横断面,时间跨度短,主要人物基本一以贯之,以期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但是在《老生》中,贾平凹大幅度扩展了视野,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都给予了关注;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一再转换,一个时期的故事结束,下一个时期的故事另起炉灶换一个村镇;老生“我”是线索型人物,四个故事中的主角在不断进行变换,这样就形成了走马灯或者是折扇式的结构方式,大大扩展了作品容量。其实,这不仅是一种结构方式,更深层次是反映了小说创作中作者处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路。
但是,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尽可能反映更多人的命运变迁,在以往的小说中并不罕见。比如现代的《四世同堂》、“激流三部曲”、《围城》等;“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以史诗效果为追求;文革后也不乏此类创作,比如《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古船》、《白鹿原》、《炸裂志》等等。那么,与其他人的作品相比,贾平凹的《老生》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他笔下的历史,既不是个人史,也不是家族史,也不是村镇史,更不是战争史革命史,而是融合以上各种历史的大杂烩。一个历史阶段聚焦一个村镇,村镇里活跃着的是性情命运各异的不同的人们。这口历史大“锅”里的味道有浓烈的死亡血腥,有黑暗荒谬的权谋算计,有底层人艰难挣扎的辛酸,有无底线无下限的罪恶经济,偶尔有温暖感人的爱情和苍凉的歌声作为调剂。历史,本来就没有那么经纬分明正义凛然,历史的原初面目就是混沌的模糊的。
《老生》没有正义凛然的政治理念,也没有沉溺其中的感官沉沦,而是选取民间老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所谓的历史,对身在其中的老百姓来说不如吃喝拉撒睡触手可及。在书中,政治、革命、阶级、经济发展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的背后最根本的动因,不外还是或大或小的利益作祟:匡三参加游击队的目的是为了“要吃饱”,秦岭游击队在墙上写的标语除了“参加游击队,消灭反动派”,还有“打出秦岭进省城,一人领个女学生”!土改最活跃分子后来成为农会副主任的马生说,“千里做官都是为了吃穿,谁不为个嘴?!”正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口腹之欲,所以他上任后,大肆公报私仇,中饱私囊,逼死人命,罪行罄竹难书。“这些受利益驱动的颠覆和骚乱,……只会带来暴力频仍、血流成河。”③
在《老生》中,历史的动荡和转折充满了偶然性和随机性,没有规律也没有逻辑,历史的河流四处漫溢,而个人不过是被操纵拨弄的小蚂蚁。历史对人的虐待和漫不经心,在两个人物的命运上尤其突出。一个是戏生,一个是匡三司令。
文革后的戏生是命运最为充满戏剧性和提线木偶色彩的,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的一生就是在权威人士的操纵下不断匆忙上台扮演和转换人生轨道的,从做村长带领全村搞农副产品基地(滥用激素农药),到矿区看煤(色情交易),到周老虎式的造虎寻虎(骗政府补贴),到种植当归成为首富,他的每一步人生转折都是在老余的指挥和扶持下完成的,也几乎每一步都充满着肮脏与罪恶。具有雄厚背景的县人大主任的儿子老余也从中获得了政治资本,步步升迁,从镇政府文书到副镇长,到副县长。可叹半截子戏生风光一生,神奇腾挪一生,不过是他人升迁的工具和一枚被利用的棋子。
如果戏生是被操纵利用的小人物,他的命运身不由己,那么那些所谓的大人物或者英雄呢?他们是否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作为后来西北大军区的司令,书中没有渲染匡三的革命功绩,反而把笔墨放在了寒微之时和老年之时。少年时期他以流浪乞讨偷鸡摸狗为生,后来因了老黑一句“要吃饱,跟我走”加入了游击队;而在红色革命时期,匡三不过是老黑的跟班。在残酷的血与火的战争年月中,游击队其他人员全部受刑而死或者战死,匡三因缘巧合幸存下来。历史跟游击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多少条人命谱写的功绩幸运地落到了这个资历最浅的幸存者身上,所以有了日后他的平步青云。在后来的日子,匡三成为高踞云端的神话一样的人物,手握重权却始终神龙一般不见其首尾。但是,这个呼风唤雨的神秘人物正式出场却是让人大跌眼镜,戏生眼中的匡三司令是这样一幅相貌:“匡三司令已经很老很老了,脸很小,像放大的一颗核桃,头发却还密,但全白着”。而且戏生梦寐以求的这次会见,以首富戏生大唱情歌之后他被警卫踢得鼻青脸肿的闹剧形式猝不及防地结束了。金碧辉煌的神龙一下子在世人眼中显露出其不堪入目的荒唐真相。匡三尚且如此,在历史冷冰冰的随意之下,普通人命运更是狼狈不堪。所有的人,都无处也无法逃脱历史的狰狞。
如果用关键词来概括《老生》中所反映的各个历史阶段,红色革命时期是暴力与杀戮,土地改革时期是权力与掠夺,文化大革命前后是荒诞与恐怖,改革开放之后是经济领域的疯狂与灭绝。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各个领域的革命和改革在百年中国都尝试过上演过,其手段和后果从流血牺牲到权力暴力,从灵魂控制一直发展到大规模群体性的不择手段,从被动到主动,从个别到群体,五花八门的“革命”愈演愈烈。“‘革命’经久不息,并将适用于一切世俗政府形式;它并不建立新的世俗秩序,反倒持续不断地动摇着一切尘世建制的基础。”④匡三,老黑,马生,戏生,这些人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者或者成功者,但在他们身上,人性恶的一面同时也展露无遗甚至占了很大比重。革命的意义何在?土改的目的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工作到底该怎样展开?发家致富该采取怎样的手段?这些人为代表,所交出的是血淋淋的时代答卷。
历史是嗜血的,它轰隆隆的前行轨道上处处充斥着触目惊心的景象。这些原本应该被压抑的丑恶东西,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便纷纷奔涌而出,以饕餮,性,贪婪、妒忌等等形式充分膨胀起来;而且从群氓追求多吃半碗饭多占半亩地的蝇头小利的“平庸之恶”扩散蔓延成大规模群体性丧心病狂不择手段的严重作假,每个人都成了“我们中间的罪犯”⑤。犯罪的破坏力发展到了惊人地步,是“甚至时间所具有的那种出了名的疗治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也失效了”⑥,风起于青萍之末,从《老生》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种恶是如何一步步一代代加剧并最终吞噬了整个当归村。中华大地上,有多少当归村?
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对真实的忠实记录
贾平凹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焦灼的危机意识,“以文学的艺术的去表达这个时代,在表达中完美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的坚挺和伟大,是我们的良知和责任,虽然目下的文学艺术被娱乐和消费所侵蚀,所边缘。但是,我们相信,文学艺术依然还顽强,依然还神圣。”⑦而贾平凹的这种责任感其实一直在演变的。在最早诸如《腊月·正月》、《小月前本》等流畅优美充满乐观精神的美文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人病了,命途多舛的《废都》1993年出版,他敏锐地发现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异化,2002年出版的《病相报告》更把社会病态推进到了战争年代。在《古炉》的后记中他直截了当地说,“而文革呢,一切真的就过去了吗?……而不触及‘文革’,这是在做不能忘却的忘却吗?”“我觉得我应该有使命”。⑧除了反映病象重重之外,他还曾经试着开药方,2005年出版的《高兴》中,他的药方是近似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2011年出版的《古炉》中,他又说“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方法。”⑨但也仅此一句而已,轻描淡写,或许治病并非他的本质追求。
果然,三年之后出版的《老生》中,他放弃了治病,也不再借助知识分子外壳来代言,基本也彻底消弭了《带灯》式小布尔乔亚的细腻浪漫,甚至连他标志性的扑朔迷离的神秘主义色彩也基本散去。比《老生》出版稍早一些的2014年初,贾平凹曾经这样夫子自道,“作家艺术家生存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决定了我们的品种和命运,只有去记录去表达这个时代。以我个人而言,我想,我虽能关注、观察这个身处的社会,我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开不了药方,我难以成为英雄,我也写不出史诗, 我仅能尽力地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⑩。《老生》中,他采取了最直截了当也是最震撼人心的写法,秉笔直书的方式单刀直入——把那些最血污、最罪恶、最肮脏、最荒诞、最虚伪的东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摊在了太阳底下。须知,努力还原本真,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和担当,“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⑪。我们发现,在《老生》中他从大声疾呼的呐喊者变成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史官,把过去积攒在心里梗在喉头的珍贵原始经历公布于众,“能真正地面对真实,我们就会真诚,我们真诚了,我们就在真实之中”。⑫既敢于揭开红色革命的血污襁褓,也无惧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纷纷乱象,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真实,是他当下的基本坚守,记录者,是他当下努力的角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是一个永远的言说者和批判者。”⑬
他的真实,既不是鸡零狗碎琐屑无聊的生活下脚料,也不是政治话语规训过的“本质的真实”,磅礴的历史风云和沉重的现实迷雾,都被他举重若轻地化为民间老百姓的真实生存百态。《老生》一反常态地极少作者擅长的细腻心灵写真,而是采用了粗粝的人像速写,虽然我们听不到这些人的内心语言,也不知道主要人物的长相,但是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件连接一件,观其行知其心,在繁杂的事件中人物的灵魂从面目模糊的外部轮廓投射出来,而且从名字到命运,基本都经过了作者精心的雕琢,所以书中的人能够站起来立得住。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把一个个的独特人物拼凑起来,就见微知著地形成了一个历史和社会的嬗变史或者是病变史。其实,贾平凹之前曾经表达过这样的写作理念,他说,“我们不但需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体制,更应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中国社会基层的人事怎样个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干什么,想什么,向往什么。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入地细致地看清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在这样的作品里鉴别优秀的,它的故事足以体现真正的中国,体现出中国文学的高度几何和意义大小。”⑭
当然,《老生》把现实事件稍微改头换面录入作品的做法也引起了争议,比如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爱情天梯”事件、“周老虎”事件,“非典”事件等。之前余华的《第七天》由于太贴近现实,被诟病为“新闻串烧”。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作家情感立场与文学态度彷徨于无地的表征。当代作家和评论家一直想给文坛情感寻找一个立身之所,从早期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政治立场、到后来热情澎湃的启蒙理想、到客观冷静的零度情感、到自由自在的真实的民间立场、再到悲悯同情的底层立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生活永远比戏剧更精彩,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大趋势之下,作家们发现自己在狂飙突进的现实当中无所适从,无法给自己捕捉到的生活碎片准确命名,这导致作家们写作态度与文学立场的混沌。变化,有的时候只是无法坚守不得已而为之的,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些简单粗暴的写作手法。《第七天》和《老生》中这种直接粘贴复制生活进入文本的做法即是一种症候表现。尽管贾平凹们也在思考“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⑮但是写作立场模糊不清这个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历史与文学的结合难免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境。
历史的繁华与荒凉之处,现实的平静与热闹之所,皆是人影憧憧,他们的俯仰歌哭是时间长河中最真实的姿势与声音,而他们琐碎的生活场景与卑微挣扎沉淀成了巨大历史的厚度和浓度。贾平凹看到了他们的悲苦人生,听到了他们的呐喊与彷徨,用笔忠实地记录下来。“二十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⑯花甲之年仍然挥笔不辍的贾平凹用《老生》扫描过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大地上的最真实最惨烈的图景,足矣,“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⑰
【注释】
① 刘勰著:《文心雕龙》,刘乐贤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0页。
②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③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④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⑤ [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⑥ [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⑦ 贾平凹:《责任与风度》,《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
⑧ 贾平凹:《古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3页。
⑨ 贾平凹:《古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5页。
⑩ 贾平凹:《责任与风度》,《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
⑪ 贾平凹:《老生·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
⑫ 贾平凹:《老生·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
⑬ 丁帆:《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0月31日。
⑭ 贾平凹: 《穿过云朵直至阳光处》,《美文》2014 年第 10期。
⑮ 贾平凹:《老生·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
⑯ 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82页。
⑰ 施正康、朱贵平编:《圣经事典》,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作者简介※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