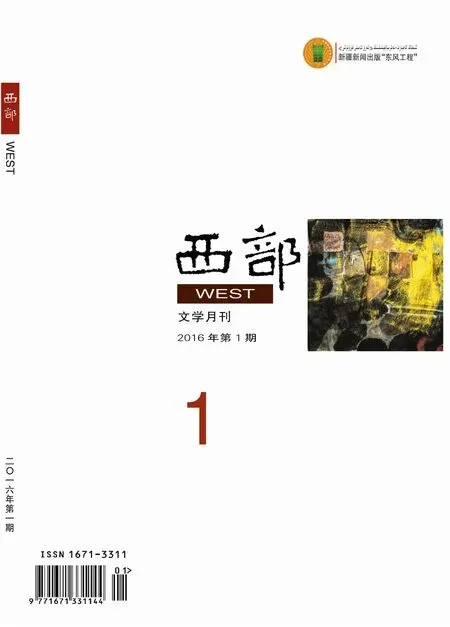八月三十日
蒋 蓝
八月三十日
蒋蓝
早晨六点即醒,看看窗外,也无风雨也无晴。凉飕飕的,晦暗、低垂的厚云拖曳残余的夜色往西缓慢飘去,给我剩下的,是一个低矮而阴霾的蜀国初秋。云在天空壅塞,当云被风撕开时,蓝色的天穹灵光乍现,突然以我难以想象的阴沉状态出现。阴霾之后是阴云,云又像是漂洗过的,在河沙一般的天空逐渐洁白。
给父亲的灵位上香,他在九年前故去。母亲现远在加拿大汉密尔顿市的姐姐那里休养,她昨晚打来电话问我好。母亲说我是早上八点钟左右出生的,为辰时。按照流行的星座,我属处女座,这星座似乎对我不利。
吃完一碗面条,我打开电脑,修订昨晚没有完成的一篇文章《卡地亚之豹》。这是词典式散文专著《豹诗典》当中的一章,猎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尚之都巴黎具有非同寻常的寓意,它牵扯到当时最负盛名的女性——意大利“暗黑女侯爵”玛切萨·路易莎·卡萨提,丽人烟视媚行,宠物就是豹,有印度猎豹和非洲黑豹,女侯爵具有展示怪癖嗜好的狂热愿望。比如,在深夜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她独自带着两只戴宝石项圈的黑豹溜达,身影像墨汁让古老的街道模糊不辨,但暗黑女神与黑豹互为彰显;再比如她曾以蛇作为项链,裸体穿起皮草外套招摇过市……当时众多艺术家都以她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她的生活场景与凸凹身体俨然成为巴黎艺术家的一块想象飞地。她以活着的蛇作为项链并不为人知地在夜间散步——名贵皮草下是她的裸体,牵着稀有的印度豹,这些豹的脖子上戴着钻石镶嵌的项圈。不管她往哪里,总能塑造风潮、制造天才,甚至让最守旧的王公贵族忘情赞叹。
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写《豹诗典》,但我的生活与豹无关,手里有一对来自天山的雪豹爪,成为了我唯一的缅怀之物。时间差不多了,我才跟女儿打通了电话。女儿十一岁了,利用暑假随妈妈外出,昨天才从泰国旅游回来,有一肚子见闻要对我讲,还特别说,为我买了礼物。我说,我不开车来,骑电动车来接你。女儿同意了。女儿从小不喜欢汽车,总说头晕,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我用自行车载她逛街。
今天是星期天,一早人车不多,我顺一环路飞速前行,再拐道插入一条静谧的小马路,沿沙河一侧的林荫道曲折北行。今天是我五十岁生日,除了比平时起床略早,似乎没有感到有丝毫特别。河水泛着白色,河畔的丝丝河风夹缠着牛毛细雨,仍带有一股特殊的野水气息。深吸一口,往事就扑面而来。这种古河流,在成都已经很少了。
一晃眼我在成都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熟悉这座城市的经脉,目睹了它的田畴渐渐成为高楼林立的集镇,也目睹了大量的茂密林被经济扩张的欲望剃成阴阳头,最后成为整齐划一的景观树。记得我的三十岁、四十岁生日也是在成都度过。满四十岁前一天,父母专程从老家来成都,父亲带来一瓶他放了十几年的五粮液与我同饮。第二天我送父母去火车北站,回到老家父亲就开始发病,检查结果是肺纤维化,此时距离他逝世刚好一年。
接到女儿,我仍然原路返回,顺着沙河走。女儿还没有变嗓,童音清脆,讲芭提雅,讲人妖,讲大象、鳄鱼表演……我静静听,没有答话。
哦,记得我与女儿差不多的年纪,父亲开始训练我和姐姐的篮球与田径。一早跑步,下午打篮球。老家周边没有正规体育场,我们沿着公路跑步,从东兴寺到王爷庙。为准确计算距离,身为工程师的父亲有一把两米的钢卷尺,他和姐姐就两米两米地测量,再用一根锯条在路肩上锯出一个口子,一直测量出两公里的准确长度。我记得,最后的终点那里,锯出的是双线。那里是龙凤山山麓,斜斜的岩石面,镌刻有冯玉祥将军1944年7月15日来自贡市举行爱国献金运动时所题写的“还我河山”四个隶书大字。父亲说,字是冯玉祥住在自贡市盐务管理局宿舍(北院,即今中共自贡市市委所在地)时写下的,那里是我爷爷后来在盐务管理局工作时的办公室。
我开始锻炼耐力,风雨无阻,一直跑到了初中阶段。父亲用卷尺测量出来的那段距离,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阶段踪迹史。十几年后,城市道路改造,路肩石砂岩被拆除了。
2014年初春之际,我修订十二稿的三十万字非虚构之书《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门岂运交错的历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我前后踏访二十五个县市,查阅了三百万字史料,在一种近乎被掏空的状态下,我意识到我正在靠近一个限度,我渐渐感觉到了它明晰的存在,甚至触摸到它的裙裾了,但这个限度又滑手而出。我实在精疲力竭,已经不大容易回忆起它的容颜,但是我知道,顺着我的行踪,我一定会与之相遇。显然,它远比父亲在路肩上锯出的刻痕更难以捉摸。这就意味着,我的踪迹史其实是我的文学踪迹史,它追求人生的完整表达,而非历史的完整呈现。今年初我又开始了《踪迹史》的修订工作,补充了近十万字。草蛇灰线,藕断丝连,刀头舔血,有火就有灰,包括突兀而峭拔的剔骨还父、剔肉还母,我的踪迹彻底融到了历史的踪迹当中。我手里没有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得涅公主的金线。我走的路告诉自己,迷宫是连续的,陷阱下面还有陷阱,我根本不需要奇迹。
中午在蜀府宴语酒楼吃饭,来了十七位客
人,绝大多数是夫人单位的同事,我的朋友仅有四位。她经营十几年的公司,在债务与季候的重压下,准备彻底放下了,这是最后的午餐。我吹熄了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但不想吃。三瓶二十多年前的老茅台喝完,就散了。我恍悟,纸上的踪迹史,那些孜孜以求的历史人物的踪迹,一当踏上他们行走过的道路,用自己的踪迹去印合他们的踪迹,我不但从泥土里获得了一段充满体温的往事,也让我的踪迹一寸一寸入到往事之中。我是时光的一个线标,也是空间里的一个点位。我就像那些沙河边垂钓者鱼竿上的浮标,一动,就拽皱满河秋波。我的半生不过在天地之间划出了一小段踪迹,甚至,还没有父亲在路肩上锯出的刻痕清晰。
黄昏时分,我送女儿回去后,再次路经沙河。星垂天宇,丛林低伏,大群蝙蝠在低空密集穿梭,但是我分明听到了子规鸟凄切的鸣啼,声音靠近金属。乔木的萧萧落叶在水面漂摇,贴水而飞,就像是一头花豹把自己身上的花瓣一片片撕扯下来。落叶不像是独自凋零,倒像是有红叶题诗的急不可耐。落叶不是随波逐流,它们一会儿侧身而立,一会儿俯仰闪避,在一股大势的默许下它们大部分绕开了河道里的障碍,但还是有一些落叶搁浅,其中有几片又终于旋转挣扎而出。我想,从远方河心升起的黑暗里,一定有一双手在等待落叶的归帆。我看见四周多是悠闲的散步者、不停狂吻的大学生,当然,还有气急败坏的绝望者醉倒在河边木椅上……
我所说的大限,如果是一种智慧和福分,似乎越过了我所听见的风声。如果说,孔夫子眼中的“天命”是关于主体存在、发展和变化的一切总体概括的话,那么“知天命”是他的自况与自傲,自谓具有了判断自己生存环境和前途以及周围事物走向的能力。我不能去评说孔夫子的见解,我不是努力要回到事理的真实,而是我的脚就站在真实的地界。真实不是挺括的刀锋,真实是柔软的,但又不能随心所欲。尽管在年轻岁月里,我早就注意过真实、真相、事实的分野,那时我的思想随笔就是为从事实里提炼真相,到了如今,我不再刻意去着意它们的差别了。
我有两年不看电视了。也许是酒意,睡到半夜醒来,开灯写诗《生日的下半夜》,算是我的五十岁自寿:
我从醉意中冷醒
看见月光在阳台栏杆上与金属调情
雾霭低回,花香可疑
醉态酩酊的女人
在成都的窗下唱歌
街灯加大了她的飘摇
她随手拾走了灯杆的影子
所有的灯在风中摇摇欲坠
与其说我早已独自成行
不如说是渔父载我渡向写作之河
我腰下无剑
只交给他一根肋骨为记
天心月圆之下
听见那个女声把锦江越推越宽
还能听到小兽的哭泣
水光里堆满赌博与火焰
如果有一个声音唤我归去
我会立即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