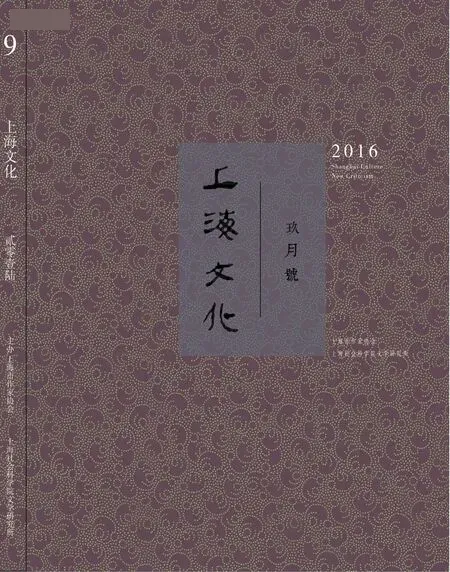钱锺书与吴兴华的骈体文学论
张治
钱锺书与吴兴华的骈体文学论
张治
骈体文以骈俪对仗为句式特征,重藻饰与用事。历来论者可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以骈体文为纯粹的骈文,即通篇皆骈者,于是排斥散文句式的混入,有意与散文(即唐宋之古文)分庭抗礼;另一派则以为骈体文可以骈偶为主,结合散文句式的优长,强调骈散会通。这两派在清代可分别以阮元和李兆洛为代表。阮元是《四六丛话》作者孙梅的门生,并受力诋唐宋古文的凌廷堪之影响,后著《文言说》,标榜“文必有韵”、“文必尚偶”,将单行的散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李兆洛服膺姚鼐的古文成就,但不满桐城义法所谓刻意地无所依傍、不求工整,他编选《骈体文钞》即多选骈中有散、散中有骈的文章,并声称“后人欲宗两汉,非自骈体入不可”①。
民国时期,就骈体文学发表研究观点的学者,尚有刘师培、李详、孙德谦、钱基博、刘麟生、钱仲联等人。刘师培尊阮、汪等扬州诸子,故也标举六朝骈文为文学正宗,其横扫桐城古文义法的《文说·耀采》一篇,多袭孙梅之成说。李、孙、钱诸辈则皆主骈散合一的观点,尤其孙德谦《六朝丽指》声称“骈散合一乃正格”,影响最大,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就拈出孙氏“骈文尤贵疏逸”的观念,总结为“疏逸之道,则在寓骈于散”。
这些可贵的意见除了列入文学史研究者的参考文献里去,能否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发生作用?众所周知,骈文从前就是考验读者学问功底的“睡媒”,至于现代中国,更成为远离我们语言应用和阅读经验的骨董。白话文学兴起之后,骈文和桐城古文一样,都成为五四新文学建设者们呼吁打倒的腐朽文言形式。胡适在其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中列出文学“八事”,其中“须讲求文法”、“不对仗”两条都点了骈文的名,至于其中的“滥调套语”和“用典”两个弊端,也是历来攻讦骈文末流容易犯的毛病。胡适终生反对骈文,至晚年在《胡适之口述自传》中还说:“骈体文有欠文明”,“是中国语文的蛮夷化”。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骈偶工整的句式不见得就总是没有生命力,就连陈独秀所写的另外一篇新文学的宣言文章《文学革命论》中,所谓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其实就是工整铺排的骈俪句式之延伸。胡适身后,毛子水为其所撰白话墓志,也不免要靠“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这样的对偶修辞来壮其声势。因此看来,崇骈抑散的文学观固然难行其道,但寓骈于散的办法不仅是很难废除的,而且也是蕴涵着汉语文学发展之生机的。本文以吴兴华、钱锺书两位新文学家兼现代学人为例,描述其读书治学中所表达的骈体文学观念,并试图探索其观念下所依托的中西文学比较之资源,庶几于文脉兴替间往往被忽略的新旧传承之处有所察见。
吴兴华(1921-1966)少时即入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并发表现代新诗,后来毕业留校任教,逐渐转向学术研究。虽然本业为西方文学,但他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甚为用功,时人以“小钱锺书”目之。自言四十岁前不著述,而年方壮年即不幸去世,因此没有多少传世的学术撰作,《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是其中难得的一篇代表作。②
《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系晚清常州武进学者屠寄(1856-1921)所辑录的清代常州骈文作家总集,有光绪十六年(1890)广州刻本。凡三十卷(另有叙录一卷),收作者四十三家,骈文五百六十九篇。清人编选的骈文总集,除了屠寄这部之外,如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及姚燮之评本、张鸣珂之《续编》,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还有姚燮《皇朝骈文类苑》,王先谦《十家四六文钞》、《骈文类纂》,大多颇有影响。吴兴华原籍为浙江杭州,于江苏之常州并无地域上特别的渊源关联。之所以唯独推重这部总集,原因当在于乾嘉以降常州诸家在沟通骈散之对立上的观点,能够使吴兴华在对骈体文学走向式微之命运的焦虑中抓住些许可资称许与推重的论题。南桂馨曾称:“骈文至常州经儒,风骨始邃。汪氏作而骈散之迹泯,阮氏起而文笔之界明。申叔崛兴,则又视前此诸家有进焉”③,实际分明是拿常州文家的成绩作为铺垫,着力在褒扬汪中、阮元为代表的扬州文脉,并以刘师培为集大成者。这往往也是后世论骈文流变者所具有的观念,就连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在树立白话文学所要打到的标靶时,也是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对立,前者针对的就是阮元所倡导的《文选》作为文章之垂范及“崇骈排散”的“文笔说”④。至于立场未有如此极端的常州骈文诸家,于是就隐匿在背后,无论扬、抑,皆少人注意了。吴兴华显然有感于此,试图挖掘骈散会通之说在汉语文学长时期发展中的合理性,才会特别撰述此文。他在开篇即引述龚自珍脍炙人口的诗章,“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⑤,并断言常州在清代文学的特殊地位:“至于词与骈体,更没有一个地区可以与它竞争。”这可能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后者在《谈艺录》一书中也是将龚自珍这首《常州高材篇》视为“常州学派总序”,并且首先肯定阳湖派古文的“文体不甚宗韩欧”⑥。但是吴兴华并不将自己的表述置于古典文学谈艺语境之内,而是表达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文体焦虑,在开篇就谈到了阅读这部骈文合集时产生的一些沮丧情绪:
这些富丽堂皇、雕琢精巧的文章今天还能给读者什么呢?它们铿锵的音调,一度曾被认为如此悦耳,经历时代的推移,不是已经接近喑哑无声了吗?它们苦心安排的文字图案,还能给任何人美感享受吗?隶事用典这一套传达手段,不是已经走向它们的反面,变为把作者和读者隔绝的障碍了吗?即使退一步说,让我们鼓起勇气,克服偏见,力求备有一定的修养,掌握一定的知识,“穿透”这层镂金错彩的外衣,结果又会怎样呢?“以艰深文浅陋”的评语转加到这些作家当中某些人身上并不算过分。
他举清初陈维崧《上芸麓先生书》的一节文字为例,谓“这无异是文字上的疲劳轰炸”,所言事情极为简单,却以言辞包裹上了厚厚的外壳,费解而又无意义。这种形式上的复杂讲究,往往吸引了作者一部分注意力,“这种注意力的牵引是横向发展的,它与思路逻辑、叙事层次等纵的方向的运动势必有些抵触。因此用骈体就不易进行深刻的说理论辩,不能写作情节贯穿的小说”。更严重的问题,是古典时代作者、读者之间共同的世界观、道德标准、文化修养已经不存在了,骈文作者“失去了读者反应的协作”,这是造成骈俪文言在现代中国失去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而此文的意义,即在于接下来的追问:“经得起淘汰的有什么?”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设者,或当以为这是毋庸回答的问题。钱玄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笼统设立的骈文这一批判对象,引向以六朝《文选》之学为根柢的扬州派,虽也斥为“文妖”,却实际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桐城古文一派的重要武器。⑦除了章门弟子于六朝文章多少有所回护之处外,也是由于骈文写作的门槛比较高,在“雕琢的贵族文学”被打倒之后,吴兴华所谓“读者反应的协作”没有了,也就不会发生太多坏的影响。但在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心目中,拒绝载道的骈文和充满文学自觉与思想自由的六朝文章,都有若干可许之优长。

吴兴华在论述中列出了若干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显得很有说服力。但他对于西方古典文学语言的掌握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因其著作太少且英年早逝,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以上他所有的例证,都来自英文研究著作的引述。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可以得知,来自西西里的高尔吉亚(Gorgias,即吴文中之“高基亚斯”)是第一个给古希腊的散文著作带入修辞技艺的学者,他的文辞好以短碎对称之子句进行铺排,效果非常类似有格律的韵文。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即列举了他的《泛希腊集会辞》中的十个例句,以强调其短小子句之间的“文义对偶”(ντθεσι)、“结构骈俪”(παρσωσι)和“音声协韵”(παρομοωσι)。⑧而修昔底德(即吴文中之“图库底狄斯”)的史书之散文,本即以文句精雕细琢而闻名,德摩斯提尼则多少学习了他的风格。但西方古典文学也刻意求工的声律与用事二端,并非骈文独有的特长。若论最特别的,其实只有对仗这一个方面。于是吴兴华又举出近代西方文学中的意大利马利尼派(Marinismo)、西班牙龚果拉派(Gongorismo)、英国尤弗依斯派(Euphuism)三个名目,说他们“都以对仗见长”,但究竟如何见长,吴文未示一例。他比较熟悉的可能还是英国文学,然而也是用二手文献,言及18世纪英国诗人写散文时对于骈俪风格的注意。那么是否这些曾经出现的流派会对欧西文学的发达兴盛产生了积极作用?抑或也如中国的骈体文一样属于时间过程中的淘汰物?吴兴华只提到近来大家重新注意到这些风格的价值和意义,也许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回答这些问题。但他所举出的例证试图说明的是,如果我们以为追求“欧化”的国语文学是一个方向,则西方文学并不排斥和缺乏骈偶、协韵与用典上的辞章雕琢。中西对比之下具有的共性,在古今沿承中都能形成传统,由此可以认为:“骈文有近乎诗的属性,它所运用的手法,都有修辞学上的根据,它可以产生独特的、不能用散文代替的效果。”德国古典学研究中,如布拉斯(Friedrich Wilhelm Blass,1843-1907)、诺顿(Eduard Norden,1868-1941)等人曾提出所谓的“形式散文(Kunstprosa)”这一概念,其中强调古希腊拉丁文中都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子句在段落中之和谐关系对于文辞节奏的作用。⑨早在1928年,五四白话文学的倡导人之一傅斯年,反对古文,但认为文饰之言是有必要的。他在中山大学讲文学史,就引介了德语中的这个概念,以为等于是《易传》所谓的“文言”,其中举例如希腊罗马时代的演说词,都并非普通口语,而是文言。又引恺撒的名言Veni,Vedi,Veci(傅译作“我往矣,我见之,我克之”),以为又有双声又有叠韵。由此看来,傅斯年的见解可算是吴兴华此文的一个先声。


钱锺书(1910-1998),较吴兴华年长十岁,又得寿终。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没有多少专门讨论骈文的文字,但辑其著作、书信与札记手稿里的散见资料,可知其在讨论骈文时所持之意见与吴兴华的观点颇为接近,且相对更为深入全面。

及至《谈艺录》中,又论“八股文实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略改上面这段话几个不关键的字,又加上一节:

再对照《管锥编》中论扬雄《羽猎赋》的长句对偶(“徽车轻武,鸿絧緁猎,殷殷轸轸,被陵缘坂,穷夐极远者,相与列乎高原之上。羽骑营营,昈分殊事,缤纷往来,轠轳不絶,若光若灭者,布乎青林之下”),又举左思《吴都赋》、仲长统《昌言》、《颜氏家训·兄弟》篇及《隋书·孝义传》类似的长联,钱锺书论道:

玩其词意,并联系他始终所持有的汉代文(无韵)、赋(有韵)有骈体之萌芽的看法,除了关于八股为骈文支流的讨论之外,显然钱锺书是反对将六朝骈文的“语整而短”的句式视为正统的文体标准的。故《谈艺录》所补引的谢汲、孙梅之说,其实和汪瑔一样“少见多怪”。
既然骈文并非始自六朝,俪偶对仗原本就是文章的一种手法,故而单纯地排斥一端,独尊骈体或散体,在钱锺书看来都是“一叶障目”的成见。《谈艺录》说: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一文中曾说:



病起晚春的池塘听莺声恰恰
朝晨深园的僻径看柳絮飞飞
逸兴登山人猜为有为的盗贼
芙蕖出水诗工如无缝的天衣

其每分子之性质,皆凝重坚固;而全体之运动,又迅疾流转。故分而视之,词藻凝重;合而咏之,气体飘动。此非昌黎之长江秋注,千里一道也;亦非东坡之万斛泉源,随地涌出也。此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

日照粪壤,不损其明;钻石入火,不损其坚;水有蟾蜍,不染其毒;鹪鹩棲鳄吻,不为所吞;贤者不涉遐想,不动绮思。冬青耸出掬林;薜荔召笼磐石;柔茵能当利刃,此非物之常乎?


❶《养一斋文集》卷十八,《答庄卿珊》,光绪四年刻本。
❷ 此篇为吴氏遗作,发表于《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
❸ 《刘申叔遗书》卷首序六,民国二十五年(1936)宁武南氏校印本。
❹ 钱玄同致陈独秀、胡适信,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6期,第3卷第1-3期。
❺ 《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龚自珍全集》,第494-4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❻ 《谈艺录》,第134页,中华书局,1984年。下同。
❼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375-3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❽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ⅲ 9,见罗念生译本,第170-17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其中所谓“音声协韵”,又可分成头音押韵、尾音押韵和词语重复三种情况。
❾ Friedrich Wilhelm Blass, Rhythmen der attischen Kunstprosa, Leipzig, 1901;DieRhythmenderasianischenundrömischenKunstprosa, Leipzig, 1905. Eduard Norden,DieAntikeKunstprosa, Leipzig, 1898.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