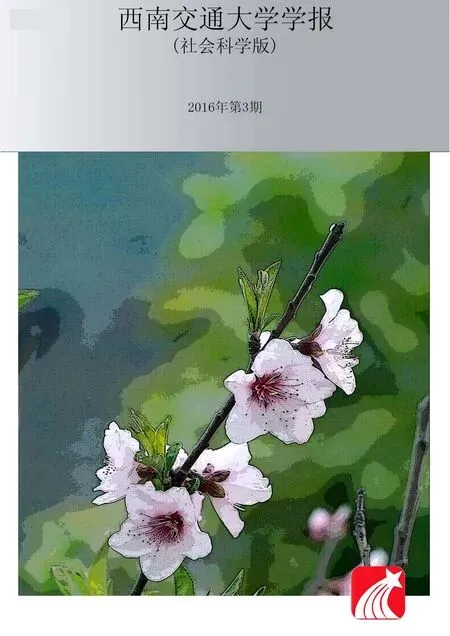“辨正新学之违僻者”:晁说之《儒言》述论
王治田
(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新加坡 637598)
“辨正新学之违僻者”:晁说之《儒言》述论
王治田
(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新加坡 637598)
晁说之;《儒言》;王安石;新学;党争
晁说之《儒言》作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时值蔡京为首的新党当政。其书专为批评王安石“新学”所作:在经学思想方面,晁说之批评了王安石舍弃汉唐注疏、统合六经的做法,并对其废弃《春秋》,推崇《周礼》以及宗尚孟子、杨雄,参合佛老进行了抨击;在具体的学术方面,晁说之认为王安石的学问有割裂琐碎、苟为异辞和牵强附会之病。此外,晁说之对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托古改制、党同伐异、滥用权势的做法也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批评。由于此书作于新旧党争激烈化的背景之下,因而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在今天看来,这部书除了对于我们认识晁说之的思想有一定意义外,对于研究王安石及其学术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及文献学价值,然而历来并未有对此书的专门研究,而王安石研究者也较少注意此书,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儒言》一卷,宋晁说之撰。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一字伯以,又字季此,因慕司马光之为人,自号景迂,清丰(今属河北省)人,晁端彦子,元丰五年(1082)进士。苏轼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荐之。崇宁中,以元符上书,落第邪等,遭到放斥。靖康初,官至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后终徽猷阁待制。建炎三年卒,年七十一。晁说之博极群书,善画山水,工诗,通六经,尤精易传,有《儒言》一卷、《晁氏客语》一卷及《景迂生集》二十卷传世。
《郡斋读书志》卷下著录《儒言》一卷,云:“右从父詹事公撰。其书盖辨正王安石之学违僻者。”是书为批驳王安石“新学”所作,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书中原注云:“玄黓执徐仲秋己丑。”时当徽宗政和二年(1112)壬辰,正值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如日中天之时。当王安石开始变法之时(熙宁六、七年),晁说之方十五、六岁,曾随父游淮南、两浙,结交旧党人物苏轼、刘恕等,由此奠定了其一生反对新法、新学的思想基调。徽宗即位后,晁说之即上《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对新党及新法大加批评。不久,蔡京上台,新党当政,大兴党狱,晁说之便因此落邪中等,遭到黜斥,隐居嵩山〔1〕。当此书写作的政和二年,晁说之方在明州(今浙江宁波)造船场任上。此前蔡京虽因物议一度被疏远,但在政和二年之初,又被召回朝,复为太师,封楚国公。五月,蔡京至阙,赐第京师,三日一至都堂议事①。可以说,此书写作之时,正是蔡京达到权力最顶峰之时,其一方面针对王安石的“新学”而发,另一方面其实正指向了当时的当权者——蔡京。这也体现了作者写作此书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由于《儒言》作于新党当政之时,因此书中不得不有所避忌,多有闪烁其辞、隐约晦涩之处。加之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今已亡佚,我们很难一一找到晁说之每一条批评的具体所指,这给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儒言》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但由于对于王安石的学术及思想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可资凭借,笔者足以勾勒出此书所论的大致轮廓。总体来讲,《儒言》对王安石的批评不仅包括了其学术和思想,也延伸到了其新法的某些内容。其时,在王安石的诸多批评者中,多只有对其学术或新法的零星评论,少数是专门针对王安石的某些著作而作,如杨时的《神宗日录辨》、《字说辨》(见收于《龟山集》卷六、卷七)。像《儒言》这样专门而全面评论王学者并不多见。此外,由于晁说之年轻时为了应科举,对王安石的“新经义”有过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其批评也多能做到有为而发。因此,《儒言》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王学及其传播的一些状况,便是一份极好的史料。以下笔者将从晁说之对王安石思想、学术、政事三个方面的批评对《儒言》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概括②。
一、对王安石思想之批评
晁说之对王安石思想的批评,不仅着眼于立论,更涉及到了对其思维方式的批判,这对南宋学者如朱熹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指出新学之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舍传疏,合六经
关于宋代的“疑经”思潮,学者已多有所论③。而所谓“疑经”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摒弃汉唐注疏。这一风气经宋初学者的发扬,在真宗、仁宗期间达到高潮。王安石继承这一学风,一方面认为经书是圣王之迹的记载〔2〕,如其《书义序》云:“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另一方面主张舍传而求经,即抛弃汉唐注疏,直接求诸经典,以得圣人之意。他批评汉儒章句之学说,云:
今衣冠而名进士者,用千万计。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则否,蹈道者则未免离章绝句,解名释数,遽然自以圣人之术殚此者有焉。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而曰圣人之术殚此,妄也。〔3〕
虽然晁说之本人订《古易》、黜《诗序》,也是宋代“疑经”风潮的一分子,但他对于经典的怀疑是以扎实的文献研究为基础的,并未笼统地反对汉唐注疏,这与王安石的托古改制、以意解经大为不同。针对王安石鄙薄汉唐注疏的观点,晁说之批评其“未为知本者”:
言《书》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诗》者,既耻言毛氏,而又不知齐、鲁、韩氏之辨,果以《诗》为何《诗》邪?言《周礼》者,真以为周公太平之书,而不知有六国之阴谋,地不足于封,民不足于役,农不足于赋,有司不足于祭,将谁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师儒尚众,而古法之变自弼始。虽以短弼,实不能出其藩篱,何以语古邪?《春秋》《孝经》则绝而不言,未为知本者。(〈知本〉)
此外,在王安石看来,六经乃先王之陈迹,其中记载的圣王之道乃出于性命之理。“先王之道理,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4〕既然六经出于性命之理,则其间必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王安石采取了“以经解经”④的办法。他说:“又,子经以为《诗》、《礼》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学,则惟《诗》、《礼》足以相解,以其同理故也。”然而,王安石的这种做法被晁说之批评为淆乱六经:
古人谓:“读《诗》如未尝有《书》,读《书》如未尝有《易》。”⑤盖知六经之意,广大无不备,而曲成无所待也。在昔汉时,六经各有名家之博士,并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为已多矣。今六经纷然为一说,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则一,而经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讲合六经⑥之说,恐不足尚也。(〈淆乱〉)
晁说之不仅认为六经不能相混,就是诸经各家也自有师承,不容羼杂:
卜子夏首作《丧服传》,说者曰:“传者,传也。传其师说云尔。”唐陆淳于《春秋》,每一义必称“淳闻于师曰”。《诗》则有鲁故、有韩故、有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毛诗故训传。《书》则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新〉)
案:汉儒极重师承,家法森严,但这一局面在唐初修订《五经正义》后便被打破。晁说之在这里却旧话重提,重严家法,其实是在批评王安石的舍故求新。需要强调的是,晁说之批评淆乱六经,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六经是相互割裂的。反之,他批评那些“一经之士”云:
五彩具而作绘,五藏完而成人。学者于五经,可舍一哉?何独并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谈经者为鄙野之士,良以此欤?汉武帝命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⑦。今日一经之士,又如何哉?盖为师者,专一经以授弟子;为弟子者,各学群经于其师,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⑧(〈一经之士〉)
可见,晁说之真正主张的是知其分而后知其合,这与王安石“六经统出一理”的解经法大不相同。
2.尊《周礼》,废《春秋》
对于《周礼》一书,今文经学家讥之为“战国阴谋之书”,而古文经学家以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⑨。而王安石更认同古文家的说法,其《周礼义序》中说:“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晁说之却对《周礼》嗤之以鼻:
言《周礼》者,真以为周公太平之书,而不知有六国之阴谋,地不足于封,民不足于役,农不足于赋,有司不足于祭,将谁欺邪?(〈知言〉)
然而,对于王安石不甚重视的《春秋》,晁说之却十分尊崇。《儒言》第一条即云:
儒者必本诸六艺,而六艺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论六艺,亦已末矣。纷然杂于老释申韩,而不知其弊者,实不学《春秋》之过也。(〈春秋〉)
《春秋》三传,《公羊》、《谷梁》属今文家,《左传》属古文家。然而,唐初修订《五经正义》,于《春秋》独取《左传》杜注。由于古文经学家更多将《春秋》看成是一部史书,如杜预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刘知几则进而从史学的角度,讥《春秋》“十二未谕”、“五虚美”等,其实对其不太重视。直至中唐谈助、赵匡、陆淳等出来,方重新统合三传,推求其中之微言大义。
有宋伊始,学者承唐代谈助、赵匡、陆淳之旧,尊尚《春秋》。石介云:
六经皆出孔子之笔,然《诗》《书》止于删,《礼》《乐》止于定,《易》止于述。《春秋》特见圣人之作,褒贬当时国君世臣,无位而行诛赏,不得如黄帝伐蚩尤、舜流四凶、禹戮防风、周公杀管蔡,明示天子之法于天下也。故其辞危,其旨远,其义微,虽七十子莫能知也。⑩

四民各有业,一业者富,二业者贫,三四焉者流离死亡矣。童子于经,轻就而易叛,既以可耻。若其白首,而崎岖岐路者,不亦可惭哉?杜预不以《公羊》《谷梁》杂《左氏》,范宁亦恶《左氏》《公羊》之轹《谷梁》,其志终可尚也。(〈业〉)

3.宗孟扬,参佛老
《孟子》在汉唐本为诸子之一家,中唐以后地位提高。而《孟子》地位的上升,与王安石的推动也是密不可分的。王安石尊孟,《答龚深甫书》云:“孟轲,圣人也。”〔5〕《答王深甫书三》云:“夫孟子可谓大人矣。”〔5〕神宗朝,《孟子》与《论语》均成为科考的必考科目。元丰七年五月壬戌,神宗下诏以邹国公孟轲配享文庙,背后均有王安石的推动。晁说之则认为孟子“其学卒杂于异端”(见〈孔孟〉条),未足为圣。
同样,于汉儒中,王安石独推扬雄。其《扬子》诗曰:“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思入无伦。”〔6〕并认为扬雄乃继孟子能承续儒家道统者,其《答王深甫书三》云:“孟子没,能言大人而放乎老、庄者,扬子而已。”而晁说之对于扬雄的批评也不少:
圣贤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谓其言有天地之殊绝也。盖圣人之言,不特无以异乎贤人,而其是是非非,亦无以异乎众人。不苟訾不苟毁,天下之达道也。果如贤人之言近如地,则众人之言将在九泉之下乎?虽然,圣贤之言无辨邪?曰:均是言也。圣人之言为圣言,贤人之言为贤言。(〈圣贤之言〉)
夫所谓贤者,能为理之所宜,而非为人之所难也。如舍所宜而论所难,则君子之恺悌不及小人之奇险矣。或难或易,在彼而吾之诚心一也。岂以彼之难,夺吾简易平康之操哉?扬子云自以事莽为难,而有是言乎?(〈贤〉)
扬雄屡论圣人、贤人、众人之别,《法言》云:“‘众人则异乎?’‘贤人则异众人矣,圣人则异贤人矣。’”又,《重黎篇》云:“或问贤?曰:‘为人所不能。’”〔7〕而晁说之则以为,圣人、贤人与众人并没有大的差异,只在乎诚之一心尔。案:“诚”本是《礼记·中庸》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程颢云:“《中庸》言‘诚’,便是神。”〔8〕张载《正蒙·诚明》篇对“诚”有专门论述。《儒言》中多有引横渠之说,晁说之以其反驳扬雄,当是受了张横渠的影响。

何晏、王弼倡为虚谈,范宁罪之,甚于桀纣。弼以其言言《易》,犹近似矣。晏之谈《论语》,则又何邪?颜子“屡空”,先儒皆说空乏,晏始斥之,自为说曰“虚心知道”,不知言之愈远,而愈非颜子之事也。或以无相无作为空,则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于释学,而释学讥其失己之传。果谁之学邪?(〈何王〉)
案:杨时《字说辨》引《字说》云:“无土以为穴则空无相,无工以空之则空无作。无相无作,则空名不立。”“无相”之说,正出佛家,与“有相”相对,指摆脱世俗之现象认识所得之真如实相。而王安石以之来解释儒家之“空”,因此受到了晁说之批评。同时,杨龟山亦评之云:“作相之说,出于佛氏,吾儒无有也。佛之言曰:‘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则空之名不为作相而立也。工穴之为空,是灭色明空,佛氏以为断空,非真空也。太空之空,岂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无此说。其义于儒、佛,两失之矣。”(《龟山集》卷七)杨龟山认为王安石以佛理解字,实际上既不合佛法,也有乖儒说,只能是两面不讨好。而晁说之的批评与龟山之论可谓如出一辙:
经言体而不及用。其言用而不及乎体,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缓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释氏体用事理之学。今儒者迷于释氏而不自知者,岂一端哉?(〈体用〉)
“体用事理”之说,出自佛家,盖以真如之相为体,以是心演化诸生灭因缘相为用。而事理之说在佛家各宗派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大约以因缘生之有为法谓为事,不生不灭之无为法谓为理;以凡夫依迷情所见之事相为事,圣者依智见所通达之真理为理。概括言之,理为真实界,事为现象界。王安石以佛理解儒经,故而遭到晁说之的批评。又如:
《易》以大人、圣人为一位。而不达孟子答问之言者,以大人未至于圣,《书》之“圣神文武”为一,已而为庄子荒唐之言所惑,则复自有神人。横渠先生亦云:“圣不可知为神。庄生缪妄,又谓有神人焉。”(〈大神〉)

庄生毁弃礼义,不知物我之所当然者,廼始语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礼安义适,宾主百拜,不知其劳,宁论忘不忘耶?(〈忘〉)
儒者之言无难易,斯可行也。著为事业,传之后世。苟得吾言者,其行与吾均也。庄老之徒则不然。其言甚大,而听之溺人而易悦。如“无为为之,不治治之”之类,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诸!(〈言浮〉)
这里切切告诫的“儒者”、“君子”之徒,当是对那些“新学”的追随者而言。
二、对王安石学术之批评
思想与学术是密不可分的。晁说之对于王安石学术的批评,其实在上面已经涉及了一些。下文主要谈其对于王安石《三经新义》及《字说》具体内容的批评,大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割裂琐碎,有欠浑融

或曰:“有户则斤之矣。”是恶夫有所者,本诸庄老而云尔也。吾儒者居其所而不迁,唯患无所,彼岂不戾哉?盖放之四海而准,孰非吾所尚?谁戕我也耶?彼以不善为善之类,皆学庄老之过云。(〈所〉)

《诗》不知礼义之所止,而区区称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独在《诗》?(〈诗〉)
所谓“不知礼义之所止”者,盖指《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而言。只要是言,均有法度,不独在诗。王安石的解释显然过于浅薄。
琐碎之病除了体现在解析字义的滥用“右文说”上,还体现在解释字句时的割裂语义上。王安石似乎很喜欢咬文嚼字,甚至把很多连绵词都拆开来逐字解释,因此受到晁说之訾议:
同燕于一堂之上,而宾主莫分,吾无恨焉。兄弟筑室而不相为邻,则吾恨且惭矣!经本二意者,纷紊纠射之说,敢彼之责邪?其本一言,如和顺道德。而谓和道顺德,挑挞往来之貌,猗傩柔顺之辞,亦析而辨之,则破坏形体甚矣。(〈碎义〉)
案:《诗·郑风·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毛传:“挑达,往来相见貌。”王安石却将“挑达”二字拆开解释,《毛诗李黄集解》李樗云:“挑达,王氏则挑为佻字读,达为挞字读。……王氏以为诱挑开达之事乎?”〔11〕
最后,便是表现在义理的辨析上。如其将“事道”分而为二,晁说之批评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虽有至道,而无非事也。若夫君子,则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于圣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事道〉)

再如对《礼记·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解释。杨时《答胡德辉问》云:“世儒以高明中庸析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为圣人以高明处己,中庸待人。则圣人处己常过之,道终不明不行,与愚不肖者,无以异矣夫!”〔12〕
案:龟山之婿陈渊与高宗辩论时,尝谓王安石:“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己。”〔13〕可见龟山所讥弹者,实安石之说也。对于王安石这一观点,晁说之批评道:
吾儒之道所以异乎诸子者,为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万物融和,未尝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极高明,而又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刚柔缓急相济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广大精微”之类亦然。(〈高明中庸〉)
类似的批评,见〈天人〉〈心迹〉诸条。
2.苟为异辞,好逞新说
晁说之对王安石学术的批评,也在于其不能守成持重,而好为新说,如其批评荆公解《诗经》之流于“巧慧”(见〈巧慧〉条)。又如:
好苟异者,必无忌惮,而愎上侮下,将流毒海内而不可御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变异,则至理隐微,谁其正之?先儒说《淇澳》“緑竹”曰:“緑,王刍;竹,萹竹。”今廼以为一物,不知“緑竹青青”,何等语邪?先儒说《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贝锦,贝也。”今以为虺为蜴为贝为锦。(〈苟异〉)

有趣的是,晁说之将王安石的这种好为新说,与其南方人的身份联系了起来:
南方之学,异乎北方之学。古人辨之屡矣。大抵出于晋魏分据之后,其在隋唐间犹云尔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盖南方、北方之强,与夫商人、齐人之音,其来远矣。今亦不可诬也。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南北之学〉)

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昔荆公参政日,作《兵论》稿,压之砚下。刘贡父谒见,值客,径坐于书院,窃取视之。既而以未相见而坐书院为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见,荆公问近作,贡父遂以作《兵论》对,乃窃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诵之。荆公退,碎其砚下之稿,以为所论同于人也。皆是江西之风如此。〔15〕
3.牵强附会,不知变通
由于王安石“六经一贯”的思想,其在解经的时候,多不论六经之别;于六经之中,又不分三代之制,因此遭到了晁说之的批评:
智之所难适者,我所遭之时也。学之所难明者,在昔数千年之异制异时也。三代之礼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礼》之“五玉”为《虞书》之“五玉”,可不可邪?(〈知时〉)
案:《虞书》之“五玉”,见《尚书·舜典》:“修五礼、五玉。”传:“修吉凶宾军嘉之礼,五等诸侯执其玉。”《周礼》之“五玉”,见“弁师”一节:“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为之,而掌其禁令。”郑注:“子男璂,饰五玉,亦三采。”《周礼》所说的“五玉”是针对周制(若按晁说之认同的今文家的说法,则是战国时期),而《虞书》的“五玉”要上推到尧、舜时代,中间几隔千年,则其含义亦当有所不同。然而王安石却将之混为一谈,明刘三吾《书传会选》卷一引王氏云:“凡贽,诸侯圭,《周礼·小行人》:‘六币——圭,璋,璧,琮,琥,璜’,注云:‘币,所以享也;享后用琮。’则余五玉即所贽之五玉也。”此说当时即遭到人们的批评,林之奇曰:“自‘五玉’至于‘一死,贽’,皆其所贽之物。量其贵贱轻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义理于其间。王氏曲生义训,皆从而为之辞,穿凿为甚。如此等说,皆无取焉。”(《尚书全解》卷二)〔16〕。晁说之进而说道:
董仲舒曰:“《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范宁曰:“经同而传异者甚众。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呜呼!古之人善学如此,今一字诂训,严不可易。一说所及,《诗》《书》无辨。若五经同意,三代同时,何其固邪?(〈同异〉)
王安石的这种看起来不知变通的观点,主要是由其“统合六经”的经学观决定的。因为既然天下一理,六经、三代之间,自然也不会存在任何的隔阂。也正是由此出发,王安石建立了自己的训诂学方法。其《进字说表》云:“故仙圣所居,虽殊方域,言音乖离,点画不同。译而通之,其义一也。”〔17〕他认为不同的地域之间,语言文字都是可以相通的,而这种所谓相通,正是建立在义理相通的基础上。对此,晁说之批评道:
或以李斯之六书为一说,自谓得圣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异音,译而通之,其义一也。”君子谓是义之说也,非字之义也。武陵先生患汉以降,学士互相增添,字倍于古。其所感深矣!(〈字〉)
王安石将义理上的普遍性(义之说)与字义训释的特殊性(字之义)相混淆,导致其不顾时代、地域以及经典文本具体语境的区别,从而产生了混乱。表现在训诂工作中,便是喜“通训”而斥“独训”。“通训”和“独训”乃是训诂学中的术语:所谓“通训”,是指训诂过程中采取字、词常用义进行训释的方法;而“独训”是指在训诂过程中重视采取字、词的生僻义进行训释的方法。由于语言的变迁,古书中很多原有的字义都发生了改变,变得陌生,因此常用义和生僻义的关系也是相对的。古书的训释中,本应视具体情况,配合“通训”及“独训”来使用,王安石却一味斥“独训”而用“通训”,将古字古义统统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进行解释,因此多有捍格不通之处:

应该说,这样的经典解释风气是受了宋代“疑经”风气的影响。而反映在《诗经》上,便是对《毛传》的摒弃。欧阳修在自身的解经过程中,便多次跳开《毛传》,自出新义。这种风气影响到了苏辙等人。如上文所举对“观”字的解释,苏辙《诗集传》卷十四即云:“所获于其获也,又将从而观之。”卷十九解释“桓拨”云:“桓,武也。拨,治也。”训“桓”为“武”,也是一种“通训”。这些解说都被后来朱熹的《诗经集传》所继承。晁说之本人虽然也黜《诗》序,但只是反对王安石“《诗序》,诗人作自制”的说法,并没有否认毛传本身的价值,这也体现了其对宋代“疑经”风气的反思。其云:
古人训诂缓而简,故其意全,虽数十字而同一训,虽一字而兼数用。后进好华务异,训巧而逼,使其意散。两字、两训而不得通,或字专一训而不可变,或累数十言而不能训一字。嘉祐学者,犹未覩此也。(〈训〉)
这里的“古人”,显然是指的汉唐注疏,而宋人总体对于汉唐注疏是唾弃的。晁说之却表示了对古人注疏的欣赏:
典籍之存,诂训之传,皆汉儒之力,汉儒于学者何负,而例贬之欤?后生殆不知汉儒姓名、有书几种,恶斥如讐,汉儒真不幸哉!昔人叹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系之辩讷,良有以也。(〈汉儒〉)
以汉儒之说而反对当时流行的解经方法,是难能可贵的。
三、对王安石政事之批评
晁说之对于王安石政事的批评,其实是与对其思想、学术方面的批评紧密联系着的。事实上,晁说之对于“新学”的批评,都是以对“新政”的批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晁说之对其政事的批评,更多蕴含在对学术和思想的批评中。有些在上文已经提到,这里姑作一钩沉。
1.托古改制,自我作古

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所谓庶人在官者也。……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19〕
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了历史上的王莽。王莽所行王田、六管之法,就都是以《周礼》为依据。《汉书·食货志》云:“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就连王安石暴躁的脾气,也与王莽有几分相似之处。晁说之批评新学,即多以王莽拟之(见〈公议〉〈不夺〉〈淆乱〉〈幕古〉诸条)。对于王安石以《周礼》为依据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晁说之也有批评:
一道德以同风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谓一道德者,乃上之风,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声响之相从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风俗。将以刑戮胜奸,而上劳下悴矣。弊将奈何?是齐八政以防淫者,亦二术邪?(〈同风俗〉)
《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新政之初,王安石在《与王深甫书》中即谈到:
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则吾友庸讵非得于人之异论,变事实之传,而后疑我之言乎?〔5〕
王安石把“一道德”和“同风俗”作为自己新政的目的,然而在《洪范传》中,他又说道:“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后俟之以刑戮。”〔20〕也就是主张通过教化和刑戮相结合的方法来达到郅治的目的。而晁说之认为,司徒之教,重在教化而已。如果以刑戮待民,则会使“上劳下悴”,疲于奔命。这可以说是他对王安石新政中滥用刑罚的批评。
再如,王安石以为用人当无流品之别,其新政中多破格提拔新人,并且在《周礼》中为自己的做法寻找依据。其《周官新义》云:“府史胥徒虽非士,而先王之用人无流品之异。其贱则役于士大夫而不耻其贵,则承于天子而无嫌。”〔21〕晁说之对此批评道:
或谓先王用人无流品之别,不知臯陶陈九德,而俊乂在官。则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权,倒置名器,不为此论。则无以济其术云。(〈流品〉)
晁说之认为,《尚书·皋陶谟》中即有“九德”之判,可见先王并不是不重流品。王安石这样说,不过是为自己破格选拔实行新政的人才寻找依据而已。事实上,由于王安石用人过于不重流品,反而导致了用人原则的混乱。新政中,很多小人如吕惠卿、章惇、李定等鱼目混珠、得以进身便是明证。而用人不当也是新政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如对于王安石财政措施的批评:
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自天子至于庶人,用财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为地无遗利之说,何其与圣人之言乖戾邪?为其下者,不亦难哉?因以贤乎桑弘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祸天下矣。(〈地无遗利〉)
北宋立国伊始便伴随着冗官和冗兵的问题,虽然朝廷一直增加岁入,但依然入不敷出。王安石新政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新法中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均涉及到财政方面的问题,但是并未将着眼点放在如何“节流”上,而是注重“开源”〔22〕,即设法增加朝廷的收入,因此,也被目为为朝廷敛财而受到批评。“不尽利以遗民”出自《礼记·孔子闲居》,郑玄注:“不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要极力从百姓身上获取更多的财源,并试图从经典中找到这样做的根据。《毛诗李黄集解》卷十七李樗说《七月》云:“王氏为筑场圃者以无旷土,筑场于圃地。此之谓地无遗利。方其为圃则种果蓏之属,及其纳禾稼然后为场焉,岂非地无遗利乎?”〔11〕然稽诸史实,宋初的财政危机并不在于朝廷不善于增加岁入,而是在于耗费太多。新法由此成为扰民之法,备受訾议。

说“平颁其兴积”,不问欲否,而概与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三弊〉)
案:“芟角”一词本出《隋书·经籍志》。晁说之谓:“不顾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济私欲,而困众论者,谓之‘芟角’。”(〈三弊〉)芟芟,角长貌。张籍《山头鹿》诗:“山头鹿,角芟芟,尾促促。”芟角,谓长角也,盖喻人之喜逞怪异之谈、以哗众取宠者,类此鹿角芟芟高者也。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对经典胡乱加以解释,因此受到了“芟角”的批评。
2.党同伐异,排摈异己
王安石个性强烈,自视甚高,其过于激进的改革措施无疑为其新法的推行增加了难度。许多本来可以争取的盟友,如欧阳修、程颢、苏轼等,都被他推向了敌对的一面。士人评价其“好学泥古”(唐介语)、“狷介少容”,正中其短。晁说之批评道:
温公曰:“经,犹的也。一人射之,不若众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呜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顾肯伸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摈前儒,颠倒五经者,亦宜媿诸?(〈的〉)
真正的君子是不会通过诋斥他人来使自己的行为获得正当性的,王安石的这种姿态,恰恰透露出了对自己的不自信。王士祯《居易录》卷十六云:“此谓安石排摈韩、富、文、司马诸公之异已者。”王安石的这种党同伐异的做法被晁说之比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朝的文字狱历来备受斥责,晁说之却称之为“善焉者”(见〈善术〉条),正话反说,正是对王安石的讽刺。又如:
国家因党与而倾亡,经术因党与而不明。《春秋》以传而分为三,董仲舒、江公、刘歆于三家始倡其所异而隄防之。杜预、何休、范宁又辟土宇而兴干戈焉。毛诗初异于郑氏,而王肃申毛,孙毓理郑,皆相待如冦雠,愈出而愈怨矣!元行冲叹其“父康成兄子慎,宁言孔圣误,不道服、郑非”,良有以也。(〈党〉)
宋代的党争是历代中最为激烈的一个。由于宋代的党争是以士大夫为主体,因此,其争论的焦点不光包括政治路线,还涉及学术思想的争论。欧阳修尝作《朋党论》云:“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且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为这种党争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经庆历、熙宁直至宋末的激烈争斗,国家的实力也在内耗中极大地被削弱。晁说之这里虽然说的是经学中的党争,事实上也包含了对政治上党争的反思。
3.滥用权势,破坏祖法

对此,晁说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见〈弃旧〉〈不得已〉条),认为王安石的“新学”乃是淆乱视听,使得先儒旧说无由得存。这已经算是很委婉的批评了。他更认为,王安石的“新学”之所以能横行天下,并不是因为其本身的学术价值,而是由于王安石凭借当时的权利和地位强行推行的结果,所谓“传势”,而非“传经”:
张禹专帝与太后之宠,所谓《张侯论》者,廼盛于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内,其五经之注,学者尚之,至于勒为石经。逮夫禹死浩诛之后,无一人称道其说者。则前之所传者,非经也,势也。(〈传势〉)
晁说之甚至将王安石与一些历史上的乱臣贼子相提并论:
尒朱荣、晋公护无君大恶。既死,庙而祀之,以配圣人。范阳间祀安、史为二圣。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则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祀圣〉)

晁说之对王安石的另一批评,便是其对祖宗之法的破坏:
姜至之先生谓商周之所称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远及异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则亦悖矣。(〈先王〉)

害辞未至于害意,害意未至于害教。害教则三纲五常絶矣!谓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咈之,类其害教,奈何?(〈害教〉)
在晁说之看来,王安石的狂论不仅是对宋朝家法的破坏,而且有悖于儒家经典的精神,表面上是宗经尊上,其实是为自己的新法寻找政治资源,是一种“害教”行为。
四、余论:《儒言》文献价值略窥
《儒言》由于是专门辨正王安石之学所作,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因此其流传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书收入晁氏《景迂生集》第十三卷。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儒言》一卷”,可见是书当时已有单行本,然《宋史·艺文志》并未见著录,或许当时已经失传。其后也一直未见诸家目录著录。至晚明,晁瑮宝文堂嘉靖三十三年(1554)刻有《晁氏儒言》一卷,今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另有同年与《晁氏客语》的合刻本,不知是从晁氏文集中厘出者抑或当时别有家藏本。祁氏有澹生堂余苑明抄本,题名《晁氏儒言》〔27〕。是书之收入丛书者,有《四库全书》本,题“儒言”一卷,亦未知出于何本。另有清初《学海类编》本,民国《丛书集成初编》据以排印。

《儒言》引或曰:“有户则斤之矣。”当为王安石《字说》中讲“所”字的佚文,然而张宗祥先生辑录《字说》佚文时,并未收此条文。再如《儒言》中讲到“关关”一词,云或曰:“和而有通意。”今仅见罗从彦《豫章文集》卷十四引杨龟山有此说,然据晁说之此处所引,当为王安石《诗经新义》的佚文。然而,迫于时代环境,晁说之在批评引用之时,多以“或曰”“世儒以为”等名之,显得有点闪烁其辞。但我们只要明白了《儒言》专为辨正王学之旨,就可以确定这些佚文出自荆公经学。再如“善不及美”(善美),以“交泰”说《泰誓》(燕书)等,现在尚未找到其他佚文作为佐证,但基本也可以确定是来自荆公之说。另外有一些条文,亦可以通过与同时其他的解经著作相参照,确定是荆公之说,如说“可”为“仅辞也”。今仅见南宋郭雍《易说》卷二及卷四提到这样的说法,但参照《儒言》,当是来自新学。所有这些条文,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研究王安石的经学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看来,此书具有极大的整理和校勘的必要,需要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京传》作“二日一至都堂治事”。案唐尚书省署居中,东有吏、户、礼三部,西有兵、刑、工三部,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总辖各部,称为都省,其总办公处称为都堂。宋金沿之。元丰改制后,遂以尚书省的都堂为宰相办公所在,因此也称都堂为政事堂。
②本文所引《儒言》文字,均以《嵩山文集》卷十三所收本为底本,个别地方据《学海类编》本和《四库全书》所收本加以校勘,且由于体例所限,除特殊需要,不出示校勘记。下文中所引《儒言》文字,仅标篇目,特此说明。
③参见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④参见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按:“以经解经”本为西方神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在解释《圣经》的某一段经文时,必须注意到整本《圣经》中其他经文的相关含义,此为解释《圣经》之一项基本原则。而李祥俊借此来指称王安石用各本经书来相互诠释的解经方法。
⑤此出李翱《答朱载言书》:“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见《李文公集》卷六,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本。
⑥《汉书》卷九十九:“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第4140页。
⑦《资治通鉴》卷十九“元狩三年”:“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胡三省注:“汉时,五经之学各专门名家,故通一经者不能尽知歌诗之辞意,必集五经家相与讲读乃得通也。”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第636-637页。
⑧《汉书》卷三十:“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第1723页。
⑨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刘歆、何休语。见《十三经注疏》第6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⑩石介《与张泂进士书》,见《徂来石先生集》第164页,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按:笔者此处与陈植锷先生断句有所不同。























〔1〕张 剑.晁说之年谱〔C〕∥晁说之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83-94.
〔2〕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0.
〔3〕王安石.答姚辟书〔C〕∥王文公文集(卷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94.
〔4〕王安石.虔州学记〔C〕∥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402.
〔5〕王安石.王文公文集(第七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81,86,83,85-86.
〔6〕王安石.王文公文集(第七十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776.
〔7〕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26、399.
〔8〕程 颐,程 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9.
〔9〕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百三十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4:5660.
〔10〕王安石.王文公文集(第二十九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338.
〔11〕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二)——诗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5,53,167、182,113.
〔12〕杨 时.杨龟山先生全集(第十四卷)〔M〕.台北:学生书局,1974:696.
〔13〕脱 脱,等.宋史(第三百七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630.
〔14〕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1554.
〔15〕朱 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71.
〔16〕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
〔17〕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36.
〔18〕林之奇.上陈枢密论行三经事〔C〕∥拙斋文集(第六卷).北京:线装书局,2004:643.
〔19〕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9.
〔20〕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84.
〔21〕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三)——周礼〔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22〕钱 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69.
〔23〕脱 脱,等.宋史(卷三百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619.
〔24〕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81.
〔25〕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上海:世界书局,1936:491.
〔26〕脱 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550.
〔27〕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M〕.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1.
(责任编辑:武丽霞)
Criticism on Contraventions of the New Theory: On Ruyan by Chao Yuezhi
WANG Zhi-tian
(SchoolofHumanityandSocialScience,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Singapore637598)
Chao Yue-zhi;Ruyan; Wang An-shi; New Theory; Party Conflict
Ruyan(StatementofConfucianism) by Chao Yuezhi was composed in the 2nd year of Zhenghe(1112 C.E.)of Huizong’s reign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n the New Party was in power. It specifically criticized Wang Anshi’s New Theory. In the aspect of Confucian thoughts, Chao criticized Wang of abandoning the commentaries by Han and Tang scholars, synthesizing and integrating the six classics. Wang Anshi’s despising Spring and Autumn and praisingZhouli, upholding Mencius and Yang Xiong and introduction of Buddhist and Taoist thoughts were also blamed. In terms of concrete academic methodology, Wang was considered to bear the shortcomings of incomprehensive and trivial explanations and enthusiasm of novelty and new sayings, thereby making many eisegesis and wrong conclusions. Meanwhile, Chao Yuezhi made criticisms by innuendo on the implements of restoring the antiquities, alienating those with different views and abusing his power during Wang’s reforms. As this book was writt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vere party conflicts, it is of great contemporaneity and pertinence. Except for its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cognize Chao Yuezhi’s thoughts, this book is of considerable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value to study Wang Anshi and his academic thoughts. 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any special research on it and it has seldom raised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which, I have to say, is regretful.
2015-09-22
王治田(1988-),男,山西阳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E-mail:wang1139@e.ntu.edu.sg。
I206.2
A
1009-4474(2016)03-01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