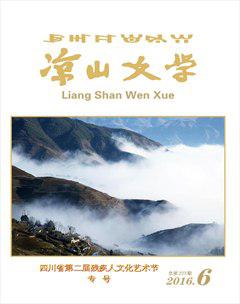“世界以痛吻我 要我回报以歌”
巴久乌嘎
人生刚刚开始,朱仲顺就承受了这个世界所有的悲凉、艰辛与绝望,一切与阳光、美好、温暖相对立的东西,在他幼年时就缠绕上他,并以另一种无形但有重量的方式沉沉地压在他的心间,犹如梦魇。
“别趴着,站起来,胸挺直,头昂起。你铭记老人的教诲,把它蝶化成拓荒之梦、奉献之梦。商海浮沉,风雨搏击,大浪淘沙,生命因报效桑梓更加怒放。”这是2014年年初“感动凉山2013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给朱仲顺的颁奖词。因为有着十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现在又是文学期刊的编辑,我对类似的活动和其间涌现出的人物有着特别的关注。看了朱仲顺的故事,头脑中出现的就是开篇那段并未经过严格组织的文字。
很难说我那种近距离认识朱仲顺并与他攀谈的冲动何以如此长久,以至于我都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对州残联的朋友说起过自己的意愿。州残联教就科副科长蔡文的电话如约而至。蔡文说张建英理事长和她要去会理、会东看看两县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建设情况,附带看望一些残疾朋友,“可能见得着朱董”,问我去吗。我清楚地记得我说过,残联去会东下乡,车有空座一定记得叫上我。蔡文的这个电话显然是说“车上有座”,而且有确定的出发时间:2015年7月20日上午8点。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可以聊的还真不少。不过,无论从何处起头,最终自然会回到朱仲顺这里。张建英在计生卫生部门都任过职,她说,初到残联当理事长时也有过为残疾朋友服务就是尽可能地多为他们争取一些“利益”的认识,“显然,这种想法是肤浅的,”她说。不少残疾的兄弟姐妹“不等、不靠、不要”,还真的可以教育健全人,“2013年和2014年凉山残联的工作连续两年在全省获得一等奖,我就说与大家的辛勤努力分不开,但辛勤努力的动力就恰恰来自我们服务的对象,这个群体是好样的。”说完还列举了一串名字,言下之意,朱仲顺很突出,在凉山却绝不是一枝独秀。我明白张理事长的意思,但有着农村生活背景的我还是关心同样生活在农村的朱仲顺是怎样“成人”、“成器”的。
朱仲顺大不了我几岁,我知道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积淀得最为丰厚的“土壤”:贫穷与愚昧。自然,贫穷与愚昧之上衍生的,就是可以要人性命的歧视与偏见。
朱家的“这个娃都会成器吗?”今年78岁的陈绍云是看着朱仲顺长大的,他说,这就是当时大家对他的完全一致的怀疑。“现在他成器了,大家都沾他的光了。”
“像蛇一样爬行。”这是朱仲顺童年的写照。1965年,朱仲顺一岁。一岁的他突然罹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双下肢残疾,用现在的标准来说就是“一级重残”。
“刚刚想要看清世界的广大,命运却残忍地剥夺了他行走的权力。”朱仲顺的同学这样感叹。
在这位同学的记忆中,朱仲顺从上学第一天起,往返于学校和家的路途中他都在痛苦地“爬着来爬着去”。
孩子都顽皮,农村的孩子更甚,加上忙于地里活计的大人疏于管束,无论是学前的玩伴还是上学后的同学,都有不少人把朱仲顺当做“怪物”、“玩物”,轮番在毫无反抗能力的朱仲顺身上“骑马”。
现在回忆当初,朱仲顺的同学都有“不堪回首”的负罪感,尽管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伤害了别人多深,但长大后想来这样的行为“就是自取其辱”。他说,大家现在都不提这些,老朱也不提,“就像没有过似的。”
无法行走,甚至不能直立,他以最低的视角观看这个世界,以自己的身体丈量着路径,鼻子距离路面如此之近,可以让他清楚地说出路在嗅觉中的反映——那是一种“可以刺激出眼泪的强烈的酸和烧心的辣”——所有这些,都包含在这样一个词汇中:屈辱。
由“路”带来的屈辱在朱仲顺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痛,历久难消。最终真正能够释放或者缓解这种疼痛的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后。2012年,朱仲顺48岁。此刻的他已经是会东县“规上企业”仲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朱仲顺的家乡距离县城5公里,有一个甜美的名字——“葡萄村”。
“名字虽好”,环境条件却“不敢恭维”。村畜牧防疫员陈昌玉说,他到这个村来工作,“连走路都恼火。”家畜家禽的防疫工作,大多集中在多雨的春秋两季,村中的那条小河暴涨,不仅没桥,还可以冲毁两岸的农田。陈昌玉时常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苦不堪言。“现在好了,骑着摩托,可以随便到每家每户的院坝。老朱的功劳。”
对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朱仲顺总想为它做点什么,“我有十分力气,就不会只为家乡尽九分的责任。”如他所说,葡萄村的事他不仅有心,而且有情有义,表现在行动上就是竭尽全力,全力以赴。500万元对2012年的朱仲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无偿出资500万元对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仲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更是一个风险意味十足的决定,但朱仲顺就是一个“认准了就干定了”的人。沿河新建葡萄村公路对家乡交通的改善无疑意义重大;而更为重大的还在于这条路的修建有效保护了河边的粮田,荒芜了20年的83亩水毁田地也将得到恢复。谁都知道,后者对祖祖辈辈靠土地吃饭的葡萄村人意味着什么。结果,“个体老板”朱仲顺出了“550万还多”,不过,是“笑起给的”,葡萄村的乡亲作证。
“一旦让我开始,将永远没有结束。”公路好了,乡亲们称赞的话语还在耳边回荡,朱仲顺的目光却又盯上了村里的桥。“修路架桥,本不可分。”时隔一年,一座30多万的惠民桥在故乡的小河间横跨着,乡亲们说,这桥怎么看都“顺眼”,虽说平躺在河上,但笑眯了看就“像一道彩虹”。
在诸多类似修路架桥的善行义举中,朱仲顺还是对小岔河乡“小七队”的那条水泥路印象深刻。“小七队”太闭塞,交通太不方便。这条他在2013年出资40多万拓宽、铺设的水泥路,通往偏远,故而也鲜有关注。但山里人特别记情,山里人也特别感恩,无以回报使受益了的他们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除了在修路前陪村干部来背朱仲顺上山所表达的敬意,路修好后,大家私下里把这条路叫做老朱给我们修的“幸福路”。
朱仲顺近些年来获得的荣誉不少,他是2013年“感动凉山十大人物”之一;凉山电视台“今晚8:00”完全由观众“票选”出来的“凉山好人”;他还获得过首届“巴蜀慈善奖十佳爱心慈善楷模奖”以及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范人物。
纷至沓来的荣誉面前,生性低调、向来谦逊的朱仲顺更多的是觉得自己不够格、受之有愧,甚至表现得有些腼腆羞涩。但当他听到山里的同胞把自己帮助修建的一条路叫做“幸福路”时,老朱的眼眶湿润了。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而是因为这个普通普遍到大有“抄袭”之嫌的称谓把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的一条“路”同“幸福”紧紧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成为这样一组词汇:朱仲顺,路,幸福。
多少年来,在朱仲顺的潜意识中,“路”和“幸福”是一对“天敌”,“路”就是痛苦,“幸福”就是不用去“爬路”。有时候,路就是“无路可走”的“路”,路甚至可以直接说就是对不能正常走路的他实施的一种暴力,暴力的名字叫做“羞辱”。
对“路”的偏见与“仇视”,是朱仲顺多年“秘而不宣”而又郁积于心的块垒,年近半百之时,终于冰释。这是他此际一个近乎崭新的发现,为大家修一条通往“幸福”的大地上的路,也就同时为自己筑就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心灵上的路。
倘若一个四肢健全的人突然具有了飞翔的能力,会是怎样的欣喜?没有多少人能够准确回答。但朱仲顺在九岁那年有过“飞了起来”的切实感受和欣喜。
爱有的时候表现得太残忍,所以,对它的理解往往容易滞后。这是朱仲顺多年以后的慨叹。“爬行”了一天回来,父母在院子里又有木桩“伺候”。朱仲顺的双手平举,被捆绑在这上面,目的是让他学会站立。不知有多少时日,精疲力竭回到家中的朱仲顺,内心诅咒着一切,他诅咒父母的残酷,他诅咒嘲笑、讥讽、羞辱,也诅咒悲悯、同情、关注。很多时候,累得不行的他,头一偏,在自己的肩头睡去。
朱仲顺后来知道,妈妈和爸爸这样做,是因为妈妈看见了他被骑的惨象,“妈妈说这是奇辱”。
九岁那年,一切发生了改变:当他能够拄着木棍勉强站立行走之时,“飞了起来”的感觉占据了一切。在这样的高度,世界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景象。
“在你当时看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与朱仲顺面对面,我想问的问题不少,但一直都在回避一个关键词:痛。“痛吗?”这个问题被我生生地压在喉头以下,我知道这几乎算不上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可以以一个问题存在,那是因为生活有时真的太不讲道理,太“不仁”,把太多的苦痛压在了一个太弱小的生命之上。
朱仲顺是我采访过的数以千计的人当中“特别能说的一类”,面对我顾左右而言他的状态,他显得主动,笑容频次也高。
见面伊始,朱仲顺的笑容是从我想帮他坐上椅子的细微举动开始的,他用娴熟的动作和微笑缓释了我的尴尬。
“我可以和别人一起吃饭了。”朱仲顺说。他的解释是,一个爬着上厕所的人,谁愿意跟你一块吃饭呢?农村的旱厕,除了屎尿横流,还有厕蛆满地,无需“看别人的脸色,自己都想躲得远远的”。
也许是想起了那时的委屈、无助、无奈,朱仲顺有所停顿。
最终,朱仲顺还是没让话题中断。只是,如此之近,我看见讲述告别无以言表的被孤立、自我孤立以及怀疑人生的过程时,朱仲顺的笑容已经了无影踪,当说到母亲“伟大”时,眼圈从泛红到热泪盈眶。
怕自己反应过度,出现两个男人相同的情形,我匆忙把目光转向别处,最终也只能落在眼前的茶杯那里,接下来就犹豫在喝一口和不喝一口之间,身处两难。
“我妈妈是最伟大的。”朱仲顺善解人意地转移了一下视线,以轻松的口吻讲起并没有太多文化的母亲在自己能够拄拐行走后自嘲地说“我是反动派,你是江姐,你是被拷打得会走路的”。“我母亲最伟大。”朱仲顺说到这里时,有泪光的微笑中闪现出了童真。
拄着拐杖,朱仲顺完成了小学。同样,拄着拐杖,朱仲顺初中毕业。但就在此时,梦想中的“飞翔之翅”再次“折翼”:高中不招这样的残疾人,中专连考试的机会都不给这样的残疾人。
“所谓路就是无路可走!”他没有了读书机会,在那个年代对身有残疾的学生来说,几乎就意味着没有了未来。青春的骄傲、人格的尊严是一团烈焰,现实的冰凉冷漠、粗暴无理是一把利刃,两者时刻对峙,总是处于弱势的朱仲顺承认,自己曾经不止一次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观感:自杀。
他记得课本中鲁迅那句有关路的话,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初中生朱仲顺从理论上懂得其中深意,从情感上也懂得父母让他站起来走路的深情,他别无选择,只能往前走,尽管走得很茫然。
一年多的时间中,朱仲顺拄着双拐,几乎每天都从早上出发,到5公里以外的县城去寻找“出路”。早出晚归,他得到的答案不少,比较有“可行性”的方案集中在两个方面:有人提议他“云游四方”,博同情,“吃天下”,乞讨为生;有人建议他“学算命占卜找口饭”……这些,朱仲顺或碍于情面犹豫,或出于愤怒坚决,都给出了同样的回答:“不。”
朱仲顺知道当初给自己出主意的人,都是出于好心,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生命和尊严同等重要”。
朱仲顺用一个“不”字,体现了自尊,守护了尊严。“其实说到底”是不想让双亲失望,他俩曾因为看到自己能够“站起来拄拐走路”喜极而泣。
他记得九岁那年站起来以后,虽然说不好但心里已经知道什么才叫“一撇一捺”是个“人”,顶天立地做个人。
“我没有问人要过一分钱,”朱仲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到州府西昌硬是用四毛钱度过了三天两夜。“身残没有办法,心残就不行了。心残就无志,无志就没有尊严。咋个做人?”
仲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虽说是朱仲顺的“个人企业”,但员工从组建之初的20人发展到现在的150人,有一个数字总在代表朱仲顺的一贯的观点与立场,“一些人更需要有尊严地生活而不是简单的活着”,因此,公司的员工中有残疾人56人、下岗职工26人。
扶贫也好,济困也好,扶志最要紧,“‘志气的‘志,”朱仲顺说。
赵中明小不了朱仲顺几岁,是仲顺的老员工。请他坐坐朱董的椅子,他拒绝了。他是管生产的副厂长,“级别”有别的原因,还是尊重的因素?赵中明面对我的玩笑,选择了笑而不答。
接下来的问题,他就回答了。他说与朱董比“走路他差我,能干、头脑我差他,会东县难找!”
赵中明是二级残疾,他觉得自己不对的地方是一级残疾的朱董来开导自己。“懒心淡肠”是赵中明一度的真实写照,明知道工作难找,除去此家,再无分店,可他就是“没有心肠”好好干。“没有心肠”,换言之就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朱仲顺找到了他,就谈到了那个“志”字:“志,是一个男人要有一颗心,不服输的心。”两人交流一番的结果,有了解决的“方案”:“男子汉何患无妻。”
现在,赵中明是中层,“月收入4000好几,老婆也在这里,有工资。”赵中明说“有心肠”好好干了。
一旁的沈兴惠插话,说:“老赵,平时很会说的,今天怎么紧张了?”
老赵的回答是:“私底下可以,挨拢了就不行了。”零零碎碎的几句以后,表达出了“媳妇也是老朱撮合的”这个意思。当然,还有一件再踏实不过的事,“五险一金”全缴,五十五岁时,老赵就和仲顺的所有员工一样,坐着拿工资了。
赵兴惠心直口快,说自己是国企的下岗职工,“一下岗就到了仲顺,可以说,朱董对大家是一样的,但下来关心残疾员工还是要多一些。”她举了两个“最让我感动”的例子,给宁得贵生病期间全额工资奖金,帮助买轮椅;为一位姓赵的员工联系成都的医院,三天两头电话不断,垫钱付费,“比家属都还要急。”
赵兴惠的感动,其实也是佩服和敬重,对朱仲顺。
朱仲顺就坐在我的对面,话题又回到了他特别重视的“志”上。“帮助残疾人也好,健全人也好,扶贫为下,扶志为上。”
几年前,紧邻葡萄村的岔河村残疾人史万田,“不说话了。”朱仲顺去看望他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史万田的语言能力在退化,”原因是他足不出户,不跟人交流。朱仲顺给他买了轮椅,鼓励他走出家门,并给史万田的家人出主意,在公路边开了一个小卖部。
现在,史万田的日子虽谈不上宽裕,但有了保障,人也变得爱说爱笑。看到州、县残联的同志来看望自己,还很主动地提了一个要求,说有家企业在发污染补助,“别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他希望残联的领导能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周围熟悉史万田的人发出感慨,说史万田这几年又变好了。
钟灏现在是仲顺矿业的网络管理员,五年前的一次车祸让他失去了一条腿,当时他二十岁。他的家在宁南县城,是独子,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了。”进入仲顺以后,朱仲顺对他的要求格外不近人情:“不许懒着不动,要锻炼身体;不许一个人呆着,要多跟别人说话。”当时心情极度郁闷的钟灏极度反感,现在他明白了董事长的苦心,“他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一个‘烂好人,批评教训起人来,嘴巴很厉害,心却很好。”
一个人有了志,“才可能与人平等,也才能融入社会。”朱仲顺说。
给七十岁以上的村里老人发慰问金,朱仲顺的这一做法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但老朱坚持了七年。葡萄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几十上百号,而且逐年递增,这笔钱总数不小,但分到个人手里的却只有一两百元,怎么看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傻事。可是,老朱说这件傻事是一件明理事,做这件事讲的就是一个字:“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元素,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基础。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儿子关心老人,媳妇不关心老人;女儿关心老人,女婿不关心老人的现象还普遍”。仲顺做这件事,就是在尊奉传统美德,为村里的晚辈后生们做引领,做示范。
同样是身教,朱仲顺拖着残疾的双腿,执意到达了野租乡。
野租乡是会东县彝族聚居的高寒山区,在打工潮的裹挟下,这里的小学生大都成了留守儿童。朱仲顺给这里的孩子每人定制了一套崭新的校服后,觉得“真正的关爱是必须亲自送达”的。他给孩子们讲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老师讲自己永世难忘的成都知青老师,目的是“让孩子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成才的志向;让老师更加爱岗敬业,多付出一些心血,因为留守儿童更需要关爱。”
说着话的老朱突然问我一句:“你说,简单的捐三五万的东西,和我亲自去给老师、学生说几句心里话,哪一个更有含金量?”
在会东,朱仲顺是公认的一个平和低调的企业家,但他也有自己的“野心”。这个“野心”就是:实现职工收益翻番;在城区新建一个四星级酒店,以增加企业和员工收入,支持会东经济发展;为每位员工在县城建一套福利房,解决职工住房问题……
老朱的“野心”是有底气的:通过一系列评估,仲顺矿业的利润点正在向利用废弃资源与矿山废石转移,这将为企业带来更为长久的发展空间和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新近发现的伴生矿“松香玉”储量丰富,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当然,老朱的“野心”中始终包含着让残疾与非残疾的员工能够平等而有尊严地生活在一起的意图。
在旁人看来,朱仲顺达到了人生的某种高度,规上企业董事长,资产达到5000万的个企老板,成功人士,“里子面子”全都有。但他说,从前的生活中阴霾太多,那些“阳光”显得尤为珍贵。
他自己就是凉山州委、州政府奖掖的“民政先进工作者”,是凉山州残联第二届、第五届主席团委员。“残联是我家,大恩不言谢。”他说,人生中值得感恩的还有太多,“都应该铭记”。
1983年1月3日,县劳动局、二轻局举办的城镇青年缝纫培训班,团县委帮助他参加了培训。学习结束后,他借一百元钱买了一台旧缝纫机开始搞缝纫加工。这一做就是八年,他做事认真,价格公道,在赢得好声誉和好收益的同时还带出了三十多个小徒弟。
1988年,他带着妻儿到县城开了稍大一些的服装加工店,并开始探求更大的“空间”。
1992年1月,县残联成立了残联福利公司,他被招聘到公司任经理并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这些就是我残疾人生阴霾天空中的阳光。”
朱仲顺前半生笑容少了一点,后半生微笑就多了一些,好像印证的是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话,更像是证实奋斗者总是先苦后甜的理。不管怎么说,如今的他在同学、朋友的眼中是“年过半百,青春茂盛”。
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有著名的诗句:“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世人的解读中,大多认同这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极高境界,抱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亦不在少数。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朱仲顺的每一步,“无疑都在朝向这样的境界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