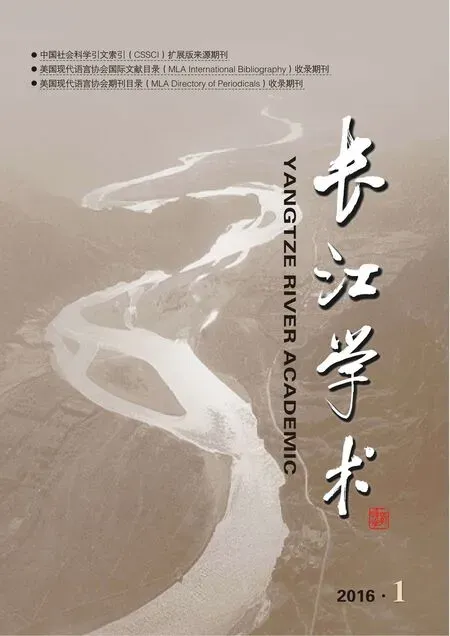侦探外衣里的诗心
——旅美华裔作家裘小龙访谈
〔美〕陈璇
(美国林登伍德大学人文学院)
侦探外衣里的诗心
——旅美华裔作家裘小龙访谈
〔美〕陈璇
(美国林登伍德大学人文学院)
在侦探小说中加入大量的中国古典以及西方现代派诗歌,是裘小龙写作的一大特色,现代诗歌翻译家与诗人的背景和身份使他的侦探小说别具一格。裘小龙不仅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陈查理(Charlie Chan)的东方形象,而且还让西方社会看到了一个更商业、更现代的中国。访谈内容主要围绕着裘小龙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展开,即便“这不是一个写诗的年代”,但是裘小龙却以独特的方式在他的侦探小说中继续着诗的探索。
诗歌意象派翻译侦探小说历史反思
裘小龙,男,1953年出生于上海。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因翻译T·S·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的诗作而出名。1988年,获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前往T·S·艾略特的故乡——美国圣路易斯市,研究现代主义诗歌,并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并定居圣路易斯,现专职从事文学创作。2000年,他以一部英文小说《红英之死》征服了西方读者,成为第一位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小说奖”的华人。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了9部“陈探长系列”侦探小说,这些小说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使裘小龙享誉世界。同时,他还出版了三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选集以及一部短篇小说集《红尘岁月》。
2015年12月,一个温暖的午后,笔者在美国圣路易斯市裘小龙先生的寓所,采访了裘小龙老师。
一、关于诗歌
问:前不久,您最新的侦探小说《上海救赎》(Shanghai Redemption)入选Wall Street Journal 2015年最好的十本书籍之一,可以说,这是您获得美国主流社会认可的又一次证明。但这并不是您的作品第一次获得殊荣,早在2000年,您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红英之死》就赢得了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小说奖,因此,许多评论家都称您是一位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华裔作家,请问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说法?
答:也不能一定就说是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吧,这得看从哪个角度来说。其实,以前WallStreet Journal也评过我的另外一本书,说是他们认为——不仅仅是那一年,是所有从古到今吧——最好的十本小说之一,但是这个WallStreetJournal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么权威。至于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这就看你怎么去定义了,我在旧金山的一个朋友,他也是用中文写作的,他有一次在国内的报道上也这么提过,但他的定义就比较简单,他说如果你进到美国书店,你能看到他的书,不是偶尔一次,而是几乎每次去都能看到,那么这个大概就算是美国人能接受。因为他觉得,主流社会也好,一般读者群也好,如果觉得你的书不值得一看,或者说书店都觉得这个书以后是卖不掉的,那么这就比较难说了。这是他的一个定义,算是一家之说吧。
问: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您不仅能够用第二语言英语进行文学创作,而且还得到了英语社会的普遍认可,并获得了极高的荣誉,这太不简单了!您是如何从一位中国诗人转变为一个在西方社会颇受关注的侦探小说家的呢?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大,那么,我们今天的采访能不能从您在国内的求学和创作生涯谈起?
答:我最早是在77年考入华东师大的,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第一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当然后来被取消了,就是说就算你没有念完本科你也可以去考研究生。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因为当时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77年底第一次恢复研究生考试,那时没有这么多符合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去考研究生,所以就破格,只要能考得过,你就可以去读。我是大学念了半年之后去考的,因为那时候想得也很简单,反正考不上也不算什么事,我可以继续念我的本科,所以我就去试,然后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78年就去读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当时我考的是外国文学专业,我的导师是卞之琳。那时的情况是这样,首先你必须过了初试跟复试,然后定专业的时候导师选学生。导师选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个人可不可以搞诗歌,当时卞之琳老先生要我写诗,他说如果你要跟我搞诗歌研究呢,你自己得会写诗,所以我就给他写了几首诗,他看了以后还挺满意的。
问:在这之前您创作过诗歌吗?
答:没有。当时写完以后,卞之琳先生跟其他几位老师讲,说可以,他要我,说我的诗写得不错。其它几位老师就跟我说,老卞都讲了你这首诗可以拿去发表了,我后来就真的拿去发表了,从这以后我就开始了写诗。我后来还听我的另一位老师讲,当年徐志摩对卞之琳也是一样,徐志摩比他更极端一点,他都没有经过卞之琳的同意,就把卞之琳的诗拿去发表了。所以这批老先生,现在想起来,确实对年轻人的帮助和提携很大,就是他不是很在乎条条框框的东西,他就是只要我喜欢,就这么做了。
问:您曾说过,当年卞之琳先生都是在家给您授课,颇有古风“弟子”的意味。作为卞之琳先生的关门弟子,您能不能谈一谈当时在他家上课时的情形,以及他对于您在诗歌创作和翻译上的影响?
答:当时我们社科院是没有自己的研究生院的——有研究生院这个名,但是没有这个地儿,我们是借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地方上课,所以老师上课确实很不方便,连教室都没有,要上课还得跟北师大打招呼。卞先生带我的时候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他也不喜欢到北师大来借个教室给我一个人上课,他觉得挺没劲的,因此他就说,那你每个星期到我家来上课吧,他那时住在北京东城区的干面胡同,我每个星期就去那儿上课。其实想起来,他对我的创作影响确实挺大的,因为他老先生上课可能跟现在学校里上课不一样,他很随便,去了以后大家就坐下来,没有任何提纲地乱聊,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又因为他是诗人,他有时就比较喜欢讲自己怎么写诗歌,以及跟谁跟谁交往,谁的诗写得怎么样,谁的诗写得不行,就讲这些东西,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反正大家都是很随便地聊,没有像后来那种很正儿八经地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关系其实更多地就像是种弟子到家的感觉,就是你去了当然也有上课的成份,而更多的是有一种师生情谊在里面。但是有时候他也会问我,你最近写了什么诗啊,拿出来看看,然后就给我分析诗歌。我想这对我以后写诗的影响很大,其实包括我写小说也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因为他48年在英国的时候就在写小说。当年他那部小说基本上是快写完了,但是50年代初回国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小说太资产阶级情调了,就把它烧了。然后到他带我的时候,他自己也后悔了,他说这个东西要是不烧就好了。所以后来他鼓励我说,以后你也可以写小说啊,不一定只写诗歌。想起来可能那个时候就觉得他那个英文小说是很神圣的,因为始终没有看到过嘛,不知道他写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在我心里种埋下了一颗写小说的种子吧。
问:我看到您除了发表诗歌作品以外,1984年您还发表了一篇中文小说《同一条河流》,那应该算是您的第一篇小说创作吧?
答:对,我大概就写过这么一篇中文小说。那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那个之前和那个之后都没再写过,可能当时正好上海文学的编辑部有几个朋友,大家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说起有这么个故事,大家说能写成小说我也就这么写出来了。但是正儿八经地搞小说创作,是我到美国之后的事情。
问:您当时还在国内的时候,作为诗人和诗歌翻译家在文坛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了,中国的八十年代,诗歌氛围很浓,您所经历的文坛及诗坛情形是怎样的呢?
答:当时八十年代的诗歌特别火,这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真是特别火。那个时候北京的《诗刊》每个月的印数是10万本,当时所有的报亭里面都能看到《诗刊》,文学青年也是很时髦的一个事情。我是88年底到美国来的,那时上海电视台还经常找一些诗人去做节目,说明诗歌还是蛮受重视的。诗歌流派也很多,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朦胧诗人是一批,他们的诗是属于半官方性质的,(官方没有怎么去打压它,但它又确实不是官方讲得太多的。)另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第三代、第四代诗人,我跟他们都有一些交往,但是其实哪一派我都算不进去,如果硬要分派的话,我可能应该是属于学院派的,但是当时中国是没有学院派这个讲法的。很奇怪,当时中国搞创作的基本上都不是一本正经在大学里念书的。我跟他们交往不是太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当时有很多的时间是在翻译诗歌,后来我到社科院工作,我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写评论,主要是写外国文学评论。虽然我和这些诗人经常有来往,但是并没有特别去说大家要是一个流派啊,一个风格啊什么的。而且那个时候,不仅仅是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其实也很火,当时像艾略特的诗集,都是好几版好几版地印,一拿出去就销完了。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真是跟现在不一样,就是年轻的作家不管是诗人也好小说家也好,都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重任,觉得要改变这个社会。想起来蛮有意思的,一方面你特别容易碰到麻烦,就是说如果你这篇东西被上面点名了,你就是bigtrouble,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挺高兴的,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有影响,上面都点你名了,那个时候确实有一种匹夫有责的感觉,就是真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能改变社会,至少在某一方面能改变一点,我想这种感觉现在大概都没有了。
问:您觉得这种能改变社会的感觉,是青春的激情使然,还是当时整个的社会环境确实赋予了诗歌这种能力?
答:我想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但是后者的因素可能更大一点。因为第一,当时确实是受众大,你在《诗刊》发一首诗,至少有十万个读者,你就会觉得,我这个确实能影响到很多人。当时有些诗从诗性的角度来讲,它的艺术造诣并不怎么样,但是它确实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有一首诗的题目是《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作者是叶文福,现在想一想,这可能也就是像口号一样的政治宣传,但那个时候,我想看的人肯定都不止十万个,它确实能让大家认识到官僚的特权以及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大家争相传阅,看的人都是热血沸腾的。第二,当时经常有些什么笔会啊作协会议啊等等,国家都挺重视的,当时开作协会议和作家代表大会,规定总书记是要出席和讲话的,而且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我曾去开过一次,那种感觉真好,就是会给你一种你真的是在参与国家的建设的感觉。在那种情况下,就算你不那么青春,热血也是会沸腾起来的。
问:您在当时还参加过哪些诗歌活动呢?除了诗歌翻译之外,还参加了诗歌研讨啊朗诵啊这些活动吗?
答:那个时候诗歌朗诵还不怎么普及。诗歌活动方面,我参加了1986年的第二届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我的印象是当时几个朦胧派、后朦胧派诗人都来了,他们是作为正式代表受邀请来的,还有一些人是不能官方邀请的,他们也来了。当时中国文坛还是蛮复杂的,很敏感,但是那次会议我的印象蛮好,大家都是会上讲,会下也讲,讲得很多也很热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次正好碰到胡耀邦那个事件,北京有学生上街游行,所以搞得气氛也蛮紧张的。)另外,因为我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大概也是86年吧,有一个中美作家会议,它当时是每两年一次,一次在中国开,一次在美国开,中国方面会派一个十来个人的代表团,美方也组织一个代表团,大家就一些文学问题进行会谈。那个时候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big deal,因为那时出国确实也不容易,而且你还是经过多次筛选出来代表国家出去的,所以确实是big deal,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当时这个中美作家会议搞得真是挺隆重的,中国也特别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可以跟美国的作家在文学上直接交流。
问:80年代后期出现了各种诗歌民刊,然后以民刊为中心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诗歌流派,您当时有没有参与哪一种诗歌流派?似乎在当时那种青春激情的裹挟下,很难不加入任何一派吧?
答:我跟他们都有些接触,但是也算不上加入哪一派。当时那些诗人真的是很青春,他们会在之前没跟你打过任何招呼就过来敲你的门,说我是谁谁谁的朋友,他们说你的诗写得好,我今天就来看你,然后你就陪他聊天,有时候来的人还会说,我今天晚上旅馆还没有找到,那行啊,那你就住在我这儿吧。上海当时有一个大世界,后来改成青年宫,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落了,但是建筑还在,就是西藏路那个口子上,它以前是一个entertainmentcenter,很popular。那时候里面有一个搞宣传的,跟我同样的年纪,同名,叫王小龙。他那儿是当时上海的大本营之一,而且因为我跟他的私交也蛮好的,我家离大世界又特别近,所以他们那儿经常有人来,我也过去和他们一起聊。再加上王小龙还是正儿八经搞宣传工作的,所以他那儿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天南海北来的人很多。大概两年以前,我还在洛杉矶时报给他写过一篇诗评,他们当时正好需要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中国这些搞诗歌的人现在都已经被大家遗忘了。他现在在国内拍纪录片,也搞得很好,但是遗憾的是诗歌这个东西再没有时间去搞了,很多其他的诗人也都是差不多的境地。但那个时候,确实是只要有朋友来了,没地方住,那就在大世界住下来,当时他还在那儿开班讲诗歌,搞得蛮热火的。在当时的诗人中,我跟王小龙算是走得很近的,他当时是写城市诗,写citylife的。我比较喜欢他的风格,他基本上以口语入诗,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中表述深厚的意蕴,但更为难得的是,他能够把诗的节奏感处理好。我觉得中国现代诗有一个问题其实始终没有解决好,就是它的节奏或者说音乐性的问题,因为古典诗是讲究平仄的,它的韵律都是现成的,只要你懂它这一套就行了。但是,现代诗,比如说徐志摩的一些诗,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念、还能记得起来,不一定是因为它蕴含了什么大的思想,他的诗像《再别康桥》啊《沙杨娜拉》啊,这些诗都有现代汉语的节奏,或者音乐感。王小龙的诗呢,跟他们不一样,但他也是在往现代汉语诗的节奏上下功夫,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可惜后来整个大坏境就不让他继续往下走了。我的老师卞之琳,他也曾专门就现代诗的节奏写过一些文章,他就认为,现代诗不可能像所谓豆腐干诗一样,每一行都几个字,他认为现代诗需要一种自然的节奏,他将这种自然的节奏叫做“顿”。就像英文中有iambicfeet,每一行诗有5个feet,或者6个feet,那么中文呢,因为你不可能以单词作为foot的单位,你只能将一个词组或者意义组作为一个“顿”,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三个音节,尽管七个字,那么一行诗里面,譬如说,第一行是五个顿,那么第二行最好也是五个顿,当然,你可以有一些变化,但是不应该第一行来十个顿,第二行来三个顿。但是卞先生的这套,也主要是在理论上提倡,他到后来也没有坚持下去,因为后来写诗的好像都顾不上这个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体,都不应该忽视现代中文诗歌中音乐感、节奏感的问题。当然也有不少人在这个方面做了尝试,但是现在大多数诗人对这个问题都是顾不上的了。
问:现代的这些诗歌中您觉得比较有印象或者节奏上做的比较成功的,您能举出几个例子吗?
答:王小龙有几首诗我觉得很不错,比如说他有一首诗叫《纪念》,是写给他的父亲的,我觉得在节奏上他做得相当不错。然后他还有一首《出租汽车总在绝望的时候到来》,也很好。我觉得他的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幽默,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中国诗大都是抒情,有时候甚至是滥情,而他就能一方面好像在抒情,一方面好像自己在挖苦自己,这一点也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但在中国诗中就比较少见,就是它一方面抒情,但同时它又头脑保持得比较清醒,就是说,这个东西,说到底它也就那么回事,不值得要死要活的,有一种客观的距离和反讽的态度在里面。
问:您当时从事诗歌翻译多还是创作多?在您的朋友圈里面,您主要是以一个翻译家的形象出现还是以一个诗人的形象出现?
答:可能在写诗的圈子里面他们更多地觉得我是搞翻译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哪儿都不沾边,这样也蛮好的。对于他们搞理论的来讲呢,他们觉得你是写作的。我的记忆里面,当时作家协会下面是分组的,有诗歌组,有翻译组,我至少是两个组,我记得当时翻译组我还是小头头,诗歌组我也是成员,等于说我是跨界的。我觉得这样也有好处,因为当时除了政治之外,有时候大家竞争得也很厉害的,特别是写诗歌的都有一种我要当老大的气势,而我呢,因为被搞诗歌的认为是搞翻译的,所以可以远离这些竞争。当时谁要做头呢,还确实是蛮神气的事情。北岛可以算是当时诗歌的头头之一,我跟北岛基本上是同一代人,北岛他作为头,其实也是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最早的时候,他们的作品被几个汉学家拿到了,翻译到了国外,然后因为他们政治上有些地方,按照当时的标准看起来是比较敏感的。因此这就把他的名声给炒起来了,因为当时上面越是点你名,你就越红。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国外有些汉学家把你作品翻译出几首了,或者上面点了一下,像北岛的诗歌当时有一阵子是能发表,但是一年譬如说只能发表两首,它内部是有一些规定的,这种消息一经传出以后,他就很红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几个朦胧诗人,像北岛、杨炼、舒婷,都是当时确实比较红。还有一些年纪其实跟他们差不多,比如说王家新、李小雨等人,他们当时都是在《诗刊》这样比较官方一点的刊物上发表诗歌,就是说他们的东西主流刊物登得比较多一点,可能就没有那么红。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确实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其实也蛮好的,反正我哪儿都不太沾边。
问:您当时翻译的主要是美国意象派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而且您好像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有兴趣,因为您不仅在美国出版了三部英文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同时在您的侦探小说中,您也引用和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回到八十年代,您当时创作的诗歌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诗歌呢?
答:创作诗歌我肯定受到了意象派的影响,这是无疑的,同时我也受到艾略特的影响,我很欣赏他的那些现代主义诗歌,当然我的老师卞之琳对我的影响,肯定也有。我用中文写作的时候,受这三个方面的影响比较多。后来我改用英文写作之后,我更倾向于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去汲取素材。确实如你刚才所讲的,我的小说里面有不少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这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我觉得如果要把中国现代诗歌的成就跟古典诗歌来比的话,那确实是有一段距离的。不管是音乐感的效果也好,或者意境来说也好,还是从整个用字的技巧来说,古典诗歌都是一个高峰。而我在小说里面引用古典诗歌呢,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古典诗歌,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些是意外的因素,因为我本来是特别喜欢艾略特的,我很想在小说里面引用他的诗歌,但是我的出版商不干,他们说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版权,你要引用它的话,如果它的版权没到期,就会很麻烦,哪怕你只引用几行,都得付不少钱,否则人家是可以告你的,所以他告诉我别引。
问:所以您小说中的现代诗歌都是您自己创作的吗?
答:我有不少是自己创作的,还有不少就是把中国古典诗歌拿过来翻译成英文现代诗。在小说中加入诗歌其实最开始是一个尝试,当初我跟出版商是这么讲的,我说中国古典小说里面是有诗歌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面加入诗歌,这个也算是一个发扬传统吧,这是一。第二呢,我蛮喜欢人家讲的那种lyricalintensity,就是所谓抒情的强度,因为写小说你不可能一直就停留在同样的强度,有些时候你是叙事比较多一点,有些时候你的抒情成分可能要多一点,这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个,有些地方要blankverse,有的地方你是prose就行了,本身在narration上的intensity是应该有所区别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你放几首诗进去也有比较好的效果。最初的时候,出版社他们也不大相信,他们觉得你是写侦探小说,好像跟诗歌关系不大,但是我比较坚持,所以他们就跟我说,那咱们先试试看再说吧。结果书印了以后,读者的好评还蛮多的,书也得奖了,也有不少读者写信到出版商那儿去,说他们喜欢里面的诗歌,甚至有另外的一些出版商,说他们要帮我出版诗歌,他们说出版诗歌他们并不能付给我多少钱,但他说他至少可以帮我印,不用我出钱。所以第一本小说出来以后,我就好像是骑虎难下了,因为出版商觉得每个人写的东西都得有自己的特色,他觉得在侦探小说中加入诗歌成为我的特色了,那我就得保持下来。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最早在华盛顿大学教书的时候自己也教过一些诗歌,也翻译过一些,所以当然也有比较懒的成分在里面,现成的东西我在小说里面用一下,所以就是这好几个因素都凑起来了,侦探小说里面的诗歌就一直保持了下来。
二、关于小说
问:侦探小说在西方是一种特别成熟的小说类型,具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在写作上也有一定的模式,您的小说对西方的侦探小说进行了中国式的发挥与改造,是您对西学的了解促使您做出了这种最能够赢得美国主流市场认同的选择吗?或者说,您在最初考虑写英文小说时,是否做过这种理性的思考呢?
答:并没有,其实我本身是很喜欢侦探小说的,我以前也经常看。可能这两天St.LouisPost-Dispatch会发表一篇文章,不是我写的,但是会写到我跟住在圣路易斯的一个美国桂冠诗人Mona Van Duyn之间的一些交往,她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但是她已经去世了,以前我每次去她家,她家里都放着侦探小说。很奇怪,有不少诗人,都喜欢侦探小说,可能觉得写诗蛮累的,就看看侦探小说换换脑筋。
问:或者是不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性呢?在您的侦探小说《红旗袍》的破案过程中,您多次提到“意象”这个词,给我的感觉就是,是不是您写侦探小说的过程与您写诗或者解读一首诗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答: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艾略特也蛮喜欢侦探小说的,他的诗中那种意象之间的跳跃,就像你讲的,可能就像各种线索,有了这些线索你才能弄明白一首诗。美国有一个批评家,叫艾伦·维利(Alan R.Velie),他在谈《红旗袍》的时候也谈到过跟你接近的观点,他就认为陈探长是将解析艾略特时磨练的分析技能运用到对谋杀案的侦破中,说我实际上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西方批评方式在写这本书。但是,回到我怎么会去选侦探小说这个问题上来,因为我96年还是97年的时候第一次回国,你知道中国你六、七年不回去变化就特别大,当时我看到上海的变化就觉得蛮惊讶的,所以我就想,我可以写点东西来记录一下这种变化,我当时确实写了一首诗,一首英文长诗,后来也发表了,但是我自己并不满意。我觉得如果你要写社会的变化,诗不一定是特别好的媒介,因为诗歌主要反映的是你自己的心灵,而当时感受到的那种震惊,那整个的震撼的感觉,哎呀,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诗歌是写不出来的,因此那时就想写小说了。写小说呢,我最早并没有想过要写侦探小说,但是构思中的主人公跟现在的主人公有点接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就是希望借这个主人公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社会会有这些变化,整个的前因后果都好好地想一想。但是,我碰到了一个结构问题,因为我没写过长篇小说,因此结构就特别难掌握,但是侦探小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几个比较固定的模式和元素的,一般你首先总得制造悬念,然后你总得去破案,最后你总得有个结论,所以我就想那干脆把我要写的东西放到这么一个现成的模式里面去,这也是偷懒的一个办法,结果没想到出版商看了以后很喜欢,然后跟我说,你还得往下写,于是我就这么继续写下来了。但是,事后想起来,我确实也受到了西方一些侦探小说的影响,因为现在西方侦探小说当中有一个流派,就是所谓的社会学流派,sociological,他们的重点不是说谁杀了谁,而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文化背景当中,这样的案子会发生。那么,这个就跟我的初衷其实蛮接近的,因为我本来就想写这个社会的变化,人物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在无意当中我也就进了它的这个路子了。写这个路子最有名的是两个瑞典作家,叫麦·荷瓦儿(Maj Sjowall)和派·法勒(Per Wahloo),我受他们的影响蛮大的,其实很滑稽,他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初衷是要写资本主义的黑暗,结果写着写着就成了出名的侦探小说家了,所谓sociological approach就是他们开的头。
问:您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一定的中国背景里,在特定的时期,中国出现的很多词汇可能就简单的几个字,但它的背后却蕴含了很多的心理暗示的内容,外国读者对于这些就很难完全理解,您在您的英文小说中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呢?
答:你这个观点很对。有一次我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学会议,国内有一个作家叫韩少功,他写了一本书叫《马桥词典》,被翻译成英文了。当初这本书要找commentator,我谈的就跟你的观点很接近,我说这个东西很难,因为在一个语言里面,譬如说“知识青年”这个词,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就自动地加载了好多积淀的成分在里面,就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当时是没办法的,是不想去也得去,后来就逼着你到农村去什么的,一提到这个词,所有的联想就全上来了。可是这个东西,你用英文来写,它就是educatedyouth,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根本就没有那种联想意义的,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就跟中国读者读到的完全就是两回事情了。“文化大革命”也是,我这一代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是很心酸的一段经历,而一般的西方读者,他们看到culturalrevolution,他就会认为革命还是好事情的嘛。所以这个东西要解释清楚确实很难,因为如果你是写academicpaper,没关系,你可以在下面加“注”,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而你写小说是不能这么做的。处理这个到现在为止对我来讲都是蛮困难的一个事情,我争取尽量地通过背景描写,通过对话,或者有时通过设计一些小的场景,使这些东西让英语的读者以及其他语的读者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但是我不能去加注,一加注这个小说就读不下去了,这样一来reading flow就给打断了。
问:您以前从事的是诗歌翻译和创作,是相对严肃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现在您创作的是侦探小说,如果大家把它定义为通俗文学,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
答:我自己倒觉得这个没什么,我觉得,第一呢,如果我写一本很modernist的、很现代主义的或者很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只有两三百个读者的话,那我宁可写我这个。因为我觉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它跟读者的接触当中,作品写出来没人看,那也就是没有生命了。但我也试着在侦探小说的模式里面尽量地加入一点其他的文化的、知学的,以及其他比较严肃的东西。比如说明年五月份将出版的第十本侦探小说《BecomingInspectorChen》,我在形式上就把它打乱了,每个章节都是一个相对独立故事,这些故事都跟主人公陈超这个人有点关系,都跟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么一个inspector有联系。这可能也是所谓后现代派的观点,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人的身份是一种赋予,但是我觉得,其实人的身份是在跟其他人的交往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它从来不可能说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建构过程有时候连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些事情看起来跟陈超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过了多少年以后就影响到他会去做现在这个决定了。以前传统的小说人物多是平面人物,这个人就是这么回事情,或者说这个人是因为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变成了怎么样,但是有时候很多人和事你是很难用一句话来讲清楚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你是做了什么样选择所以你得接受怎么样的后果,但问题是,好多选择都是人家在给你做,并不是你自己做的,所以你才变成现在这样的人了。就像很多时候选择是被推到陈探长面前的,比如说80年代国家为大学生安排工作,所以本来是热爱文学的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名警察;很多选择也可以被与自己有关或者无关的人轻易决定,而自己可能完全不知情。在《Becoming Inspector Chen》中,我就想通过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反思陈探长在中国这么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是如何成长为现在的陈探长的。
问:对于您的侦探小说系列的评价,西方社会很多赞誉,但是在国内也有一些消极评价。可能因为您写到文革以及文革对现代人心理造成的一些影响,再加上您身处西方社会,这些消极评价估计难以避免。东方主义是您很熟悉的西方理论之一,那么,您在小说创作中有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个问题?
答: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从写第一本书开始我就有意识的尽量不要去搞东方主义那一套。在一本小说里面,我还故意借主人公的口对美国来的一个警察专门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好像都觉得中国人是留着辫子的,只会martial arts,只知道kungpao chicken,其实你们这个观点不对,他就拿自己举例讲,说他也蛮喜欢你们美国的艾略特的诗歌,他也喜欢英语,所以不要老是把东方主义这套东西拿去套。其实,我应该说是从第一本书开始,就有意识地避免去写一些像有些电影里面那种比较落后的、或者原始色彩特别浓的东西,应该说我写的都是相当现代的,而且都是写发生在大都市里面的故事,我觉得东方主义是应该避免的。至于“文革”,我觉得,第一,我没有一本书是直接写文革题材的,我确实写文革对这个主人公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经常会在书里面写它对人物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我觉得,现在国内对文革的处理有的时候有点像掩耳盗铃,这不仅仅是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浩劫,而且从整个globalage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本身都是很值得反思的,人性的黑暗,我们必须要正视。像文革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是写的太少了,而不是太多。因此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的一部分,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就一定要写出来,如果说国内的批评家要怎么想,那我就管不了这么多了。有一些官方的批评,比如说我写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因为要去讨好西方读者,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新批评里面有一个观点,叫做intentional fallacy,就是说去猜测一个作家的意图是很荒谬的事情。因为说实话,有时候作家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你凭什么去说我写这个就是为了要去讨好西方读者呢,这个我觉得是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譬如说,你举出例子来,我是哪儿讨好了西方,或者说我写的这个不是真实的东西,这个可以大家拿来讨论,说我这个是夸张得过头啦,或者这个完全是编造的,但往往事实比小说中写的还要严重多了。所以像他们这种说法,基本上我也不会去理会,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问:现在国内把像您这样在海外进行文学创作的华人作家称为离散作家,您如果同意这种称呼的话,您觉得您更属于哪边,您觉得在哪边让您更有一种安定的感觉?
答:我觉得其实随便用什么称呼都行,这个无所谓,这只是一个标签。但是我自己呢,有好多西方的读者问过我,说为什么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怎么去写西方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完全有能力写西方的小说的,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也跟他们讨论过,我说,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因素,我觉得我在写中国的东西的时候我有自信,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能写得怎么好,但是至少我写中国的东西我还是有把握的,但是要我写西方的东西,譬如说写美国人或者写法国人,我就不那么自信。
问:在您的侦探小说大获成功之后,您创作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红尘岁月》,我很喜欢这本书。如果说侦探小说使您获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在您赢得一定的声誉之后,您是否会多创作诗歌以及像《红尘岁月》这种更具文学性却在市场上不占优势的作品?
答:确实是这样,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现在,比如说出些诗选或者翻译诗选,以及包括出版像《红尘岁月》这样的文学作品,这个从经济收益上来讲,它们肯定不如侦探小说,但是我现在基本上能做到不一定在意这个事情,只要我自己觉得有意思,我就可以出版。
问:您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三部中国古典诗歌选集,在编选的过程中,您比较倾向于选择哪一些古代诗人的作品呢?
答:这里有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以前,有一个翻译中国诗歌的美国学者,叫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他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说翻译诗歌还得考虑你翻译过来以后这个翻译过来的诗还有没有那个form,或者说读上去还是不是一首诗,如果你翻译过来以后读上去不是诗了,那他就不用这首诗了。我是很赞同他的这个观点,但是具体来讲呢,因为我以前喜欢意象派诗歌,我觉得有些诗它在中文里面很好,比如说像杜甫的一些诗,议论性较强,从中文文字来讲很好,但翻成英文以后,很难将原诗的文字韵味转达出来。这倒不一定是说翻译者的功力不够,当然,翻译的人的功力不到,确实也是个问题。一些议论性的诗歌,它有好多典故,这些你在英文当中是翻不出来的。但是有些诗歌呢,比如说像李商隐的诗歌,他用意象、用象征用得比较多,这种诗你翻译的时候比较取巧,翻成英文以后,它还是一首诗,所以我选的时候,我就选翻译过来还能是诗的。当然有时候翻译过来不是,我扔掉的也有的不少。就是说,你必须翻出来以后读起来还有诗的味道。那么,有些像通过意境、意象、象征来表现的诗,我就选得比较多,而那些议论得比较多的诗,在中文里很漂亮,在英文里却是没办法传达的,我就选得比较少。有些杜甫的诗,他的议论是很好的,像“两朝开济老臣心”,你翻成英文是什么意思呢,两个朝代,一个老official,他很loyalty,西方读者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就是没办法翻译出来的东西。而意象呢,在这个语言里面它是一个意象,你翻译过来以后,它还是一个意象,当然可能它的内涵会有一点不一样,但这个还是能搬的。
问:您现在主要从事哪一些工作呢?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还在继续吗?
答:有。有一本诗集也是将在法国和意大利先出版,叫《陈探长诗选》。
问:《陈探长诗选》?它选的都是您在小说中用到的诗歌吗?
答:不一定,光用小说里面的肯定不行,因为读者会觉得是受骗了,都看过了,你得有些新的,就是小说里面还没有的,或者小说里面只用了一部分的。其实这也是一个trick,因为你说是我的诗选,人家不会去买,而说是陈探长诗选,人家就去买了。出版社就是靠陈探长的fans来保本,至少不赔钱。但是,这个诗选在英国和美国,到现在为止还在研究当中,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还是不能赚钱。文学评论方面呢,前两年我去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碰到那儿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教授,他是教creative writing的,他现在有一种写批评的方法叫Fictocriticism,虚构批评,我蛮喜欢的。他所谓的虚构批评,就是把批评文章写得不像学院派,有的时候像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段经历,但它又不是写一个短篇小说,它往往就是讲一段自己的小的经历,将这段经历跟他要讲的文学的东西联系起来。我看过他几本这方面的书,我自己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前阵子也写了几篇这种所谓的虚构批评的文章,因为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小说写得多了,也不想再去写那些人家看上去就只是学院里面的东西,而更倾向于写一般的读者也可以读的东西,但是呢,这也不会妨碍你在这个里面去讲你所谓现代的、后现代的东西。
问:您觉得您现在还在维持着一个学者的身份吗?还是更多的是一个小说家的身份?
答: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我觉得写小说,那些批评的理论肯定还是要去看的。如果说我写的东西跟其他侦探小说作家写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就跟我的文学理论的背景有关系,我比较喜欢那些理论的东西,这些理论你不一定要在小说里面直接去展现,但它肯定还是会影响你的创作,而且这个影响会给你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
A Poet Under a Detective’s Cloak: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American Writer Qiu Xiaolong
〔US〕Chen Xuan
(School of Humanities,Lindenwood University)
Infusing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classical and western modernist poetry into his detective fic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features of Qiu Xiaolong.Qiu’s background and identity as a translator and a poet make his detective fictions distinctive from others.Qiu not only creates a new Chinese character which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Charlie Chan,but also introduces a more commercialized and modernized China to the western society.This interview mainly focuseson Qiu’s poems and detective fictions.For him,even though“this is not an era for poetry”,Qiu has been continuing to explore poetry creatively in his detective fictions.
Poetry;Imagism;Translation;Detective Fiction;Historical Reflections
责任编辑:方长安
陈璇(1983—),女,湖北武汉人,美国林登伍德大学中国研究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