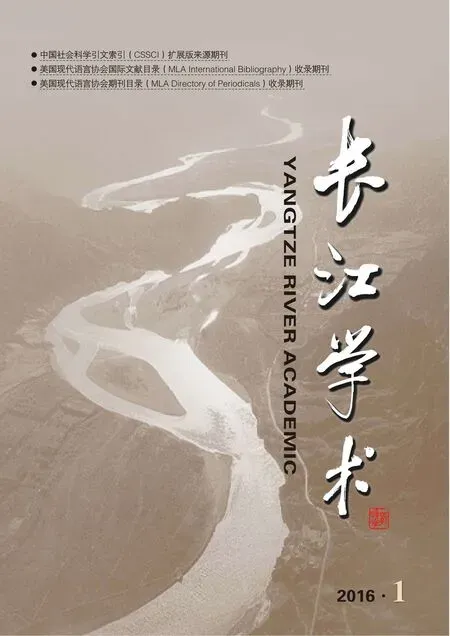莎士比亚:神秘的当代人
〔英〕约翰·吉利斯著张东燕译朱宾忠审译
莎士比亚:神秘的当代人
〔英〕约翰·吉利斯著张东燕译朱宾忠审译
如何理解扬·阔特在其著作《莎士比亚与我们同代》中所说的莎士比亚“与我们同代”这一观念?本文试图说明这一结论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体现着某种矛盾关系。人们对当代性事物的理解通常是该事物为世人“熟知”,但是阔特从现代主义戏剧学的角度重新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将莎剧的当代性理解为某种疏离的力量,它异化莎剧中为人共识的内容,释放其中具有爆炸性的潜在内涵。本文将通过讨论近十年以来上演的两出令人震撼的莎剧表演,反思阔特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出两者均以神秘的方式展现了莎剧的当代性特征,同时均体现了不为当代观众所了解的现代社会早期的文化思想。上述两方面彼此紧密联系:正是莎剧文本中无法被当代社会同化的部分造就了导演新锐和富有疏离感的现代主义演绎。
当代性疏离性现代主义
如何理解扬·阔特(Jan Kott)所说的“莎士比亚与我们同代”?乍一看,这一论断不言自明,阔特却不作如是观。在《莎士比亚与我们同代》(1960)①Jan Kott,Shakes,peare Our Contempotary(London:Methuen,1964).《国王》一章里,阔特告诉我们,之所以“莎士比亚与我们同代”,概因他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之间有太多恒久不变的共通之处:尤其是两者均视历史为“宏大的机械”(《理查三世》)或“梦魇”(《麦克白》);都对国家监视倍感压力(《哈姆雷特》);对人生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由此看来,莎士比亚之所以与我们同代,乃因时代从未发生过根本变化:言下之意即所谓历史运动不过是个无限循环,而历史在不断重复着自己造就的梦魇。正如1985年,在纪念《莎士比亚与我们同代》出版二十五周年研讨会的开场白里,约翰·艾尔索姆(John Elsom)所说的:
阔特好似一位老派的悲观主义者。莎士比亚与我们同代这一论断背后隐藏的理由是人性恒常,不会发展前进,这实在是绝望悲哀的想法。②John Elsom,“Is Shakespeare Still Our Contemporary?”(1985,6).
但问题没那么简单。阔特的论断暗含某种完全与众不同,富有现代主义色彩的逻辑。对此,阔特在1960年撰写的《李尔王》与《哈姆雷特》这两章里,有所暗示。在1985年召开的研讨会上,阔特则著文明确阐述了这一逻辑。他指出,莎剧舞台呈现的最佳形式是大胆前卫的先锋剧形式,惟其能转化原剧怪异之特色,使之完全符合当下的审美需求。阔特自问:“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代性’一词呢?”
它当是两个时代之间的某种联系,一个时代在舞台之上,另一个则在舞台之外。一个时代属于演员,另一个则属于观众。③John Elsom,“Is Shakespeare Still Our Contemporary?”(1985,6).
阔特乐于用矛盾体的意象描述这一历程。莎剧的深刻和怪异使之如镜子般照射出当代社会,当代人从莎剧的“另类”和“与众不同”里认清自己身处的时代:离奇夸张,骨子里与表面的“玻璃特质”背道而驰(这一十分恰当,自相矛盾的意象出自《比报还一报》2.4.123,意指某种物体,它既是实体,又是映照实体的表体)①Stanley Wells,Gray Taylor ed.The Cxford Shakespeare:Complete Works(London:Clarendon Press,1998).。
如果“矛盾的”是形容该历程的一个词语,“辩证的”则是另一个。莎剧能对当今世界作出反应,就像位交际家,谈论的是对方——现代导演、演员、观众亦或读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阔特进一步指出,莎剧文本体现了“双重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构架下,莎士比亚影响着诠释者,而诠释者也影响了莎士比亚。因此,当今对莎士比亚文本的诠解受到了诸多人物的影响:十八世纪的霍尔德与歌德,十九世纪的维克多·雨果,以及二十世纪中叶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各自的历史阶段,他们视莎士比亚为同代,而他们自己也成为莎士比亚的同代。“同代性”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建立在历史上各种同代性基础之上②Stanley Wells,Gray Taylor ed.The Cxford Shakespeare:Complete Works(London:Clarendon Press,1998).。
既然此时未曾遗忘彼时,那么现在就与历史相连。反映当下时代的本领使莎士比亚戏剧成为一个历史视阈,一个莎士比亚与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家和痛苦不安的哲学家之间不断神遇的历史。人人都在莎士比亚身上看见自己。参照不同年代译本而创作的日本莎剧表演,就原原本本地展现了这一观点。
德里达与阔特所说的历史是带启蒙主义色彩的历史。具体说来,通过阅读莎士比亚,他们重新想象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在文本这面镜子里,时代照见了自己;在文本的竞技台上,时代演绎着自己的创世纪。对阔特来说,莎士比亚在某些时代更具当代性,也就是说在某些时代里,文本中的时间与当下时间这对辩证体双方的化学反应来得更为剧烈。此话怎讲?我们何以断定身处在一个莎士比亚更具当代性的时代?或者相反,在我们的时代里,莎士比亚不太具当代性?阔特并未就此详谈。不过,我斗胆揣测,是在危机时刻,莎士比亚更像与时人同代。所以,在柏林墙倒掉的年代,他更像是德里达的同代。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著作《历史的终结》里感叹柏林墙的倒塌似乎使历史走到了尽头,因为特定的历史观(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历史观)已走到了尽头。
同理,莎士比亚也像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阔特的同代。彼时阔特身处东欧极权制共产主义国家(波兰)。阔特意识到自己正身处现代主义高涨的时期,一个由贝克特、爱洛尼斯克、布莱希特和萨特领军的时代——存在主义、荒诞主义与革命作家轮番上阵——正是在这一时代,他乐于阅读并饱含想象力地创演莎士比亚戏剧(比较书中《世纪之中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或游戏终结者》两章内容)。正是危急时刻能够明示世人应向莎士比亚索取什么,正是危机时刻使世人用全新的眼光与炽热的心灵重新理解莎士比亚。⑤Jan Kott,Shakespeare Our Contenpotary(London:Methuen,1964)57—74,127—168.
我还想再斗胆揣测一下莎士比亚为何在某些时代更具当代性。当人们能从他那里获得更多智力、道德、精神和政治财富时,他就更具当代性。我们需要这些财富面对自己的时代,在它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记,成为最优秀的人,无论身处的时代如何严酷。欲知库马尔卡统治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波兰局势何等严酷,不妨看看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在自己书序里的描述:凌晨四点被秘密警察叫醒。身为知识分子的阔特就像牛虻一样活着。从莎士比亚身上发现自己是种积极昂扬的姿态,它解放思想,鼓舞人心,激发斗志,“与莎士比亚同代”,借哈姆雷特一语中的的话来说,意味着“时代颠倒混乱”(1.5.189)。哈姆雷特的这句台词在德里达脑海里挥之不去,《马克思的幽灵》满纸尽书“时代颠倒混乱”。德里达眼中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所谓历史终结的年代,既与过去断裂,也在某种意义上与现在断裂,因为它背离了辩证法。
总之,在危机四伏的年代,在过去已经走远,现在不知何去何从的断裂年代里,莎士比亚便具有更强的当代性。这把我们带回老问题上来:我们如何断定在自己的时代里莎士比亚具有更强或更弱的当代性呢?此外,这问题重要吗?当然,这问题教人无从下手,人们也给不出明确的答案。但依我看来,与莎士比亚同代的问题事关重大,可是大多数行头翻新、腔调时髦的当代莎剧表演对此却从来不屑一顾。
就在今年夏天(2013),我在伦敦国家剧院观看了由尼可拉斯·海特那(Nicholas Hytner)出品的《奥赛罗》:它看上去当代感十足,因为奥德赛和同伴穿戴得犹如驻阿富汗的英美士兵。舞台设计也是如此。整个背景——威尼斯和塞浦路斯——令人联想到阿富汗或伊拉克的前线基地,完全是电影《拆弹部队》和《射杀本·拉登》场景之翻版。尽管是一场优秀的当代表演,我却认为演出者并未深入考虑表演当代性是强是弱的问题,因此我要说它的当代性弱。当代性弱的表演虽然紧跟时代,在妆容上尽显当代本色,但在真正的存在意义上,不见当代性。它们没有试图去真正理解我们的时代是“颠倒混乱的时代”,去针对性地探讨时代中潜藏的存在性、历史性和政治性问题。我们再次回到先前的问题上来:如何判定当下的莎剧表演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呢?对此,我的见解是当代性强的表演当出人意料,神秘莫测。它以惊奇的手法表现时代,令人感到陌生震惊,而不是去抚慰人心。它绝非中规中矩,而是怪诞离奇。阔特1960年写就的著作里最精彩的,关于李尔王的章节便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将《李尔王》视作贝克特、爱洛尼斯克和布莱希特式的怪诞剧,而不是布莱德利或索福克勒斯式样的悲剧,实在令人震惊。阔特怎么想到用“怪诞”这一手法的呢?它源自何方?该手法当代性强烈,极富政治意蕴(考虑到波兰当时的局势)。1956年,仅在《莎士比亚与我们同代》发行前一两年,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在未公开发表的《诸神之死》一书中,将波兰政权想象成一具僵尸。他不止一次地将视线投向《哈姆雷特》。“在丹麦,有时一切都烂透了,”柯拉柯夫斯基说的丹麦实指波兰,他指出那是个“腐烂凝滞的国家,是由坏疽菌构成的坏疽体”①Leszek Kolakowski,GodHappy?(London:Basic Books,2013)17,18.。柯拉柯夫斯基邀众参加埋葬统治意识形态的哈姆雷特式葬礼:
这岂是普通葬礼。它恐怖怪诞,因为死尸全然不知已死,反倒以为游行正在兴头上,欢天喜地,大呼小叫,一边把参葬人员赶走,一边狂笑不已。②Leszek Kolakowski,GodHappy?(London:Basic Books,2013)17,18.
这幅葬礼景象,怪诞十足,俨然莎士比亚笔下的“欢乐的葬礼,哀愁的婚礼”(1.1.12)之基调。照此看来,正是令人血脉贲张的时代图景令阔特采用贝克特和爱洛尼斯克的审美维度,视《李尔王》为荒诞作品。悲剧(阔特称其“牧师戏剧”)由此被怪诞剧(阔特称其“小丑戏剧”)取而代之。
真正的当代性怪诞范式也具辩证性,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至关重要。维克多·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PrefacedeCromwell”)中为此提供了先例③Victor Hugo,“Preface de Cromwell”,Cromwell(Paris:GF-Flammarion,1968)61—112.。在书中雨果慨叹,时至法国大革命,历史已不再是出悲剧,而变得离奇怪诞了。也就是说,雨果身处的历史时代,不只是暂时的“颠倒混乱”,而是已病入膏肓。受阔特启发,柯尼斯·泰南回顾彼得·布鲁克出品的《李尔王》时,引用了雨果的论点。“让他安息吧,尊贵的李尔,”泰南低吟。人们不再照原有的方式来演绎此出莎剧了①Kenneth Tynan“,King Lear:A Review”,Peter Brook:A Theatrical Casebock(London:Methuen,1988)23—26.。
为说明用意,我再另举一例。这次我将从哲学角度,而不是戏剧角度来阐述,不过我依旧以《哈姆雷特》为例来表明某种激进的、对当今时代的理解。我的例子是保罗·瓦勒里(Paul Valèry)的著作《思想危机》
他头脑无比清晰,思考人类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这比人类如何从和平走向战争更阴暗,更危险……“那我呢?”他问自己,“我,欧洲之智,将变成什么样子呢?”③Paul Valèry,CTISIS OF The Mind(London:Athenaeum,1919)4.
瓦勒里引述哈姆雷特时表露的焦虑、绝望和另类想法吸引了我,哈姆雷特正“注视着不可胜数的亡灵,他捡拾的每一个骷髅都曾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们似乎排列在一个辩证的延续体上:利奥纳多……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由此可推及)瓦勒里本人。然而这个延续的序列并不体现进步。名望显赫的故人回答不了令他焦虑难安的问题。无人能提供可使哈姆雷特了解自己的知识(哈姆雷特无法从众多的骷髅中辨识出什么)。他们不用同样的声音说话,不合唱,也不对话,说不出什么有用的名堂。瓦勒里笔下的哈姆雷特忧心忡忡,找不到任何东西,帮自己勇敢地面对困境。可他却不能停止张望,不能不继续在巨大的墓地里捡拾骷髅。
简言之,瓦勒里笔下的哈姆雷特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因为它令人震惊不已,那迫切的需求使人不安,心生神秘,怪诞之感。它昭示,甚至激发德里达借哈姆雷特预言西方历史将分崩离析,走向终结,辩证的历史进程即将走向自身的反面。
若要莎剧,无论其文本还是舞台表演,呈现出强烈的当代性,就当使表现手法出其不意,而不可因循守旧,死守老套路不放。同时,这也暗示着莎剧表演上的重大改变,使之体现当代社会对莎剧的解读。当代性强的莎剧表演也不是随心所欲,任意发挥,它甚至可以把在莎剧安插在更大的戏剧框架内。现在,我要谈谈两场新近上演的《哈姆雷特》——在我看来,两者都以上述手法,呈现出强烈的当代性。那既疏离文本,又疏离当下的怪诞思想着实震撼人心。第一场由柏林纳·肖比纳(Berliner Schaubühne)出品,2011年11月,我在伦敦巴比康剧院观看了演出。他由曾执导莎拉·卡恩(Sarah Kane)戏剧(《爆炸》、《菲德拉之爱》、《被清洗的》)该书成于一战之后,浩劫中巨大的死亡人数令瓦勒里强烈意识到文明的衰亡。“文明与个体生命一样终将死亡”的想法始终萦绕在他的心中。欧洲会像尼尼微和巴比伦那样,顷刻间化为乌有。更糟的是,文明会突然失忆,变得焦躁不安。哈姆雷特在郁利克骷髅头前的沉思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欧洲的身躯自深处剧烈地颤抖,她全然察觉自己今非昔比,眼看就要失去意识。这意识沉淀在千百年层层的苦难里,由成千上万的精英铸就,见证过无数地域、种族与历史上的不谋而合。她仿佛要拼尽全力,护卫身躯和心智,于是乎,在迷蒙中,她回想从前。②Paul Valèry,CTISIS OF The Mind(London:Athenaeum,1919)4.
在瓦勒里的凝想中,死亡的前景促使欧洲疯狂地意识到属于她的思想遗产:
她在记忆、所作所为和祖先的生活态度里寻求庇护、指导和慰藉。如此这般,焦虑不安,思维错乱,于现实和梦魇中来回逃遁,活像掉进夹子里的老鼠,惊恐不已。瓦勒里用哈姆雷特象征几近焦躁的欧洲心态,凭借记忆,极力从丢弃的传统垃圾里掏摸财富,自我拯救。
此时此刻,站立在横跨巴塞尔和克隆,广阔的艾尔西诺之上,我们的欧洲,像哈姆雷特那样注视着不可胜数的亡灵。不过,这是个智力发达的哈姆雷特,冥思着生与死的真理……他拾捡的每一个骷髅都曾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是利奥纳多,这是梦想天下太平的莱布尼茨,那是康德,康德之后有黑格尔,黑格尔之后有马克思,马克思之后有……
哈姆雷特无法从众多的骷髅中辨识出什么。但试想他遗忘了它们!他还会是自己吗?的托马斯·欧斯特米尔(ThomasOstermeier)导演。该演出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它彻底推翻哈姆雷特的思想英雄形象,推翻其假作疯癫的知识分子形象。欧斯特米尔呈现的哈姆雷特是彻头彻脑的焦虑狂。此外,舞台设计也令人称奇,但却毫不歪曲原剧。
【幻灯片1】整个推进式舞台的地板做成一个泥坑,喷淋龙头的喷洒使它愈来愈泥泞。泥坑上方,长长的柏斯帕有机玻璃平台由下面承载它的类似塔架的装置(即舞台侧面装有滑轮的装置)前后、上下晃动。一台支架桌横放其上,看似在泥坑上浮动。【幻灯片6】此外,一个类似台口的装置也在上下晃动,其上悬挂着金色帷幕,与支架桌大体相连,可以自行移动。整体背景由这三个基本元素构成,彼此之间幻化出无穷组合。【幻灯片2】在这两个元素——泥坑和宴会桌——之间,大量液体来回喷射(分别暗指排泄和摄食)。桌上的杯瓶被反复倒空,四下散落。泥坑里的喷淋龙头不停喷水,一会儿被用作背景,一会儿被当成演员手上的道具。另一个衔接剧情的液体是血液。举例说,克劳迪斯在祷告之前,在平台上痛饮并溅出巨量的“鲜血”,随后步入泥坑,用喷头淋湿自己,双膝跪进泥坑,开始祷告。这些舞台元素,尤其是泥浆,创造性地串联起戏剧里不同的瞬间。试想那反复使用的热点——泥坑。表演伊始,泥坑后方就上演了给老哈姆雷特举行的葬礼:棺柩横放在露天墓场上,掘墓人缠绕绳索,放下棺柩,接着自己走下来,身后拖着克劳迪斯。之后,在修道院一场中,哈姆雷特在这里几乎强暴了欧菲利亚,把她的头摁进泥浆。在密室一场里,哈姆雷特在这里放倒了王后。欧菲利亚的葬礼也被安排在这里。如此一来,厌女主题就与死亡主题互为联系。骷髅头也是在泥坟里找到的。【幻灯片4】有好几次,哈姆雷特简直就是在吃泥:一次是他对欧菲利亚和王后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时,一次是埋葬欧菲利亚时。此外,还有其它泥坑场景,也颇令人难忘。哈姆雷特在宴会桌上对王后说“我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时(1.2.85),抓起大块泥巴,朝她的餐盘扔去。克劳迪斯高谈哈姆雷特“孝思不匮”(1.2.93)时,拍打哈姆雷特的后背,使他俯身摔进泥坑里。“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1.2.146)是在泥坑里喊出来的。诵读“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一段台词时(2.2.294-312),哈姆雷特面朝泥坑,静坐宴会桌一隅。
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所有角色都怪诞不经,甚至到了像丑角的地步。哈姆雷特显然发了疯,王冠倒扣在头上(人们永远不会在英国人出品的莎剧里看到如此不敬之举)。自始至终,哈姆雷特疯疯癫癫。【幻灯片7】克劳迪斯虽然正戴王冠,却长着个红鼻子,既像小丑,又像染上了鲜血(注意看他额头)。【幻灯片5】哈姆雷特完全不是“斯文人”,而是侍宠的顽童和危险的疯子。【幻灯片3】此处,他在胁迫欧菲利亚。拉尔斯·艾丁格,哈姆雷特的饰演者,看起来很胖,邋里邋遢,穿着松垮走样的衣服和肥肥大大的裤子(你们看不到他这副尊容,不过,我的描述足以给你们留下了他肥胖的形象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他角色都苗条健康,也较显年轻。王后与他的反差尤其大,因为王后与青春貌美的欧菲利亚是一人分饰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要把哈姆雷特的外形弄得如此不堪?这自是有意的选择。【幻灯片6】在剧中剧上演前,拉尔斯·艾丁格为出演剧中剧王后而脱去了上衣。其时,我们发现,艾丁格一点也不胖,他匀称修长,年轻帅气,和其他演员别无二致。那究竟怎么回事,究竟他哪里让我们觉得他肥胖呢?为饰演王后重新着装时,艾丁格穿上了胖女人的行头——尤其醒目的是下垂的双乳和鼓鼓的肚腩,“这一个太坚实的身体”(1.2.129)实指他母亲的身体,女人年老色衰的残旧之躯。
我希望所说的一切也足以表明,柏林纳·肖比纳出品的《哈姆雷特》与惯常所见的舞台表演大相径庭:后者的表演往往忠实地呈现全本,或者,至少不会大幅删减或修改剧本。欧斯特米尔的自由改编则超越常规,独白被大大压缩,仅保留只言片语,在演员口里含混不清,抽搐哆嗦地重复着。就这样,哈姆雷特的内在被系统地否定了,而他的内在恰恰是他感染力的主要来源。欧斯特米尔的作品与任何英国本土的作品(即便受了阔特思想的熏陶)都相去甚远——主要在于,无论哈姆雷特多么激情万丈,勇敢坚毅,或者多么沮丧绝望,英国人都不可能令他这般疯癫和难看;他们的表演也绝难这般另类。这出表演自然令人瞩目,不过,这又如何?如此颠覆哈姆雷特十九世纪以来广为流传的经典形象,究竟意义何在?
首先,它突破了《哈姆雷特》的悲剧模式,带给我们一出怪诞剧,类似阔特笔下古怪的李尔王。(比较而言,阔特关于《哈姆雷特》的评论更传统,不那么教人吃惊)。从根本上说,阔特诠释出一个英雄式的哈姆雷特,不同于歌德所说的软弱却奋进的浪漫主义者(“精致,纯洁,高贵,有德行,却缺乏使之成为英雄的强烈情感,”“在重担之下彻底崩溃,既不能承受,又无法摆脱”)。阔特笔下的哈姆雷特是“天生的反叛同谋”,反抗剥削者与其同伙横行霸道的警察国家。这没什么不可以。阔特显然在就事论事。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这一反极权统治的《哈姆雷特》已变成西方民主国家表演的范本。换而言之,它成了弱当代性和假当代性作品的范本。说它们假,是因为它们跟在阔特身后,人云亦云,不去反映自己的时代,却哆哆嗦嗦地山寨阔特描绘的共产主义波兰。我数不清已看过多少这种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光彩的哈姆雷特表演了。
欧斯特米尔的《哈姆雷特》不跟风阔特。那它的意义又源自何处呢?它强烈的当代性在与谁对话?吊诡的是,我以为它至少对应了《哈姆雷特》批评史上遭人遗忘的一个阶段,即提出反哈姆雷特主义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G·威尔森·奈特(G Wilson Knight)的一篇《死亡大使:论哈姆雷特》(“The Embassy Of Death:an essayon Hamlet”)使反哈姆雷特主义为人所知。在奈特看来,哈姆雷特不是软弱,而是头脑和精神都患了病。这并不是说哈姆雷特没有遇到真正的麻烦,而是说他变态地迷恋这些麻烦,把自己弄得神志不清:
从头至尾,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部戏……死亡才是真正的主题...因为哈姆雷特的病症在于他的思想和精神的死亡。奈特认为,比起身边相对健康的普通人,哈姆雷特更显丑陋,令人不安,惫懒消极。①G.Wilson Knight,“The Embassy of Death”,The Wheel of Fire(London:Routledge,1989)17—19,28,32.
抛开父亲被谋杀不谈,哈姆雷特身处的世界是健康蓬勃、和和顺顺、幽默诙谐、浪漫幸福的。惟有他面色苍白,沉湎在死亡意识里……这意识像恶疾般传播给旁人……②G.Wilson Knight,“The Embassy of Death”,The Wheel of Fire(London:Routledge,1989)17—19,28,32.
总之,剧中真正的问题人物是哈姆雷特,而非克劳迪斯。在我看来,在欧斯特米尔之前,从未有人上演过威尔森·奈特这一版的哈姆雷特。他呈现的哈姆雷特与威尔森·奈特描绘的病态的哈姆雷特如出一辙。我倒不是说,欧斯特米尔曾读过威尔森·奈特的文章。事实上,我认为,欧斯特米尔对病入膏肓的哈姆雷特的塑造,得益于他执导过的萨拉·凯恩的戏剧作品。凯恩的戏剧不是悲剧,而是雨果和克拉科夫斯基式的怪诞剧(或许出于无心)。此外,她的戏剧既不表现痛苦(在对立原则之间挣扎),也不表现辩证(正论与反论的对立),而是反映内爆。内爆首先源自凯恩对生活环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伦敦)本真的生存体验,也源自她与使自己深受启发的两位先辈的对话:贝克特与塞内加。若说凯恩作品之荒诞不经源自贝克特,那么她作品的野性和内爆则源自塞内加③Graham Saunders,“The Beckettian World of Sarah Kane”,Zina Giannopoulou,“Staging Power:the Politics of Sex and Death in Seneca’s Phaedra and Kane’s Phardra’s Love”,Sarah Kane in Contex(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0)68—79,57—67.。何谓内爆?格里高利·斯达利(Gregory Staley)在研究塞内加的新书里指出:在希腊悲剧和神话故事里,魔鬼是与英雄较量的外部力量(如《俄狄浦斯》中的斯芬克斯),而在塞内加作品里,魔鬼盘踞在英雄的内心。所以:
魔鬼不是受文明教化的英雄需要制服的外部力量,而是盘踞在英雄内心的欲望化身。它们是……“具有人形的邪恶”。④Gregory Allan Staley,Seneca and the Idea of Traged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119.
塞内加笔下的俄狄浦斯内化了斯芬克斯;在塞内加的世界里,恶魔出没于宫殿之中,而不是像希腊悲剧所表现的,藏身于山高水深、人迹罕见之处。塞内加展现的英雄一不追寻,二不捍卫,三不痛苦。他只是在拼命制造自己身上已有的东西:恶魔,“某种有待解释的,不自然,异常之物”。而这就是我所说的“内爆”。看过欧斯特米尔导演的《哈姆雷特》的伦敦观众无不震惊。无论如何,演出令伦敦人深受刺激。伦敦向来是国际银行业各种难以道明的问题发生的震中;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会顷刻间被愤怒的市民占领月余。伦敦暴乱——暴力愚蠢自发的爆发——即将在朗朗晴空下引爆,就像塞内加描绘的那样。因为对欧斯特米尔和凯恩来说,古典戏剧——莎士比亚戏剧也罢,塞内加戏剧也罢——是触发时代神经的场所,是缪斯和密探。它是时代的图景,刺激潜藏其下问题的催化剂和一面镜子,“给时代看一看自身演变发展的模型”(3.2.23-24)①Gregory Allan Staley,Seneca and the ldea of Trage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96.。欧斯特米尔的《哈姆雷特》深具当代性,因为它完全遵循了阔特提出的当代性理论,尽管理论本身更具辩证色彩。正因如此,它与诸多当代性寡淡的所谓当代莎剧大相径庭。真正的当代性作品不会依葫芦画瓢地表现人所共知的东西;它是斜睨,是残片,是预感,是神秘。
Shakespeare:the Uncanny Contemporary
〔UK〕John Gillies.Trans.Zhang Dongyan.Proofread.Zhu Binzhong
How to understand the idea that“Shakespeare is our contemporary”,put forward by Ian Kott in hisin 1960?The essay tries to illustrate that being not self-evident,the statement actually indicates some paradoxicalrelationship.Unlike people whoregard contemporariness assomething already“well-known”by theworld,Kott approaches Shakespeare’s plays from a modernist perspective,and interprets the contemporariness of his plays as an estranging force,which serves to alienate the commonly accepted meaning of the play,while disclosing the explosive potential implications.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wo overwhelming performances of Shakespeare’s work in the recent ten years,the essay makes a reflection on Kott’s theory,pointing out that both performances manifest Shakespeare’s contemporarinesswithgrotesquerepresentations,and display theculture and thoughtoftheearlymodern society littleknown by contemporary audience.The two aspects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it is the unassimilable parts of Shakespeare’s play that drive the directors to stage their offbeat and estranging modernist recreations.
Contemporariness;Estrangement;Modernism
责任编辑:涂险峰
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es)(1947—),男,目前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ssex)文学电影戏剧学院教授(Professor of Literature,Film and Theater Department),主要从事跨媒体艺术的教学和研究。
朱宾忠(1963—),男,湖北竹溪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张东燕(1974—),女,河北辛集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讲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