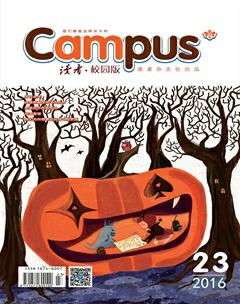小编絮语
温彬
少年时(大约十一二岁吧)我有在每晚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枕侧放着的一摞书过一阵子就会更新,但那本被我翻烂了的《泰戈尔诗选》,那些年一直翻来覆去地读,总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泰戈尔作为一位真正人格洁白的诗人,他的诗句素朴、清纯、温情、洁净,可以说贯穿了我少年的读书生涯。
身边的朋友都戏称我是个“诗人”,如果这个称号真的成立的话,那么天竺国的诗坛巨擘、亚洲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泰戈尔,他之于我的意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滋养了我的“诗心”。
年幼的泰戈尔身处令自己虔诚以对又充满好奇的大自然时,看到天边那蓝灰色的云载满浓密的雨点,看到夜的黑暗将那幻影之门打开,他的内心深处充满最深的喜悦,于是他写道:“世界上空无一物,一切都在我的心里。”同样地,当我读到这句诗时,那样一种朴素但又立体、宏大的情愫油然而生。
翻开《飞鸟集》,那静谧的抒情,如画的描绘,那深深的怅惋里淡淡的诉说,每一次的细心咀嚼或者深情朗诵,都会让我觉得,自然的精神和精神的自然,再没有人能比泰戈尔在这部诗集里领悟得更加深刻,表达得更为完美的了。
再到《吉檀迦利》—这部意为“献给神的赞歌”的诗集,更是泰戈尔的巅峰作品。诗中那些神秘、深邃、典雅、诡谲的语言,集中展现了深受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双重浸润的泰戈尔的非凡表达。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我不能从春天的财富里送你一朵花,天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片金影。开起门来四望吧。从你的群花盛开的园子里,采取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在你心的欢乐里,愿我感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把它快乐的声音,传过一百年的时间。”
木心有一段话说得很有趣,他说:“伟大的诗人,如屈原,往往在生前就已知道自己一定会永垂不朽。每个大艺术家也都在生前公正地衡量过自己。有人熬不住,说了出来,如但丁、普希金。也有一种人不说的,如陶渊明,熬住不说。”
对照木心的观点,我们读了上面所引《园丁集》里的这段话,该如何评价呢?这是泰戈尔意识到自己的不朽,婉转地向百年后的读者传达他的预感吗?我认为不是。泰翁百余年前与后世的读者对话,仍然是他一以贯之地以那颗恬淡开阔的心,为人们种植每个人心中安然盛放的欢乐,从而使我们与平凡庸俗的世界获得暂时的隔离。
假如你用心去品咂泰戈尔的诗,你会感受到那一盏明亮不熄的灯火,温暖地照映你疲倦的心灵,不会使你产生陌生的疏离感,也不会感到其他文学可能具有的遗世而独立。
那是穿越了数不尽的时间和空间,一个生命对许许多多个生命的指引;那是哪怕当我们走到归途尽头,缓缓回望这一生,含笑吟唱起泰戈尔留给我们的文字,额前必然有光明永驻的无尽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