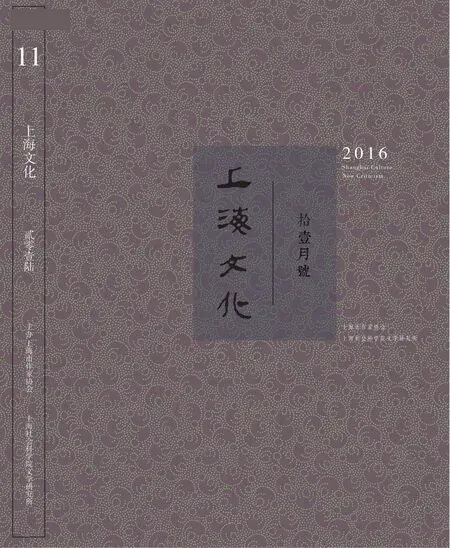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格非《望春风》
项 静
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格非《望春风》
项 静
一
格非在漫长庞大的“江南三部曲”之后,以《望春风》单纯而强势回到“故乡”,像是一次告别故土的文学仪式,格非对于这部作品慨然定下基调,“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每一次文学意义上对乡村、故土的回望,如果不是无效地重复,必然要走一条氤氲之路,在看不清楚的视野中,坦露那些真诚的见闻和心绪。乡村生活积聚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审美,在地者直接或间接地以之谋生,围绕着居住地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时至今日,乡村生活在文学和社会中的意象修辞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间的复杂歧异一直是各种话语纷争的地盘,格非选择了最宽泛意义上文化记忆的视角。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特别论述了文化记忆对于人们的影响,人总是被或日常或具有更多私人意义的物所包围:从床和椅子,餐具和盥洗用具,衣服和工具,再到房子、村庄、城市、街道、车船。人对这些物形成了诸如实用性、舒适性和美观性的认识,并从某种程度上也将自己投射其中。因此,与乡村有关的人与物也反映了人自身,让他回忆起自己、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先辈等等,人曾经生活过的世界是最可能一触即发的时间索引,这个时间索引和“当下”一起指向过去的各个层面。
《望春风》是“我”讲述的村庄往事,它从简朴、内敛的淳朴往昔到在时代大潮中风雨飘摇,急剧重组、分崩离析的过程,外在于村庄的是196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变迁历程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人们的生活、情感方式,它保留了超越个人的时代信息和资料。如果把这些组成小说的叙事流切分成块,正好可以暗合文化记忆的四个外部维度,模仿性记忆(“我”在儒里赵村的模仿性学习成长),对物的记忆(四时风物的描写),语言和交流的交往记忆(对人们交往的观察),对居于其中的集体意义的传承(村庄消亡中的挽歌情怀)。叙述者 “我”是一个作家,小说呈现了一个在中国社会中并不具有典型性的作家成长史,他不像我们当代文学史中常见的从农村进城的名家们,被写作改写了命运。包括作家本人在内的整整一代作家,比如莫言、张炜、阎连科、李锐、贾平凹等等,他们或者土生土长在乡村,或者有过长久的乡村生活经历,乡土写作成为他们浓重的印记和标签。“我”是一个从没有进入当代文学系统的局外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格非在总结自己从先锋到现实主义的创作转变时说,“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新奇、冲动、走极端甚至凌空蹈虚,给我的创作打上了特立独行的印记,但也留下了过于注重修辞的隐患;这三十年来,对普通人与普通生活的‘发现’让我打破了通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观念的变化无疑会反映到创作中来,成为我个人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调整”。《望春风》是这个调整的继续,“我”的视角可能是对于既有的呈现乡村巨变的文学话语、程式、意象的一次有意的转移和疏离,当然更可能是幻想中的革命,毕竟重重帷幕之后的主导者依然是局中人格非。
“我”的全部文化修养和文学积累是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邗桥的图书馆看过百十来本并未详细述及的书。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简略勾勒出叙述者的养成记,首先是在私塾中受教于同村的赵锡光,读书写字的时候并不多,大好光阴,多半用来讲史论古,念叨那些令人不胜其烦的陈年旧事,包括显赫的村庄历史:儒里赵村原籍山东琅琊,是时代簪缨的名门望族,永嘉时代迁至风光秀丽的江南,择吉地而居。祖先们人才辈出,曾出过丞相、进士、方伯、武状元。昭明太子在读书之余,常到这一带赏玩山野风光;刘裕起兵时,曾在村后的磨笄山上射下一只金雕;刘备在甘露寺喝的酒是从我们村运过去的;苏东坡在常州卧病不起时延请我们村的神医赵龙豹给他诊病,乾隆皇帝每次下江南都会在这里驻跸,陈毅、赵孟舒给他弹过琴等等。这些由民间传说和真实几番加工过的集体记忆性的村庄史,代表了这个村庄的辉煌、人才、文化风景和人生观、教育观,也是有形村庄的无形组成部分。作为一个赋予村人身份和认同的空间,是一个被唤醒的空间,它也塑造和给予“我”全部的思想和文化教养。耳濡目染赵锡光和父亲算命先生对世态人心的观摩,“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是了解那个地方的人,越详细越好,越客观越好……观察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其余的都是小事”。这是对本土本地的认知方式和关于自我确
认的知识,与古朴的村庄史、生存方式、民风民俗密切相关,也为“我”村庄观察者的作家身份提供了前史。
另一部分文学教育来自于邗桥图书馆的沈祖英。格非说他是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话,在这些对话者之中,荷马的《奥德赛》、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艾略特的《荒原》、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等,在小说中可能都是从沈祖英这里获取的, 所以“我”对沈祖英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我喜欢她干干净净的样子,喜欢她的胆小和恬静,喜欢她脸上那种充满揶揄却欲言又止的神情,喜欢她身上让人无法接近的深切的悲伤”。 沈祖英推荐“我”读《奥德赛》,在这个图书管理员那里领会了另外一种有别于乡村世界的人间情怀:每个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岛,可以互相瞭望,却无法互相替代,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沈祖英对黄庭坚的《登快阁》极为推崇,“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情。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这首诗是古典士绅社会的文人写照,孤独寂寞和知音难求,这对于“我”能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姿态,成为一个特立独行者是非常重要的。“我”身上那种不言而喻的末世情怀,对自然世界的渴慕,对人世的疏阔旷达,对人生的悲悯,既有现代意识又有古典情怀,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
小说的第三部分,叙述者跳出来插话,“您知道,我这个人知识贫乏,见解浅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才华。我之所以写下这个故事,就像春琴所说的,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如此而已。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也还读得下去,我要感谢你的耐心与大度。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只能对你说声抱歉。除此之外,并没有多余的话要讲。”这是终结和反抗某种写作方式的宣言,也是一次低于一般叙事者的声明。在拒不提供教谕和历史观念的小说中,“我”那控制不住的寂寞悲伤,对事实上不存在的母亲的依恋,难以言喻的对时间和故地留恋,四处遗漏的老年情怀,时间、人生、空间的具体形象在过度的抒情性中获得圆融——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格非说,他十七岁离开家乡,了解最多的,就是这块土地,那个村庄里的人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方式、表达感情的方式,还有他们的语言,没人想去保留,但它们却是极其重要的。在他看来,不少人早已不在,但可通过时间机器让其重返,“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文学可以让他们回来”。于是“我”和春琴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回到了出发之地的废墟上,重新过上童年时代的生活。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写作动机,“等我们两个人都死了,这片地方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也许没人知道,这里原先有过一座千年的村庄,村子里活过许许多多的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我告诉她,其实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试着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写作回归到最初的“故事”,一个讲给本土本地的自己人听的故事,因为“我”的视野限制和作家格非的有意为之,他拒绝教谕和宏大题旨。
在以堂兄赵礼平为代表的强权社会迅速取代和冲击乡村生活之后,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痕迹,可能很快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望春风》通过乡村社会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书写者及其视野,重新构建了写作与乡村的关系,让他们的经验和生活在文学中获得平等的权力,并且以他们自己的视角和声音来证明时间的流逝,着力摆脱精英主义式、貌似底层实则是俯视者、审视者们的呈现方式。撇开文学本身的虚构性和作家身份不谈,繁复的伤感主义式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此类写作的批判性和深广度,但它变得单一而纯净。
二
从宏大回归微小,回归到一个生命的内在需求,拒绝被遗忘 ,就像福克纳《野棕榈》中那个失去祖母的叙事者,“当她不再存在时,我记忆的一半也就不在了,而假如我不再存在时,那么所有的记忆也都不在了。是的,在忧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的是忧伤”。《望春风》中所有的忧伤最根本上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和人在时代风浪中的不由自主,以及对于生命最初美好时段的复归而不可得,由此时间是小说的第一主角。
小说由三个章节组成,分别对应三个时代,第一章是父亲的时代。故事的开始声调是平缓的,一个算命先生的儿子,母亲远走异乡,由身世带来的敏感让他在解放初期的江南村落中成为一个细致的观察者,他的观察对象是村庄的一切,从世态人心、人生哲学、乡村秩序到微末之变。1960年代的中国乡村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归属,半塘春琴家的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明示了社会的翻天覆地,已经是革命之后的声息,但依然保存着前革命时代的乡村社会形态,一个稳定的乡村共同体。村落给人的感觉是安静,村庄常态里最基本的是风景风光和人情 , “当我跟父亲走到风渠岸边,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听到村里那熟悉而温暖的舂米声,看见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的一盏油灯,在院子里‘喔嘘喔嘘’地叫唤着,正把母鸡赶进鸡窝,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宁静、踏实和甜蜜吧”。这个村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算命先生是当地一种繁茂的职业,赵孟舒能够带着一个漂亮的妓女王曼卿在村里颐养天年,也接纳了身世不明的外乡人唐文宽。小说中大段抒情和向往的时空都属于这个时段,民间的复杂人伦依然存在,村子中有许多秘密,半遮半掩,半新半旧。在面对天灾人祸时,半塘寺的瘌痢和尚还是被春琴的母亲请来算命,不过他的禳解之法已经无法实行,“如果是在旧社会,非常好办,让这个小把戏跟我去庙里做和尚,我保管他无病无灾,寿比彭祖,可如今是新社会,不兴出家的”。瘌痢和尚在火灾中丧命,春琴妈妈又找到父亲赵云仙解决命运的难题。新时代的干部梅芳对“我”父亲的嫌弃和“我”对她的厌恶,是新旧交替时代的情感冲突,但其中夹杂着个人私事,并没有公共意义上的黑白分明,也没有发展成为不可遏制的冲突和斗争。
第二章是德正时代,德正与父亲、“我”的关联是小说第一章主人公的重要行动力,那一次大抒特写的半塘之行背后其实是父亲的一次重要政治安排。为德正说媒,将春琴嫁给德正,这是一个算命先生长远的人生筹谋。德正开启了儒里赵村的新时代,他在政权更迭中因为出身贫寒,偶然的机遇被选为农委会主任,他在村里的大部分工作是两件大事,学校落成,把磨笄山推平填沟壑造田。德正的上台,跟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上台是同构的,一个穷孩子翻身做主人的故事。从一个没家没产,安顿在祠堂里的孤儿轿夫,被选为一村之首。他的政绩也受到了肯定,维持既有的乡村生态,并带来新生的气息,小说中对德正时代的1973年初春有一番深情描述,“新垦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茬油菜,漫山遍野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酿蜜……赵德正把便通庵修葺一新,作为知青的宿舍。随后,他在知青点的边上新盖了七八间矮平房,建了一处养猪场”。
格非说《望春风》是从第三章开始写的,如果同样以时代命名,余闻的时代是属于堂哥赵礼平的时代。赵同彬说,礼平“为人险恨,又一肚子坏水。对它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规矩’二字”,礼平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余闻交代了村里所有人等的命运归宿,他们几乎都能跟赵礼平攀上牵连,从高家兄弟到小武松、朱虎平、梅芳、春琴等,在赵礼平的时代都湮灭了曾经的虎虎生气,它们像村庄一样成为废墟。《余闻》是第二章最后一部分所预言过的翻天覆地重大事变的结果。余闻是来自今天的现场消息,上一个时代人们故事的下文或者余波,依然在传颂中,余音袅袅。巨变是在潜流中开始的,比如村里唯一一个大地主赵孟舒之死,他死于新时代的批斗,死于维护个人尊严,唐文宽被撤职,安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村里接受劳动改造等,是政治带来的变迁。赵同彬一劳永逸地取代了老菩萨唐文宽的地位,唐文宽接连不断地向孩子们兜售那些谁也听不懂的怪话,再也无人发笑,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小五义》故事,开始让位于同彬口中那些让人心惊肉跳、呼吸急促的《梅花党》、《一把铜尺》、《绿色尸体》以及全国各地的离奇见闻。堂兄礼平开了第一家胶木厂,公私不分,钱已经多到可以带上全家去杭州旅游。一直到最后,朱方集团让村庄变成废墟,是时代发展和经济变迁使然。赵德正先是被捉,遭受游行的凌辱,回到自己最初的岗位,回祠堂当仓库保管员,1976年得了白血病。收到母亲的召唤,“我”离开了儒里赵村,梅芳自我觉醒,辞去革委会副主任一职,可能是命运的起伏波澜。总之,儒里赵村在各种不可抗拒中走向废墟,余闻中的人事变迁就是一场生命的巡礼,叙述者、作家和故事中人互相映衬投射。
三
小说的另一个主角是儒里赵村的秩序,《望春风》前两章的外形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史,母亲远离村庄,成为另一个秩序(城市和革命)里的人,父亲怀揣着一个秘密在1966年自杀,于是“我”成了一个父母空缺的少年,在村庄里接受教育(父亲赵月仙对人心的理解,唐文宽的故事闲话教育,赵锡光的识字教育),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伦、日常和变异,最后被遥远的模糊的站在革命前沿的母亲接走。实际上小说的主角是儒里赵村的社会秩序,村书记赵德正与“高家帮”(主任高定国、高定邦和他的副主任妻子梅芳)虽然一直不和,但也没有陷入“斗争”思维,在关键时刻,“高家帮”都是出手援救赵德正的带头人。比如涉及“文革”一段历史,小说中没有许多小说中惯常的“戏剧化”,而是把那些波折融化在儒里赵村的社会秩序里,上面有人设计陷害书记赵德正,最后的结果是被村里的男人们反将一军,并没有触及他的生活和安危,一切也就不了了之。赵德正去职之后,燕还旧窠,仍回祠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妻子春琴说“定邦这个人还算有良心”。王曼卿这个被赵孟舒带回村庄,后被唐文宽接管的风尘女子,有着跟赵孟舒、唐文宽令人艳羡的生活情调,又和村子里的男人们纠缠不清,居然也维持着和谐,就像冯师娘容忍丈夫的相好文英最后伺候赵锡光。
从这些细节来看,对于历史的表现,《望春风》给出了许多解读式的呈现,借着一个村庄的有机运行,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漫长的历史,以及当代历史上最被叙述关注的“文革”年代。革命(母亲的系统)和反革命(父亲的上线们),其实都是以非常微弱的余波方式到达这个村庄的,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是以一个秘密的方式存在,有待时间来解开。正是村庄既有的秩序,让人们各司其职,各安其安,让唐文宽这样怀着秘密的外乡人成为村中少年们的快乐之源,让赵德正这种孤儿,也能在成为书记后,有模有样地规划大事。当然也会创造出像堂兄赵礼平这样不守规则秩序的“叛逆者”,聪明而蛮横,成为秩序的破坏者,也是未来历史发展中走向强势的人。对曾有秩序的呈现,当然有格非所说的偏见,“惟有我打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才是值得终生守护的地方”。这种信念和“偏见”是历史真实,也是文化虚构之物, 就像“我”母亲在最后一封长信中,把儿时的故乡视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折返之光所照射的“往昔”,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建构,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作家对过去的重塑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文化记忆框架下的自由组合。但关乎强烈情感的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无论是对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平静时光的选择和深描,还是对小说中重要人物“父亲”、赵德正、春琴等人的讲述,都印证着作家的折返心绪,但乡村秩序的终结者比如赵礼平、具有更复杂的文化修养和神秘经历的唐文宽的内心呈现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福斯特说,人与人之间的事,根本没找到什么可用的精密武器,恐怕只有人类的心灵来担当这项任务了。赵礼平、唐文宽等人依然半遮半掩的人生,或许可以承担更多的文本任务,或者也就是这种余闻旧事、欲说还休的方式才是非戏剧化的往昔真意。
“我们服侍过大地母亲/近来又敬拜过太阳的光辉/不觉之中/支配万物的主/最爱被人精心护理/真真切切的文字把此在/诠释得清清楚楚”(荷尔德林)。时间出现了断裂,往昔之物和意义几成废墟,相关的人试图跨越这个裂痕与之前保持联系,《望春风》是为了联系的文本护理,需要那个被选中的“我”真真切切地书写。一本小说最后的考验是我们对它的情感,正如我们对友情或对其他无法解释的事情的考验那样。《望春风》单纯明晰一如时光掠过田野,忧伤不经遮掩地配备给每一个普通人,“我”(作家)的出身和愿望要拒绝和避开既有的文学套路,以自己的方式去打散和整理故乡的记忆,回到最基本的文学功能,回到普通人的心灵中去。文学浮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人,曾经的生命历程和他们的消失。《望春风》没有判断和指摘,它更不会去刻意营造自己的乌托邦,它用黄金时代的辉煌词汇包裹现时的废墟,让这些实有之物在时间河流中折返、唤醒进而升腾,冲决克制的情绪,悲伤和抒情恣意流淌。
编辑/吴 亮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