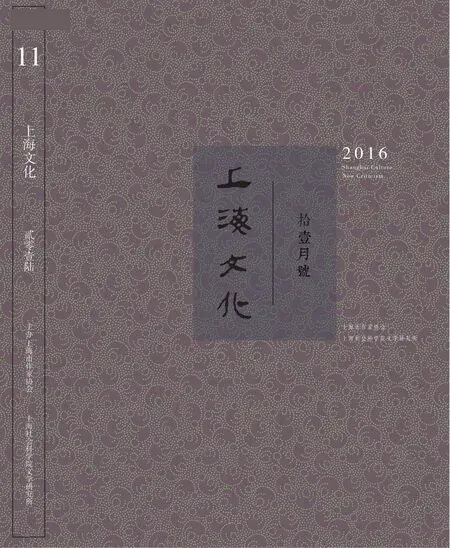我们总是比生活既多些又少些读双雪涛
木 叶
我们总是比生活既多些又少些读双雪涛
木 叶
《平原上的摩西》(以下简称《摩西》),是近年所读堪称惊艳的极少几部小说集之一。作家双雪涛的《天吾手记》、《翅鬼》,乃至曾析分开来发表的《聋哑时代》(《安娜》、《我的朋友安德烈》等),与这个集子里的中短篇光色互见,彼此应和,一种气象正静静升起。
一
他的语言非常有小说感,他是为此而来的。“我的睾丸突然剧痛……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阉了才好”(《我的朋友安德烈》),“我这身板,放个屁自己都得晃悠”(《生还》),作者不避雅俗,直抵要害,行文鲜异而准确;“我知道你糙,但是你也不要嫌我细”,“他们相互需要,也让彼此疲惫”(《摩西》),这两句均略带对仗性,有理有情,老辣而清新;“病是理性的,或者换句话说,是写实的,而死亡,是哲学的,换句话说,是诗性的”(《长眠》),这话抽象,不管不顾,又不失形象,纵是你未必认同,也可感受到它对小说中远方、恩义、理想性行动的潜在指涉——以上不免有些断章取义,然可会其大意,有兴趣的人亦不妨寻觅这些花朵或枝叶所在的整个植株,感受自下而上或自内而外的生命力。
他写人物对话一般不加引号,有一种漫不经心的生动。《摩西》里,庄树作为实习刑警和几个老警察一起抓捕在逃多年的杀人犯,“其中一个人刚从矿下上来,看见我们在等他,说,我洗个澡。老警察说,来不及了,车等着呢。走过去给他上了手铐。他的头发上都是煤渣,我年少时的玩伴,随便哪个,看着都比他强悍多了。他说,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老警察说,让他们去看你吧。在奔机场的路上,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早来就好了,我把那娘俩坑了”。就像相识已久或是有约在先,双方的对话很是“默契”,透出层次感:见有人在等(是否他也在等警察?没反抗,却隐含着较量);提出要洗澡(因了尊严抑或其他);老警察否了他,理由是车在等(又是“等”,而这车瞬间升至某种高悬的威权);他想看看家人,老警察说让他们来看你(宾主易位,心境迥然);一路无语,只说警察来晚了(责人还是责己?几多释然几多遗憾)。这不是他所写最出色的对话,也不属于本篇小说的主体故事,却充分体现了个人与自我、家庭、社会和公权力的碰撞,一个微型的“罪与罚”。值得补上一笔的是,都是小学三年级便认识的字,作者不难为读者,但深者得其深。
他是爱读诗的,喜欢诗歌语言的“童贞”,喜欢语词间的相遇和韵律。《长眠》里,融入了自己的诗作,他曾谦称,“写得很差,不入流,算是过了一把瘾”,其实那些诗句有些野逸与劲道。当我见他在《大路》里化用海子关于黑暗的诗,捏了把汗,读罢觉得妥帖,她说,“我一直以为黑暗是从天而降,今天才知道,黑暗是从地上升起来的”;他说,“可能黑暗一直在,只不过光跑掉了”。《走出格勒》男主人公在有些囧的情境下背诵了曼德尔施塔姆写列宁格勒的诗:“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两处化用均是将诗歌名篇融入俗常叙事,隐去了作者与篇名,前者和故事情节若即若离,而对光与暗生成方式的巧妙引入,颇有益于小说中对成长问题的辩证;后者除了情境恰切,唤醒对生活之城以及陌生形象的感受力,还成为了小说篇名的一个来由。
“语言是小说的源头,也许现实是另一个源头,但是我总觉得语言是一个更重要的源头”,他对语言的及物性和虚构性均有持续的摸索。
他的行文,注重节奏,句子长短相配,发力的往往是短句,一不留神就给你一拳。有时又如古人用兵所讲究的“围师必阙”,呈现一种未完成感,而意思又都在那里了,以空白言说,以空白召唤,余音缭绕。《大师》尾声,和尚赢了棋,临走时留下一语:“我明白了,棋里棋外,你的东西都比我多。如果还有十年,我再来找你,咱们下棋,就下下棋。”什么东西?当真就下下棋?意犹未尽,却胜似说了,对于文中父子与小说读者而言,这种不像结束的结束开启了一个新的行程。
也许和家乡风物不无关系,他的文字里有着朔风之劲,也有着欧风美雨洗礼后的雪映明月,语言冷硬,不动声色,而又平易幽默,有效推动叙事,丰满了人物形象。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他所心仪的作家汪曾祺的话,他很可能读过,并深有会意。是的,语言不是像桔子皮一样可剥可扔,也不是附丽的粉黛。
并非一个人说自己看重语言,便能写好,这里有天赋,有想象力,也有看不见的勤力与砥砺,又须得是一个卓越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穿行于人间烟火,世俗而笃定,敏于生活之肌理,长于语词之调遣,语言如水,想说的意思都生长在里面,沐浴其间,不是简单的美与不美,而是“自然而又突然”,极具感染力,而又不无远意。
我喜欢双雪涛的原因,可能还在于真的阅读时自己并不会特别在意其语言,甚或会忘记它们,而是为其文字对时代生活超拔的翻译能力和塑造能力所吸引,投入其中,投入那些虚构的人物,及其真切的命运。
二
“那是一种努力……和他的真正存在一起走向语言,被现实击中并寻找现实。”现实、语言、存在、努力……诗人保罗·策兰的洞见,引我更深入地去思考双雪涛的文字与小说实绩。他与现实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更主要的是一种迷离,包含相互辨认、赋形和深度转化。而有了“努力”,所谓的“击中”将是相互的。
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大多涉及成长与青春,典型如短篇《跛人》和长篇《聋哑时代》等,无论是远行,人与人的相遇相失,还是社会的洗礼,即便在《大师》、《摩西》中,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心迹亦均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我不喜欢“青春小说”的说法,在这一概念的明确性之中恰恰隐含着一种固化和窄化。他的写法,与流行的青春叙事不同,至少决不是那种早已被命名甚或写烂的“残酷青春”。他写青少年,写校园,却又越出校园和教育问题,指向庞然之物和幽秘之境,青春向前向后均有着暧昧而攸关的延长线。他想必了然,青春是无法逃出去的,只能经历、领受、挥洒,汇入烦杂而深切的生活。他的一个优异之处,正在于写出了生活潜在的面目。
他在一篇小说中写道,“人无论多小心翼翼地活着,也得损坏”,而书写这种生命历程中的小心翼翼及其损坏,可以说是历史上无数经典小说共同的动人之处。这令我想到曾看过的一篇文字,其中有一段关于“既多些又少些”的妙论,很是触动我,可惜一时寻不到出处,不过我还是愿意将它移用于此:我们总是比生活既多些又少些。多些什么又少些什么呢?理应多些阳光和美好,少些黑暗和罪恶,而事实上,我们往往是反着的,会比生活本身或当下所能提供的多出来忧愁、迷惘、虚伪、欲望、暴戾、堕落,而少了真挚、良善、宽容、勤勉、坚韧、温馨……书写那些少掉了或多出来的东西,那些可见或不可见的“不足”与“有余”,正是一个小说家的职责所在。小说的要义,在于发掘与揭示,也在于完善与葆有。
埃里希·奥尔巴赫曾探讨过《蒙田随笔集》中的一个名句:“我们最伟大最光荣的杰作就是生活得当。”实则,生活原本已不易,得当就更为难得,过犹不及,不及亦属冗余。无疑,双雪涛看到了这样的困难,但他又不甘于此,每每会在作品中试探自己的人物,甚至看着他们任性、放肆,或是为造化所弄,进入急流与暗夜,露出破绽,或进行奋争,直至有所验证。某种意义上,这也包含对作者自身的拓展与考验,幸运的是,他带来了下棋的父子、傅老师、李斐、安德烈和安娜等鲜活而独特的形象。
细节上,他从不马虎。《跛人》里写到去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天安门的意涵厚重而复杂,风筝的所指似乎明了却也未必,两者结合在一道则越发邃远而有意味。在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上,跛人现身,女孩消失,男孩折返,似乎一切未及展开,却又已然改变,在这里揭晓的仿佛是一个“抵达之谜”,一种不言自明而又各有期许的远方,一颗属于自我而又万众瞩目的飞翔的心。
进一步而言,因了人生的缺陷与不满足,在他的小说里,往往会应运而生某种引领性的东西,我视之为“内在的光源”,尽管有时它可能是以幽暗或谜的形式出现。《长眠》里是起因于一个诗友的死亡,一份情感的失落,偏偏是这些否定性的因素,使得主人公不计风险地前往那个塌陷中的镇子,并有所为;《大路》中奇异的女孩引领着一个问题少年,跨越时空去体会“活着到底值不值得”;《大师》里十年复十年,两个人念念不忘的是一盘棋,胜败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并愿意不断重新开始……
《摩西》的开端和展开均有板有眼,如何收束,是读者暗暗期待的,也非常挑战作者。对目前的结尾,人们有赞有弹。湖心,小舟,男女二人,曾经的玩伴,而今一为警察,一为嫌疑人。她说:“傅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如果一个人心里的念足够诚的话,海水就会在你面前分开,让出一条干路。让你走过去。不用海水,如果你能让这湖水分开,我就让你到我的船上来,跟你走。”他答道:“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然后,他把手伸进怀里,绕过自己的手枪,掏出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漂着,上面那层塑料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至此,小说戛然而止,静悄悄地完成了双重的发现,既是对真相的发现,也是对自我的发现——发现凶杀案真相之外另有真相,发现自我的已然与未明。在那一刻,历经世事的延宕错失与千回百转,警察庄树和嫌疑人李斐化作了彼此精神上的“摩西”。而那种指引,最终又离不开每个人自身的挣扎与领悟,这便是来之不易的“生活得当”。
在现实面前,在生活之中,我们的“多些”与“少些”,可能是注定的,无奈的,也可能成为营养、策励与成长,它们是那些在阳光与风到来之前被忽略的缝隙和山丘。
三
双雪涛的作品,我最后读到的是《翅鬼》,而这是他早初之作。封面标有“第一届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作品”,“《幻城》后再现绝美奇幻国度”。不止一名论者谈及,他由所谓的类型小说转入严肃文学创作。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作品并不很多,却题材多样,手法不拘,就故事的质地而言,《翅鬼》无疑是佳构,是写给那些一出生就有翅膀的人,以及那些心底可能生出翅膀的人,勇气与自由是他们的磨难与宿命。
“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这一开头,值得传诵。寥寥十数个字,全息了整部小说,故事的大门就此开了一条缝,一束强光打在地上,尘与人将开始闪烁、摇曳。关键是,后续的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故事接住了这股气。读罢掩卷,不禁想起米芾的话,“振迅天真,出于意外”。
至于雅与俗,纯文学与类型文学,在他那里,并不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或者说正是这些元素的并存,成就了他文字的独特。
他的作品,讲究趣味,“警惕寡淡和无聊”。或许还可以加上智性、逻辑性,当然是在较为宽阔的意义上而言。《摩西》即为典型,细细推究也许过于希求精巧与圆满,不无赘笔,然而无疑是一件珍品。
他思考的问题和一些意图,都在生活化的细节中得到了实现。就像广受称道的《大师》中的描写,“那时我十五岁,鸡巴周围的毛厚了”,单凭这两句,也许尚无从判断走向与优劣,但你无法否认其间的敏锐与直率。作者紧接着写道:“在学校也有了喜欢的女生,一个男孩子样的女生,头发短短的,屁股有点翘,笑起来嘴里好像咬着一线阳光。”能写出这么七荤八素的漂亮文字,想必内心是妖娆而彪悍的。因为他最懂得,一个懵懂的少年,拥有无尽的好奇心,一旦真的投入到棋局或是生活之中,必会有太多的领悟。
他向往那种简单与复杂,那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他干得不错。
他在纸上重塑家乡的艳粉街,刻画世态人情,有着结结实实的细节、承转,有着对不断折叠的时空的延展和追问。
他的很多小说,都有些像中国史书传统中的纪传体,当然,他所注目的是凡俗中的不凡不俗者,写奇与异,并不是最难,即便写素常之人,依然能充满活力和新意,这就叫手筋了。写出迅速变化的时代的生活质感,绝非易事。他冷眼看取而又哀矜,注目的不是那些“被公共化”的人生,而是自己所发现之种种,以有悬念的语言,带来有悬念的故事和心灵。
他的写作时间并不长,“迅速”便找到了自己的声调与路径。于此,我不想隐瞒自己的偏爱,也不想苛求。只是有几句话还想说一下:有时,作者先行的设定压住了人物自身生长的可能,形而下的功夫和形而上的思考可以更好地结合。在怪力乱神方面有不小的潜质,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释放。在长篇小说上的综合造诣,还没有中短篇那么得以彰显。另外,对这个世界,这个最好也最坏的时代,对于自己,还可以更加锋利。人生的局限,人性的光暗,期待着创作者去探勘,去邂逅,去“发明”。
编辑/张定浩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