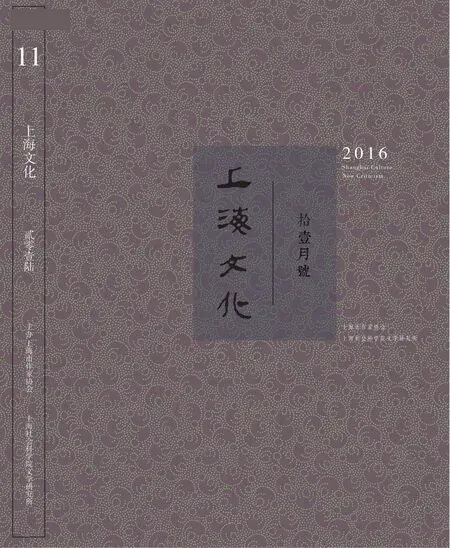伊丽莎白·毕肖普*
海伦·文德勒 叶 美 译
伊丽莎白·毕肖普*
海伦·文德勒 叶 美 译
毕肖普诗集《地理学Ⅲ》中的诗歌,其引人注目的品质是在家庭生活和陌生性之间持续地情感转换。换任何一位诗人,这种交替行为都会被看作是有争议的,但毕肖普能做到自然而然而非刻意区分,凝神注视而非故意取舍。所以尽管她的旅行诗歌总是带给我们异国情调之感,但其实陌生感并不是只依靠书写异国情调才能获得,同样要获得亲切感不必一定要写此时此地。(因为在她的诗歌中,熟悉的事物经常用房子、家庭、爱人、家来命名,所以对毕肖普而言,实际上她关心的是家庭生活而不是那些熟悉的事物。因为反常事件其实很容易发生在家庭生活内部,甚至会最令人不安地出现在客厅的壁炉旁边,所以同样可以说谈论陌生性比谈论异国情调更真实可信)。
为了展示其诗歌中家庭事物和陌生性完美结合时相互之间是如何渗透的,必须回溯诗集《旅行问题》中的一些诗作。《六节诗》中的构成元素几乎完全一目了然——房屋、祖母、奇迹小火炉、历书。但眼泪这一陌生元素最终使整个房屋显得怪异。尽管祖母藏起眼泪,只说了句:“该喝茶了”,孩子还是感觉到了她噙着的泪花,并将它们通感到各处——茶壶跳动的水珠,屋顶的雨,祖母的杯中茶。
……而孩子
正凝神茶壶上微小坚硬的泪珠
如屋顶滂沱的雨水
在炽热的黑色火炉上疯狂起舞。
……历书
在孩子和老祖母头上
悬停,半张着翅膀
她的茶杯溢满深棕色的泪水。
孩子对世界的感受只呈现在他的画作里:一栋线条僵硬的房子。(我说“她”,是从诗作里的亲属关系来推测,其实孩子的性别不确定)。孩子需要表达出她感受到的眼泪,所以她在画中“添上……一个人,胸前扣着纽扣,仿佛完美的泪珠” ,当“小月亮们从历书的书页间/泪珠似的,滑落到孩子/在屋前精心布置的花床中时。”
《六节诗》结尾的三行诗,聚集了这幅拼贴画的所有元素:
该种植眼泪了,历书说。
朝向神奇的火炉,祖母俯身歌唱
而孩子画下另一座隐秘的房屋。
孩子父母的缺席是这些眼泪心照不宣的原因,虽然表达含蓄却一目了然。因为祖母的所有言行,孩子的一直沉默,神奇小火炉勇敢的欢唱,房屋的冰冷难耐,和其冷清的氛围都无疑代表了孩子家庭生活经验中反常事件的存在——反常这个词,尤其对孩子有效。当诗中开始出现家庭住宅时,所有事情都不应该不可捉摸。而事实是家庭住宅经常令人不可捉摸,没有什么比发生在家庭生活内部更叫人费解的了,这给毕肖普提供了反复抒写的诗歌主题之一。
书写家庭生活使毕肖普的诗歌表达非常特别。当她明白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她也常常像孩子一样说话。《六节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诗中她以永恒的孩童式的口吻讲述了一则故事。不仅采用寓言式的措词,而且让人物关系保持固定,尤其是排列式的结尾,历书、祖母和孩子三者不变的身份犹如一副中世纪的绘画,其中历书代表支配一切的宿命,祖母代表了老派规则,孩子代表青年信仰。最后三行不动声色地记录了悲伤、歌唱、宿命、奇迹的同时存在,可是尽管它们的关系是并列且“地位平等”,但最终强调的却是不可捉摸的事物,即使发生在家庭生活内部,也会使这首诗成功地并入了陌生性的轨道。
诗集《旅行问题》中最后一首从另外的角度打破了平衡,最终朝向家庭生活。这首取名为《加油站》的诗歌一开始看起来毫无美感,至少在这位叙述的目击者眼里。加油站肮脏、浸满油渍、弥漫着油味;父亲一身脏西装;他的儿子们蓬头垢面;一切都看起来“肮脏透顶”;甚至有“一条黏糊糊的狗”。叙述者,虽然内心怀着“高雅人的恐惧”,但却不能从不断涌现的生活细节中移开视线,因为这里虽然是个加油站,却非常不可理喻地让人感受到家庭生活的乐趣。“他们住在加油站吗?”讲述者疑惑不解,竟然看见门廊处有“一套破烂,浸满/油渍的柳条家具”,狗“非常舒服地”躺在草席沙发上,连环漫画,铺坐垫的小凳和“一盆硕大的多毛秋海棠”。我们发现自己对这个最没有希望的地方产生了幻想,使人心怀对家庭生活的幸福憧憬,这憧憬是作为意义的证明,作为“爱”的证据而出现的。是否我们的宗教信仰只是我们安居乐业天性的一种表达?
这些毫无用处的植物
这些不合时宜小矮凳
哦,哦,上面还铺着坐垫
为什么,它们原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坐垫晒着某人的刺绣手艺。
某人浇灌后植物才繁茂,明亮
或粘上了油迹的缘故,也不是不可能
某人精心地摆放了金属罐
看起来整齐地一字排开
这样上面字母可以连着读出来
埃索-索-索-索
它们一直排到轰响的机动车那里
某人爱着我们大家。
从形而上学方面发出疑问并从神学方面来讨论,诗歌表达了尘世中人类“可怕但愉快的”行为之一就是要驯化周遭环境,即使是像加油站或是漆着“跳动玫瑰花蕾的”巴西卡车这样纯粹的工业机械之地。
家庭生活容易因为遭遇死亡而陷入危机。一般来说,家庭成员是亲密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文学中写家庭生活的精髓之作是《雪困》。当死亡入侵家庭内部,古老习俗规定尸体要先停放家中,此时死亡在强迫家庭成员屈服它蛮横的权威。史蒂文斯的《冰激凌皇帝》将家里冰冷、缄默的尸体与葬礼上烤肉行为荒诞地联系起来,可以说,当烤肉味香飘进厨房时,人们在死者面前大吃大喝的原始冲动被看作没有同情心,粗鲁和野蛮的,即使是在我们已“文明化了的”社会里。毕肖普《新斯科舍省的第一次死亡》,还是孩子的诗人对家中的会客厅里“小表亲阿瑟”棺材进行了一番联想:
寒冷,寒冷的会客厅
母亲摆放阿瑟
在胶版复印品下
那里有爱德华,威尔士王子,
亚力桑德拉公主
乔治国王和玛丽皇后。
再下面的桌子
站着一枚被阿瑟叔叔
即阿瑟的父亲
打中并制作成的潜鸟标本。
孩子无法追忆死亡的全部细节。但却对棺材记忆如新,熟悉的事物在她眼里都开始变形:潜鸟标本活了过来,他的沉默看起来是自愿的,它的红玻璃眼珠在观察:
自从阿瑟叔叔的一粒
子弹射中了它,
它不曾说一句话。
它保持自己的原则,没有谴责人类……
阿瑟的棺木犹如
沾满糖霜的小蛋糕,
被红眼睛的潜鸟从覆满积雪的
冰冻的湖面直直地盯视。
成人们串通一气,说与死者的交流仍旧可能,他们吩咐孩子说:“和小表亲阿瑟/说再见,”要求其将一束山谷百合送到死者手心。孩子参加了这场荒诞的表演,她先是想象会客厅的寒气使它成为杰克·弗罗斯特的领地,当他画“加拿大枫叶林”时也在画阿瑟的红头发,接下来想象胶版复印品中的“一对豪华的皇家情侣”已经“邀请了阿瑟作为/宫廷最小的侍卫。”阿瑟的死亡带来了会客厅中弥漫着压抑情绪,这导致孩子建造了由客厅、棺材、尸体、胶版复印品、潜鸟、霜人、枫叶林和百合组成的格式塔。孩子的压力过大,以至于怀疑和沮丧感控制不住地涌上心头——不是担心他最终的命运,哦不,孩子确信阿瑟变成了“宫廷最小的侍卫” ,那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半是宫殿,半是天堂的,人丁兴旺的大家族;相反,她的困惑是他怎么到达那里。
但阿瑟怎样才能抵达那里,
紧握一束小百合的他
眼睛闭得紧紧地
外面道路都深埋雪中?
家庭生活是脆弱的,它最终会被死亡带来的陌生感击溃。死亡来临之时,甚至即便在它发生之后,对陌生环境的驯化工作仍在继续,这一切都是超越家庭生活保证的替代,某些人坚信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母亲的房屋里,坚信“某人爱着我们大家”。在家庭生活以一种形式遭到打击后,用另一种形式重建它的努力就已经开始。毕肖普诗歌中对死亡的定义是将要放弃驯化世界,然而再次试图重建更多形式的亲密感,反之,对生命的定义就存在于从陌生化到亲密感,从未知到已知,从隔膜到钟爱的情感转化中。
任何家庭生活都不安全。生命的中途我们就可能遭遇死亡,所以在毕肖普的诗歌中,恰恰就是在熟悉的事物中间,我们感觉越熟悉的事物其实越神秘。这种隔膜带来的痛楚,就是《在会诊室》的主题,其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家庭生活内部。1918年,一个七岁孩子,一边在等待牙医诊室里的姑妈,一边读着《国家地理杂志》。场景平淡无奇:“全是成年人/御寒套鞋和长大衣,/灯光和杂志,”但两件事情使孩子焦躁不安,首先是杂志上的一幅画:“裸体黑女人们脖子上/成圈地缠上金属线/像灯泡卡口。/她们的胸令人惊恐。”第二个是嘴里突然发出“哎噢!疼痛的叫喊/—和姑妈康苏埃拉声音一样”。孩子头晕目眩,感觉自己的喊声是以“和其他家庭成员相似的声线”发出的,并马上意识到作为人类族群之一,她和她们相比的独特性和共性何在。
但我感觉:你是一个我,
你是其中的一个伊丽莎白,
你是她们中的一员。
为什么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呢?
我和她们多么相似——
皮靴,手臂,我感觉我有着
和其他家庭成员相似的声线,甚至
还和《国家地理杂志》上
那些吓人,松垮垮的乳房相似—
就是它们把我们连在一起
或昭示着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吗?
在《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这首诗里,惠特曼也谈及了一个相似的瞬间,也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疑惑:
……那种真实感,那种唯恐最后成为泡影的忧虑,
那些白天黑夜的怀疑,那些奇怪的猜测和设想,猜测那现象是否属实,
或者全是些斑点和闪光
那些大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他们不是些闪光和斑点又是什么?
这是惠特曼的风格,瞬间的迷失后他让自己沉浸在海洋和天空的自然世界。这也同样是毕肖普的风格,在候诊室滑向“黑色,汹涌的层层起伏的/波浪下方”之后,她也返回一成不变的清醒的现实,尽管这现实的选择被感觉所支配。
战争在继续,外面是
伍切斯特,马萨诸塞州,
是夜晚,是积雪和寒冷,
是1918年二月的
第五天。
孩子渴望在自己的世界里掌握最不熟悉的事物,渴望在候诊室中把《国家地理杂志》中的异域事物与身旁人们的膝盖、裤子和衬衫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法她把令人恐惧的陌生感和熟悉事物——她自己、姑姑和“家庭声音”共同编织在一起。最后,野蛮人会被驯化了吗?她自己会变成了不可知论者了吗?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压垮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她感到浑身瘫软。语言辜负了六岁的孩子。“啊——我说不出任何/话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轻描淡写其实每个字都铿锵有力,毕肖普在诗歌中常常这样做。事实是作为孩子的她,被意外事件所震惊,“熟悉”和“陌生”这两个概念已经丢失了所有意义。“安德森夫人的瑞典孩子,”史蒂文斯说,“也许也曾是个德国人或西班牙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的一首诗歌曾被毕肖普翻译成英文(他的三音步诗体可能影响了《在会诊室》):
Mundo mundo vasto mundo,
Se eu me chamasse Raimundo
Seria uma rima, nao seria uma solucao
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和宇宙的名字同韵,就像“Raimundo”与“mondo”同韵,这就会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出现一种和谐,并且把世界驯化成适合人类居住的行为好像就是可能的。但德拉蒙德说,它只是一个韵,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在会诊室》中的孩子发现她不理解这个世界,她太年轻了,不能用意志控制世界或是用爱驯化世界,她滑入了黑暗的深渊。
在《诗》这首诗中(“大约和旧版钞票一般大小”)诗人无心地盯视着他叔祖父创作的一副小画,并且开始了对世界驯化这个主题的另一番思考。她无心地盯视——也就是,直到她相信自己曾住在画中的风景的那一刻的到来:“天堂,我认出了这个地方,我知道它!”,在这首杰作中,“这个地方”被描写了三遍。第一遍的语言形象,精确、激昂、风趣:我们认为,这种描述是纯粹的视觉快乐,相对来说是客观叙述。(“这一定是新斯科舍;只有那/可以看见三角木房/漆着笨拙的棕色暗影”)。下面的诗句就是对风景的第一遍描述:
榆树林,低矮的山坡,一个细瘦的教堂尖塔
——那是一抹蓝灰色——会不是吗?前景中
一群细小的牛在水草上
每只牛刷刷两笔,但一定是牛;
两个微小的白鹅在蓝色的水里
背靠着背都在吃草,一个斜斜的枝条
上面站着一只野生鸢尾,浑身白色兼黄,
从颜料管中挤出来的颜色鲜亮的线条
空气新鲜,寒冷;那是早春的清冷
透明得像是块玻璃;半寸蓝天空
下面是青灰色的暴风云。
然后叙述被相认中断——“天堂,我知道它!”,随之而来的是双重的变形:思绪冲出了画框,把画中的场景抛入一个背景久远的、记忆中的乡村风景,并且以一个本地人的口吻说出画中的件件事物的名字。
天堂!我认出这里,我知道它。
这是后面——我几乎记起了农场的名字。
谷仓位于草地后方。就在那里
轻轻一抹的钛白色。塔尖的阴影处,
那里画笔轻柔,人眼几乎看不见的地方
一定是长老会教堂。
那是格莱斯皮夫人的房子吗?
那些特别的鹅和牛
都在我的时间之前大方地生活着。
虽然主体和绘画之间存在着联系,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当做一幅画,被认出其价值的人所描述——这里钛白色轻轻一抹,那里精心地寥寥几笔。并且场景一直向后移动——那些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鹅和牛。但是在诗歌结尾时诗人将自己和画家联系起来。他们俩都爱上了地球上这个微不足道的一角;它曾在他们的生活中存在过,在他们的记忆和艺术中存在过。
艺术“模仿生活”并且艺术就是生活
生活和对生活的记忆被压缩得多么厉害
他们彼此相互侵占融合,难以区分?
生活和对生活的记忆已经渐行渐远
朦胧,在一块布里斯托尔画板上
朦胧,但多么生动,细节多么打动人心
——我们拥有的自由越小,
我们对尘世的信赖越少。不会多。
在遥远的世界某处,有一小块土地曾被居住,被驯养、被记忆、被想象、被纪念,甚至因此而永垂不朽。称永垂不朽是因为在第三遍描述这幅画时,不仅仅是用眼睛来观察——不管是用鉴赏家的眼睛或是用怀念往昔的当地居住者的眼睛——而是被心灵所照见,因曾经在其中生活过而有所触动。不再有任何提及画笔,笔刷或颜料或优质木板的文字;我们身心已经完全融进场景中。
……不会多。
说到我们和他们共同
生活场景:嚼草的奶牛
挺拔,颤抖的鸢尾花,河水
依旧因春天的融雪而轰响,
尚未砍伐的榆树,还有那些鹅。
尽管在场景中,件件事物给人的深刻印象部分是因为用了现在分词,(嚼草的奶牛、颤栗的鸢尾花、轰响的河水),同时也因为对前面章节的名字的反复重提(奶牛、鸢尾花),现在去除了“染料的”修饰,(“每只牛刷刷两笔”,“从颜料管挤出”),从前面两次重复的“融雪后暴涨”的“河水”,尤其是从“尚未砍伐的榆树”的预言中。最不可能的是,“尚未砍伐”这个词那时拒绝在记忆的场景中让身心全部投入其中。这个既是孩子也是诗人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为一幕剧草草准备的舞台布景——戏剧演出一旦结束,背景就会被拆除,幻觉也跟着消失。这首诗已经把读者带入了我们称之驯化的过程,首先通过对奇特的地形的相认,然后对熟悉事物的相认,再后来情感由陌生变成钟爱,最后把读者从已陷入的亲密感中解放出来。驯化随之而来,几乎不可避免,那些已被摧毁的事物,严格地说是灾难,这是《一种艺术》中的主题:
母亲的表不见了,我弄丢了它。还有,瞧!我拥有的
三栋爱宅中的最后一栋,或倒数第二栋也不见了……
两座美丽,可爱的城市,我也弄丢了。还有许许多多
我曾拥有的其他领地,比如两条河流,一个大陆……
并不难掌握
尽管它看起来(写下它!)像是灾难,
那是一种对抗灾难的腔调,带着无所畏惧的反讽。
针对驯化和丧失的整个循环过程,更直接的叙述可以参见《克鲁索在英格兰》这首长篇独白诗歌。克鲁索安全地返回到英格兰,他的自传体回忆录非常详细地揭露了,只要爱是缺失的,对自然的驯化就不会完美,也揭示了独自一人在殖民过程中的艰难过程。
……我已经做了
有关其他岛屿的噩梦
那些和我的岛屿相连的,数量
多得数不清的,连成一片的岛屿,
好像青蛙的卵变成岛屿的
蝌蚪,意识到我不得不
一个个在上面住下来,直到
最终标记出它们的植物群落
动物群落,和地貌。
克鲁索在对自然的驯化过程中(制作长笛,蒸馏家酿啤酒,甚至从红浆果里提炼染料)产生了快乐的情绪(我感觉我深深爱上了/岛屿上各种小小的工业),但除了海龟,山羊和海龙卷的陪伴,社交生活的缺失导致他产生自我怜悯的心里和渴望被承认的希望的落空。陷入哲学思考的克鲁索给一个火山命名为“绝望之峰”,既表达了他的忧伤,也表达了他的期望。岛屿的风景已经被驯化所改变,都是“人工改造过的”,但只有星期五到来后,驯化才真正转向家庭生活:“仅仅当我想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哪怕再多一分钟的时间,这时星期五来了。”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欣喜之情的克鲁索只说出索然无味,因此也是最深刻的话。
星期五是漂亮的。
星期五是漂亮的,我们是朋友。
……他有一个漂亮的身体。
爱逃避语言。克鲁索以地理学家的精确眼光详细描述了火山、海龟、云、熔岩、海龙卷和海浪的面貌,但家庭生活实现前,他只会打手势和做些简单的描述。
最后,毕肖普在概括性的叙述中,先是重申在对宇宙的驯化中,人类的生活才有意义,之后思考了一旦驯化领地丢失,意义也会随之丧失。
那里架子上放着刀——
它弥漫着意义,像一尊耶稣受难像
它在继续存在……
凭记忆我知道每一个裂口和刮痕……
现在它不再看着我。
鲜活的灵魂已经枯萎。
我的眼睛停留在上面,然后又移开。
和驻足在存在和使用中的驯化的意义不一样,家庭生活的意义是神秘且永恒的。结尾的独白说:
本地的博物馆征求我
将一切留给他们:
长笛、刀、干瘪的鞋……
有人怎么会想要这些东西?
——而星期五,我亲爱的星期五,死于麻疹
十七年前正值三月到来之际。
驯化最终朝向的目的是心灵,它一旦生根发芽,就会永远保持自己“鲜活的灵魂”。
对家庭生活永恒的和坚不可摧的忠诚,甚至没有受到死亡的影响,是毕肖普把诗歌意象转向主题时,力争要达到的行为。但我认为在《麋鹿》这首诗中,对生命经验的讲述更为深刻,这首诗没有提及人类持久的排斥感,而是依次展示了一系列深刻的,莫名其妙的满足感,每一种都弥足珍贵。这首诗中,土地的驯化是一层意思,家庭生活的美好是另一层,非人类世界崇高性的存在是第三层意思。
诗歌的前半部分,描述了世界地形中一个美丽无比的地方,即朴素又奢华。新斯科舍的潮汐、日落、村庄、雾、植物群、动物群和人们安静地布置在这首诗中,好像为了一次最后的告别,当讲述者旅行结束前往波士顿时。这首诗,像一幅乡村风景画, “有点过时的”样子。
巴士开动。光线
逐渐加深;雾
暗中浮动,咸味,稀薄地
靠拢过来。
它的冰冷,球形水晶体
凝结,滑落又栖息
在白母鸡的羽毛里,
在灰色光滑的卷心菜
在西洋玫瑰
和十二使徒的羽扇豆上;
甜豌豆紧挨着
湿的白绳子
白涂料的栅栏上;
熊蜂安静地爬行
在毛地黄里面。
夜晚正式来临。
精美的,惹人注目的,对白色的吟咏,悬垂、停落、接近、爬行的夜晚合唱曲,每个分句都妙笔生花,全部是告别的氛围,对母鸡、甜豌豆、雄蜂的瞬间相认全都在言说着温柔,渴望的灵魂,通过这种方式,风景被清晰地描绘了出来。
当黑暗降临,醒着的灵魂慢慢被诱惑进“一次梦幻的流浪/…/一个温柔的,听觉的,迟钝的幻觉。”中间部分的章节体现了向童年的回归,当讲述者想象巴士里压低的声音,说着“陈年旧事”。
祖父母的声音
不间断地
谈着话,漫长的时刻:
一些名字被提及
事情终于被澄清
以他们独有的方式说着话
在羽绒坐垫中
安详地,持续着……
现在,现在一切都好
刚好睡觉
就像所有的夜晚一样。
生命,在这首诗所描绘的世界中,目前只包含两种元素:钟爱的风景和钟爱的人,他们都已经被驯化过了,并且这些人都过着家庭生活。祖父母在聊着村庄的人情世故:
他说,她说
某人拿到了退休金;
死亡,死亡和疾病,
这年他重新结婚,
这年(一些事)发生,
她在分娩那天死去。
那个儿子已丢失
当纵帆船被发现时。
是的,他酗酒
他越来越糟,
当阿莫斯甚至在商店
也开始祈祷,但
最终家人不得不
把他送进疯人院。
“一点不假……”那个特殊的
肯定词,“一点不假……”
突然,倒吸一口气,
带着叹息,和认命的样子。
这一节,乡村谈话别具一格,它带来的悲伤也和前面描述性的唯美风格不同,毕肖普把自己和《抒情歌谣集》的华兹华斯连在一起。一瞬间,家庭情感就是一切。阿莫斯疯了,儿子葬身大海,母亲去世,女孩变得越来越坏——这些都在《迈克尔》和《荆棘》中有所描述。一连串名字唤起的是强烈的家庭纽带,它们变成了诗歌的一种形式,而新斯科舍的“草地、山峦、白桦树”的风景则是另一种形式。我们知道,周围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们也知道“生命就是如此”(就像叹息声“是的”所暗示的那样)。这首诗看起来结束了,但就在讲述者下意识地准备打瞌睡,发生了意外,月光下巴士停了下来。一只麋鹿在乘客中间产生惊奇的感觉,它“高如一座教堂/普通得如一只马,”乘客们“嘀咕着惊叫/天真,温柔地。”麋鹿迟迟没有离开。
她磨蹭着时间
查看巴士,
庄重地,超脱尘世的样子。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感觉了
(人人都如此)这种甜蜜的
快乐的激动?
这种快乐是什么?
《大多数》中,弗罗斯特使用了这个寓言的变体。与毕肖普的诗一样,有一个造物被看见从“密不透风的森林”走了出来。但弗罗斯特的野兽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诗人所祈求的是“对应的爱,最初的反应”,但“坠落的化身”证明那不是“人类”,也不是“附加在他身上的某人”,而是一个巨大的雄鹿,一出现就消失了。弗罗斯特的造物是男性的,毕肖普是女性的;弗罗斯特是粗暴之力的代表,毕肖普是“安全如一匹马般”的造物”;弗罗斯特的是一次挑战,毕肖普是一个保险安慰。在这两首诗歌中,从森林中走出并渐渐接近的造物,都扮演的是在前华兹华斯时代上帝扮演的那个角色,而在华兹华斯那里这个角色是人类扮演的——一个寄生的人,一个古老战士,一个乞丐。这些人类存在物,当它们出现在华兹华斯诗歌中时,部分符号化的,部分非人类的,就像寄生的人部分是雕像,部分是海兽,并且就像《肉体的宁静和腐烂》的老人是“不知不觉陷入”一种平静状态,它更像是动物所具有的而不是人类的属性。惠特曼说:“我认为我可以改变并与动物同住。”预示了一种现代性,也就是在寻找人类替代物时,不是从神那里,而是从动物中。动物的生命是一种纯粹的存在,有着它们自己的宏伟端庄,它向诗人保证了存在的无穷无尽。毕肖普的麋鹿同时是母性的,神秘的,温顺的。如果巴士的乘坐者,在他们人类的工具中,注定活在乡村世界里灾难和疼痛的知识里,在瞥见某个高贵的庞然大物,即使是一个模糊的,荒诞不经的一个,他们就会感觉轻松的快乐,这个怪物存在于他们的叙述和叹息之外,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当巴士开动,“黑暗再次降临”时,“模糊的麋鹿气息”只留下“酸酸的汽油味”中。
《麋鹿》是一首纯粹的直线性诗歌,伴随着巴士旅行的开始,我们被要求全神贯注于整个旅程。每一个依次出现的事物转瞬即逝——我们先见到乡村风景,然后是人群,最后是麋鹿。但这种想要整体地讲述——感觉这首诗完全是深思熟虑出来的——寓言地表达,都显示着事物的排列井然有序,而不是任意为之。这首诗从成人眼中熟悉的乡村风景开始,然后是在童年时瞥见的没完没了的礼节,再到对人类悲伤的叙述,最后到另一个世界的快乐存在,它从密不透风的森林中走出来,允许自己被注视。那种熟悉东西的背后,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人们所熟悉的事物,都存在于陌生性和神秘性之中。正是这种神秘性引起那些嘀嘀咕咕的交谈,间或夹杂着被人类的兴衰沉浮所激起疼痛的叹息声“是的”。它保证了诗人可以大有作为。它依靠的恰恰全部是对驯化的冲动。尽管人类的努力是朝向对荒野的消除,但知道地球上的存在物比我们人类的已知范围还要大,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了。伊丽莎白·毕肖普的那些关于驯化和家庭生活的诗歌,在最后的分析中,依靠的恰如其分的对神秘替补物的阐释,它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赋予一种快乐,它比人类创造的熟悉世界的福祉陌生得多。
编辑/张定浩
* 本文“Elizabeth Bishop”,原名Domestication,Domesticity,andtheOtherworldly(《驯化,家庭,超脱的尘世》),译自Helen Vendler,Parf of Nature, Part of us:Modern Amerian Poe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97-110. first appeared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Winter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