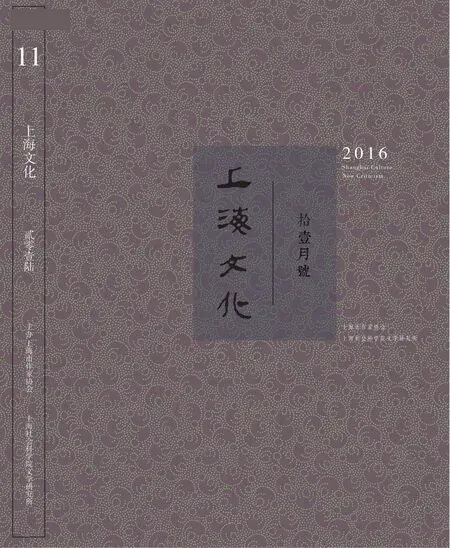浮生若梦,小说如歌读东君小说
汪广松
浮生若梦,小说如歌读东君小说
汪广松
一
东君小说林林总总,看似纷纭散漫,要而言之则不出三记,这便是他的长篇小说《浮世三记》的内容:《解结记》、《述异记》和《出尘记》。《解结记》祖述“阿爷”,《述异记》记述“阿婆”,《出尘记》则宪章“外公”和“舅舅”。这三记既是人生血脉的来路,又可以用来建构小说脉络:“解结记”,“解”与“结”音韵相同,都是一口气,只是调子不同,一仄一平,一解一结;“述异记”是这口气的变化,“出尘记”则点明气的归处,三记形成东君小说的总体气象。
三记不仅仅是总体,也构成东君单篇小说的内在理路:解结——述异——出尘,它们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又寄寓了作家的情感与思想。小说《长生》开篇就写“我”是个闲人,工作单位不大不小,换岗后生活单调,不料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慢慢出现,于是他就开始徒步上班,是为“解结”。接着他遇到了长生,又通过长生带出了胡老爷的家族史,这一部分是小说主体,与“我”并无直接关系,可称“述异”。最后,小说又把“我”带回河边晒太阳,顺着河流慢慢前行,在下午的散漫中想着看戏,吃鱼丸面,长生及其故事譬如浮生一梦,而从梦中醒来则是“出尘”。
三记也可以说是一记,即“解结记”,它们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某年某月某先生》有位东先生,他在不惑之年困惑起来了。这些困惑有思想方面的,比如最近出的一些事情让他无法解释,但从小说来看,主要是身体性的,而且他想女人,可是与他交往的三位女性突然间都消失了。于是东先生就住到了南方的一座山上去,把手机埋在地里。他的“出尘”能够解开他的结吗?与《长生》不同的是,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与东先生有关,不像《长生》是借别人的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东先生在山里有一场 “艳遇”,但这场艳遇实在不像艳遇,倒像两个人在清谈,从中又引出了女子的另一段“艳遇”。当东先生吹着风,想抚摸她头发的时候,她又消失了,一场“异遇”就此结束。东先生对自己说:“到任何一个地方,生留恋之心都不是一件好事。不为什么而来,也不为什么而离开。这样子就行了。”他挖出了埋藏起来的手机,开机发现先前的三个女人居然同时发给他内容相似的短信,不过,他只是静默了片刻,就把手机关掉,彻底埋葬。这似乎可以说东先生解了他的结,只不过是以“出尘”之思来实现的,在小说里,解结、述异、出尘,最后都指向“解结。”
人生百态,各种心结,是否可以解开?小说《解结记》写阿爷死后,一个道士来唱“解结歌”,这种歌“是为死者解除一切世上的冤孽和怨恨”,仿佛一了真的可以百了;而“我”与小伙伴们的仇怨也在最后得到了和解。这种“解结”情怀以各种面目出现在东君小说里,就连《苏蕙园先生年谱》这类不以“解结”为主要情节的小说,作家也不忘在小说结尾安排弥留之际的苏蕙园与同父异母的妹妹相见,譬如唱一首“解结歌”。《阿拙仙传》中,一位日本老兵晚年来华忏悔,他的忏悔书也算是一首“解结歌”吧?进而言之,那位苏蕙园先生的年谱,还有阿拙仙的传记,也都不妨看作是传主一生“心结”及其“解结”的过程。小说集《东瓯小史》里的人物大抵如是,只不过“结”到什么程度,“解”到什么程度,小说各有不同。
有些时候,“解结”作为一种技巧在小说中得到应用。《范老师,还带我们去看火车吗?》(下文简称《范老师》)开篇就写道:“林大溪的女人死在林小溪的床上,林小溪死在林大溪的女人的身上。”然后小说就围绕这句话来展开,一步步揭开真相。《在肉上》小说主人公林晨夕醉酒后被人“强奸”,她要找出真相,解开心结。《回煞》开篇就设置一个悬念:禅房里的一位法师情不自禁地念出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让读者很容易产生“解结”的阅读动力。
不过东君小说对于“解结”不求甚解,有时候是一边解一边结,解了再结,结了再解,甚或不了了之。小说《左手·右手》写得很短,却正因为短显得简洁有力,恰成“解结记”之核心原型。小说写东瓯有一个怪人,左右手互为仇敌,左手常常趁右手不备陷害右手,如抠其皮肉,或者放在火上烤。怪人无奈,请问看相先生,说是左右手前世已结夙仇,若要解结,应去请教高僧。高僧让怪人每日听他说法,以图化解。怪人每次绑着左手听经,有一日高僧让他松绑,未料左手一获自由就突然发狂,掐死了高僧。怪人只好用右手举刀,砍掉左手,自此消了恶念,出家为僧。但是,右手还常常伸到空荡荡的左袖中摸索,似有愧意。
小说开篇附会了左右手的善恶之别,左手为恶,右手为善,这是第一重结,可当先天;其二即是双手的前世今生多有结怨,可当后天。结有两重,解是三解,看相是第一解,高僧深入一层进入心地,虽然都不能解,但次第似不可免。最后是自解,方向正确,但方法有误,
右手断左手,好像是解了,一了百了;但意犹未尽(也不可能尽),不是简单的除恶为善,何况还欠高僧一条命,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东君小说里的“解结记”往往如此,若已解,若未解,若已结,若未结。小说里的各类人物、事件大都有因有果,却也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回煞》里的僧俗二途、《相忘书》中的父子恩怨、《拳师之死》的情与仇等等,因果互倒,解与结层层相因,若有解,若无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君小说及其写作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小说家本人的一个“解结记”,它包含了解结、述异和出尘。写作是一抒胸臆,作品内容是述异,成果则是一种不同程度的对自身和时代的“超越”,可当“出尘”之思。因为三记,他的小说具有某种力量。他在《浮世三记》的“序”里说道:“我相信文字的水滴可以穿透石头般坚硬的现实,深入人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点温润。就是为了这一点信念,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慢慢打磨我的作品。”这一点信念其实很强大,那“一点点温润”也相当了不起,它们赋予东君小说一种难能可贵的“认真”的品质,只是,短篇小说是否具有水滴石穿般的能量?人生与作品是否能够在时间的长河中同生共长?这一点信念或者也构成一种“心结”吧?
二
东君小说的风景几乎全在路上,在“述异”。故事情节有时候是不重要的,一些边边角角、枝枝叉叉的地方反而更有趣味。少数时候,通篇小说反倒不如某些段落、某些句子来得有趣。《先生与小姐》结尾写道:“这屋檐上的瓦片、屋后的竹叶,都是世间的无情之物,但被夜雨打过之后,就变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了。”就像这篇小说里写到的“笑贫不笑娼”,故事本身并不稀奇,可是经过“夜雨打过”(即小说家的渲染)之后,就有些声情并茂的意思了。这里的“夜雨打过”正是一篇“述异记”,而且小说里关于“雨”的描写格外动人。
《述异记》中的阿婆,被人们视为“仙姑”,其行事也无非是说魂道鬼。这类小说在东君作品中为数不少,不妨通称为“述异小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笔记小说的传统,不过东君的“述异小说”并不以鬼神为主角,而是人在那里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又或者痴人说梦,颠三倒四。小说《恍兮惚兮》的核心故事是:一个女人死了男人,她以为男人的灵魂附在另一个男人身上,这另一个男人就以此行骗。小说写得恍兮惚兮,如梦似幻,倒也符合“述异小说”的总体氛围。长篇小说《树巢》,从《序言》看立意很好,欲借家族叙事反思传统文化,可是开篇就写马老爷的吃与拉,接下来写女人竞斗“小脚”,还要请评委来“相脚”,然后就是大傻、大力士、怪兽、神灵、上帝、仙姑等等粉墨登场,《序言》里的一点好意思几乎全部淹没在一群愚痴当中,令人惊异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世界!
对于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这类荒诞感并不陌生,看到东君小说《夜宴杂谈》写人们在苦等顾先生,而顾先生始终不出现,会自然地想起《等待戈多》里的那一幕吧?《鼻子考》“考证”鼻子与性欲的关系,小说主人公一个喷嚏就破坏了一桩“好事”,令人嘀笑皆非。《昆虫记》中的“我”以跳蚤之眼看世界,看到一个奇怪的世界,仿佛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壳虫再次变形,跑到东君小说中去历险。《鼻子考》与《昆虫记》是东君早期小说,虽然近期小说有意向中国古典传统回归,但这种荒诞感仍然以新的面目延续了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东君“述异小说”里的荒诞感并不具有“西西弗斯神话”式气质,但也不完全是“仙姑式”的装神弄鬼,它的特征可以用东君小说里的语言来讲,就是“实事求是地撒谎”。在小说里,这是“苏教授”的特征。东君小说有好几篇都写到“苏教授”, 如《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苏教授的腰》、《我能跟你谈谈吗?》等,虽然不是同一篇小说,但其中的“苏教授”不妨看作同一个人,他辗转于人生各个战场,面对情场失意、子女不肖、生死考验,表现出各类人格,但都有这种“实事求是地撒谎”的风格,一本正经地说一些“不正经”的话,一本正经地干一些无聊之事。在《夜宴杂谈》中,一批高人雅士非常严肃、非常学术性地讨论《崔莺莺别传》的版本问题,宴会结束,苏教授“蹲”在一扇屏风后面,“默默地做着提肛肌收缩运动”,这个动作无意中赋予了小说的某种荒诞气息,深于他的一切语言和论文。
东君“述异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记述“异人”,像《侠隐记》中怀有“绝艺”的民间“高人”,如“剑圣”、“盗圣”等,又或者是《异人小传》中性格、行事迥异于人的平民、官员、手艺人等,这类“述异记”一般篇幅不长,却足见东君的小说家才能,《异人小传》里的短篇甚至可以说是东君最好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位“寂寞”的理发师,自己给自己理发,剃了头发,揭开头皮,又把手伸进脑浆,取出一块腐烂的肉核,然后又把脑浆放回去,缝上头皮,粘上头发。这个过程写得不动声色,却读来令人屏住呼吸。小说最后还要搭上一笔,写理发师接近“透明的虚无”,冬日里晒太阳的时候,脑海里“再也没有旧日恋人的影子了”。如此解结、述异和出尘,确有几分水滴石穿之感。
“述异记”有时候成为“变异记”,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说写作的需要,情节发展一变再变。《范老师》的开篇写一个凶杀事件,后来当事人林大溪出来指证人们看到的并不是真相,但警察不相信,认为林大溪被吓出了毛病,但小说并没有接着往下写,一变变成范老师杀人。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几乎个个都不可理喻,然而这对于小说来说却非常方便趁手,因为每到不合常理之处,只要一“变异”,小说就可以接下去了,而读者往往并不深究。
“变异记”的另一个方面是人物性情的变异,小说人物一旦经历重大事件的变故,性情立刻大变,这个变往往是向“异”的方向变,或者说是向“不好”的方面变。《出尘记》中的“舅舅”得知“外公”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当即离家出走,混迹街头,最后死于非命。苏教授发现妻子又回到她的老情人(也是他的老对手)那里,几近崩溃。更有甚者,《在肉上》的冯国平一直郁郁不得志,遂成变态人格。“变异记”中也有“正变”,即是从不正常变成正常,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变“异”为“不异”,相当于“拨乱反正”。这往往发生在生死时刻,譬如苏教授在遭遇绝症时思考生与死,荒诞之中亦有几分庄严和平实。
“述异记”中还有一些“异人”,如慧业文人苏蕙园、琴者洪素手、僧人左耳等,他们的“异”恰恰是“正”,只是因为异于流俗而显得卓然不群,因为不肯同流合污而显得超然尘外,因此,“述异记”也不妨是“出尘记”。
三
如果东君小说只有“解结记”和“述异记”,那还不算秀出,东君小说的卓异在于“出尘记”,有了“出尘记”,三记才有了成为一座小说“大厦”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出尘”并非指出离红尘,而毋宁说是走出人生之迷潭。倘若浮生如梦,则小说如歌,写作是一种向上、振拔的努力。
小说《出尘记》写的是“外公”和“舅舅”之死,题目中的“出尘”完全可以当作死亡的另一个说法,但也并非仅仅如此,“外公”竹庵先生确有“仙气”。他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喝酒能喝出茶趣;住在竹庵里,种竹是为了能听到风吹竹叶的声音;他在天井里安置水缸,是为了映照天心的月亮;养鹤,是养一种在野的心气;种花,种的是善念等等,这些风雅之姿确有几分“出尘”气象。
不唯《出尘记》,东君的多数小说都有一种超然物外的闲情逸致,小说里的“我”是个“最不紧要之人”,当然也就做一些“最不紧要之事”。他往往是个旁观者,对现世若即若离,在介入一段红尘后,末尾总能抽身而出。《他是何人我是谁》中的“我”与两位诗人一同到了拉萨,到了拉萨或相当于一次“出尘”吧?小说的核心故事发生在两位诗人之间,“我”是个旁观者;故事里的人往往梦醒不分,或者说处在“梦醒两界”,而关键又在于“梦”。“我”最终是辞职了,跑到拉萨“郊外”的一个村庄,“在陌生人中游荡”,真是“出尘”之至。这种感觉,可用小说里的话说,“我们紧紧地拥抱了一下,迅速分开,彼此间也没留下一点余温”。这里的“我们”固然是指人与人,也可以引申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吧?
“出尘记”的总体气质,用东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飘然思不群”,它是小说家暗暗向往的精神状态:“思”寓于“群”,而又能飘然而出。“飘然思不群”是东君小说至为可贵的精神品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出尘记”偏向“不群”,未能安然地回到人群当中。小说《听洪素手弹琴》写得通体风雅,琴者洪素手品格高洁,颇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意味,但她不群是不群了,却未能“寓于群”,这使得小说有一种孤高、清绝、悲情,弱化了小说力量,洪素手雅人深致,反不如竹庵先生的几分迂阔来得活泼。《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写的是东君小说中常见的僧与俗,然而,高僧不见得高,俗人其实还是俗,世间与出世间含含糊糊,不辨僧俗,何况子虚与乌有。因此,“出尘记”或者成为“困尘记”,又回到“解结记”中,要脱困而出,必须另寻出路。
东君小说有格局,有意境,有向上振拔之路,小说才能亦好,但他的小说似乎欠缺一种把人心拔亮的东西,一旦有了这光明,即在尘泥中也是出尘,而这恰恰是“出尘记”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
我们读东君小说,往往欣赏其淡然悠远的意境,仿佛窗明几净,月色如水,有一种阴柔的美。实际上,东君小说的“暴力感”充足,有一种杀心凛然刚烈,虽说不是杀气腾腾,但按捺不住一口无明之火。《在肉上》罕见地写了一个性变态,小说写得不动声色,可是冯国平的“性暴力”呼之欲出,而林晨夕一刀捅死“性侵者”(实际上是她丈夫),若有快感。东君小说不少地方写到用刀杀人,好像很痛快,有些场面可称血腥,多数小说则写得“如一抹淡远的秋山”,暴力掩盖在那些“旧而静”的行文风格里,“冲淡”得闻不见血腥味,只是偶尔一露峥嵘。或者与之相应,东君小说常常写到“死亡”,一个人莫名其妙就死掉了。但这些死亡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就不一定,洪素手的丈夫就没必要死,《梦是怎么来的》中的王大木也是活着才好。
东君小说大约受到明清世情小说的影响,在写到女性时,很多地方不用名字,直接用“妇人”、“女人”来指代,女性面目模糊不清,有些时候就流露出几分“狎呢”姿态。小说《范老师》中,林大溪前去戏弄阿兴的女人,他把女人抱到床上之后,塞给她一块巧克力咬着,不让出声,“女人咬了半边,另外半边攥在手里,悄悄地递给趴在眠床底下的奀三”。这种“风格”在东君小说中并不是主流,但也不少见。这些闲笔大约是写得手滑,还有些手笔则可能是为了小说写得好看,一味求变,最后只能用“怪异”来弥补故事能量的不足,它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来的姿态、气味,给东君小说总体上的明净添了一层阴影。
另一层阴影或者来自小说的用典与讨论。我们不能把小说写成思想论文,但正如东君自己所说,好的文字背后必须有“独立思想、个体经验、生命能量”。可是如果小说家的思想并未澄清,经验、能量不足就用知识、怪异来凑,讨论往往容易流于皮相,那对小说反而是一种损害。
要见万物之明,需要将力量一点点地收进去,收藏至至密之时,也许是光明大放之日。《震·大象》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令人恐惧的东西不是别的,或者就是埋藏在人心中的“洪荒之力”;“以恐惧修省”者,不是要去释放、夸大或者变异,而毋宁是戒而慎之,密而藏之,澄而清之,纯而又纯。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