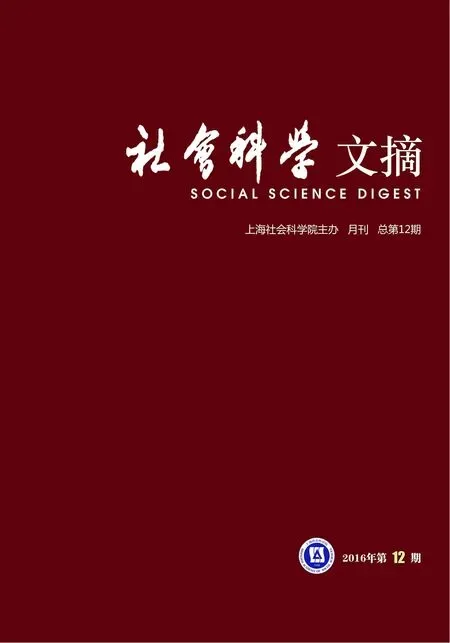如何认识“跨境民族”
文/马戎
如何认识“跨境民族”
文/马戎
“跨境民族”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杂志和报刊上出现“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国民族”)的提法。1988年申旭、刘稚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出版后,以“跨境民族”为主题的著作陆续问世,如金春子、王建民编著的《中国跨界民族》(1994)、马曼丽主编的《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1995)、赵廷光的《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1998a)和《云南跨境民族研究》(1998b)、周建新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2002)和《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2008)。与此同时,正式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和文集逐年增加。
一些研究者认为“我国的跨国民族研究,应该说是伴随着冷战后频繁的国际地缘冲突,于20世纪末叶兴起的一个民族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近年来,跨国民族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认为可以发挥这些居住在国境两侧“跨境民族”成员在“民族认同”方面的优势,提升边境省区对境外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发展跨境贸易和劳务输出,振兴我国边境省区经济。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约有30个跨国民族,总人口为6600多万人”。在百度文库中有个“中国的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词条,按语族-语系框架详细介绍我国各“跨境民族”及境内外相关“民族”的名称及基本情况。这些研究的重大缺憾,就是忽视“跨境民族”本身即是一个仍然需要深入分析和论证的核心概念,忽视了这个概念是一个涉及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边界和国家认同的敏感话题。
“跨境民族”这一概念的基础是“民族”概念
顾名思义,“跨境民族”这个概念表示某个“民族”的成员分别居住在国际承认的国境线两侧,居住地“跨越”国境线。在现代国家的国境线两侧生活着祖先血缘有一定渊源,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相同或相近的群体,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为战争或外交争端在两国划定边境时没有依照当地传统群体的自然居住边界,把同一个部落、同一个族群的成员划在边界两边。边界划定后,由于政治、宗教、经济等原因,一个族群部分成员迁移并定居在临近国家境内,其中有些人获得迁入国国籍,有些保持原国籍。
这些跨境居住但共享祖先血缘、语言文化特征的群体,是否应当被称为“跨境民族”?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nation)吗?如果我们把汉文“民族”译成英文“nation”,“跨境民族”是否应译成“a cross border nation”或“a nation crossing border”?
“民族”(nation)概念在西方的出现与其初始涵义
无论是中国历史文献还是欧洲近代之前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汉文的“民族”和英文中的“nation”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指出:“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霍布斯鲍姆认为,“‘国家’‘民族’及‘语言’等词汇的现代意义,要到1884年后才告出现。……1884年之前,‘nation’(民族)的意思是指‘聚居在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境内的人群’;有时也意指‘外国人’。不过,到了1884年,民族则意谓‘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或‘该国所辖的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民族’意谓‘统辖于同一政府之下、一国人民的集称’”。
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
“民族”概念从西方国家向其他地区传播后产生的变异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近代西欧出现一个“公民的‘民族’模式”(a civic mode1 of the nation),其核心要素为:(1)历史形成的领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体(宪法指导下的民法、刑法体系),(3)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所有国民都是权利平等的公民),(4)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拥护共和政体)。西欧陆续建成一批新型“民族国家”后,科技、工业和军力迅速加强,开始在亚非拉地区进行军事侵略,刺激了亚非拉地区社会政治精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潮,催生这些地区的新型国家建构,在亚洲和东欧地区出现一个由外力催生的“族群的‘民族’模式”(an ethnic mode1 of the nation)。这个模式有3个要素:(1)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2)在情感上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效果;(3)对本土文化(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换言之,在西欧的“公民的‘民族’模式”中,人们的核心认同是对新政治理念(反对世袭等级制度,争取公民自由与民主)和新政体性质(反对封建王权,建立共和国)的认同;而在东欧亚洲的“族群的‘民族’模式”中,人们保持了对祖先血缘、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传统认同观念。
东欧和亚洲国家缺乏现代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它们的“民族”模式只是在组织形式和话语方面对西欧政体的模仿。像中国这样被动接受西欧“民族”概念同时保留强烈传统认同意识的国家,很容易把有强烈政治意涵的“民族”(nation)和体现血缘与文化传统的群体(在西方国家被称为“族群”)(ethnic group)混为一谈,把国内的这些“族群”(ethnic group)也想象为“民族”(nation),并把它们称作“××民族”。
“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产生及其与“民族”的区别
现代国家通常会包括在祖先血缘和语言文化方面存在差异的不同群体,有些是建国时即划定在国界之内,有些后来迁入。作为该国的国民,根据“公民的‘民族’模式”,他们与其他国民一样同属一个“民族”。那么应当如何称呼这些具有血缘、文化差异的群体?
“ethnicity”首次出现在1972年版《牛津英语字典》(Oxford Eng1ish Dictionary)的“补遗”(Supp1ement)和1973年版《美国传统英语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1ish Language)中。“ethnicity”通常在汉文中被译成“族群性”或“族群”,而相应的“ethnic groups”一词普遍译作“族群”。对于“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之间的实质性差异,西方学者作了大量阐述。“族群(ethnic group)成员是由文化联系组合在一起的,……族群这一术语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恰当地引起人们对文化相似性的关注”。学者们强调了“nation”的政治属性及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ethnic group”的性质是“文化相似性”和“群体共享的祖先神话”。
从“族群的‘民族’模式”中衍生出“跨境民族”
正因为在“族群的‘民族’模式”中,人们通常以“族群”的内涵(血缘、语言等)来理解及使用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民族”一词,所以东欧和亚洲国家很容易把境内的各类“族群”也称作“民族”,“族群的‘民族’模式”很容易占据主导地位,把本国具有“血缘共同体和特定文化”的群体如哈萨克人、蒙古人、朝鲜人等群体理解为“民族”并冠之以“民族”的称呼。一旦这些“民族”成员出现跨境而居的现象时,也就连带地出现了“跨境民族”的提法,这是话语生产中“路径依赖”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国际政治体系和话语,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对相关话语的解读与反应。我们清楚看到,把中国那些跨界居住的群体称为“跨境民族”,这个提法和概念在现代世界的国家体系里是有问题的,也会对这些跨境群体成员的国家认同带来负面影响。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中华民族这个层次才应当视为当今国际上通用概念的“民族”,译成英文是“Chinese nation”,中国内部的蒙古族在汉文中应当称作“族群”,译成英文应当是“ethnic group”。在这个逻辑框架中,中国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蒙古族群(ethnic Mongo1ians of Chinese nation)。不管历史上的分分合合,今天的蒙古国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蒙古国的国民是蒙古民族(Mongo1ian nation)。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是“哈萨克民族”,中国和蒙古国境内的哈萨克人应当被称为中华民族内部、蒙古民族内部的“哈萨克族群”。
如果我们说中国的蒙古族属于“跨境民族”,那就表示中国蒙古族和外蒙古属于同一个民族。有的文章写道:“蒙古国的蒙古族与哈萨克族均是与我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蒙古族虽然在历史上曾被分为漠南蒙古(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蒙古(今蒙古国)和卫拉特蒙古等,但都属于同种同源的一个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经济、生活方式、服饰、饮食习惯等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诸多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由于历史命运的不同,现今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度里300余年的生活经历,使蒙古国的蒙古族和我国的蒙古族之间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文化特征。”
根据欧洲传统民族主义理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追求“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的一致性”。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强调要坚持“民族自决权”,指出“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之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无论是根据欧洲经典“民族主义”理论还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居住在蒙古国、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蒙古民族”成员是否应当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国家”?这对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将会带来什么冲击?居住在我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三个国家的蒙古族民众多年来已经与其他族群混居并融入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追求“蒙古民族的统一”这对三国的蒙古族民众来说,是一种可行和最佳的政治追求和生活安排吗?
1949年后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构建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称谓在西方人和日本人的诱导下就开始在国内流行,汉人反满排满的狭隘“汉民族主义”一度甚嚣尘上,中国人在对“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上已呈混乱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顾颉刚先生在抗日战争危急的1939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顾颉刚,1996),试图正本清源。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参照苏联的思路和制度设计,在全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识别出56个“民族”,同时保持“中华民族”提法。使“民族”这个重要的核心概念被用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体层面上,无疑造成对“民族”这一概念内涵理解和应用方面的混乱。长期以来我们把中华民族译为“Chinese nation”,把中华民族内部56个“民族”译为“nationa1ity”。许多国家的《入境签证申请表》中的“nationa1ity”一栏要求填写国籍。美国学者郝瑞(Stevan Hare11)认为中国人把境内56个“民族”译为nationa1ity时,“中国的民族学家们完全误译了‘民族’。他们真正要说的,与其说是nationa1ity,倒不如说更像ethnic group一些;就此而言,他们对这些‘民族’(等于ethnic group)的分类就是不恰当的。……伴随人民自决观念形成,术语nation和nationa1ity就与政治独立或政治自主权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国外友好人士的提醒和外交部敦促下,21世纪初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文译名从“State Nationa1ity Affairs Commission”正式改为“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按英文理解即是处理“族群事务”的机构。
如果把一国境内具有“血缘共同体和特定文化”特征的群体称为“民族”,那么由此萌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潮”将会导致通过“民族自决”途径实现独立建立“本民族”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这对所在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然造成威胁。苏联和南斯拉夫政府把国内许多具有共同血缘、文化特征的族群识别为“民族”,并在个人身份、政策待遇等方面把各“民族”成员加以区分,通过特殊的行政区划建制(自治共和国等)将这些族群“领土化”(the territoria1ization of ethnicity)。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苏联共产党政权本身。”当中央政权出现政治危机时,正是在这一思路下进行的“民族建构”最终导致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以民族共和国为单元发生政治解体。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国内实行的“民族构建”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同样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和相应制度构建、政策设计的中国,是必须严肃思考和讨论的。
境外相应国家对中国提出“跨境民族”的反应
中国学术刊物、报纸、学术会议出现“跨境民族”提法后,越南政府和学术界明确表示不承认存在“跨境民族”,认为越南苗族是越南民族组成部分,中国苗族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民族认同”。越南学者不承认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是同一个民族。居住在中国的京族(旧称“越族”)只是有越南血缘的中国族群。
我国蒙古族在蒙古国被称为“中国人”(Chinese),我国哈萨克族到哈萨克斯坦,我国朝鲜族在韩国都被当地称作“中国人”(Chinese)。这些国家的“民族”概念非常清楚,不承认存在“跨境而居的民族”。中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各邻国都担心中国是否将借助“跨境民族”概念建立跨界群体认同,再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把境外“跨境成员”及其居住区域并入中国。我们在分析“跨境民族”这个概念时必须考虑境外国家和民众是否接受这种提法,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政治疑虑和外交纠纷。
建议国内今后慎用甚至弃用“跨境民族”的提法
中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一定要慎重思考“跨境民族”这一概念及相关用法,或者考虑改用“跨境族群”的提法。如果参照现代国际规则的国籍、国际法和护照制度,不存在“跨境民族”(cross border nations)。但是,我们可以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跨境族群”,回溯区域历史演变的足迹。在国境两边居住的人群在祖先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方面有可能具有相同特征,在历史上曾同属一个政治实体。我们尊重历史和他们的祖先记忆和文化共同性,但是对于这些特征应当从“族群”的角度加以解读。对于边境地区的政治历史过程、人口迁移、文化传统和认同观念的演变,今后仍然可以作为学术界的研究主题,但是这些研究一定是超越今天的国界和公民身份的学术探讨,不涉及国籍和领土,而且应积极争取邻国学者的合作,化解对方的疑虑,努力把一些政治敏感的历史问题转变为纯学术的研究专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摘自《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