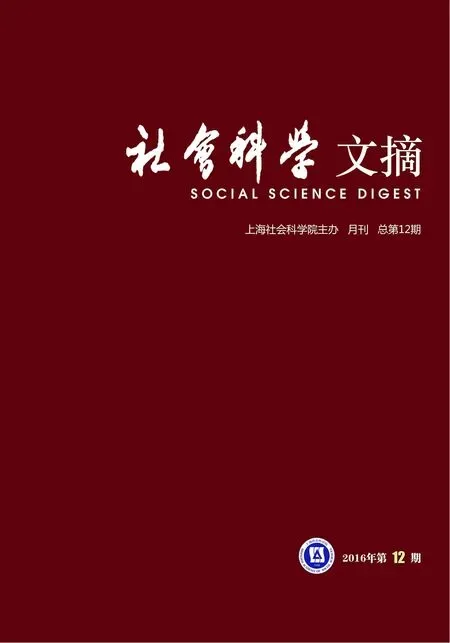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探究
文/杜芝明
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探究
文/杜芝明
有“西南”记录以来,人们对“西南”方位或区域的认识日益丰富,而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地域是历代认识“西南”区域的核心与基础。王朝疆域下的宋人“西南”区域观念正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演变,又为元明时期“西南”区域观念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北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
北宋,包括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川峡四路是宋人“西南”区域的核心;随着“西南”少数民族空间范围认识的发展、演变,荆湖路(民族地区)、广南西路进入到人们的“西南”视野。
川峡四路是“西南”的中心区域。《益部方物略记》所载“益为西南一都会,左阻剑门,右负夷蕃”,反映了宋祁站在中原看待“益州”的“西南”地位,而益州路是“西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四路以整体区域纳入“西南”的是邓绾、曾巩,邓绾的“蜀控西南五十有四州之地”即川峡四路,“蜀”为西南区域的组成部分;曾巩又直接将“西南之地”与蜀地等同起来即“西南之地……属部为四”,更加凸显蜀地在西南的核心地位。邓绾所言“边鄙”并非四路边缘,而是汉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分界;曾巩更加明确指出“西南之地”即川峡四路,包括了“吾民”与“列州成县”的“诸蛮”(“内杂溪谷”)两大族群,而外临“殊俗”类的族群并不属于“西南之地”。
相对于邓、曾二人强调“西南”的大区性,宋人多继承秦汉以来“西南夷”的认识来强调“西南”的方位性、区域性,如宋人对“羁縻马”产地的认识、对“西南蕃”这一新民族称谓内涵的认识等。从川峡四路管辖范围及少数民族分布格局看,宋人“西南”少数民族的空间格局已不在局限于“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如夔州路,除了“西南夷”、“西南蕃”族群外,还包括了今渝东南、鄂西地区的“西南溪峒”族群。
荆湖路部分地区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身份进入宋人“西南”视野,特征明显,这与以邓绾、曾巩等为代表的宋人眼中的“西南-川峡四路”在内涵上存在明显区别。《华夷图》在夔州路、荆湖路、广南西路接壤区域的空白处留有“宋建隆以来,溪洞诸酋请内属,皆命为刺史”之句;同时或稍晚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在相同位置有“溪峒诸蛮”字,且在“辨古今州郡区域”有“溪洞蛮”条。两图标注没有“西南”之词,但“溪洞蛮”之分布区域与《宋史》记载基本一致,宋人冠以“西南”记录较多,如关于五溪地区西南少数民族的记录。而位于五溪外、作为荆湖北路治所与南北、东西交通咽喉的江陵府也被称为“西南一都会”,强调以东京为中心的“西南”方位观、区域观,反映了荆湖北路在统治中心的方位及作为“西南”区域的思想。荆湖南路全州有“西南溪洞”分布,但只是“西南”少数民族分布的区域之一。
广南西路以“西南诸道”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之一、西南重要政治中心进入“西南”视野。广南西路知南丹州莫世忍所持“西南诸道武盛军徳政官家明天国主印”,应是开宝九年(976)宋王朝赐南丹州酋帅莫洪㬫之印。这说明,宋初南丹州蛮已是“西南诸道”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与宜州及西南夷接壤”的地理位置说明了原因;此时该区域进入了人们“西南”视野,“西南”既是方位词,也是区域概念。除族群因素外,因“襟蛮带海、用兵遣将之枢”的地位,静江是“西南都府”,但静江府并不位于广南西路的西南,那么“西南”就是包括广南西路在内的区域概念。
北宋人“西南”区域观念已经超越秦汉代史家以来以“西南夷”为核心认识的“西南”空间,既包括川峡四路,也包括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西路;既包括了华夏地区(巴蜀北部),也包括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巴蜀南部、荆湖路、广南西路)。
南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
南宋,随着统治中心东南移,“西南”方位与区域观念呈现出三大特点:(1)川峡地区作为军事部署的三大区域之一,“华夏”区域以“西(蜀)”地位频繁出现;(2)川峡路的民族聚居区域仍以“西南”少数民族特征留在了“西南”区域内;(3)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西路的“西南”地位更加明确、稳固。
“利州路”成为宋边疆区域,但非“西南”范畴。李纲在《论襄阳形胜剳子》的方位观具有代表性:从全局及军事部署来看,有三个方位即东南、西南、西北,川陕位于西北隅;以襄阳为中心看,存在两个方位即西、东,川陕位于西。明显,随着统治疆域、中心的变化,川陕地区(利州路)作为边疆,已非“西南”地域范围。同时,文献中也有关于西陲、西帅、西兵等大量记载。另一方面,宋人统治中心、方位观变化使巴蜀地区(“华夏”)“西蜀”的称呼更频繁,如“大抵国家用度,多靡于赡兵,西蜀、湖广、江淮之赋,类归四总领所”。“西蜀”指代巴蜀地区在汉代以来皆有记载,这是以全疆域角度看待巴蜀地位,与此处“西蜀”内涵有别。人们普遍以“西陲”“西蜀”等称呼巴蜀地区,说明巴蜀地区作为“西(蜀)”的区域地位成为了主流思想。因人们对以“西南夷”“西南蕃”“西南溪峒”等为代表的“西南”族群认识,川峡四路少数民族区域仍留在了“西南”区域内。
荆湖路是西南中心区,正如李纲说“湖湘屯重兵”是“置子于西南隅也”。《宋史·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的总论及内容包括了夔州路、荆湖路等少数民族,而以荆湖路为主,囊括了荆湖南路与荆湖北路的五溪地区(叙、辰、锦、溪等州)、沅州、靖州等区域。“总论”反映的可能是元代史家思想,但是由于元代短暂、史家生活年代横跨宋元,而且《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以及《宋史·蛮夷四》“西南诸夷”、“黔涪施高徼外诸蛮传”总论与《宋会要》记载基本一致等线索看,该“总论”也是宋人思想并无疑问。赵升在“归顺”“归明”“羁縻”等注解中关于“西南蕃蛮溪峒”分布的记录与《华夷图》《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及南宋时期的《地理图》记载一致,“西南蕃蛮溪峒”主要分布于荆、广、川峡地区,“荆”地区主要包括了荆湖北路的西南区域(五溪地区)与荆湖南路。荆湖路虽因军事战略需要(“西南隅”)整体纳入“西南”,但仍以少数民族分布格局为主要特征,而赵升注解、《宋史》总论通过对宋人思想的总结最终以具有民族特征的整体区域纳入到“西南”范围。
在大量移民迁入,开发步伐加快等背景下,人们对广南西路“西南”族群特征、区域地位认识得更加清晰、明确。一方面,凸出族群的“西南”属性。广南西路是赵升眼中“西南蕃蛮溪洞”分布的三大区域之一;平州地处三路(荆湖南、北路与广南西路)接壤,是兼制三路少数民族的中心,具有“西南重镇”的地位,此“西南”不仅包括了平州,还包括了三路部分区域以及更广区域。范成大说“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其外则西南诸蛮”,“西南诸蛮”的分布格局决定了“西南”包括整个广南西路。另一方面,凸显“西南”的方位、区域特征。琼州帅守韩侯壁、朱熹皆曾说:琼州“在中国(中州)西南万里”之外,琼州位于“中国(中州)”的“西南”成为士大夫的共识!那么比“琼州”更“西”的广南西路其他区域明显也位于“西南”方。朱熹在《辞免知静江府状一、二》中说:静江守臣“实兼帅司职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寄”,体现其权力范围是整个广南西路,“西南一面”强调统治中心的西南,更强调广南西路“西南区域”的地位。周去非也说:“(广西经略安抚使)帅府既内兼西南数十州之重,外镇夷蛮几数百族”,“西南”强调方位、区域双重内涵,“数十州”即广西“所领二十五郡”是“西南”的组成部分。
南宋时,利州路(川陕地区)“西(北)”边陲地位与巴蜀“华夏”区域、“西(蜀)”地位更加凸显且已成为主流思想,少数民族聚居区因“西南”族群特征留在了“西南”;统治中心坐标变化理应导致荆湖南、北路地位的变化,但军事战略重要性、族群分布与地理环境相似性等因素导致其“西南”地位的进一步发展;不论族群的“西南”属性,还是方位、区域特征,广南西路的“西南”地位在此时得以确定。
宋人“西南”区域观念的地位
宋人“西南”区域观念是以往人们“西南”方位观及以“西南夷”地理空间为核心认识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对后世人们的认识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宋人将川峡四路的腹心区域(“华夏”)与少数民族聚居区(“蛮夷”)作为整体纳入“西南”视野,具有大区性,这是先秦秦汉以来关于“西南”方位、区域观念融合、演变的结果。先秦秦汉以来人们关于“西南”的认识,首先强调方位观,其次据指向性、民族分布等因素而具有区域概念,或将“华夏”、“蛮夷”两个区域割裂开来,或具有局部性,如晋人郭璞对“西南有巴国”的注释,虽然包括了“华夏”与“蛮夷”两大区域,但只是巴蜀部分地区。这一阶段区域观念的非完整性即非大区性具有普遍性,直到“西南道行台”管辖范围的明确。行台省在魏晋时已存在,而“西南道行台”在北齐时已出现,但与巴蜀毫无关系。隋开皇二年,在成都置西南道行台,具体管辖范围不明。唐代对“西南道行台”管辖范围已有明确记载,包括了“华夏”、“蛮夷”两大区域即总管府所辖22州(都督府所辖10州3都督府)的范围。西南道行台设立及管辖范围说明完整“西南”大区的概念至少在唐代已出现了。西南道行台对后世地方行政区划产生深远影响,宋代川峡四路衍生于最初的“西南道行台”,邓绾、曾巩二人的“西南”区域思想也许受“西南道行台”的影响,但二人不是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而是从区域角度,且与“西南道行台”管辖范围有所异同。因此,包括腹心区(“华夏”)的“西南”大区思想当萌芽于隋唐,初步形成于北宋,最终形成于元明时期。
(二)作为人们认识“西南”区域核心与基础的“西南”少数民族地理空间被宋人继承、发展,从而决定了“西南”区域思想的发展、演变。“西南”少数民族地理空间主要经历了“巴蜀西南外蛮夷”、“蜀郡徼外”、“交州之西南”变化,除“交州之西南”外,具体内容与《史记》基本一致;五代刘昫虽无表述,但《南蛮西南蛮传》内容与《史记》也基本一致。其变化反映出人们方位观、坐标中心的变化即以巴蜀为中心到以蜀郡为中心再到以“中国”(以郡县为特征)为中心的变化。在其基础上,宋人的“西南”族群,一方面,出现与以往空间上存在异同的“西南蕃”、“西南蕃蛮溪洞”等新的族群称谓;另一方面,将非“西南夷”的巴郡南郡蛮、南越等族群纳入到“西南”族群中来,从而使川峡路东南部、荆湖北路西南、荆湖南路、广南西路等成为“西南”新区域。这是地理环境、族群分布格局相似性情况下,“西南夷”区域认识泛化的结果。宋人对“西南”族群空间往往以“汉牂牁郡地”、“杂则荆、楚、巴、黔、巫中”等具体空间表达,凸显了“西南”是方位观、区域观的融合。
(三)北宋到南宋“西南”区域思想的发展、演变为后来区域思想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北宋,川峡四路以整体进入,既包括“华夏”地区,也包括“蛮夷”地区。南宋,川峡四路的地位主要呈现两个特点:(1)“华夏”地区位于统治中心、疆域的“西”方的地位更加突出;也有人仍以“西南”称之,这也许受“祖宗之疆”思想、仍以“中原”为中心的方位观影响。(2)“蛮夷”区域因历史原因、地理环境、族群分布格局的相似性,“西南”区域地位并未发生变化。荆湖路以“西南”少数民族形式进入“西南”区域,到南宋才基本完成“西南”化进程。广南西路,在北宋已进入人们的“西南”视野;南宋,“西南”的方位性、区域性则更加清晰、明确,说明广南西路已具有了比较稳定的“西南”地位。荆湖路、广南西路两大区域在宋代或初步完成“西南化”,或已具有稳定的“西南”省份地位,这为包括四川、两湖、广西的“西南”大区整体思想在元明时期的形成奠定基础!
综之,宋人“西南”区域观念具有方位观、区域观融合的特点,这是疆域盈缩、统治中心变化、族群、军事、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一方面,因地理环境、族群分布格局等相似性,宋人将川峡四路、“西南蕃蛮溪峒”地区作为“西南”大区概念认识外,其余记载只是区域的局部;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不具有必然性,如对人们“巴蜀西南外蛮夷”认识的影响并不显著、有些宋人的方位观与区域观未随坐标中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观念也就不具有了非此即彼特性,而只是凸显与弱化的关系。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摘自《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原题为《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及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