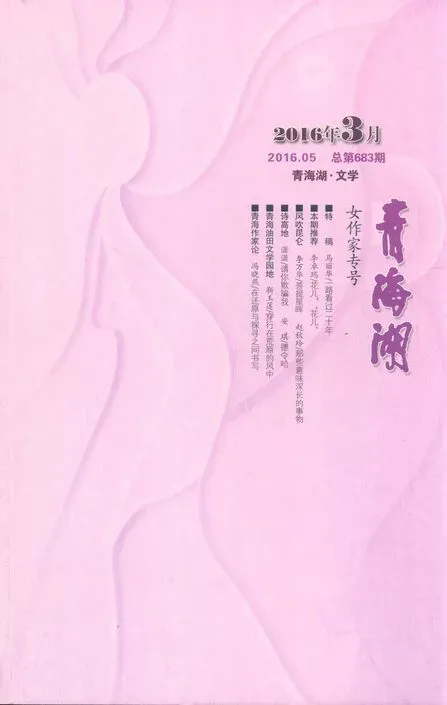寒 衣(短篇小说)
权芳
寒衣(短篇小说)
权芳
这地方叫“吴家”,但此地人口音叫做“吴呀”。意思是说,这村里大部分人家姓吴。此地有很多村子就是这样命名的,比如“柳呀”“张呀”“顾呀”。或许是很久很久以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地,然后某一天,来了一群人,逃难的,或者犯了重罪被朝廷发配的,走到这儿一看,地方不错,有山有水,土地肥沃,干脆就在这儿居住下来……
姑娘在听,但她的心思不在这上面。男友说一句,她敷衍地点一下头,披肩长发跟着甩一下。她是第一次来这里,要不是男友带她回老家,她还真想不到乡村的秋天竟这样美丽。她是南方人,又是城里人,即使偶尔见过乡村的秋天,那也完全不是眼前的这种景象。姑娘的眼睛不够用了,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都看不够,又不能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她的惊讶,只能一个劲地轻声“呀”“呀”着,伴着略微夸张的表情。她是个摄影爱好者,这年头似乎谁都是摄影爱好者,人人挎着长枪短炮或者只是一个卡片机,到处“咔嚓咔嚓”着,照人,照景,照猫,照狗,照山,照树。很多年轻人还用手机拍照,现在的手机都有拍照功能,像素还挺高。很多年轻人还用手机拍照,一边照,一边发微信,发微博,上传“手机相册”。总之,他们用相机和网络,实现了生活的复制或者现场直播。这姑娘胸前挎的是一架尼康D80,现在来说有些过时了,但也正说明她是个资深摄影爱好者。她每隔几分钟端起相机,眯起右眼,略微半蹲或者踮脚,对着某处庄重地“咔嚓”一下。其实不用这么刻意地取景,在这里,闭上眼睛,随便举起相机“咔嚓”来一张,就绝对是一张可以参加摄影大赛的作品了。姑娘的心思就在这上面呢。她甚至已经给这些照片起好了名字:《金秋》《丰收》《喜悦》《鞭炮》……她甚至给最后一幅作品《鞭炮》配了一首短诗:是谁/绽开了幸福的笑脸/是谁/挂起了金黄的鞭炮/让那清脆的呼唤/响彻乡村的秋天。
小伙子对女朋友的心不在焉没有丝毫的不高兴,相反,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得意。他一边带着不耐烦的表情瞅着一个劲拍照的女朋友,一边快乐地低声嗔怪她:哎,就知道拍照、拍照,真不知道这地方有什么可拍的!你真是少见多怪!你这么乱拍,当心一会儿有人骂你!我们这地方的人很厉害的!他一边说,一边转着眼珠四处瞄着,看人们有啥反应。这村子不大,统共二三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门前有人,院里有人,房顶上有人。对他们两个陌生人的闯入,他们其实并没特别在意,只是不经意地抬起眼皮看一眼,就继续忙他们的事。与眼下成山成海的玉米比起来,这两个陌生人实在算不了什么要紧的事,他们愿看就看吧,愿照就照吧,反正也看不走一粒玉米,照不走一粒玉米。阴了好些天了,那些垂在头顶的云彩好像马上就能拧出水来,让人每天都担心。好容易昨天起放晴了,得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时间,让那些刚从地里收回来的饱含水分的玉米尽可能多地吸收阳光,赶走它们体内的水分,让它们在太阳的抚摸下变干、变硬、变轻、变小,这样才能换成钱,或者打成玉米糁子。一旦晾晒不及时,或者晾晒时间不够,那些玉米就会像没睡够却硬被叫醒的娃娃,蔫蔫的,笨笨的,呆呆的,这样的玉米就不值钱了,打成糁子也又“僵”又“死”,没人喜欢喝这样的糁子。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手,他们嘴里说的话,全在这铺天盖地的玉米上,没人有工夫去搭理两个闲得发慌的年轻人。晒玉米又是一项繁琐的活儿,得先用结实的粗木搭起“架子”,再三四个一组地,把这些玉米成功地一个个搭到“架子”上。这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常听见谁家的夫妻或父子为了搭玉米架子而发生短暂的争吵,一个嫌架子搭歪了,一个嫌搭得不够高。可是,当家家户户的门前、院里和房顶上到处是一个个、一排排的玉米架子时,那就非常壮观了。那一串串的玉米分明就是一串串金黄的、硕大的鞭炮,散发着饱含水分的甜香,整个乡村变成了金色的海洋,金色的森林。
一对小情侣就在这金色的世界中行进着。这是近半个月来难得的响晴天,天蓝得炫目,太阳火辣辣的,一丝风都没有,两人走得浑身燥热,姑娘的头发被汗水浸湿,湿哒哒地贴在两颊。小伙子索性学当地人的样子——把裤腿高高地卷到膝盖以上,再把短袖衫反折到胸部,露出半截肚皮。姑娘望望男友白白净净的肚皮,再望望那些人黑黝黝的肚皮,不禁哈哈笑了。来来来,我给你照一张!姑娘掏出手机,对着男友的肚皮“咔嚓”了一张。然后,她低下头,很快地发了个朋友圈,并附上一个调皮的表情。尼康D80终于没电了,她把它挂在男友的脖子上。男友无奈而幸福地笑笑,任凭女友举着手机到处乱照。
姑娘再次举起手机寻找拍摄对象时,屏幕上远远地出现了一个人。这人扎煞着两只手,慢吞吞的,姿势有点像一只蠢笨的鸭子一般,向这边慢慢走过来。这人在手机屏幕上慢慢变大时,姑娘看清了,这是个女人,看起来应该上了年纪了,可是一下子又说不清有多大年纪。看她的身板,像是六十不到;看她的满头白发,又像是八十好几。这人慢慢慢慢走到姑娘面前时,站住了。她抬手慢慢地拨一下脸上的头发,眯缝着眼睛,对两人说:回来了?接着,又往前伸伸脖子,更使劲地眯着眼睛,对着姑娘说:这女娃长得真俊。她甚至伸出一只手,打算摸摸姑娘的头发,但她的个子太小,尽力地伸长了胳膊,也仅仅摸到了姑娘的肩膀。她的声音有些干,有些沉,有些硬,是那种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声音。与这嗓音相伴的,是她浑身那么一股说不出来历的气味——浑浊、潮湿、陈腐。这些都有些让人不舒服,至少,不会给人带来愉快的感觉。
姑娘一边赶紧做出微笑的表情,一边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女人,再转头望望男友,意思是:你家亲戚?男友也望望她,意思是:我得想想,或许是我家的哪个远房亲戚?男友以前对她讲过,他的家族很大,亲戚众多,到处都有,但大部分他都不认识,毕竟他从上大学起就离开故乡,至今差不多快十年没回来过了。
对面的女人再次说:你回来了?你好几年没回来过了!这次男友毫不迟疑地接上话了:啊,回来了!前儿回来的!国庆放假七天!男友马上换上当地方言,显得热情洋溢。他是个聪明而机灵的小伙儿,脑子反应很快——否则怎能在大城市立足并且带回个南方姑娘呢?不管这是谁,不管认识不认识,总之,礼多人不怪。回句话又不损失什么,笑一下也不损失什么。小伙子用胳膊肘捅一下女友,女友也赶紧变出一个大大的笑脸。但这大大的笑脸也只能居高临下地传递给对方,因为这女人实在是太矮小了,站在对面只到姑娘的胸部。姑娘一直埋怨父母没给自己一个高挑的个子,现在却感觉到了自己的高挑。对面这女人简直像个没长开的孩子,不但矮,还瘦,还干。要不是她花白的头发和身上穿的夹袄,单看她的身子,谁都会以为这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现在看清了,女人手里还拿着两只玉米。女人挥舞着两只玉米,说:走了半天路,嘴干得很吧,走,赶紧进屋。她把一只玉米倒到另一只手里,空出的手牢牢抓住了小伙子的胳膊。小伙子吃了一惊。这女人的手枯瘦得像鸡爪,但力气很大,五根手指像钳子牢牢地卡在胳膊上,甚至让人觉得疼痛。不不不,我们不渴……我们得赶紧回家,一会儿没班车了……过几天再来看你吧……小伙子急急地拒绝着,一边在心里使劲地思考,这究竟是哪位亲戚。试了几次,小伙子绝望地发现,以他的力气,他根本无法挣开这女人的一只手。或许是他常年坐办公室,缺乏锻炼,竟然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婆有力气。不过,现在他确定了,这女人的确是他家的某个很久没见面的远房亲戚,她认识他(或许还是看着他长大的),但他不认识她。他思忖着,该怎么称呼她。就她的年纪来说,她应该是她的长辈,但这也不一定,或许她年纪大而辈分小,要是称呼错了那就尴尬死了。小伙子只好嘴里含混不清地噜噜着,什么也不称呼,只一个劲地说着客气话,同时使劲地想抽出自己的胳膊。原本他只是带女朋友到处转转,没想到越走越远,走到这个“吴呀”来了。他可没打算进到谁家去喝口水。再说,要是走亲戚,总得买点水果、蛋糕之类的礼品,空着手怎么进门呢,会让人家笑话的。他保持着脸上的笑容和嘴里的客气话,脚下却暗暗用力,气沉丹田,双脚像被万能胶粘住一样一步也不挪。僵持了一会儿,那女人终于放开了他。可还没等他嘘口气,那女人顺手把玉米扔到路边,两只手抓住了女友的手,拉着她往前走。女友猛地望向他,他从女友的眼里看出一丝惊惧。女友扬着眉,张着嘴,他知道一个轻轻的“啊”被女友堵在了喉咙里。她是个典型的南方姑娘,温柔秀丽,胆子小得像松鼠。他知道,女友这个表情是被吓住了。他想,女友也感受到了那女人手上的力气吧。他不知道,女友是被一股凉气“冰”着了。那女人的手一挨着她,就像一大块冰突然被谁塞到了她手心里,吱吱的凉气顺着手臂往上窜,再分出无数的枝杈,一瞬间就遍布全身,使她的体温瞬间降了好几度。姑娘似乎听到了凉气顺着血管拼命奔跑的声音。她再次惊惧地看着眼前的女人,对方却并无异常之处。她只是比一般这个年纪的女人更老,更瘦,更干。对方抬起头望向她,浑浊的眼里只是平静的恳切,仿佛他们的拒绝才是天底下最奇怪的事情。那女人就这么一直拉着她往前走,瘦小的身子一弓一弓,像是一个赌气的孩子拉着妈妈去给她买玩具。她的样子使姑娘有些厌恶,但也牵动了她心底的某处神经,使她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一步步向前走而没有拼命地挣脱开来——反正挣脱她的手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她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个教养良好的姑娘惯常的微笑。
这女人的家非常凌乱。这是第一印象。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这家的门前、院里、房顶上,凡是稍微平整些的地方,都晒满了玉米,到处金黄灿烂。不同的是,别家的玉米编得好看,晒得齐整,这家却是横一个竖一个,玉米架子有高有低,玉米串儿有大有小。院里的空地上铺满厚厚的玉米粒,几只母鸡在上面走来走去,不时把玉米粒儿刨得四处乱溅。断了把的铁锨、破了一只轮胎的架子车、沾满泥巴的簸箕和笤帚……到处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稍不小心就会被绊一下。院子里很安静,除了几只鸡的咕咕声,再没有别的动静。这过分的安静与眼下由于玉米丰收而营造的火热喧闹的气氛极不相称,显出那么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来。第二印象是脏。当然了,与凌乱相匹配的,不可能是洁净。墙壁是脏的,蛛网乱结,白灰斑驳,像一块块的牛皮癣。门窗是脏的,黑乎乎的一层油腻像是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正屋里那炕上是脏的,看不出颜色的被褥们皱巴巴地挤成一团,一股陈腐呛人的气味直钻鼻孔,让人恶心欲吐。屋子中间竟然还生着一只小小的铁皮火炉,炉盖揭开着,炉火已经半死不活。这一切,是两人费了些力气才逐渐看清的,因为这屋里实在是太暗了,简直像是一脚从白天跌进了深夜,过了好几分钟,眼睛才慢慢适应过来,屋里的这些东西才像浸在显影液中的照片一样,慢慢慢慢地一样样在眼前淡出。伴随着这黑暗,是一种奇怪的冷。不错,是冷。外面艳阳高照,所有的人都是短袖短裤,还热出一身汗来,一进这屋子,像再次被那女人的手抓住一般,气温又陡然降了好几度。姑娘甚至打了个小小的喷嚏。那女人立即再次拽住姑娘的胳膊,一个劲地劝说他们“上炕”。炕上暖和,炕上暖和!看把我娃冻的!这过分的热情使姑娘唯恐避之不及——就算真是数九寒天,就算她真的快被冻死,她也是绝不愿意坐到那么一个肮脏难闻的炕上的,何况现在实在不是需要上炕取暖的季节。但小伙子从这句话里立即判断出,对方是他的某个长辈。此地人对晚辈表示亲近,会称晚辈为“我娃”。反复对比衡量后,小伙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是他家的某个亲戚,或许是父亲那边的,也或许是母亲那边的。总之,只有身为长辈的亲戚,才会用“我娃”来称呼他。一辈子没离开过此地的母亲也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我娃回来了!”“我娃想吃啥饭哩?”“我娃工作好不好干哩?”母亲也这样称呼自己的女友,“我娃长得细眉大眼哩!”“我娃这头发乌黑油亮!”一遍遍地夸奖着她,进进出出地给她拿好吃的:苹果、梨、柿子,搞得女友都不好意思了,小伙子却有那么一点得意——这说明母亲对自己的女友是欢迎的、肯定的,甚至已把她当做自家人了。要知道,在这里,“我娃”可不是随便称呼的,搞不好就有占人便宜、欺负人之嫌,招来别人的一顿好骂。
现在,那女人就这样,一声声“我娃”“我娃”地叫着,踮着两只脚,颤巍巍的,进进出出的,给他们拿这拿那:无非也是苹果、梨、柿子之类。这个季节,正是这些东西的天下。这些东西被那女人双手捧着,急慌慌地摆到桌上——那小方桌也油漆剥落,油腻厚重。他们当然不会去吃它们,连碰都不会碰。那女人一个劲地拿起一个苹果,又拿起一个梨,又拿起一个柿子,硬往他们的手里塞。出于礼貌,他们接过了这些水果,再放回到桌上——不知怎么,连这些水果也是冰凉冰凉的,就像刚从一堆冰水中捞出来。然后,她原地转了几个圈,终于搬了个小木凳,坐在了他们的对面。他们都松了口气,她终于安静下来了。这意味着他们有机会起身告辞了——在这儿多呆一分钟都像在受罪,时间仿佛停滞,一进门他们就深深后悔了,尽管对方是自己的某个亲戚。
但是,他们的告辞行为屡屡失败。每当他或她礼貌地站起来,刚要开口说话时,那女人总会不失时机地开口,我娃想吃啥饭啊,油泼面成不?我给你做去!我娃吃个苹果吧,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哩,你看,又大又红!我娃……她的语速极快,显出一种急切的、不容置疑的神情,仿佛他们不再次坐下去就是天大的不对。他们只好一次次站起来又坐下去,痛苦地熬着时间——坐够了时间,她总会同意他们告辞离开的。难熬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她的目光。不知怎么,她那属于上了年纪女人的、昏暗浑浊的眼睛,此时竟灼灼发光,在黑乎乎的屋子里就像两团小小的火苗。这两团火苗一言不发、一秒都不退缩地炙烤着他们,像要把他们“轰”的一下点着。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显然,女友也觉出这么点不对劲来,但是这感觉来源不明,只能说是直觉。他从女友望向他的眼神中看得出来:此时女友的心正被疑惑、无奈所纠缠,她正无力地想要摆脱它们。他只好这样向女友解释:我们这里的人都极为热情好客。这解释连他自己都觉得勉强。
那女人第N次提出“我给我娃做点饭去”时,他们果断地站起身,不容置疑地提出告辞。为了防止对方再次伸手来捉,他们巧妙地抢先一步跨出了房门。那女人的手扑了个空。他们松了口气。但是,在跨出房门的同时,他们听到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突如其来的哭声,像是谁的喉咙被人狠狠扼住后拼尽全力发出的一声呜咽。他们被这声音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不得不同时转身去看个究竟。
他们骇然地看到,她正在拼尽全力地哭,浑浊的眼泪从指缝里一缕缕渗出来。看得出来,她是想号啕大哭的,但她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哭声只能变成一阵阵的抽噎——就像汹涌的河水不得不从一根细小的管子里流出,就像发怒的狮子不得不被关在窄小的笼子里。她双手捂着脸,全身发抖地哭,看起来悲惨无比又莫名其妙,甚至有点可笑。现在他们终于确认了自己的直觉——这女人,有那么点不正常,精神方面的。她一定是认错人了,再或者是又犯病了,而他们恰恰配合了她的犯病。
他们下定决心要走,不去理会她的呜咽。现在,尽快离开这里是最好的做法。然而,她忽然在呜咽的间隙里喊出一声:“海娃!”这一声也是拼尽全力的,因此这一声显得格外突兀而响亮,足以让每个人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一声作为直接证据被他们采信——她真的是认错人了,错把他们当做自己认识的某个亲戚了。这下他们反而放下心来。认错人是常有的事,何况这女人那么大年纪了——她看起来像六十岁,又像八十岁,在农村,都属于很老的年纪了。海娃你又要走啊,饭都没吃哩!吃了饭再走吧,吃了饭,肚里不空,心里不慌呀!她拼命地咽下呜咽,急急地说出这么一大串。她的一头白发更凌乱了,眼睛更红肿浑浊了,脸上纵横的皱纹都被眼泪濡湿。她抬起头,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嘴巴张开着,露出空空的牙龈。她显得滑稽可笑,也可怜。他们再次心软了,他们叹着气说,不行,得走哩,得去工作哩!显而易见,此时纠正对方的认错人,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只要哄着她,顺利地告别她,就万事大吉了。于是,他们(主要是小伙子,她一点不会说此地方言)反复说他们得回去工作哩,他们干的是公家的活儿,不敢怠慢哩!看得出来,那女人对“工作”两字带着莫大的崇敬,一听他们这么说,她也只好松开了抓着他们的手。但是,她还是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说出了最后一句话:那,海娃,我给你做的棉衣,快做好了,你试试吧?马上入冬了,你们那边冷,得穿棉衣哩!
他们几乎是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去试棉衣的。谁会拒绝这样的一个要求呢,试一下衣服又不费什么事,何况显而易见,试过衣服,他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告辞了——天色正一点点暗下来,这是告辞回家的最好理由。那女人走到那面肮脏的炕前,反复劝说叫他们坐在炕沿,然后自己脱了鞋,撅着屁股慢慢上炕,一直爬到炕的角落,慢慢慢慢掀开那些皱成一团的被褥,轻轻地取出了棉衣。然后,双手捧着棉衣,慢慢慢慢地下了炕。
快试试吧,看看合适不合适……她说。
她的话还没说完,女友已经捂住了嘴巴。又一个大大的“啊”被她堵在了喉咙里。她是一个教养良好的人,即使这几乎使她晕厥的惊吓,也没能使她失了教养——伸手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受到的惊吓吓到别人,几乎是她的本能。她没工夫也来不及看男友的反应,就已经被他一把拽着,飞也似的逃了出去。
他们是逃出去的,像两个千辛万苦逃离监狱的犯人,唯恐再次被抓回去。再慢一步,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虽然事实上什么也不会发生。黑夜已完全降临,一张大网一样罩得他们透不过气。家家户户都亮起灯光,人在说话,狗在叫。这一切像是不真实的电影背景,他们在背景里不真实地奔跑着,慌里慌张,跌跌撞撞。他们惊异于白天看到的那个金色的、美丽的乡村倏忽不见了,仅仅因为是黑夜降临了,还是因为那个女人、那奇异的棉衣?
但是,说实话,那棉衣,有什么奇异的呢,无非就是那种给死人穿的、红红绿绿的、纸做的衣服。那的确是棉衣,的确絮着厚厚一层棉花。应该是新棉花,那突然而至的新棉花的香味,闪电一样穿透一切的黯淡和肮脏,让他们猝不及防,反应过度。
责任编辑邢永贵
作者简介:权芳,女,生于上世纪70年代。2006年开始业余写作,有短篇小说、散文等发表于《中国铁路文艺》《青海湖》《青海作家》《芳草》等文学期刊。现供职于青藏铁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