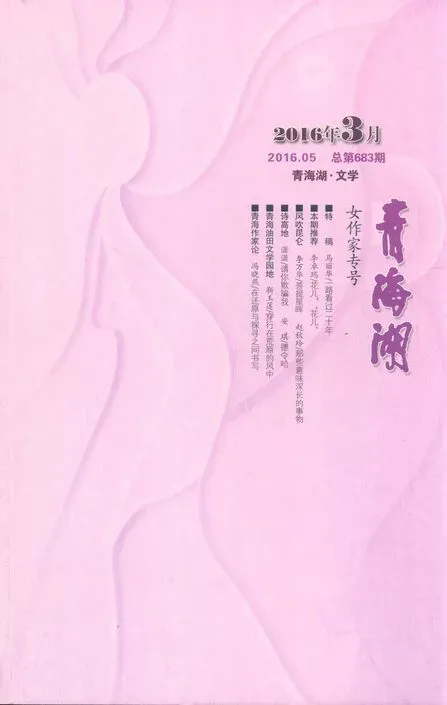静穆中的嘶鸣与飞跃(评论)
——刘大伟近作简评
冯晓燕
静穆中的嘶鸣与飞跃(评论)
——刘大伟近作简评
冯晓燕
诗人王家新喜欢探访哲学家和诗人的故居,荷尔德林的努廷根、席勒的马尔巴赫、海涅的杜塞尔多夫、艾米莉·狄金森的阿默斯特……正如荷尔德林后来在诗作《当我还是年少时》中动情追忆努廷根“我在神的怀抱里长大”一样,诗人们最初的栖息地赋予他们对于爱、痛苦敏锐的感知力。这个具有个人色彩的记忆和生活经验的原生地,在日后的若干岁月中将成为诗人“语言的家园”和不断穿越后最终抵达的精神居所。对于在高原一隅、湟水之畔出生的诗人刘大伟亦是如此,那个居于达坂山和龙王山之间被称作“林川”的村落,以及随着年龄的稍长穿行其间的湟水之滨,便成为诗人成年后无数次用目光浸润、言语摩挲的土地。
刘大伟诗歌隐喻的基础不是来自历史和时间,而是来自地理和空间。湟水河岸的故土在诗人自我思想建构过程中起到的塑形作用尤为明显。一方面诗歌的自我主体意识在地理、空间特性中逐渐生成,北方乡村漫长的冬季、清静甚至沉默的空气铺陈了刘大伟精神气质的底色。同时自我的生成和地方性的复杂关系,使作家主体又进行着不懈的自我改写,不断增加自我内部的认知距离,发展主体自我的多重性。
地域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诗歌经验形成的基础,我们的感受和情感从本源意义上来讲是在具体的事物秩序中产生的,进而可以在纯粹的思想中提炼、升华。思想有它的可见性,诚如“观念”的形成基础是“观看”,是从视觉感知起步的。刘大伟诗中“可观”之物众多:显得清晰的溪流、游向浅滩的鱼群、被大雪覆盖的一座城、背负夕阳微尘拂面的朝山转湖的藏人、飞扬如瀑的鬃毛、描摹冰花的孩子。如此这般事物见证了诗人的个人记忆、亲历的事件及其间的快乐和痛苦。而诗人与世界的美学关系,主要是通过这些目光来建立联系,诗人的职责之一就是把目及实见的存在之物变为内心的元素,把世界内心化,随着岁月的流逝、诗人的移居,记忆变成审美的经验。因此,在清晰的溪流中诗人看到“薄薄的命运”和“悖谬的世界”;在游向浅滩的鱼群中看到“时间的叶片”;在大雪之城中看到“破碎”和“疼”;在飞扬如瀑的鬃毛上看到“不断弹射颠沛的灵魂”;在转湖藏人的身上看到“引渡灵魂的语言”。
刘大伟的诗作,诸如《湟水谣》《等一场风把我们吹绿》《戈壁》《林川雪》《驰骋》中的事物、地点和风光,在隐秘地化为诗人自我认知的符号。对河流、树木、村庄的书写已经成为构筑抒情主体和话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它们的言说者对美学化话语主体的自我确认。同时诗人又与描摹的世界拉开距离,从事物的细节中抽身而出,把情感一丝一缕地抽出来,像在黑暗中吹箫,和雪后的沙粒一起带给人夙夜匪懈的沉缓诉说。刘大伟的诗是个人化的、静穆的,在不断探寻的旅程中,伴随着一种不为旁世所牵动的知识分子冷静的智性和与生俱来的孤寂心境。“太阳升起来了,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蕴藉温暖,雨水流淌/你走过青海荒域,沙棘如灯……触摸怀头他拉的矿石,结构精美/你看到一个人住在沙粒上/孤独成王”(《戈壁》)。诗歌用微妙的语言接续孤独沉思的诗歌传统,对一个地域所包含的意识结构的探索在自我主体意识的复合书写中不断显现。
《孤树》的开篇“卸下冠冕,山河轻盈/青海长云裹紧我细小的破碎”,在广袤的高原地域中,诗人的自我体验常在这“细小的破碎”间,“沙尘”便在“世间所有的静谧已变作震颤”时孤绝扬起,“铺满一个人的苍穹”。“我知道,这些小小沙粒/行走在广袤的天地间,身不由己/它们微弱的身世,源自/针尖般的宿命”(《格尔木沙尘》);“尘埃,风阵,合力掀起一个人的轻……挑破时光泥泞的暗门”(《北杏园》);“我不敢张口,生怕/满世界的尘埃,裹挟了金色词语/让青草倒伏,来路迷蒙”(《方向》);“身世,尘埃里变色的骸骨/有谁会前来认领”(《这个世界没有名字》)。在这“飘散于天际”如“时间的颗粒”的“尘埃”,是诗人个性主题鲜明的自我体认,也是人类在洪荒宇宙间亘古恒长的精神标的。这与阿赫玛托娃诗作中关于“尘埃”的体验意蕴相通,“在傻瓜的每一句蠢话之上,/在每一粒尘埃上,我战栗”(《你赋予我困顿的青春》)。与此同时,诗人把“尘埃”与少女的温性隐喻连缀,意味深长。“雨滴降落,由大风安抚/那些飘摇的身世,为落尘认领……那些叫落尘的女子……任由清风明月,扑满深秋之怀”(《那些叫落尘的女子》),坚硬、弥漫“飘落生活碜牙的微尘”在这里有了温润、清朗的质素,有了“白牡丹和紫青稞”植物的气息,带着“时光里走漏的记忆”使得诗作中美学化的话语主体丰盈、饱满,静穆、孤绝的美学品格在旷野、落雪、孤树、冰川的书写背景下有了诗人刘大伟独特的印记。
地域给诗人的教诲是复杂的,地域是想象力的产物,也是近乎无法逃脱的命运的载体,诗人孤绝的自我经验还来自于对待生命中生与死主题的书写。在塔儿湾,《孤树》《等一场风把我们吹绿》等篇什在微观的层面描述诗人同时遇见和面对的两个世界,以及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生死相依。“多么稠密,带着湿湿的表情/像你的大眼睛,告诉我——世界寒冷……如果,在找到你的那一瞬/风把我们吹绿,我会将你高高举起//像一株蒲公英举着生命里/揪心的小花黄”“铭刻,剥落……你收好一小撮土/留给我揪心的蓝色”。这种“揪心”的感受大概是人类对于失去生命挚爱的最动人的心理体验的描绘。
在刘大伟的诗篇中,地理特性和自我特性似乎是一个相互发现的过程。当诗作触及这片地域上生存的动物、植物以及活跃的人物时,静谧、孤冷的笔触便会鲜活、灵动起来。“一只蝴蝶飞跃骨头,翩然于我们的头顶”(《一直蝴蝶飞过》),绽放、妖娆的蝴蝶穿越时间,似乎是从远古走来;“马群依旧在远方,嘶鸣如弓/声声带箭,不断弹射颠沛的灵魂/而现在,我们回来了”(《驰骋》),奔驰的马穿越空间,从文明与迷惘的栈道中穿过最终驰骋草原;绣鞋垫的妇女“从彼此的阅读中,松动着/越缝越密的怅惘”(《绣鞋垫的妇女》)。诗人孤寂的性情在故乡人情的温暖中提亮了描摹的色度。在近乎于戏剧情境的描画中,我们看到晨起烧茶的老奶奶,人物的举手投足间细致的临摹,在“她悠然的话语里,含着一个暖暖的春天”(《烧茶的老奶奶》);除了烧茶的老人还有回归百里林川温酒的“我”,“温着整个世界……在你投向窗棂的柔波里/深深沉醉”(《温酒》)。这些故园的人们如同霍夫曼斯塔尔所言“那时,与我们共同度过漫长岁月的人/和那些早已入土的同胞/他们与我们仍然近在咫尺/他们与我们仍然情同手足”。而那个在旷野大雪中、在尘埃密集的风中、在荒城沙粒中孤绝成王的男子,此刻也终于在这“低矮的屋宇内”安享“一个殷实的暖冬”,这是诗人远行后无数次回眸远望不断穿越,最终回归的精神故居。
故土地域给予诗人静穆、孤寂的精神气质,由此诗人努力创造出一种令人动情的智性与情感融合无间的美。其间有沉静、灵动而触动人心弦的情,无论是怅惘的、忧郁的还是欢快的、热烈的,都是“生命的美的瞬间的展开”,诗人用一种天乐齐鸣的清音“等待冰河裂出春天”。
本栏目实习编辑张殷馨
作者简介:冯晓燕,女,1980年出生,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