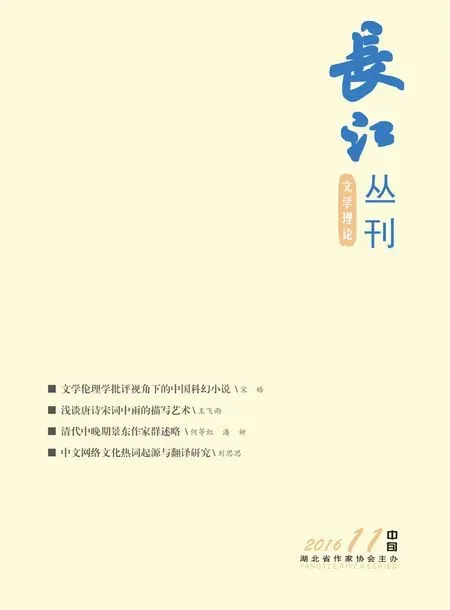试论“科学派”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积极启示
张明旭
试论“科学派”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积极启示
张明旭
伴随“后理论”时代的来临、文学理论“合法性”危机的呈现、“中国问题”的凸显,对于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焦虑和文论建设的急迫召唤再次成为焦点。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发展,当代文论的“合法性”危机如何解决,当代文论的“中国问题”如何自洽与他融,当一系列追问令人不知所措时,“科学派”的理论建构给了研究者积极的启示,为当代文论建设与发展展示了新的维度和可能性。
当代文学理论 科学派 启示
一、重拾科学精神,架构历史维度
20世纪是文学理论“黄金时代”,各种流派及思潮纷至沓来,论辩不止,没人能预料到热度会下降的如此之快。如今的文学理论早已不再以一个“有用的、不断进步地”的姿态受到研究者的追捧,在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多重打压下,其存在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自身的学科归属和科学性质在一浪又一浪的声讨中不断被遮蔽。文学理论真的“无用”了吗?文学理论真的要退出思想和时代的舞台了吗?文学理论“科学派”的诞生,使上述问题得到了有效的回应,文学理论的未来与发展方向,也在其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学科话语的整体性反思”与“科学”维度的重拾下愈发清晰和明朗。
“正如大多数哲学谬论一样,困惑的结果总是产生于显而易见的开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特别小心对待这个‘显而易见的开端’,因为正是从这儿起,事情才走上了歧路”[1]。这句话好似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一时间激起千层浪。研究者纷纷对所属学科的“开端”及其“显而易见”进行溯源和反思,来自证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在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的转折点又产生了新的分歧,有人提倡“科学”,有人坚持“经验”,僵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文学理论的研究也陷入这种纠结之中。当问题难以继续研究时,逃避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一时间“碎片化”、“后化”、“文化”的研究成为理论研究者的新宠,但这表面的繁荣实则是学科走向衰弱的开始。
“科学派”以“元科学”、“元哲学”为借鉴,以对学科性质、基本概念、基本范畴与范式转换的梳理与厘清为理论建设的出发点,通过对文学理论“金字塔”中元理论的深入钻研,对学科整体及整体性做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反思与批判,并坚定地认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重拾科学精神是不可或缺的,批评了反对在研究中引入“科学”的观点。在“科学派”的相关著作中,研究者指出诸多关于“科学”的论争犯了简单对等与指向混淆的错误,而极力排斥“科学”则不仅是受到文学“救亡”情绪的左右,更困于简单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及模式中暗含的等级秩序与暴力逻辑的束缚,妄图“以暴制暴”。反对者认为在文学理论研究甚至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大谈所谓“科学”不是“救”而是“毁”,是自我的“堕落”,这是对“科学”的污名。他们所反对,与其说是“科学”,不如称为“科学残余”或“砍掉脑袋的科学”更贴切,因为它早已丧失了内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质”,成为一种硬的、僵化的存在。因为某一部分或阶段出现了误差就断然否决“科学”本身,就会犯因噎废食的错误。“科学派”基于大量资料的整合与话语回溯,得出结论“人文学科形成的过程表明,科学是内含于人文之中的,二者是合而为一的”[2]。可以说,文学理论研究中“科学”的重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所必需的,因为科学是“一种以人的存在为根本目的的不断发展的特殊的文化认知过程”[3]。
在重拾科学精神之上,还要架构历史维度,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将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大潮中,继续以开放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姿态为其导航。在当下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历史维度的缺席导致“抛弃历史意识,主观臆断,以某种预设的观点来肢解历史的情况相当普遍”,这种“史”、“论”分离的研究策略,使文论成为“无源之水”,丧失自身的“实践品格”,极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4]。历史维度不是历史相对主义,引入它只是希望在其“干预”下,使具体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入,从传统中借鉴,挖掘特殊性,谋求发展。在同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中,促进理论自身的完善,使中国当代文论在具有创新性、前沿性的同时又能显现厚重的“历史感”。
科学精神与历史维度在横纵之间为文论的发展设立了开放的、未完成也永不会完成的框架,使其在历史中透析科学的内蕴,在科学中贯通古今中外,预判未来。在这样一种互证互助的态势下,文学理论的研究也会因为保持了自身的学科性与科学性、可理解性与可沟通性而愈发清澈与澄明
二、复返文学基点,回归基础研究
文学与基础研究可谓是文学理论生存与发展的两块基石,而对文学的坚守与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就是“科学派”提供的第二点启示。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理论应该是一个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学科范畴,在学科化的过程中,应形成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问题系统及其演化规律。恰恰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文学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困境:学科自性特征和独立性日益丧失”[5]。无论是以往的“寄生”地位,还是当下的“交叉”与“他者化”现状,文学理论的学科位置都十分尴尬,无法独立自身,这对于一个学科的界定和发展而言是非常可怕的。故此,“科学派”力求为文学理论进行学科定位与系统框架建设,使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肯定。“科学派”不否认以往的学科化、专业化限制了学科的发展,也不否认跨越与交叉为学科带来的机遇,更认为“交叉”与“跨越”是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承认“交叉”与“跨越”的目的性地位,它们对文论研究而言只能是手段、方法,真正的目的是回到学科自身。他者只是一个参照维度,不能取代主体位置,否则就是本末倒置,造成研究对象的错位与结论的偏离。最好的约束就是回到文学基点,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以往对于文学理论的苛责,很大一部分是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脱离了实际,但这恰好反衬出指责者未能正确理解文
学理论真正的对象是什么的失误。文学理论的真正对象应该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科学派之称为“亚理论”),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在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反思与探索中完成自身的建构。有的学者认为理论应该联系实际,作为文本形态存在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就是文学理论的“实际”,如果文学理论所汲取的资源对象不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理论可以忽视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而是强调对“文学现场”保持一种“无隔”的距离。
其次就是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基础研究即是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它有别于应用性研究,涵盖学科的基本问题视域、基本范式结构和普遍运作规律等,这样的一种重视是“科学派”对于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偏热点、偏时髦及泛文化的纠正与反拨。重新回归基础研究不是文学理论的倒退,而是为自身谋生存的必要手段与必须途径。因为当一个学科对自身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处于“失语”状态时,其存在的合法性就遭到质疑和抨击。理论的缺席是一切狂欢之后的学科根基动摇甚至坍塌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基础研究的回避与忽视,则是为理论的衰败奏响哀乐,基础研究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是重中之重,无可替代。
在知识爆炸、批评泛化、学史扩容的当下,如何选取文学理论的对象尤为重要,必须在泛化之中选取文学理论真正需要的、真正利于学理发展的,否则一切只是徒劳。守住文学基点,坚持基础研究,代表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与清醒的认识,这不是倒退,而是基于理论家与理论共同体、学科责任与学术追求而提出的两条“金线”。在辩证的基础上、抓住主导,双管齐下,以期达到治标更治本的效果。守住不意味着排斥,基础不代表不关注前沿,彼此自成一体,互相催发,才能返本开新。
三、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学派争鸣
对理论而言,自身问题的确立与研究主体的钻研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派”站在这一立场提倡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学派争鸣是及时的,也是必需的,这也是其为建设呈现的第三点启示。
一个好问题、真问题的提出是理论发展的助推剂,而“一种理论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所能做户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它产生的新问题”[6]。然而国内学界的问题意识却并不鲜明,针对理论研究的“浮躁风”与“空话风”,“科学派”提出强化问题意识就是希望用研究主体的“有效”研究,切实促进理论的发展。因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性质不在于描述而在于建构和反思,在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于不停留在对‘是什么’的说明上,而是去追问‘为什么’和‘应如何’”[7]。强化问题意识意味着研究主体不能只安心于做理论被动的接受者和阐释者,而是要成为主动的追问者与探索者,不断对理论自身进行质疑、反思和追问,这不仅是主体的权力,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问题的研究与没有灵魂的生命几乎是同一个意思。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是文学理论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8]。
理论的发展仅凭借不断衍生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固然重要,可没有研究主体对其探讨、争论,问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可仅靠个体间的争鸣,从深度、维度、广度与影响力而言作用又不甚明显,学派则可以化缺为优。当下的研究主体往往是各自为战,这极易导致理论研究趋向“分散化”与“碎片化”,故此“科学派”提出学派划分的倡议是必要的。有的学者曾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大致划分为七个流派萌芽和雏形(“唯物派”、“实践派”、“科学派”、“审美派”、“宏观派”、“形式派”、“生态派”),虽略显简单,但确是一种拓荒的努力[9]。这样的学派呈现,不是为了划分“领地”,也不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利益秩序”,而是希冀以这样的方式促使文学理论的研究自觉化、全面化、集中化,在争鸣中深化问题,促进理论的长足发展。
四、结语
“科学派”文学理论以科学精神为基始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支柱,以问题意识为核心,以实践品格为立足点,以学派划分为导向,希望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大环中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同在,异质性与异构性同存的多维度的良性循环空间。这必将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为中国问题的凸显和解决,为中国语境的呈现与分析、为中国化的全面推进添上厚重而深刻的一笔。
[1][美]H.G.布洛克,滕守尧译.美学新解[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02.
[2]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
[3]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7.
[4]金永兵.后理论时代的中国文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70.
[5]金永兵.后理论时代的中国文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60.
[6]转引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9.
[7]李龙.理论前提的批判和学科话语的整体性反思[J].《扎根》第二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95.
[8]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9.
[9]参见董学文,金永兵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2008:50~81.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