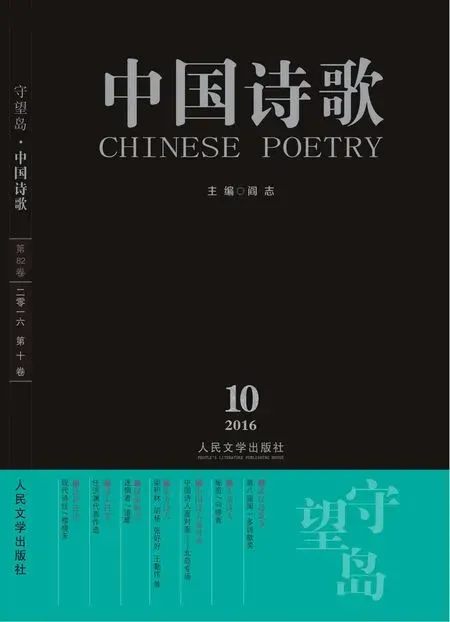中国诗人面对面
——北岛专场
□主讲人:北 岛
主持人:阎 志
中国诗人面对面
——北岛专场
□主讲人:北 岛
主持人:阎 志
时间:2016年8月25日 地点:卓尔书店
阎志:谢谢各位读者。新的一年,我们再次相聚在了卓尔书店,又迎来了我们的武汉诗歌节,迎来了我们的首场“诗人面对面”。请允许我用我的罗田普通话,为大家主持今天的活动。相信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诗人,在座的各位朋友都认识。这是一个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都绕不过去的名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一个转折点。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他来到武汉诗歌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北岛老师!下面,请北岛老师跟我们的读者先说几句,欢迎。
北岛:朋友们,首先,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我变成一个明星了。其实这些年来,我很少参加活动。四年前我中风过,所以言语不多。今天我回到了武汉,武汉在我记忆中很确切的时间是1976年,那时候我在武汉,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可以说,我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下面,我会讲一讲我的背景,写作,和我的生活。
阎志:我想先讲个故事。在三十年前,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做梦都想要一本书。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他梦了十年,没有找到这本书。有次帮朋友搬家,无意中看到这本书,非常高兴,酒也不想喝,酬劳也不想要,只希望主人能够把书送给他。这个小伙子就是当年的我,那本书就是《北岛诗选》。下面,我想代表大家问几个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北岛老师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然后,我会把话筒交给你们。首先,我想问北岛老师,一个人的选择在关键时刻是非常重要的,您选择了诗歌,应该说对中国诗歌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您为什么选择诗歌?在七十年代,明明有很多看起来更安全、更有前景的选择。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谢谢。
北岛: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职业。我原来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后来在高一的时候,遇到文革学校关闭了,当时所有的学校都关闭了。我从1969年开始当建筑工人,从1969年到1980年,一共11年。其中我有6年是混凝土工,另外5年是铁匠。可以说,我的过去和文革有一定的关系,我的写作和我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文革,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69年所有的中学和大学全部关闭了。可以说,当时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是农民,我是另外的百分之十,我是工人。我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六建,当时工作地点在北京郊区,也即现在的河北。我最初的写作和毛泽东有一定的关系,毛泽东喜欢古诗词,写得很好,他的37首诗我都能背下来。当时我的很多同学都在写古诗词,我也写,但是写得不好。主要是抒发情感,怀旧和告别。怀旧是怀念家乡,告别是因为面临分别,同学们都分配到不同的地区和厂房。我还记得在1970年的春天,当时我们三个同班同学,在北京颐和园的后湖划船,其中一个同学读了一首诗,把我给震住了,作者就是食指。所以可以说,食指就是中国朦胧诗的第一人。食指只比我大一岁,1948年出生,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字。当时他的诗歌都是手抄本,我也抄过,抄的过程中,我提出一个可能性:我为什么不写新诗呢?所以,我从1970年开始写新诗。我手上现在拿的这本诗集,是我1972年到1988年间的诗歌作品。还有一些1972年之前的作品,我觉得水平不太够,就把它们淘汰掉了。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诗歌的可能性,就是从文革开始的,如果没有文革,那我还是一个普通学生。我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当时数学成绩特别差,未必能考上大学。我原本就不喜欢当学生,之前在北京一所很一般的学校,后来到了北京十三中,再后来到了北京四中。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所有的学校都关闭了。我觉得挺好,终于不用上学了。所以我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其实不光是我,很多当代的这一批诗人,根本不用上学。在座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在上学,我认为,上学把很多人都毁掉了。包括阎志,你也写诗吧?
阎志:对。
北岛:你也没好好读书吧?(大家笑)
阎志:当时主要时间都用来写诗和谈恋爱。
北岛:你要是读硕士和博士就惨了。我们现在谈论文革,文革其实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不讨论这段历史。作为我们来说,在那个特别的时代,特别的背景下,我们是一种很独特的可能性。我当建筑工人的时候,跟上百人睡在一个帐篷里,条件特别差,我们睡的是一种通铺,每个人就一米宽。每天晚上我用一盏小灯来照明,找几块泡沫砖当临时书桌,用来阅读。所以,我的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那时候,根本看不到希望,也不可能发表。当时我有三到五个朋友,如果传播出去的话,会有很大危险。
阎志:今天有很多同学在这里,北岛老师说的读书和不读书,你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北岛老师有两句话很经典,一句是“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另外一句是“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这两句话都是您说的吧?
北岛:对。
阎志: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所以想和您讨论一下诗的功效。它对于我们的人生和生命,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北岛:很多人都在讨论物质性,讨论一件事情的有用或者没用。我觉得诗是童心的一部分。我有一个朋友黄永玉,他亲自绘编了一本《给孩子的动物寓言》,他的画看起来就像孩子画的,他是一个很有童心的人。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们也在写诗,读诗,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有一点童心。刚才阎志念的句子并不是我的诗,是我的一篇散文《波兰来客》中的句子。
阎志:对,是《波兰来客》。诗歌需要童心,所以北岛老师编了一本《给孩子的诗》,这本书非常受欢迎,几年前上市时我就买了,今天在卓尔书店有售,欢迎大家去买(大家笑)。刚才,北岛老师在开场白里提过,他和湖北、武汉有着很深的渊源,昨天我们聊天时得知,在民国时期,他的外公在湖北钟祥市捐献了一所学校,他的亲舅舅做过解放后武汉市的副市长。您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和武汉这座城市,和湖北的一些关系,以及对这座城市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后的印象。
北岛:我的外公叫孙海霞,他当时是辛亥革命的功臣,用黄兴奖励的一千大洋,在钟祥建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现在还在,我的母亲和许多亲戚都在钟祥长大。在我当建筑工人的时候,1969年至1972年,我的父母在沙洋五七干校,我经常去那里看望他们,顺便到处旅行,从长江到上海、再到黄山等地。在1976年,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我的妹妹珊珊,在襄樊附近的一条河里去世了,为了救一个女孩而牺牲。四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来过武汉。现在的武汉完全变了,记忆中的很多印象都不见了。原来印象中比较多的是小商店、码头、火车站、大桥等等。
阎志:北岛老师曾经说过,诗歌应该远离宗教。但我觉得,诗歌与宗教还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诗歌对于很多人,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是一种信仰,同时宗教里的很多文本使用的是诗的语言,所以想请您分享一下诗和宗教的关系,或者您的一些看法。
北岛:墨西哥诗人帕斯曾经说过,诗歌是在革命与宗教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我同意。我认为宗教是一种集体想象,而诗歌是个人想象。如果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除了佛教,宗教之间一直战乱不息。而诗歌不存在这些,它是属于个人的想象。我在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上,曾讨论过这个问题。
阎志:您曾提到过,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了能量而走向衰竭。也谈到过由于商业化与历史形态的博弈与合谋,造成了词和物的严重脱节。那么现在您怎么看待网络对诗歌的影响?
北岛: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叫网络时代。很巧,1972年我写过一首诗叫做《生活》,就一个字“网”。当时没想这么远。结果现在,我们都被网络时代连接在一起了。对于网络的风行,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头,仅仅是刚开始。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词叫“互联网”,就是说你买东西根本看不到实物,没有实体店,这个比较可怕。不过我也承认,网络工具有它的优势。比如微信,我每天也在看,微信上消息太多了,不管是真是假,感觉比报纸上的靠谱一点。它的渠道更丰富,传播也更便捷。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工具,诗歌走到了大众面前。公众号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诗歌的印象。以前诗歌的读者是非常小众的,现在几乎是非常普遍。
阎志:对,以前一本诗集能印上一万本就属于畅销了,现在您的诗发到公众号上,阅读量很容易就上万。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网络,感谢微信。
北岛:但依然需要警惕。诗有诗的难度,现在写诗好像太容易了,顺手拈来,几分钟写完就发出去了,由此造成了很多语言的垃圾。我现在对中文表示怀疑,是因为互联网上阅读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没认真读书,纸媒明显的少了。网络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它的破碎化,没有一个完整的对知识的理解。
阎志:对,所以还是要看书,还是要去书店。
北岛:我在这里也做一下广告。我们正在编的《给孩子的诗》等系列,现在已经出版到第五本了。作为主编,我计划编到三十本,希望留给孩子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有很大的问题,教材比较僵化,没有想象力,把孩子都毁掉了。
阎志:同样在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到明年就是中国新诗百年了,这个题目比较大。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新诗百年?
北岛:我刚刚从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回来,获得了诗歌节颁发的一个奖。其实有点尴尬,因为我不喜欢徐志摩。但是,我们还是要向他们致敬,像冰心、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等,他们是很重要的现代诗人,承前启后,像台阶一样延续着新诗的生命。他们是新诗链条中的一部分,与我们是链接在一起的。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才走到今天,所以提到新诗一百年,我们应该有所反省:我们曾经有差不多三十年时间,诗歌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
阎志:北岛老师认为,中国新诗是有传统和传承的。但是在当年,曾经有一批小子,跳出来号称要超过您,打倒您,您当时是怎么看待的?
北岛:那是1985年左右吧,当时有一个说法叫“打倒舒婷,pass北岛”。当时那一瞬间我也挺生气的,但是后来想想,应该是这样,所有的一代人都会面临挑战。就像当年我对艾青他们那一代人的诗歌,也质疑过。我认为,诗歌正是需要一种新的形式、语言和想象,才不会永远停止在那儿。
阎志:您怎么看待自己在百年新诗里的位置和作用?
北岛:回过头来看自己,我的写作从1970年开始,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但是我的命和运是相互冲突的吧,原本我是一个建筑工人,但我不相信命。那时候写作条件艰苦,也不能出版,而且有政治危险。后来我们顶着挑战,在1978年办了一本杂志叫《今天》。这本杂志由一批当时重要的地下诗人创办,比如多多、食指等,他们可以说是地下文学的潜流。《今天》杂志我们从500本起印,后来增加到1000本。在中国的当代诗歌中,可以说《今天》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那一时期的诗歌被称做朦胧诗派,但我认为叫今天诗派更合适,因为所有的诗,最初都是在那里出版的。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不理解诗歌,以为诗歌就是语言,但我认为诗歌改变了语言。诗就是诗,语言可以玩文字游戏,诗不可以,它从根本上找到了语言的钥匙或者密码。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当时的大学生们,包括很多的官员、商人们,都读诗和写诗,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歌从那时开启了一轮高潮。到今天,诗歌依然面临新的可能性,我们的写作依然面临新的挑战,譬如网络时代的信息碎片化等。
阎志:诗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思想的解放从语言的解放开始。我们当时在学校其实有很大的痛苦,李少君应该与我有同感。当年流行写诗送给女孩,我们就抄男诗人的诗,男诗人中当时最牛的就是北岛,但是我们很难找到您的爱情诗,后来只好去抄女诗人的诗,抄舒婷的诗。所以我想问,您当年怎么不多写几首爱情诗呢?
北岛:其实我写过的爱情诗有十几首吧。
阎志:不够用(大家笑)。
北岛:我记得跟孩子们说过,对于诗歌,爱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很多人就是因为爱情才写的诗。我估计你也是吧?
阎志:是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写给女孩子的。那么,您怎么看待与您同时代的那几位比较重要的诗人?比如顾城、舒婷。
北岛: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就说舒婷吧,那时候我们用通信联系。那些信我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舒婷留下来了。其中一封信上,我写了一首诗叫《一切》,送给舒婷。
阎志:去年舒婷就坐在您现在的位子上,她很怀念您。
北岛:我马上要参加鼓浪屿诗歌节,以前答应过她但没去,这次一定要去。
阎志:舒婷去年曾说,她是中国诗坛的老外婆。那么,您是诗坛的什么?
北岛:我是老青年(大家笑)。
阎志:北岛老师还有一个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教授。您怎么看待香港地区的文学创作?
北岛:2007年以前我在美国呆了14年。2007年我搬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香港是一个极度商业化的社会,几乎看不到一本诗集。从2008年开始,我决定筹备香港国际诗歌节,这个诗歌节隔年举办一次,从2009、2011、2013、2015到明年的2017,我认为这是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诗歌节之一,因为它的出版物和工作量非常大。我们把每一个参会的诗人的诗都以英文、中文和母语的形式出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叫国际诗人在香港,我希望能够带动香港的诗歌氛围。香港有一个优势是它的自由度,举办这个活动之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跨越地界到不同的城市,和当地分工合作来完成诗歌节。2015年在成都举办,当时诗歌节的分会场是一个叫方所的书店,居然来了一千多人。所以我想,通过香港和内地的互动合作,能够推动诗歌的影响力。我也考虑到,将来是不是要在武汉设立一个分会场。
阎志:大家鼓掌欢迎吧。香港何其有幸,一片诗歌荒漠来了一个北岛,马上就变得高大上。我现在想趁这个机会,做一个中场的转场,想请您读两首您喜欢的诗。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交给下面的读者。
北岛:你喜欢哪一首?
阎志:很多。我认为《一切》就很好。
北岛:好,那就《一切》。
阎志:等一会儿北岛老师读完了,下面的读者如果想上来朗诵也可以,但是最好不要拿书,要背下来。
北岛:我先介绍一下《一切》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这首诗写于1977年,那一年是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时间段,也和我个人的命运紧密相关。我的妹妹珊珊是1976年7月27日去世的,这首诗是一年以后写的。
(清了清嗓子)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掌声响起)
北岛:我再读一首诗。这首诗写于1990年,当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非常的孤独。今天在这里,我被你们簇拥,快成为明星了。当时在房间里,只有我和椅子,我写了一首诗,叫做《乡音》。
(稍作停顿)乡音/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掌声响起)
阎志:好。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读者。大家可以向北岛老师提问。
读者一:您能说一下,创作《回答》这首诗的历史背景吗?您当时主要想表达什么?请尽量具体而不要用诗性的语言来回答。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对这首诗的感情变化?
北岛:这首诗的初稿是在1972年,当时的名字叫《告诉你,世界》,后来在1976年做了修改,再后来到1978年创办《今天》杂志之前,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并且定稿。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定稿。我最早的作品有点类似情诗,后来有了很大变化。
阎志:下面把话筒交给我们的“新发现”诗歌夏令营学员。
读者二:首先向北岛老师表示敬意。十年前我上小学时看到《回答》,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新诗,带来很大震撼,没想到今天见到真人了。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看资料我得知,当年的朦胧诗派,也即您前面说的今天诗派,有三个崛起之说,是三个批评家提出来的,当时受到了中国文坛和诗坛的很大质疑,在这种纷争中,甚至有人受到了迫害。我想知道当时朦胧诗派面临这些困境时,您是怎么看待并且面对的?第二个,在您之后,出现了第三代诗人,以及后来的新生代诗人,到现在的80后和90后诗人,马上中国新诗就一百年了,您对汉语诗歌的未来怎么看?
北岛:你刚才说的三个崛起,一个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个是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个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朦胧诗地位的被认可,得益于“三个崛起”的理论支持。在当时,朦胧诗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争论反而起到很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朦胧诗不可能引起那么大的影响。但现在看来,这些争论几乎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去读那些书了。第二个问题,汉语诗歌的未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新诗百年,是从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的新诗开始算的,如果从三千年前的《诗经》开始算,新诗在它面前就像个孩子,只是从童年到青少年的过程。对于诗歌,我的尺度和人们不同,人们常说五年,十年,换一代人。但我认为,应该以一百年为一个尺度,所以不要着急,还早着呢。一代一代下去,还会出现重要诗人。我们只不过是铺路石吧,我自己也是铺路石之一。
阎志:下面,请我们的两位武汉读者来背诵北岛老师的诗吧。
读者三:北岛老师,我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初中时就学过您的诗。我今天想朗诵《一束》和《回答》。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一束/在我和世界之间/你是海湾,是帆/是缆绳忠实的两端/你是喷泉,是风/是童年清脆的呼喊/在我和世界之间/你是画框,是窗口/是开满野花的田园/你是呼吸,是床头/是陪伴星星的夜晚/在我和世界之间/你是日历,是罗盘/是暗中滑行的光线/你是履历,是书签/是写在最后的序言/在我和世界之间/你是纱幕,是雾/是映入梦中的灯盏/你是口笛,是无言之歌/是石雕低垂的眼帘/在我和世界之间/你是鸿沟,是池沼/是正在下陷的深渊/你是栅栏,是墙垣/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我太激动了,谢谢大家。
阎志:别激动。
读者三:我初中的时候就喜欢北岛老师,把他的《回答》抄在本子上。
阎志:这一本《给孩子的诗》,是北岛老师主编的,送给你的孩子。
读者三:谢谢。祝北岛老师健康平安。
阎志:还有谁愿意上来背诵?
读者四:我想背诵北岛老师的《明天,不》。明天,不/这不是告别/因为我们并没有相见/尽管影子和影子/曾在路上叠在一起/像一个孤零零的逃犯/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里结束吧。
读者五:我不背诵,但想向北岛老师提问。刚才您说,对新诗的未来很期待。但我比较悲观,感觉新诗目前内忧外患。中国第一本意识流小说《酒徒》,说新诗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孤儿,它不被人看好,缺少关注,这是外患的一个方面。内忧是对于新诗的韵律、节奏,没有太多的人尝试着去建设它,除了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人,他们提出了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有很多人写作新诗,没有规矩和尊崇,由此产生的乱象您怎么看?对于我们年轻人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建议?
北岛:如果把新诗百年比作一座台阶的话,我认为我们还是要比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他们高一截。我们一直在往前走,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诗歌一定要押韵。诗歌变化无穷,并不能靠纯粹的押韵来解决。
读者五:但我感觉现在很多诗就像白话,口水体。
北岛: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你要找到最好的诗来读,不能读最差的,这个很重要。比如闻一多诗歌奖,奖励某一个诗人,这就是推荐诗人和他的作品,引起人们关注。
阎志:时间有限。下面还有2个问题。
读者六:我来背诵北岛老师的《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冰上的月光/已从河面上溢出/走吧/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
我还想提问。第一个,您认为诗歌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二个,现在很多人都说“诗与远方”,我作为一个经常写点打油诗的人,体会是,诗不必远方,生活就可以是诗。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人需要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关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谢谢。
北岛: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和时代的关系。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假如你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能够写作就很不容易,你的生活注定你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诗人。我认为诗产生于痛苦中,如果你过得太舒服,太顺遂了,你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诗人。
读者七:我背一首北岛老师的《无题》诗。永远如此/火,是冬天的中心/当树林燃烧/只有那不肯围拢的石头/狂吠不已/挂在鹿角上的钟停了/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老去。背完了,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北岛老师,刚才听到您背诵《乡音》,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和感动的。请问,乡愁是否是您写作中永恒的主题?
北岛:对于乡愁,其实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我们现在回不到自己的家乡了,这是我们面临的同样问题,比如我回到武汉,现在的武汉跟我记忆中四十年前的样子相比,完全是另外一座城市。再回到我出生的北京,根本找不着北,想去一个地方,只有依靠打出租车。乡愁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的乡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前面提问的小男孩提到的诗歌韵律的问题,如果你读我的《乡音》会发现,这首诗的一三五七九句,和二四六八句之间,是有一种结构处理的,这就是形式感。
读者八:刚才北岛老师说,宗教是一种集体想象,诗歌是一种个人想象,我很有感触。当我们信仰国家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公民,当我们信仰宗教的时候,我们属于神,当我们信仰诗歌的时候,我们属于自己。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环境下,如果我们想接近自由,那么我们就应该接近诗歌,接近诗意的生活。现在有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小问题。之前北岛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诗歌意味着精神世界的可靠性与持久性,而精神需要传承,关于成功,用当前的话来说它就是一种象征,比如我们看到这首诗的时候,首先不是问这是谁写的,而是说,这很北岛,或者这很李白。北岛老师说过的话,已经成为一个流派或一种象征。我在网络上搜过您的诗,有人说那是您写的,有人说不是,我今天想把这首诗的第一段读出来,请您帮我鉴定: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安静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问题/问南方,问故里,问希望,问距离。
北岛:这个应该由读者来鉴定吧,这么差的诗肯定不是我写的。(大家笑)
阎志:剩下的时间,希望交给我们邀请来的外国诗人朋友,日本的竹内新老师,新加坡的陈先生,韩国的韩成礼女士,你们有什么问题?
竹内新(日本):北岛先生,你刚才谈到你是老青年,我比你长两岁,我觉得我应该是老人家了。但你不可能一直是老青年,也有变成老人家的一天。请问当你变成老人家的时候,你的写作主题是什么?
北岛:我们说的不是年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心灵上我认为我永远是年轻的。现在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60岁以后,我的写作因为中风停止了三年,后来我开始写长诗,这首长诗里有我的个人经历和漂泊的生活痕迹,它们交叉在一起,不可分割。我希望到70岁时能把它完成。
竹内新(日本):我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肌肉在萎缩,身体在衰老。随着身体的衰落,我的头脑是否还能健全清醒地去写作,这是我面临的一个挑战。
北岛:我在四年前中风,语言水平几乎降到零,需要看图识字,从认识火车、汽车开始,我女儿帮我训练。我认为,你一定要坚定信念,要坚持。直到我找到第八个大夫,他是一名中医,我相信中医,在他的帮助治疗下,从去年开始,我的语言开始恢复正常。虽然口语部分还是不太完整,但是写作没有问题。
阎志: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交给李强校长吧,你代表孩子们来提问。
李强:我有一个提议,北岛老师前面说想把香港国际诗歌节放在武汉举办,干脆就在江汉大学办吧,我是江汉大学的校长。
阎志:这个问题私下再议(大家笑)。在非常愉快的氛围中,我们与北岛老师一个半小时的互动就此结束了,感谢北岛老师和广大读者。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排队,请北岛老师签名。
(整理:熊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