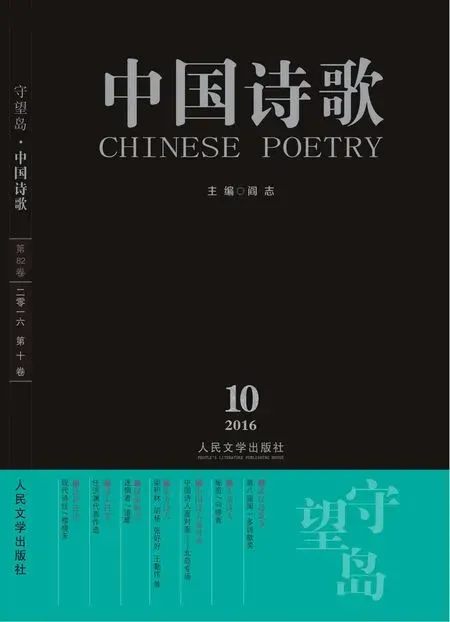现代诗经
□穆晓禾
现代诗经
□穆晓禾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我以为诗就是这样诞生的。
诗人的劳动是一种“夜”的劳动。当然,写作能像性一样,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尤其,灵感是瞬间的,完成一首诗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夜,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创作的空间并不单指狭义上的夜晚,但它一定会具有夜晚的静谧心态。所以,诗人经常在夜晚储备和沉淀情感,从夜出发又抵达夜的世界。
生活需要诗意地栖居,但生活必须造就诗意的居舍,拥有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先拥有一颗诗心,而诗心依附的是个人的知识框架,对生活的感悟程度。
艺术是有层次的,感悟高低的不同,诗艺表现出来的形式就不一样。因此,有的诗,只能悦己;有的诗,却可以娱人。
那些天生具有才华和天分的人,并非一定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像流星一样一闪而逝的天才还少吗,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人;只有那些以持久不断的勤奋和最认真的对文字训练有素的技能去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和力量的人,才能取得大众对诗人这个称号的满意程度,也才能取得个人的巨大成果。《浮士德》,就是这样的一个明证。
诗人与常人的分别在于,看待事物,常人用的是眼睛,诗人用的是心灵。
天才就是恒心。一个诗人注重质,也要注重量,没有量的诗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怀疑,诗只是曾经在他那里落居过,而没有长久地停留下来。
不断重复是在艺术领域获得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正如我们的生活一样。诗歌亦然,在一个阶段可能会重复同一种风格的文字,有时候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同一个题材,甚至连语言都有复制的痕迹。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突破自我,才能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向上发展,而后有所进步。坚持写作,像开车上山一样,迂回中攀往顶峰。
有人说,这是一个饿死诗人的时代。缘由,诗歌不值钱,没有人可以专事诗歌写作来养活自己。而献身和追求艺术的人,是不考虑他创作下的东西究竟能卖几个钱的,他们写下的东西比生命还重要,甚至比生存还有价值,诗歌就属于这样的一种艺术。而又有不少人,常打着“先解决生存”的旗号不择手段地搞钱,以为拥有资产百万才能更好地展开自己的思想,其实他们根本不爱艺术,不爱与钱无关的东西;他们以为自己很懂得艺术,其实艺术离他们很远,可能一生他们都不知艺术为何物,他们达不到那个境界,他们被艺术以外的东西蒙蔽了。一个成功的人与一个成功的诗人,他们的区别根本不在对金钱拥有的多与少上,钱不是衡量诗歌的基本标准。
诗人,是疯子,是神经病。他们疯在对金钱的不追逐,疯在不按常人的行为规范出牌,疯在活在梦幻和想象里,疯在如醉如痴地歌唱,疯在有孩童般的纯洁和天真。他们时而偏激,时而激赏,时而迷狂和冲动,他们只遵循心灵的需要,为艺术的精灵舞蹈,产生他们的诗篇。所以,世人说诗人是神经病,但他们又是正常的,他们是上帝的宠儿,是离上帝最近的那群人。
写诗是生命的一种现象,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理念。诗歌表达的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诗是有颜色的,可以溶入任何东西内,化为他们的骨血,并且开花结果。
诗,是美术院的模特,高贵,典雅,美丽,被人敬仰,专注,像一件圣品洗礼目视的大众。一旦,她出现在校外的某条街巷的门户内,或大别墅卧室的软床上,只要没有第三者,她便亮出自己的隐私。当模特拉灭灯也可以从事工作时,诗的下半身堂皇登场了。
如果,诗像灯谜一样,一下被猜中的话,大众便没有被语言击中的快感。有时候,一首诗就是一次梦境的再现,醒来,记得一些又忘记一些。所以,诗歌呈现的两种状态:被写出的和可能写出的。因此,我们欣赏石子投水的情景,我们更怀想那一波一波荡漾的水纹,向两岸滑逝的片刻。
写诗的人称做诗人,不是诗家。而写小说的人,却是作家或小说家。因为,诗最能考验灵魂的文字,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大众,无论你展现的是上身还是下身。由于,诗大都太短,那么几行,来不及说谎。像去圣庙的人们,忏悔也罢,祈祷也罢,在佛祖和上帝的面前,说的都是真心话。是个体生命介入诗歌,没人会逃离精神的需要,所以诗是诗人的墓志铭。
对一首诗歌的练习,犹如进入语境的一次历险。一座比天高的山峰,要么粉身碎骨,要么像西西弗一样,爱上这种执着的跋涉。一旦钟情于缪斯,诗人必须有勇气和信心,去探索和创造新的话语。其担当和延伸母语的劳作,做是危险的,不做却更为危险。
诗是一盏灯,诗人便是举灯人。没有诗的世界是黑暗的。他的诞生,不仅仅为了解释这个时代,还为更多的人照亮前途。当有人质疑生命的哲学意义,叫做诗人的那个人,刚好离你最近,所以诗歌始终承担了完成揭谜永恒的使命。
诗不是笑话,不是幽默,不是一种消遣娱乐的阅读,她是让你体验生命的有机状态,吸引你去找到灵魂的归宿,让你深刻地把握自己,并认识自己。人的天生好奇之心,将引导诗来答问一切,他们需要的是答案而不是过程。所以,真正的诗是撼动你,却不希求从你那里获得愉悦和快感。
当下的诗歌,只能从日常的境遇,个体生命外视和内省中,来挖掘和抵达人类命运的价值,以此拯救自身,再去导向他人幸福的历程。诗人对诗歌的阐述,依靠并达到人类整体生存的意义。
诗歌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一个人的乌托邦。那些为诗歌献身的诗人,最终否定的是生命,肯定的是诗歌。是什么断送了一个诗人的艺术和肉体生命?绝对不是诗歌。因为,我写,故我在;是否永恒与不朽,只有历史知道。
诗人不是先知,不能让我们预见明天的新闻,但诗人可作酒匠,酿造我们的生活之美。他能让我们听见大地内心的私语,他可以让我们看见高空星辰的亮光,他是黎明中用额头撞醒苍穹内那口钟的人。他用最简朴的文字,显示具有深邃事理和悠远哲思的诗篇。
诗人分大诗人和小诗人,而诗歌分好的诗歌和差的诗歌。只有好的诗歌才可以堆出一个优秀的诗人,差的诗歌并不有助于一个诗人的名誉。一般来说,只有能写出好的诗歌的人,才可心安理得地称为诗人,说到底诗人是以写下的诗歌被命名的。
一首诗歌不能让人懂,对于诗人无疑是一件悲哀的事。但中国当下又有几个陈东东那样的诗人,拒绝普通的读者,却并不妨碍他的诗歌进入当代的诗歌历史。如果只是为了研究而写作,那不是一般诗人所能够的。
其实,一首优秀的诗歌,就是把普通人的情感上升到一种艺术层次的表现。他把大众的感觉说了出来,言别人心中有,而又未能说出的,是他完成了这个工作,所以他走了出来,并给后人留下了某种作品,为大家欣赏。就是今天,我们的诗歌还是处于探索中,很多诗人也将涉猎那个领域,并背着当下不被众人理解的痛苦走了下来,伊沙就是一个例子。十年了,他的诗歌只呈现一种现象,仍没有被完全接受和容纳。
正经诗人,这个提法,有点意思。我想,可能是对于那些写粗口的诗人而言的吧,是个不错的想法,但可不可这样去定义?现当下诗歌论坛还不能完全确定地这样讲,不过我们是可以这样说,来区别某种定义和概念的。
诗歌也是记录当下事件的一个写作方式,那些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我们也可以用诗歌去表现下来,让一件有意义的事,用诗歌的语言,流传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诗歌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历史流传下来的写作,她一直就有这个功能。
对于一个成熟的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不会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什么韵律感、节奏感、音乐感的,但写的过程中,它们会是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想没有那些都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初学者,我不想说得过多,因为学习是一步步来的,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对那些不懂一点诗歌理论和技巧的写诗人,他们的诗歌写作不可能坚持太久的,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必须要补上那一课。
功夫在诗外。诗之灵感,出现的往往是一句两句话,不是整体,诗歌很难打好腹稿,给予结构和框架。所以,当灵感来临的时候,诗人还需要调动已有的储备素材,使之关联起来。一首诗歌,通常是不可预测的,只有顺着灵感,让诗句一一诞生。功夫在诗外的意思,也包含着这样的解释。
无论纵观历史,还是横看我们当代的诗人,诗人之死,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诗人之死,和诗歌是没有关系的,诗不会教人死亡,不会致人为她殉情。使诗人自杀的是生活,或是肉体上不可承受的痛苦,但绝不是诗歌。那些打着为“诗歌”殉情旗号的诗人,是伪诗人,是不了解诗歌的写过诗的人,或是正因为了解诗歌而忽悠大众的一种说法。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可是却有大致相同的两个诗人。诗人不可能成为群体,真正的诗人发出的是这个世界的独语,他们的声音往往是无法复制的。一般在一个诗人群体中只会发现一个人:惟有这个人才具有意义,他写下的诗篇是具有独立性的。世界就是这样,有红花,便会有大片大片的绿叶;诗人最终也会沦为陪衬,面对世界和生命,他又是渺小的。
要从事艺术,就得首先确立你的原则;要寻找艺术,就得先寻找为艺术的那种人生。真正的诗人,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到位。
诗歌有时候是不能解释的,但并非不可理解,像禅。诗歌像其他艺术一样,并不能被所有的人都理解,都共鸣;有些问题不能通过语言来交流,只能依靠体悟和心悟,而不同人的感悟是不一样的,一百个人眼里对诗歌的理解有一百个样。
一个诗人要尽力地去摆脱某诗人对自己的影响,不要陷入别人的写作模式,深不可拔,难以在风格、观念以及语言等方面拼力突围。我相信,在我们这代人身上,都打有席慕蓉和汪国真的烙印,并深受其害,弄到最后连诗都不会写了。受到错误的写作理念的影响,有时候是致命的。
一个诗人应该有自己的一套诗歌语言,一个诗人区别另一个诗人的标志,也往往在语言上,培养自己的诗歌语言是一个诗人最基本的要求。而仅有语言是不够的,即使操用同一种语言风格的诗人,他们的区别也更体现在对意境的把握上,惟有写出不同意境的诗人,这个人才能最终出列。
热爱艺术的人,要善良和真诚,要做到不故意去伤害别人,尤其作品更要做到这一点。诗人的心灵就是要表达生命的全程经历,诗歌就是滋润自己和他人的雨露,要做到对文字的洁净和公正,否则,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愿望,多么高的技巧,作品一旦有了瑕疵,便很难给人完美的感觉。
诗人应该是语言的提醒者,是艺术的守夜者;诗人,是世人皆醉惟他独醒的那个人;诗人的精神永远是孤独的,像头顶上空的星星一样,会发出光亮,燃烧自我,直至灰烬。
写诗是一种消耗心智的劳动,燃烧的是骨血,奉献的是盐质的泪水。诗人是为生活揭示出哲理的那个人,他的话往往是箴言,是真理。
诗人的自身经历不一定需要那么复杂,但他一定有复杂的阅历,他对周遭的事物是敏感的,他时常能感悟出别人的情感,并等同于自己。这样,诗人以超巨大的心灵,最终成就了他的诗篇。
突然发现,诗人是离死亡最近的一群人。他们的感悟往往是从死亡开始的,并能超越死亡,不惧怕死亡。所以,诗人的文字都具有生命感,他们专注的是美丽的生活,美好的愿望。诗人,一般都是经过重生的人,是可以穿梭在时光中发现各种隐秘的人。
最好的诗人用母语写作,母语不是方言,不是外来语,更不是世界语。诗人在自己与自己对话的时候,通常用的都是普通话,像梦中一样,大家能够听懂他任何语言,其实那便是诗的声音,有诗的功效。诗人,是那种可以辨别各种声音的人。
诗人的写作依靠的是灵魂和灵感,词只是负荷它们的工具,所以,有时候用什么词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所表达出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感动了,让我们歌唱的心灵倍感幸福。词的向度,是词根在七色键上跳动,犹如发出音乐之籁。
诗歌向上可以触到云朵、雨水和蓝天,向下可以触到花朵、晨露和大地。诗歌是所有事物联系的纽带,而诗人就是立于天地间那个大写的人,他是美的使者,光亮的携带者,幸福的传播者。
诗人是生活的目击者,诗人告诉你的却是一个诗意化的生活。诗人致使世人不再绝望,不再丧失信心,期待和等待的是一种健全的生活。
诗歌不是圣经,诗人也不是上帝,但真正的诗人是比上帝更能承担苦难的人,他具有天赋,他在精神上与民共处,运用天才式的文字,给大家带来灯盏,照亮前途,他不管路上有人与否。
诗人,在他自己伫立的地方歌唱,又能歌唱遥远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缺乏诗人的歌唱。因为,诗人居住的地方,四通八达,他能看见的地方超过了目及之处,所想之处。
一个民族,其语言中最纯洁的东西,就是诗歌。诗歌,是一种民族语言留存的最简洁的文字,它能承载其整个民族语言的精华和要义,因此,任何语言都能提炼出诗歌来,而诗歌对语言又能起到一种衍进作用。
是我选择了诗,而诗也正在慢慢地选择了我。即使,我去写一辈子诗歌,我也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因为真正的诗人与真正的人一样是罕见的。
因为诗的存在,人们才有了梦想;因为有了梦想,人们才有了明天;因为有了明天,现在人们才活得颇有意义。
尽管现在人们不再以当诗人为荣,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诗歌精神。在任何年代任何时期,人们都具有高贵的诗歌精神,诗意存活在人们的头脑中,潜伏在智慧源头的诗性,它会不时地荡漾在人们的心里。用诗歌精神孕育我们的生活,虽然不能无限地铺张开来,但我们是需要的,它供不应求。
诗是一种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越个人越好,越有独特性越好,越能代表自己越好。有人认为,个人化不好,没有普遍性,而恰恰相反,一个成熟的诗人,他照顾的不是一己情感,他常常能言别人心中有又未说出的那些东西,他的思想不可能是真空的,他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诗人,就是把梦从白云的高处,抵押到人间的那个人。是诗人把梦想变得真实起来,让梦不再虚无,不再是高空的肥皂泡。诗人的劳动就是把梦想变为现实的一种劳动,所以,诗人有时候活得又很辛苦。
现代诗歌在本质上呈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一己的精神世界。诗人的生命源于精神,他不是政客,更不是教育家,他不教化于人而是启迪人,他是诗和人的结合体,他是现实生活的自由者和见证人。诗人的本质是诗歌,诗歌是诗人的生命之本,是生命源头最本质的东西。
其实,在床与书桌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距离,就是一首诗的距离。
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的主体,诗人对世界观察和思考,从而诞生下语言。诗人的责任就是使逝去和即将逝去的那一切在诗中得到保留和延续。诗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
诗是一种高贵的艺术。诗是高度抽象和形象相结合的一种语言艺术,抽象赋予它以灵魂,形象使它飞翔起来。如果,一首诗歌不能让灵魂飞翔起来,不能给人以触动,让人心有所悸,那这首诗无疑是一首差诗。
把一个真正诗人的“心”刨开,我们看见的是整个的人类,我们从他那里便可了解这个世界。
诗歌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宗教。诗人虔诚地活着并部分地相信天堂的存在。诗人的阵痛来源于对生活的顿悟,诗人一生中不止得到一次重生,他常常有重新在世的感觉。
写诗是诗人对自我的一种流放,诗写到哪里,就流放到哪里。诗人的精神世界越是艰苦,诗给他的安慰就越大,诗人得到的力量就越大。诗人的苦,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精神的苦。
一个写诗歌的人对自己的诗歌必须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见,不应老是受别人思想的左右。诗歌就是诗人为自己塑造的另一张脸,可以摸到,但不可以看到,诗人经常面对的是自己的心,而不是从镜子中看见的那个人。其实,面具戴久了就很难摘下来,一个人写诗久了,他便会以为自己就是一个诗人。
写作的内在动力来源于灵魂莫名的恐惧,写诗则就是消解由恐惧带来的不安,并使之不至于扩大。
写诗,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救赎,救赎的首先是自我,然后才是他人。如果,有人从诗歌中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救赎,那是诗人写作之外的收获。
如果和一个诗人走得太近,你就会看不见他的灵魂;如果和一个诗人隔得太远,你就会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们不要总是去期待,让诗人来承担这个世界的无知,让诗人用烧灼的痛苦换取另一种阅读上的快感,让诗人燃烧自己的羽翅给我们光明。这是很残酷的。
如果面对一行行诗歌,我无话可说,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把握住诗歌这扇门里外的某个把柄。我祈祷,在我阅读的范围内,永远不要出现这一天。
诗依附于艺术,且在本质上趋向艺术;艺术依赖诗所赋予的生命而存在,并永远受诗的支配。这其中提到的诗,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那种。
诗是艺术中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会超越艺术,这是诗与艺术的实质性区别。
事物和自我借助某种概念来表达经验和认识,事物一旦被诗性认识所把握,便意味深长。
诗性直觉既不能通过运用和训练学到手,也不能通过运用和训练来改善,它取决于灵魂的某种天生的自由和想象力,取决于智性天生的力量,即使通过运用和训练学到的改善的也很难抵达艺术的殿堂。因此,这是优秀诗人和平庸诗人一生的区别,也是他们根本的分水岭。
没有诗能够单单只从概念的和逻辑的意义中获得它的生命。
当自然界的万物在某种刹那间走进了人的血液之中,并同他一道吐露出自己的情怀,这时,诗出现了,出现的还有艺术。
诗之自由,归根结底是创造性精神的自由。
梦,只有醒来的时候,才会感到格外轻松;诗,只有走进去身陷其内,才能抵达艺术的殿堂。
作品中的诗性意义,相当于诗人中的诗性经验;观其诗,就能看出其人对于诗艺的认知程度。这个尺度,同样适宜其他艺术。
一首诗产生的过程,就是诗人在直觉的精神状态下,层层领悟的过程,幸好诗歌是分行的,让思维有了递进的理由。
一首诗是清晰的还是朦胧的,它们的区别是相对于概念意义而言的。一首诗要么可能是朦胧的,要么可能是清晰的,其关键只在于诗性意义。这和普通读者的认知程度有关,却和读得懂读不懂没有关联。所谓概念,不能简言论之。
我所看见的现代绘画,还未将意象从智性中解放出来,未将感觉从自然的外形中完全地解放出来,连印象派的那些画家也难以创作出与意象主义的诗一样的等同物来。诗与画都是通过感觉生活,通过感觉说话,而感觉构成的事件的内涵,在诗与画那里,有着艺术表达的能性不同。但,诗使用的是词语,却不是色彩,所以诗走的距离更远,所能阐述的东西更多。
诗意产生于任何艺术中,如果某艺术没有了诗意,那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听音乐是感觉,而不是声音;我们看诗歌是从中体悟到什么,而不是直观文字。如果我们创造不出什么来,那么我们就要去学习别人已创造的东西,然后转化成自己的,所谓人之感情,也是渐渐受影响的。
意象不能没有新鲜感,老调重弹是没有意义的。但,意象不是放置在那儿,而是在那儿被发现。有时候同一个意象被不同的人发现,也或许在不同的时间里。诗,尤其是现代诗,担当着努力去发现意象这个艰巨的任务,它比其他任何艺术更加积极和向上。
最理想最完善的诗人能把他整个的心灵呈现给我们,读懂他,我们就读懂了整个人类。由是,艺术隶属于自然,形式隶属于内容,读者对诗人的钦佩隶属于读者对诗本身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