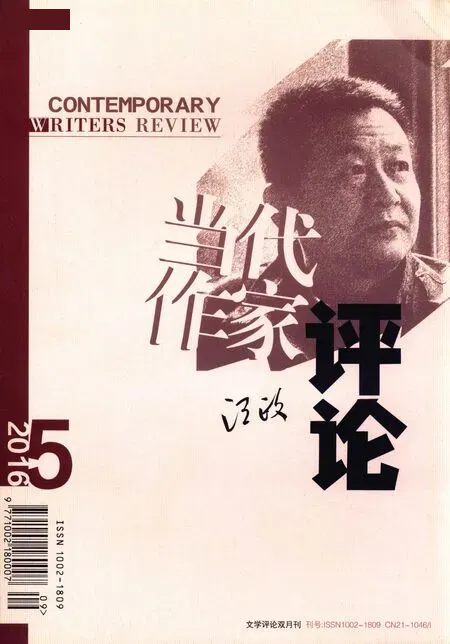超越与局限
——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分析①
吕彤邻著 汪宝荣译
超越与局限
——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分析①
吕彤邻著汪宝荣译
一、引言
在80年代末的中国实验作家中,莫言是一个突出的过渡性人物。他在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②莫言:《红高粱》,冬晓、黄子平、李陀、李子云编:《中国小说:一九八六》,香港,三联书店,1988。在中国读者群中和文学评论界迅速引起了轰动。③见张志忠:《莫言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翌年,中国“第五代导演”之一的张艺谋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1988年2月,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④有关小说与电影之间的联系,参见张暖忻:《红了高粱》,《当代电影》1988年第2期。莫言因而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第一位中国实验作家。此外,他在中国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远大于比他年轻的其他中国作家。⑤参见张志忠对此的介绍。鉴于《红高粱》对莫言的成名起到很大的作用,本章专门研究这部作品,以便把莫言的成功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
《红高粱》讲述了叙事人的爷爷(一个土匪)和奶奶(烧酒作坊的主人)之间的传奇浪漫史,以及他们在高密东北乡参与抗日战争的经历。奶奶刚满16岁时,就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了当地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患麻风病的单扁郎。余占鳌是抬花轿的轿夫之一,后来成了“我爷爷”。花轿行至半路遇到一个劫路人,试图强奸“我奶奶”,余占鳌救了她。三天后,余占鳌效仿被打死的劫匪的行径,在高粱地里强奸了“我奶奶”。至此,做爱与强奸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奶奶在认出侵犯她的人是余占鳌之后,似乎顺从了他。有趣的是,即使是男女间浪漫的激情,最初也要用强奸的方式表现出来。余占鳌后来杀死了奶奶的公公和她的合法丈夫。随后,“我奶奶”成了烧酒作坊的主人,余占鳌则当了土匪,并且占有了她。当他们的儿子——高粱地里一场风流的产物——长到14岁时,日本人来了。负责烧酒作坊的全面工作、同时可能是奶奶的情人的刘罗汉被日军剥皮零割示众。奶奶一心想为刘罗汉报仇,于是爷爷决定用土办法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伏击战打响前,奶奶挑着担子去给爷爷和他的游击队送吃的,却被日本人的机枪打死。她的儿子和情人藏在高粱地里,打死了一个有名的日军少将,于是伏击战结束了。
《红高粱》在意识形态、话语和叙事结构上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莫言把亡命徒和通奸者塑造成抗日英雄,是对既往抗战英雄人物谱系的突破。这部作品中占很大比重的超自然主义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即文学作品应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小说叙事人“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到故事涉及的事件中。此外,作者还加入了叙事人的父亲和奶奶的叙事视角。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又与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件交织在一起,使小说的叙事变得更为复杂。莫言对如此复杂的叙事视角的操纵,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常用的看似客观和客观化的叙事框架。尽管如此,与莫言的追随者们的作品相比,《红高粱》仍显得比较传统,不仅因为其“现实主义”的色彩更为鲜明,*李陀如此描述莫言小说的风格:“小说中所描绘的农村生活和人物,毕竟是我们现实农村生活的生动反映”。见李陀:《〈透明的红萝卜〉序》,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第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还因为作者想要颠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的意图过于明显,反而时时提醒我们小说中有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痕迹。
然而,这部小说发表时,正处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是它颇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小说处于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性的时刻,《红高粱》横空出世了。对当时厌倦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但仍惯读这类作品的国内读者来说,《红高粱》所展示的小说创新的形象,既不是过于陌生,也不是太令人震惊。此外,透过隐含的熟悉感的表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试图对读者期待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进行陌生化处理,并且通过纯粹的差异给读者带来震撼感,但这种差异并不需要读者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还有什么比这种差异更能吸引读者的呢?它既能满足读者对新奇事物的渴望,同时又不会引起读者对作品创新的本能的抵触。
《红高粱》与其试图颠覆的对象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明显的关联,及其在中国实验小说中所起的过渡作用,使得这部作品更为有趣。研究《红高粱》所用的某些手法,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尽管莫言和与他同时代的中国实验作家明显受到西方先锋文学的影响,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或对抗性的产物)。
对遥远过去的怀恋——表现在《红高粱》的叙事人只对其爷爷和奶奶的生活有兴趣——时常促使中国当代实验作家去探求一种明显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起源。由于这种起源并不能真的被追溯到某个遥远的过去,而是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参见王晓明:《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幻想出来的起源,一种与当代政治文化相反的镜像。
这种幻想出来的起源既游移不定,又不确定,因而从故事一开始就失落了。然而,起源的不可挽回的失落,并没有使莫言的作品不被一种历史定位更清晰的过去即正统的中国传统所纠缠。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过去,与历史根源的联结更为真实,因而与莫言作品中作为一种幻想出来的起源的过去截然不同。莫言更喜欢拒绝或至少隐藏历史性的过去(为便利起见,我称之为“第一过去”)。“第一过去”与作者对个性自我价值的信奉有冲突,而“第二过去”也即作者创造的虚构的起源则美化了他对个人主义的信奉。
通过反映共产党对中国旧传统的扬弃,被抛弃的“第一过去”的隐含意象存在于《红高粱》中。莫言通过叙事人的爷爷和奶奶的相互关系,对中国传统的性等级制度做了浪漫化处理,在功能上,莫言提供的这个实例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女权运动相匹配。莫言对叛逆力量的美化,表明了他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的蔑视,从而更为巧妙地承认了共产党开展的阶级斗争的遗产。
叙事人把他的奶奶誉为“个性解放的先驱”,说明“第一过去”即正统的中国传统正是莫言倾向于拒绝的,因为它限制了个人自由。这部小说讲述的毕竟是亡命徒和通奸者如何大胆挑战社会结构和婚姻制度的故事。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不那么显眼的主流意识形态衡量,作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某些习俗和做法是落后的。然而,在下文我们会看到,作者对正统的中国传统的有意拒斥未必能使他的小说世界从历史性的过去中分离开来。历史性的过去仍然间接控制着两个个性叛逆的后代,一是体现在其政治、社会等级制度上的共产党人,二是体现在其男性主义上的大部分中国当代实验作家。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遗产
从表面上看,投射在奶奶身上的互相矛盾的男性欲望,即渴望一个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妓女,*对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个主题的有趣分析,可参见蔡翔:《情与欲的对立——当代小说中的精神文化现象》,《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事实上,这种传统的自相矛盾的想法由于渴望女人获得有限的独立而变得更为复杂,而女性的有限独立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遗产。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鼓励中国作家塑造出叛逆、独立、敢作敢为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像《青春之歌》*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中的林道静那样的女学生,《红旗谱》*梁斌:《红旗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中的春兰那样的农村女孩,《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红岩》,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中的江姐那样的职业革命者,还是像《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中的小梅那样的家庭妇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通常都直言不讳、不守传统和性格坚强。这种强烈的个性也可以追溯到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她在和涓生热恋之初坚信自身的独立。
例如,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讲述名叫“母亲”的受压迫的农村妇女支持儿女参加革命,并把革命部队里的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儿女。*⑦冯德英:《苦菜花》,第37-38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在小说开头,族长责怪母亲让她的大女儿娟子参加社会活动。⑦在年老的族长看来,娟子的行为违反了儒家伦理,也就是以“三从四德”的名义禁止妇女在社会上扮演一个角色。在此意义上,一个妇女参加革命意味着相对于传统伦理,尤其儒家思想的独立。
《红高粱》中奶奶的独立也颠覆了儒家伦理。为人女的她不顺从父亲为她安排包办的婚姻,为人妻的她用一把锋利的剪刀不让丈夫近身,此外,她还与谋杀亲夫的男人通奸。换言之,奶奶事实上逾越了儒家伦理加诸中国妇女身上的“三从”的规矩。在这方面,奶奶就像她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那些革命姐妹。如果《苦菜花》中的族长活在《红高粱》的世界中,他会用同样的言辞呵斥奶奶,这位莫言笔下的“个性解放的先驱”,就像他呵斥冯德英作品中的女革命者娟子一样。
然而,革命女性挣脱传统的社会规范的桎梏而独立,是为了服务于共产主义事业,奶奶获得独立却显然是为了享受性自由。像男性希望一个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妓女的矛盾心理一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妇女独立概念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为了发出反抗旧社会的声音,受压迫的妇女需要独立,但妇女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有发声的自由。在此情形下,妇女针对旧社会的独立态度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严格约束。莫言对性“自由”妇女的塑造,继承了五四文学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独立女性的矛盾概念:《红高粱》中奶奶表面上享有的自由必须受到男性权力的严格限制。
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是根据个人感情选择爱人或丈夫,但其爱情的正当性往往要用她的爱人的革命品质以及集体认同这些品质加以证明。《苦菜花》中的姜永泉引导娟子走上革命道路,同时也是她的领导。他说到要革命就“不怕流血牺牲”时慷慨激昂,娟子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这位老师:“每一个字,都打在娟子那温存善良的心坎上。她振作起来,全身充满了愤恨、热爱和由此而来的力量。她恨,恨死了敌人!她爱,爱那些她没见到的革命战友,爱那些早早和刚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先烈!”*冯德英:《苦菜花》,第119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在对自己的感情沉思之后,娟子发现她爱他是因为“真正好的人谁都会喜爱的”,他是她的“领导、同志、战友”,所以她更加爱他。她爱他的身体对她所热爱的革命事业有帮助,因为她的爱不是她个人的,而是集体的,革命大家庭里的任何人都能分享她的爱。此外,她所爱的对象不只是她的爱人,还包括所有有着和他相同革命品质的她没见过的革命者。吊诡的是,尽管所有的男革命者可能有着和他几乎相同的革命品质,她却必须自始至终忠于她的爱人。
在刻画奶奶的形象时,莫言有意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革命女性的原型。显然,奶奶在选爷爷做她的情人时根本不考虑任何道德价值观。然而,奶奶临死前有关个人主义的一番独白,却颇为奇妙地让我们联想到娟子的革命口号:“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辐,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奶奶临死前这番用来驳斥社会习俗的自我辩护性质的言辞,不仅夸张,而且做作不自然,可与娟子描述自己的爱情时所用的革命口号相媲美。泛滥的情感和夸张的语言掩盖了人物内心的空虚或冷漠,因为娟子和奶奶不是自我宣言或独白的主体,而是主要充当了崇高事业的代言人。作为初涉爱河的农村姑娘,娟子主要想的是她对自己爱人的所有革命战友的情感。作为一个从未认真考虑伦理道德的农村妇女,奶奶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思考的是她越轨的性行为的意义。正如娟子向她的爱人表露情感表明了《苦菜花》作者的政治立场,奶奶临死前竭力为自己的浪漫史辩护,显示了莫言对个人主义的信奉。娟子爱姜永泉是因为他代表着革命事业,奶奶爱余占鳌是因为他是男性权力和力量的化身。“(她)自己的想法”只不过是奶奶必须顺从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在余占鳌绑架了她并在高粱地里强奸了她之后,奶奶才成了他的情人。由于《红高粱》中的个人主义建基于男性的力量,奶奶沦为被动的受害者或野蛮的男性权力展示其威力的处所。在这两种情形下,性欲,尤其女性的性欲,必须用一种崇高的或更严肃的事业加以合理化,从中可见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讨论至此,鉴于两者都采用了不少说教式的口号,《红高粱》中的个人主义可视为革命意识形态的颠覆性后裔。
这种情感上的夸张被毛泽东称作“革命浪漫主义”。毛泽东指出,“革命现实主义必须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如以上《苦菜花》引文所示,革命浪漫主义的特点是极度的抒情和激情,但始终是不涉及个人情感的。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抒情和激情必须指向一个共同的事业即革命。尽管在《红高粱》中莫言时常保留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绪,他的抒情和激情却是个人主义的。因此,莫言的个人主义的主体必须是男性。
然而,在此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也有过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性质的自我赞美。毛泽东诗词就是很好的例子。例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沁园春·雪》,《毛主席诗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正如在浪漫主义作品中常见的那样,毛泽东诗词中的大自然成了诗人主观世界的一部分。同时,“江山”代表的大自然因其具有领土的内涵而被政治化了。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自我赞美并没有很大的区别。然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想要公开抒发对革命浪漫主义中的个体自我的激情,又不会使他的政治生命遭受风险,能够这样做的唯一的合法主体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莫言在《红高粱》中把自我赞美的主体做了民主化处理,即扩大至其他人,但是个人主义的合法主体不是随便的什么人。像毛泽东诗词中夺取锦绣江山的历朝帝王一样,爷爷余占鳌也必须通过暴力征服女性身体,才能证明其高人一等的男性权力。毛泽东通过江山抒发个人的激情,而莫言借用女性身体表达他的个人激情。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不需要用暴力征服他的性伴侣,因为女主人公必须对她选择的爱人忠贞不渝。杨沫初版于1959年的《青春之歌》描写了30年代的学生运动,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一。在和她的柏拉图式的情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卢嘉川——分开几年后,林道静从女友那儿得知卢嘉川死在了狱中。为了给她与第二个情人江华的感情关系做铺垫,叙事人把江华描写成卢嘉川的好友和同志,有着和卢相同的革命品质。由于极为尊重林对卢的感情,江华在很多年后才向林道静表白了自己的爱情。当两人最终决定做爱时,林道静一想到卢嘉川仍有深深的负疚感。*杨沫:《青春之歌》,第567-568页。与革命女学生林道静一样,《红旗谱》中的农村姑娘春兰对她的爱人——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判无期徒刑的运涛*梁斌:《红旗谱》,第376-382页。——也是忠贞不渝的。
表面上看,莫言的女主人公并不想对某人忠贞不渝,因而有别于这些革命女性。叙事人多次提到奶奶是性解放的女性。然而,这种性解放仅限于言语上的、意图上的自由。尽管叙事人暗示奶奶有过不忠的举动,奶奶的身体自始至终忠于他的爱人余占鳌。因此,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还是在莫言的《红高粱》中,女性的性行为都是表征女性独立限度的代表性案例。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女性必须引导自己的性欲,使其服务于革命事业。她们像尼姑一样嫁给她们信奉的上帝也即革命。这种意识形态性质的婚姻抽取了妇女的性欲。即使是她们所爱的革命男性,其主要功能也只是革命理论的教导者。《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苦菜花》中的娟子,以及《红旗谱》中的春兰,都是因为爱人的教导成为了革命者,而且都对自己的爱人忠贞不渝。她们的爱情是对共产主义宣道者的虔诚的献身。宣道者本人通常与他们宣扬的革命事业不能分离。有趣的是,尽管革命的中国宣称男女平等,大多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描述的师生关系仍基于一个严格的性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制度中,只有像《青春之歌》中的白莉萍那样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颓废的女人才享有性自由。她对老师兼爱人罗大方的背叛,相当于对革命事业的背叛。*杨沫:《青春之歌》,第355-364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女性角色的独立主要是针对有别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规范。所谓的女性独立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打倒旧社会的一个武器。自然,一件武器必须小心看管,以免伤及武器的所有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对自己的性行为进行自我审查,《红高粱》中的奶奶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先驱”,但我们却难以要求奶奶也这么做。即便如此,她的性行为仍然是被严格保护的,是被男性的权利和暴力严格保护的。为了换得一头骡子,她的父亲把她嫁给了患麻风病的丈夫。新婚之夜,她的丈夫不顾她的拼命反对想跟她睡觉。余占鳌在高粱地里杀死了试图强奸她的劫路土匪。随后,余占鳌效仿劫匪,在高粱地里绑架并强奸了她。但是,强奸变成了做爱,因为奶奶在看清余占鳌的脸之后,似乎顺从了他。然后,为了保护她,余占鳌又杀死了她的丈夫和公公。她的儿子长到十四岁,又效仿他的父亲,试图射杀一个垂涎她的男人。作为被她的父亲、丈夫、情人和儿子小心保护的财产,奶奶的性忠诚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留给了身体最强壮的男人余占鳌,而这是他通过暴力手段得到的。在此意义上,她“自己的想法”只有符合余占鳌的想法——自认为是能够操纵奶奶性欲的唯一的男人——才有意义。
如上所述,在《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性关系往往等同于师生关系。在此语境下,革命理论知识转化为男性权力,要求女性绝对服从于革命事业。但在《红高粱》中,男性权力是以更加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出现的。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不管他们行使的是何种权力,女性都必须听从被塑造成女人的救世主和保护人的那个主人的命令。
尽管中国共产党提倡妇女解放,莫言在《红高粱》中也把奶奶称作“个性解放的先驱”,性等级制度仍深深植根于革命文化和莫言小说展现的原初的世界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妇女的独立是一件受到严格控制的武器,被用来对付革命的敌人以及传统的中国社会。在男性权力和暴力主宰的《红高粱》的世界中,奶奶的所谓的性自由要么是她的女性魅力的无害的点缀,要么是用来针对清教徒式的性行为的一件武器,但其前提是枪口不会倒过来对准武器的所有人即男性主体。由此可见,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还是莫言的《红高粱》,都把女性的主要作用看作是工具性的,因此,前者描写的革命事业和后者重构的解放人性的第二过去——对应着革命文化的理想化的奇幻的过去——都导致了对第一过去的没有言明的屈服,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和莫言都试图拒绝中国传统的父权制。
综上所述,《红高粱》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一个负面隐匿的起源(即第一过去)和一个正面重构的起源(即第二过去)形成的对照,因为中国当代实验小说家们普遍持有这一立场。“第一过去”和“第二过去”形成的这种对照,凸显了《红高粱》这部小说和不同的价值体系——包括中国传统、西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复杂且往往自相矛盾的关系。
三、对政治话语的语言颠覆
莫言在《红高粱》中试图用叙事人的家乡高密的形象重构“第二过去”。在小说的开篇,叙事人对高密的描写揭示了这种重构的矛盾性: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叙事人对其家乡高密这个矛盾实体的认知与他“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在表面和文学层面上,这似乎是指毛泽东思想话语重要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是凝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三部重要著作之一,叙事人将各种矛盾的价值赋予其家乡的形象,显然承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尊重。出身于“上中农”家庭的莫言,在他的写作中似乎念念不忘自己颇为不利的政治背景。*例如,在莫言的短篇小说《枯河》中,一个和作者家庭背景相同的男孩被他的家人打死。故事用一种自我陶醉的笔调收尾:“人们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他的父母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百姓们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他布满阳光的屁股……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好像看着我自己……”又如,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讲述一个和作者有着相同社会出身的孩子如何创造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魔幻世界,以便保护自己免受日复一日的虐待和折磨。从《红高粱》叙事人的父母的经济状况看,他们是“旧社会”中的“富农”,*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毛主席选集》,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因而在当代中国只能是二等公民。在此语境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暗指叙事人至少在其人生的短期内接受了城市的价值体系,从而拒斥自己的背景,也即代表着被边缘化的“自然世界”的农村。
叙事人对家乡“极端热爱,极端仇恨”,喻指他在农村(“自然土地”)的价值观与城市(“文化中心”)的价值观之间的摇摆。他最后选择了土地,表达了他回归出身背景的愿望。然而,尽管或者说正因为他有意颠覆这种政治话语,他的失望并没有阻止他深深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话语中。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叙事人的摇摆,反过来也困扰着《红高粱》作者本人。莫言对作为矛盾象征的家乡的情感依附肯定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莫言写作时借助于超自然主义,从而小心翼翼地远离现实主义或唯物主义,但这些根源未必能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而是在作者运用的语言上。
莫言对语言的运用时常反映出他和主流话语的矛盾关系。例如,“最”是主流话语中常见的一个词。为了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规范,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写道:“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选集》,第8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上引文字中,毛泽东在把“人民生活”描述为“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时用了三个“最”:“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此外,“唯一”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都是最高级。有趣的是,在语言方面,叙事人在描写高密东北乡“最”字用了十次。然而,由于作者把最相反的特性并置起来,同一个词产生的形象却很不相同。“最”字揭示了毛泽东的单向、独白的文学世界,而莫言对这个字的使用也是单向的。他对“最”字的使用展现了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方向迷失和碎片化交织而成的世界。将“最美丽”和“最丑陋”并置起来的逻辑是一个悖论和荒谬的逻辑。莫言及其同时代人生活着的世界确实是一个荒谬的世界。通过把“最”矛盾的种种特性赋予他的家乡,莫言使这个语言模型具有了很大的争议性,破坏了一个貌似封闭的政治话语系统。单一的最高秩序不复存在;与之相反,不同的或者准确地说是冲突的秩序存在于这个碎片化的世界中,世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莫言对家乡的描写中互为冲突的价值观的并存,可以理解为是对80年代中国的一个隐喻。由此可见,莫言把“最”字用作一个具有论辩性质的语言元素,要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常规语言现实得多。
然而,莫言对家乡的矛盾描写,不光是为了反映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境遇,还在于创造一个充满原始活力和力量的生活的意象。与莫言同时代的作家都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亲眼目睹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对他们来说,从一个明显没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过去找到这个丰富生活的意象更加容易。*对这个主题以及“寻根文学”的讨论,可参见郭晓冬:《母性图腾——知青文学的一种精神变革》,《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范克强:《寻根者:原始倾向与半原始主义》,《上海文学》1989年第3期。但问题是,莫言及其同时代的作家,不管是不是实验作家,如何才能创造这个远离他们自身生活经历的过去?具体而言,莫言如何运用一种充斥着革命话语的小说语言去重构过去?因其颠覆对象的限定,莫言小说中的“自然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这一对象即革命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处理。换言之,莫言笔下“原初的”世界相对于主流话语而存在,并决定于其对抗性。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从主观角度看,莫言的原初生活概念和历史性过去即我所称的“第一过去”几乎没有关系。如此说来,“第二过去”也即莫言创造的幻想中的起源又是什么呢?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不会使人们回到原初的世界。“算总账”也就是“彻底消灭所谓的现实借以构成的符号结构”。*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London:Verso,1989,p.133.算总账意味着古老传统的二次死亡,也即记忆中的死亡,却不能恢复中国的原初生活之美。中国的教育制度未能使年轻一代熟悉传统文化,也即一个民族的过去借以构成的“符号结构”。
在此意义上,莫言用“无边无际的高粱地”这个意象重构的原初生活之美必然是乌托邦式的,因为这绝不是回归过去,而是对现代生活的否定。正由于此,体现着这种原初生活之美的奶奶不得不在风华正茂之年死去。作者借此告诉我们:回归过去是永远不可能的。
四、高粱地和女性身体
很大程度上,奶奶例证了作者心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即回到一个想象中的过去。在小说文本中,奶奶的真名实姓很少被提及。“奶奶”一直是她唯一的名字,除了有一次村里一个唱快板的老太婆在向叙事人讲述奶奶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做出的贡献时,提到她的大号叫“戴凤莲”。此外,这段快板具有超越叙事引导本身的性质。奶奶的无名揭示了作者欲望的矛盾性:既要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女性身体,又希望这个身体是一个传宗接代的有效的工具。由于奶奶与其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如说是男性欲望概念化的对象,这个女主人公必须是无名的。奶奶被置于一个她的孙子即叙事人进不去的过去。叙事人把他父亲的出生归结于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非法情爱,从而拒斥了儒家的家庭伦理思想。奶奶年仅30岁就被剥夺了生命,因此她的孙子可以对其不受时间的侵蚀、保存完好的年轻美貌的形象充满欲望想象。
正如叙事人家乡的风貌,奶奶的身体也成了叙事人的矛盾价值观交汇的一个场所。这些价值观,革命的价值观与中国的传统伦理观,不仅相互否定,而且相互拒斥。然而,奶奶的英年早逝使得这种种矛盾、否定和拒斥作为人生的正面形象奇迹般地出现了。由于她的死使得老一代和年轻一代,性诱惑和生育,持久的感官欲望和性欲的升华协调和谐了起来,奶奶因而转变为一个作为作者欲望——基于旧事物的碎片重构一个新的世界——的乌托邦式解决方案的形象。此外,由于奶奶的身体等同于作为自然之力和原始活力象征的高密,女性身体代表的这个新世界被看作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理想化的起源,也即与作者明确拒斥的历史性的第一过去形成对照的“第二过去”。
奶奶在弥留之际回想起她和爷爷在高粱地里宣泄激情的难忘时刻。做爱行为本身和回想过去的行为都发生在高粱地里。透过她那朦胧的双眼,高粱地被看作一个用于表达她临死前的所思所想的超自然的舞台。这个舞台很大程度上就是她的身体;更准确地说,舞台成了她的身体延伸出去的空间。
父亲跑走了。父亲的脚步声变成了轻柔的低语,变成了方才听到过的来自天国的音乐。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朦胧的眼睛里,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的眼里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高粱缝隙里,镶着一块块的蓝天,天是那么高又是那么低。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罩子里罩着。
上段文字在不同层面让我们想起叙事人对高密的矛盾认知,而奶奶看到的高粱的幻象同样充满了矛盾。两者的区别在于:高密这个地理场所被叙事人描述为一个客体,因而其矛盾性是用表示静态特性的形容词揭示的,而在奶奶的感知中,高粱地通过表示动态的动词展示其矛盾的本性。
以上两种情况下,高密和高粱地是完全相同的,这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上,还体现在它们再现了一个矛盾始终未能解决的原初世界这种象征功能上。从高密变成高粱地,不是发生在地理场所的层面上,而是发生在场所与两个不同主体的关系的层面上。对男性叙事人来说,高密仍是他的行动舞台,诸如“喝酒”和“爱”,这也正是他的“父老乡亲们”喜欢做的事情。叙事人用“凄婉可人”、“爱情激荡”等静态动词把高粱人性化,因此这个被人性化了的自然世界是被动的。正由于此,男性主体与地理风貌之间仍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然而,对叙事人的奶奶来说,通过行为动词人性化了的高粱地成了表达其思想意识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高粱,正如她自己一样,有着各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几乎消失。在这个主客体被认同的过程中,对高粱的主体化将奶奶的身体转化为一个行动的物体,由此把奶奶的身体客体化。正如红高粱的故乡高密一样,奶奶也是包括叙事人在内的“父老乡亲们”所爱的对象。
奶奶把高粱看作客观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这个客观世界并没有与她的主体性完全分离开来。与之相反,在一个互相反思对方的隐喻性的世界中,观察的主体和客体很大程度上混为了一体。用于描写高粱的“呻吟”、“扭曲”等动作其实是伤重将死的奶奶的动作。莫言把无灵主语和有灵动词或有灵主语和无灵动词组合起来加以运用,这种语言偏离是他有意操纵常规化文学语言的手段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超越。在上段文字中,人与物的位置被颠倒了:奶奶被物化为一只静态的眼睛或一个戏剧舞台,而被赋予人性的高粱在这个舞台上展示着各种动作。它们既能做出动态的动作——“它们在奶奶的眼里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也能表达复杂的情感——“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通过对高粱的幻想和对比,作者对高粱的人性化处理为文本生成了双重的超现实主义效果。换言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高粱不仅是人类,而且比人类更强大,因为它们能够做出最矛盾的动作——身体既能伸展,又能扭结——同时能够感受最矛盾的情感——既能哈哈大笑,也能嚎啕大哭。这种做出最矛盾的举动、感受最矛盾的情感的能力,把高粱神化为原初世界的精灵。
通过对高粱的神化,高粱和奶奶的意识在这个充满原始活力的世界里融为一体,莫言就能对奶奶进行浪漫化处理。高粱地和女性的身体都代表着矛盾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莫言小说中的矛盾变成了一种力量、活力和自由的象征,因为矛盾带来了活力、紧张和运动。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不断的运动使任何可能存在的权威变得不稳定。这或许可以解释奶奶的大胆妄为和不守规矩,也能解释为何高粱地能做出任何乖张的行动,因为这个矛盾的世界打破了所有的条条框框。尽管如此,女性的身体以及与之等同的高密的风貌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动态运动的世界之外。作者用她的身体来再现矛盾使得一个女人几乎不可能参与到矛盾本身之中,因为女性身体的主要作用是一个呈现各种矛盾动作的舞台,而不是做出这些动作的行为人。因此,奶奶的初次性行为,即便是和她未来的情人,也必须被伪装成强奸这种暴力的性行为。再者,她必须在伏击日本人的战斗打响前死去,即是在受到日军打出的第一颗子弹的致命创伤之后。在故事中,这场战斗是彰显红高粱的世界——以最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极端享乐主义和英雄主义并置的世界——的矛盾本性的最重要的行动。在情爱和战斗中,她的身体都被用作了牺牲品,因此,身体本身用被动的方式再现了行动,却没有主动参与到行动中。
对女主人公的神化是和对她的客体化并列的。在上段文字中,奶奶和高粱有着一种交叉关系。文本中明确无误的是,读者从一个女人的视角看高粱地,貌似受邀进入了奶奶的主观世界。文本中没有明言的是,奶奶的主观世界已被高粱地所代表的大自然先行占据了。因其对高粱的反思而被神化的奶奶的意识被同样的反思行为客体化。和她身边的高粱一样,她的行为主要用于表现大自然,因此没有任何的主观能动性。奶奶和爷爷最初的做爱行为始于强奸。爷爷把自己伪装成土匪,把奶奶绑到高粱地里,接着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开始了对奶奶的性祭仪式。这一行为本身象征性地把性暴力的实施对象即女性身体和祭坛即高粱地统一在一起。对女人的强奸等于对高粱的施暴。
像奶奶一样,高粱被描述为“奇谲瑰丽”、“高密辉煌”;像奶奶一样,高粱是人们欲望的对象或她的父老乡亲喜爱的对象。高粱的骚动不安以换喻的手法令我们想到奶奶临死前的痛苦。同时,高粱的骚动不安也可以被理解为奶奶的性高潮。高粱狂乱地“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让人想到奶奶极度的感官享受。在此意义上,不仅高粱和女性身体的意象是完全相同的,而且生与死的意象也是不能分辨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女性身体的欲望也是对她的缺席或死亡的欲望,这是因为对男性主体行为的赞颂,只有献祭了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身体,才能获得认可。奶奶的英年早逝,使她具有的再现矛盾的价值成为永恒。她生了儿子,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因此把她那年轻的身体献祭出去,作为男性欲望偶像的她具有的功能就成为了永恒。由于她的英年早逝,奶奶的形象以两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得到了赞美。一方面,叙事人即她的孙子通过和她的血缘关系和讲故事的行为活生生地见证了她的过去。另一方面,她死后仍是男性强烈欲望的对象。即便她的孙子也可以把她作为无害的充满魅力的性对象加以崇拜。然而,即使奶奶生活在一个遥远的过去,她体现的女性特征仍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只有她的早逝才能得以保存下来,以便把她的生儿育女的社会功能和作为男性欲望永远的对象这种虚构的功能调和起来。
这种对两种相互矛盾的功能的调和,借助一种象征性的姿势即对奶奶的小脚的盲目迷恋得到了强化。叙事人用爱惜的语气颇为详尽地描写奶奶的缠脚,可见一双小脚是奶奶的性感和女性特征的主要来源。由于她有一双完美的小脚,她未来的公公“从众多的花朵中,一眼看中了”她。余占鳌也是看到她的小脚后被她所吸引。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缠足把妇女禁锢在一个受到限制的世界里,导致女人确实远不及男人。过去中国的男权主义者往往用色情字眼“三寸金莲”指代女性的畸形缠足,以此论证缠足有着不可抗拒的美。对一种没有性威胁的色情事物的矛盾欲望,在美的终极标志即奶奶残缺不全的小脚中得到了满足。这种标志把其佩戴者(即缠足的女人)禁锢在家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对美的禁锢促成了对她的驯化,因而有利于她的性对象。因此,女性通过成功缠足获得的吸引力与她为人母的社会功能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同时代的实验小说女作家残雪对莫言对缠足的偏爱进行了令人捧腹的滑稽模仿。她声称,八百个有着相同的男权主义美学观念的绿林好汉住在山上的一个“原始”村落里。他们的阳刚勇武吸引了几位对本文化中缺乏阳刚之气的男人深感失望的西方金发美女。她们决定带着食物去找寻这个有着完美男子气概的村落。
她们有着一种不能克服的障碍:她们的脚。她们应该知道,这八百好汉只喜欢裹脚女人……
我希望,她们永远找不到这个山村,或是在到达目的地前早就吃光了身上带的所有食物。不然,她们这一趟算是白跑了。*残雪:《突围表演》,第347-34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上段文字或许能让我们明白为何残雪不太讨她的中国男性同行的喜欢。残雪敏锐地意识到,在莫言和试图寻找男子气概的其他当代中国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有着一种内在的矛盾。莫言基于他所理解的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的价值体系,试图创造一种理想化的起源,同时拒斥他心目中的中国的历史性过去。然而,到头来,莫言重构的第二过去和历史性的过去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对作为性对象的女性的态度,在无意中和不知不觉中和他的最保守、最大男子主义的祖先们并无二致。
【译者简介】汪宝荣,翻译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
“寻找当代文学经典”专栏
吕彤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①译自Lü Tonglin,“Red Sorghum:Limits of Transgression”,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与对抗性政治:中国当代实验小说研究》),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51-74.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