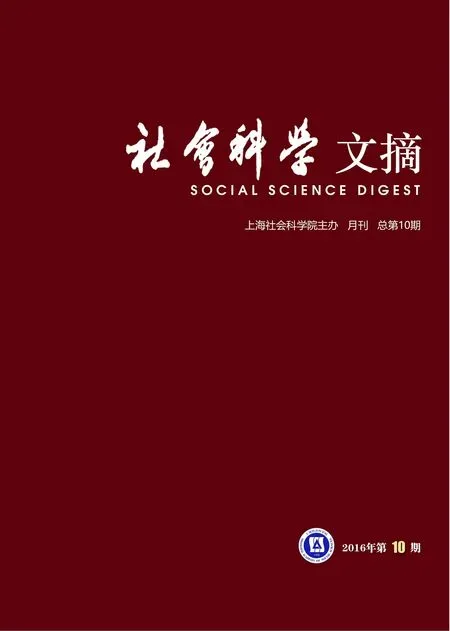近代学人从书目角度对大学国学教育的思考
文/曾光光
近代学人从书目角度对大学国学教育的思考
文/曾光光
近代中国为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异常激烈的时代。随着西方大学体制的引入与建立,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学习与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引导青年学子学习国学,近代大学中的国学大师常以开列国学书目的方式为后学指点国学学习的路径。其中较有名者有吴汝纶、梁启超、胡适等人。他们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步阶段关于国学学习及传承的思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国学教育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开列的国学书目及特点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当始自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从京师大学堂创办的那一天起,如何在近代大学中展开“国学”教学就成为筹办者必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曾开列《学堂书目》,对如何在大学堂开展中西学教学做出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
1902年10月18日,即吴汝纶在结束日本考察前夕,在《与陆伯奎学使》一信后附拟定好的《学堂书目》,这份书目详细列举了从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应学的中西学书目,可谓是一份具体的“会通”中西学的具体方案。
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师的吴汝纶显然清楚国学之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不弃“本国旧学”,又如何处理“欧洲科学”与“本国旧学”之间的关系及比例?学生的“脑力”有限,时间有限,中西学课程及相应书目的设置、开列就必须务实可行。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期间拟出的《学堂书目》就是对上述问题思考的一个答案。
按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对学生学习阶段的划分,小学堂为“七八岁入”, 中学堂为“十二三岁入”,大学堂为“十六七岁入”,这种划分大致与现代学制中的小学、中学、大学三阶段相对应。《学堂书目》中开设的书目包含国学与西学两大类,本文所论仅涉及该书目所举的大学阶段的国学书目。
吴汝纶所开大学堂国学书目包括“经、史、文、诗”四个部分,这种书目分类法显然是取法于传统中国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所列书目能系统、完整地传承国学。吴汝纶的书目分类法与古代中国图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也稍有差异。其差异一是剔除了“子”部,二是将“集”部中的文、诗分列出来。所以剔除诸子各家文章,显然与吴汝纶的学术立场有关。桐城派以古文名世,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桐城派还为清代理学的中坚,以维护程朱理学为己任。吴汝纶作为桐城古文一派末代领袖,对文、诗的重视与强调,对诸子之学的排斥都在情理之中。
吴汝纶所列书目带有很强的学派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体现为对诸子的排斥,对文、诗的重视,还体现在对桐城派古文选本的强调上。在其推荐的文部书目中,仅列桐城派始祖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一书,足见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的重视。
吴汝纶所开《学堂书目》还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在其书目中的史部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书目史部所选书籍为15部,其中5部与湘军、淮军有着密切关系,比例不可谓不重。吴汝纶先后在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中长期任职,是晚清湘军军阀集团与淮系军阀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一特殊的从政经历显然对其史部书目的选取产生了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还特别举出“中国专门学”阶段。从其具体安排看,“中国专门学”为大学堂阶段后的专门教学,有些类似今天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吴汝纶在大学堂阶段之后设置“中国专门学”,显示出他对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真知灼见。中国国学博大精深,有必要在大学阶段之后再设立“专门学”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与吴汝纶为大学堂阶段开列的国学书目相比较,“中国专门学”阶段的书目有所不同:一是书目数量大幅增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历代国学典籍精华;二是书目分类有所不同,大学堂阶段的国学书目是分为经、史、文、诗四类,“中国专门学”则严格沿袭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有效地保证了所选书目的覆盖面。三是书目的选择覆盖面广、系统性强,这在史部书目与子部书目中表现得尤为清晰,史部书目涉及自汉至清的历朝史书,子部则基本收入了诸子各家的代表之作。
胡适与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及与吴汝纶的比较
由于京师大学堂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先行者的地位,故吴汝纶在《学堂学目》中有关大学堂阶段国学读书书目的设计就具有开创性的文化意义。吴汝纶之后,专为大学“国学”学习开设读书书目的近代学者不乏其人,其中以梁启超与胡适所开书目最有代表性。
1922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要求而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所开书目列有184种书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胡适的开列的书目在《读书杂志》1922年第7期刊出后,《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即来信质疑胡适所开书目范围过窄过深。1923年4月26日,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邀撰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撰写的这篇文章及开设的书目相当程度上也是对胡适书目的直接回应。
吴汝纶与梁启超、胡适两人虽无交集,但吴汝纶作为近代中国大学的拓荒者之一,他在思考与设计大学国学书目时所面对的问题及思路与梁启超、胡适相较并无太大的差别。这种相似性是由大致相同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的相同身份等决定的。仔细推敲,可以发现梁启超、胡适两人所开书目与吴汝纶所开书目有诸多相通之处。
其一,三人为大学生开设国学书目均以传承国学为宗旨。
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为各级学堂开列的国学书目体现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西学盛行的时代对不废国学的苦心与努力。胡适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目的也是为清华学校的青年学子学习“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梁启超则以为,学生如果连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都不细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将国学的学习与传承上升到有无资格做“中国学人”的高度。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吴汝纶于1902年在《学堂书目》中所开列的国学书目是学生的必读书,而胡适、梁启超所开设的国学书目则非必读书了。京师大学堂在成立初期只设速成与预备两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科大学。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所开列的中、西学书目近乎课程书目,是所有学生的必读书目。从这个角度看,吴汝纶《学堂学目》中的国学书目对于学生而言具有强制学习的意味。1910年后,京师大学堂分科办学。在不划分专业的情况下,近代大学培养的是兼通中西的通才,而专业分科,则是培养各类专才而非中西汇通的通才了。大学专业分科的划分使国学的传承面临更大的挑战,梁启超对此认识很清楚:“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国学的学习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位置。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胡适、梁启超所开列的国学书目并不具有强制性质,只是仅供对国学有兴趣的学生参考,属于“课外学问”。虽说只具有建议性质,但胡适、梁启超都将自己的书目置于“必须”、“应该”的高度。胡适、梁启超所以将自己的书目命名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即有强调“必读”之意。这些书目“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学政治经济学,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对这些国学最基本书籍的学习不仅与“国学”的传承有关,还与中国大学培养出的学生能否成长为“中国学人”,能否“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有关。
其二,三人为大学生开设的国学书目均有学习程度上的层级的划分。
所谓书目层级的划分,即是根据学生智力程度的不同、学习时间的多寡等标准对国学书目的深浅、数量等方面进行层级划分,以适应不同类型大学生的需求。
吴汝纶所编《学堂书目》的层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学堂的高低层次分,即按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中国专门学分为四级,这种划分法其实是按年龄与接受程度为划分标准。二是在上述四个层级中再以智力水平即他所言的“资性”予以细分。如在经部书目中,他以“资性”水平再将大学堂学生应读的经部书目分为四个层级:“资性不钝者”,可读《诗》、《书》、《易》、《周礼》、《仪礼》;资性钝者,去《仪礼》;“更钝”,去《周易》;“更钝”,去《周礼》。
与吴汝纶从“资性”为标准划分不同,胡适主要从学习时间的多寡角度予以划分。胡适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出受质疑后,又拟出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如此一来,胡适所开的书目其实就分为“最低限度”与“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两个层级,其划分主要以“时间”为标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是为“有时间的”学生准备,而“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共40种国学书目则是为学习国学时间有限的学生准备的。
梁启超开列的书目本来就是对胡适国学书目的回应,故他仿效胡适的做法,在开列书目时也划分为两个层级。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梁启超列出了141种书目,随即又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共26种。梁启超所以开列两个层级的书目,主要也是从时间角度考虑。他在拟定“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时就曾说:“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
其三,三人开设的国学书目均有分类,且分类方式各有不同。
吴汝纶开列的《学堂书目》的国学书目分类法实有两种,在小学堂至大学堂阶段的书目均按“经、史、文、诗”分类,在中国专门学阶段则严格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种分类法保证了所开书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胡适开设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达184种,分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大类。虽说是三大类,细究起来,其实也就包括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两大类。之后,胡适又在184种书目中圈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40种。虽说“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并无分类,但这40种书目基本是从184种“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圈出,故两种书目的分类方法其实一样。
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读法》中开设国学书目时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共五大类共141种。他随后开列的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虽无分类,但其 26种书目皆是从他前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中择出。对比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读法》中的五大分类,梁启超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去掉了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所以去掉,显然与其难度及过于专业化有关。
显然,梁启超与胡适关于国学图书的分类都试图超越传统图书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但细究他们所选书目,从总体上看还是从传统图书四部分类法脱胎而来,只是分类称谓、分类多寡稍有不同而已。如胡适的书目分类法,其所谓“思想史之部”大致对应于“经”部、“子”部;其“文学史之部”大致对应“集”部。又如梁启超的书目分类法,其所谓“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大致对应“经”部、“子”部;“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大致对应“史”部;“韵文书类”大致对应“集”部。
尚需强调的是,胡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在开设国学书目时,所以要在最低限度的书目的基础上再开列“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与近代中国高校中西学课程并举有关。在近代中国西风日炽的文化大背景下,所谓中西学并举其实是西学在近代中国各级学校课程体系中的步步紧逼与中学的步步收缩,尤其是在清华学校这样的理工类高校,国学的空间更是逼仄。胡适、梁启超在开设国学书目所以要特别强调“最低限度”、“实在的最低限度”,相当程度上就体现了国学在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中的现实困境。
其四,三人为大学生开设的国学书目均有强烈的倾向性。
传统国学包含的书籍卷轶浩繁,从中选取百十种书目作为必读书目或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其中必然包含着选择者的倾向性。如前所述,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为大学堂阶段的学生开列的书目就体现出明显的学派倾向性。
胡适开设的国学书目的倾向性也很明显,其倾向性首先从其分类体现出来。胡适开设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主要分为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两大类。他在选择书目时所以偏向于哲学与文学,显然与他自己的知识构成与学术倾向有关。梁启超就批评胡适的书目“似乎是为有志专攻哲学或文学的人作参考之用的”。
梁启超虽不满于胡适书目的倾向性,但他自己在开设书目时也不能避免相同的问题。如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 甲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中共开列了38种书目,其中清代部分书目就占13种,其中多与梁启超本人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重点介绍的人物及书籍相关,如康有为著《大同书》,章炳麟著《国故论衡》等。这些书籍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流变由复古而走向革新,由传统转向近代转型的独特理解。
结语
近代学人关于大学生国学书目问题的思考之于今天中国的大学国学教育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关于国学书目分级的问题。大学可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开设高低层次不同程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设“国学入门书要目”、“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就分别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前者提供给那些希望在国学上有所造诣的学生,后者则是最基本的要求,即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阅读的“课外书”。又如关于国学范围的理解与划定问题。吴汝纶、胡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从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角度去确立国学书目的选择与分类,既可以保证国学书目选择上的系统性,避免片面与偏见,也不至于将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混淆。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即国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分科大学中的割裂状态。按上述吴汝纶、胡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的国学书目看,国学书目可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整体知识。在今天我国的大学本科包括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设置中,经史子集事实上是被分隔了到历史、文学、哲学诸专业中。国学的系统传承不仅需要开设“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更需要系统的专业的学习,让那些有志于国学传承的青年学生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
从此角度看,“国学”也应该在大学各专业中取得平等的待遇,占得一些之地,让“国学”以完整、系统、专业的方式得以研习与传承。这恐怕也是近年来国内的一些高校开设国学专业的一个重要缘由。
(作者系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摘自《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