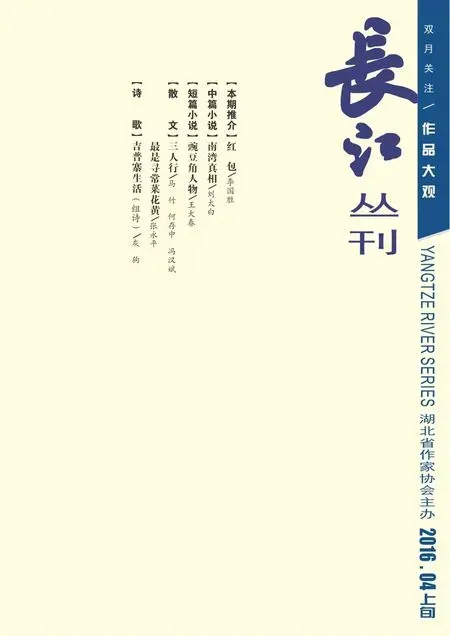圣 地(组诗)
■杨秀武(苗族)
圣 地(组诗)
■杨秀武(苗族)
一只鸟把我叫醒
我在练习死亡的时候
一只鸟的叫声像一支呼啸的箭
在凌晨三点射向我 我活过来了
窗外的一座山
是这座城市中心唯一的高度
只容得下一棵树 一只鸟
我的心 一只鸟的容身之地
我仰望一棵树一只鸟 愉悦之中
天上淌着要命的情诗和一滴鸟血
圣地
我的圣地
是长在我心尖上的一颗青春痘
让我痒得发癫
又让我痛得要命
空气
我的空气
是我身体里的神经系统
我只能感觉到 真诚和美丽
不贪 不迷 不妄
榫与卯
微笑在冰点之下积累
那一片白 与石头一样硬
太阳的冷光 磨出的榫头
恰好与卯对接一个完美
真
我老婆给母亲炖了一碗大骨汤
心和血照不见影子
母亲喝完这一碗亲情
碗在手里是一枚圆镜
照出跪乳的羊羔
感冒
从一个喷嚏开始
高烧把我按倒在床上
感冒让我比思念还难受
为什么感冒如此强大
为什么思念如此凶狠
为什么那条毛巾的高温
把她的手指
烧出几颗白色的原子弹
然后在我的背脊上反复爆炸
感冒死在一条爱的河里
思念活在一条爱河的源头
要求
我要求 在身上装一个监控
为你 我头发已经剃短
白发再难藏在黑发中
为你 我变为一块玻璃
我必须为通透承担所有责任
你是一个真理
在真理面前 我不虚构真话
在真理背后 我不虚构言行
我敢用美学突破天眼
仿佛迟来的爱情就是我的胆量
其实两个监控 早已装在你的脸上
深遂而辽阔的注视
把我所认识的汉字全部激活
我要求 把我安埋在监控里
喜欢
喜欢这条小溪
把这条老街当情人
抱在怀里 放进身体里
老街装死 闭着眼睛搂小溪
小溪明净的瞳仁里
一把伞被风吹翻了 雨中
一条小溪 一条古街 一对情人
邂逅一棵树
我路过富人区 别墅前
一棵树 全身吊着营养袋
黑色的蒙面布盖紧面部
要死不活的表情
我毕恭毕敬
在清江南岸 我看见过这棵树
丑陋到了极至 旺盛到了极限
脚趾像钢钎 把一座岩山破坏
现在像一个被拐卖的孩子
回家是唯一的想法
幻觉
我站在森林的高处
人在高处 一切都在险处
突然我看见
一个男人 目光狰狞 两手凶残
胸前一把斧头摆动
肩上的猎枪装满子弹
正冲着我来 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我自己扛着三角架
挎着照像机
一场虚惊与谁都有关
假设
假设土地一旦荒芜
乡村的虫鸣和鸟的叫声
甚至树林里的音响
就像撕破胸膛的惨叫
和泥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说
如果厌倦土地是一种进步的比喻
那些比喻反过来厌倦你时
土粒就板结为一颗颗子弹
我们就是活靶子
故乡的小石桥
我回故乡必须要见一个驼子
见就见吧 我们都是驼子
我们都不是残疾
驼子趴在溪水上看自己
岁月像个天坑
别人在背后看我 岁月像一副石磨
他生下来就驼 我生下来不驼
清明
一个小男人 背着
一个更小的男人
眼睛按住胸脯
像甲壳虫 已爬上山腰
一截死了的竹棍
一头被小男人的手死死地捏着
另一头
被一个瞎子女人死死地捏着
“妈妈慢点.....弟弟不哭......”
童音很低 没有悲伤
吊在竹棍上的清明
非常短 非常硬 非常白
铁匠铺子
“是我害了你
我这辈子只害你一个女人”
铁匠铺子的门枋上 站着两个关键词
一把铁锤不离手 四季风箱扯出头
词的骨头里
左边一个男人 右边一个女人
“打点儿 吃点儿”
铁匠铺子里的方言
在钻桩上被铁锤砸出火星子
方言淬火了 田野像泼了铜水
铁匠师傅像个叫花子
女人残疾了 天天给铁匠师傅求情
炊烟
炊烟发源女人的双手
手指的速度有奔腾万里的流量
我翻墙而过的时候
一溜烟就到了蓝色的源头
没有风的日子
炊烟是母亲耸立的旗杆
天变脸的时候
炊烟是母亲飘扬的旗帜
追赶
这么大的雪 堆在我的身上
雪像筛子筛 我的身上还在继续白肿
为昨晚一个饮酒的人通宵狂奔
脸上的红被手掌大的雪悄悄抹去
还有两行诗被脸上的红悄悄抹去
我追赶自己 一只白兔在追赶我
羊没有缰绳 兔子没有缰绳
致命的雪 无边无际的雪原
我反过来追赶一只兔子 一步一步
引入陷阱 这是我渴望了一生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