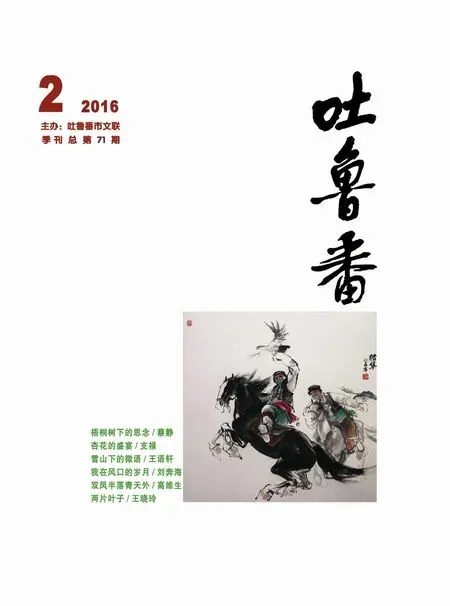双凤半落青天外
高维生
双凤半落青天外
高维生
在远处看双凤山的时候
姐夫开着面包车,从屯子里拐了几个弯,终于看见萧大哥家的房子。
姐夫在不远的五凤屯,多年前开了一个农家乐,忙时请一些短工,萧大哥常来帮工,他们相处得很好。萧大哥生在双凤屯,吃着双凤山长大,目睹一年四季,经风沐雨和落雪的变化,自己记不清多少次进入双凤山。一些资料上,误将双凤山写成双峰山,其实是重大的错误,随意更动的一个字,改变一座山的名字。但遗留下的历史,不是任何人能够修改了的。
萧大哥家地处屯子中心,木障子围出的院落,使用的铁皮大门,显得不伦不类。面包车停靠大门外时,看着我们下车,守门的小狗,不住闲地大声叫唤,准备扑过来。闻到狗的叫声,萧大哥从屋子里走出,一脸笑意地打招呼,姐夫做了介绍。几年前,我们在姐夫家里匆忙一见,还是有印象,特别是他镶的那几颗牙。
今天攀登双凤山,萧大哥是绝对的向导,他要带我进山。但有一个不成文的条件,姐夫必须帮他镘完炕,因为姐夫年轻时,在延吉市建筑公司当过瓦工。萧大哥家新掏的炕,沤干以后,镘上最后一层,才能铺地板革。水泥、白灰和沙子搅过的料,湿淋淋地堆积院子中。旁边是一个筛子,水桶和半袋子使不完的水泥。萧大哥早就拌好料,只等姐夫开工,做完这些活,他才陪我上双凤山。
姐夫为了争取时间,话不多说一句,跳上炕干起活。萧大哥用一只桶,不时往炕上送料,我插不上手,在农家小院里转悠。门前有一块菜地,架子上的豆角摘得差不多,秋风吹得叶子发黄。一丛开在障子边上的芍药花,我以为是野菊花,长白山区的深秋,它依然色彩艳丽,蜜蜂在上面采撷。我问萧大哥这是什么花,他说是芍药花,是从山中采回来的一枝,随意栽在那里,想不到扑棱一片。我对植物的知识贫乏,满山的树木,满山的草,在这里生长的人们,一辈子是吃山喝山。一朵普通的野花,如果不去探询它的文化背景,根本看不出什么意思:
芍药花虽然是一种平常的草本植物,但“芍药关”家族传颂着芍药女神的神话。原来芍药花喜清洁,怕污水的特性,并且芳香迷人,能使室内清静。其芽和面煎服,味脆美。《盛京通志》载:“英额门外猎场中,有芍药两丛相对,枝繁叶茂,附近不生杂草,所有鸟兽都不敢靠近。花开时,人不敢采摘,如有侵犯,必定害病。因此人们敬畏芍药花。农家老妇却可以摘花,插头作饰。
一种野花,在草木遍地的山间,不能再普通,积淀这么多的文化因素。它不仅是草药,可以治病救人,传承一个神话。在长白山区,一株树,一簇草,一块石,一条溪水,有神的灵性,使大自然有了神圣的庄严。
我在农家小院子转悠,双凤山呼之欲来,不能马上进山,真是难耐的煎熬。有几次,走出大门口,看着通往远处的小路。守门的小狗,被一条铁链拴住,不明事理,充满敌意的眼睛,不时地发出怒吼,做出前扑的姿势。小狗在地上滚爬,身上的毛皮不干净,看样子很多天不洗澡。它不大的脑袋,竟然发出凶狠的尖叫,花瓣一样的耳朵竖起来,不漏掉我所有的声音,我停住脚步,对视中的小狗无可奈何,转身躲进窝里,我蹲下身子举起相机,镜头对准小狗,这可能是它第一次面对镜头,听到快门的响声,被激得兴奋起来,从窝中冲出来大叫。
镘炕的活儿按计划进行,彼此间很少交流,我待在一边,坐在马扎子上,看远处的双凤山,起伏的山脉,在天边勾出漂亮的弧线。我查阅很多的资料,对双凤山的介绍,差不多都一样,毫无新鲜的东西。
在延吉市发现的“古长城”遗迹,断续蜿蜒在延吉、龙井和龙三市的崇山峻岭之中。延吉市北部山区的“古长城”,多为土筑,也有石筑,或土石混筑,大部分地段修筑在山脊的一侧,部分地段跨越山岭、峡谷及河川。根据目前调查已发现,“古长城”西自和龙市八家子镇丰产开始,经西城、龙门,再经龙井市的细鳞河、桃源、铜佛、朝阳、八道,再经延吉市的烟集、图们市的长安镇磨盘山(城子山山城附近)、东至长安镇的鸡林北山,总长达100多公里。
现在看到的“古长城”,多已颓败或湮没,只有断断续续的遗迹。在上述“古长城”遗迹两侧,还发现有数十座墩台遗址,以台址地形看,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墩台在当年就是起军事瞭望、传递信息作用的重要军事设施。延吉市地区的“古长城”,总的布局呈弧形,护卫着延吉市至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交会处间的广大肥沃的河谷盆地,构成一个十分壮观的古代军事防御工事体系。
目前,延吉市及龙井、和龙、图们的“古长城”的考古调查尚未完成,它的起点,终点还不清楚,与珲春境内的“古长城”(又称珲春边壕、边墙)有没有联系等等,也有待进一步调查考证。关于延吉“古长城”和墩台的年代问题,学术界也有多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延吉“古长城”主要是围绕城子山山城布局修建的,便认为是东夏国的“长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古长城”应该属渤海国遗存;还有的学者把这些“古长城”断代更早,认为是高句丽所修。1986年,延边博物馆从延吉市北部清茶馆附近“古长城”的墩台断面上采集了一些标本,经过做碳14的测定,其结果为距今约1500多年。
文中说的平峰山,小学春游的时候去过,一点印象未留下。平峰山位于延吉市的北部,面积约520公顷,属于高台地,它在烟集乡台岩18队的西北处,海拔高度682米。远处望平峰山的石砬子非常好看,山上生长灌木,大多是草丛,还有杂乱的石头。少年时的记忆,随着时间的逝去模糊。古长城至今未发现更多的文献记载,一些专家根据遗下的残迹,研究认为是东夏国的江城,也有的肯定始建于渤海,专家们的争论,各有理有据可依。到底是防御工程,还是金代长城,或者高句丽时期的古长城,无人最后断定。无资料可供证明,只有残迹难辨的城墙是历史的证人。
我等得有些急切,不时地看手机上的时间。
走在周家沟里
将近二十平方米的炕,镘了两个多小时,姐夫在门口出现时,我知道终于完工,进山的旅程即将开始。
姐夫顾不上洗手,我们坐上面包车,向双凤山的方向驶去。车子穿行窄小的路上,两边的房屋一闪而过,离开双凤屯的界碑,屯子越来越远,双凤山向我奔来。
面包车跑了十几分钟,在萧大哥的喊声中停下,细长的山路,继续往山上延伸,我们则攀登对面的双凤山。萧大哥不言语,他往相反的方向走,不时地站在高处,手搭凉棚,向双凤山望去。我不明白萧大哥的意图,他的举动怪异,这种不理解变成急躁。我从摄影包中取出相机,拧上防光罩,做好上山的准备。
不一会儿,萧大哥走过来,我问他看什么。他不紧不慢地说:“他在找古城墙的方位,这样走直线的路,省得走偏。”
“看到了么?”
“杂草和树木遮住,只能大约摸。”
听萧大哥这么一说,我心里没有底,望着双凤山,不知该如何破译,寻出那些埋藏的秘密。
姐夫干活累了,他不肯随我们上山,躲进面包车里,锁好门窗睡觉,休息中等我们回来。萧大哥前头走,我跟在后面,开始探寻的行走。
穿过一片“柳毛子”,这片幼树林,其实是小柳树林,当地人称为“柳毛子”。由于进山人多年的踩踏,形成一条泥土路,两边是野草和硬杂树林,平常很少有人来。我和萧大哥一边走,不时地唠嗑,想从中了解老事情。萧大哥的名字叫萧鸿图,1948年10月出生,老家是河北福宁县大所庄,1945年,因为家乡闹灾,父亲逃荒来这里安家落户,后来生下他。从此他生活在双凤山下,一辈子未离开过这个地方。1969年,二十多岁的萧大哥任民兵连长,50式冲锋枪斜背肩上,在附近的山里领着民兵训练。那个年代搞政治边防,延边军分区野营拉练派住在双凤屯里,民兵配合他们一起军训。严寒的冬天,大地被冻裂出口子,风刀割一般吹在身上,这是考验民兵的时候。夜晚零下三十多度,身穿棉大衣,头戴狗皮帽子,棉手捂子里的手不肯出来。屯子头的路口上,萧大哥和一个知青藏在苞米棵子里,透过秸秆的缝隙,监视过往的行人。因为接到公社下达的严防死守的命令,追捕逃窜的苏修特务。萧大哥挎着50式冲锋枪,睁大眼睛观察敌情,弹仓随时压进子弹。屯子里的灯光,一盏盏地灭掉,清寒中的狗都懒得叫。风吹干叶子哗哗地响,他们两个人都不戴手表,时间过去多久不知道。小知青不抗冻,一会儿扒开苞米秸尿尿,又不敢说话,怕被敌人发现目标。值了大半夜不见人影,人冻得不轻,第二天早上,小知青赖被窝里不起来。
萧大哥回忆说,1970年,有一个知青叫严伟,平时好读书写字,戴一副眼镜,打听双凤山古城墙的事儿,有一天他来请假,说要绘制一幅古城墙的地图。第二天清晨吃了一碗二米子干饭,独自背着黄军用包,登上双凤山去画图。越往山里走,吹来的风阴冷,这么大的山,空寂得叫人害怕。远处草丛中有一对野鸡叫,安静中格外响亮。我问萧大哥,山上有什么野牲口,他说有野猪、土豹子、山跳子。这几年封山养山,一些动物多起来。山跳子是什么动物,我弄不清楚,萧大哥说,当地人管野兔子的叫法。
空中有鸟儿飞过,不等我问这是哪一种鸟,萧大哥告诉我说,这是松尾鸦,学名叫长尾联,长白山区特有的鸟类。
路边有一丛榛子棵,叶子完全泛黄,果子被采摘光。我们一路走,我被山野涌来的植物迷恋住,有的根本不认识,只好求助于萧大哥。2008年,朋友从东北的家乡,带来一袋榛子。我看到一粒粒榛子,想到童年时,在姥姥家上山采榛子的情景。灯光下,我写了一首诗:
列车是一匹出征的战马
朋友乘着它回到家乡
他送的松子
在我身上的背包里
夜晚的灯下
耐心地嗑松子
白胖的松仁
躺在硬壳中
松仁的香味
扯出长长的情丝
灯光的箭
把乡思射向夜空
一粒粒生命
漫溢松脂的清香
它生长在大地上
那儿是我的家乡
双凤山越来越近,远处看它不太明显,到了山根下才发现,它的雄壮和威严。人在山中任何杂念都跑远,心情被无边的绿色染得单纯,如同回到童真时代。我的目光游荡山野间,不时地举起相机,拍下自己喜欢的画面。萧大哥在前面拐向右边,突然停住不动,我赶紧走过去,难以相信眼前的事情。
草丛中坐着戴草帽的老人,身旁放一根木棍,进山人叫它索拨棍,总是随身携带。这不是棍子那么的简单,是自卫的武器,防止蛇和其他的小动物,上山拄它,帮助自己减轻劳累。空旷的山中,棍子敲打树干,清脆声音传出很远。它有一套独特的语言方式,向远处的人交流。老人斜挎的筐里,盛着采摘的冻蘑菇,由于刚摘采不久,带着野性的气息。萧大哥和他打招呼,老人是朝鲜族,瘦弱的身子,十分硬朗,汉话不流畅,从他的神情上看,遇到我们很高兴。萧大哥告诉我说,他出生于1937年,曾经是双凤屯的老村长,1970年当村长时,他正好是民兵连长,还归老村长管呢。荒山野岭中的意外相遇,使两人都很高兴,平常住屯子中不经常碰面。70年代初期,他们在这里和军分区的官兵们搞军事拉练,演习抓捕苏修特务。
老人问我们拣山货,萧大哥忙说是看古城墙,老人说无路可上,也看不到什么。老人卷起一颗旱烟,浓辣的烟味带我们入山的深处。
体温和历史融合一起
灌木丛越来越密,杂草缠脚,登山找不到道路,全靠萧大哥扒开枝叶,闯出一条路。道路一点点地升高,陡度的变化,我们被不断地抬高。
我觉得呼吸急,不时地停下脚步,向密不透风的林中望,无法辨清里面有什么东西。我穿的鞋不争气,踩在腐殖土和落叶上发滑,几次险些倒下。我护着胸前的相机,腾出另一只手,这时我的情况,只能用身不由己形容,困难地往前走。
一条溪水横路上,水不很深,浮着枯干的树叶,中间垫几块石头,供上山过往的人通行。萧大哥利索地跨越,而我试了几次,脚才踏上面,身子在空中摇晃,两只胳膊寻求平衡,险些落进水中。对面有一架野葡萄藤,萧大哥递过来藤蔓,叮嘱我抓住。我握着干枯的蔓,好不容易跨越溪水,大口地喘气,身上已经冒汗。
往前走不出几步,我发现叶子宽大,带披针形的植物,仔细地观察,任凭想象感觉不出来,它是什么植物。我问萧大哥它的名字。他笑呵呵地说,它叫贯中,是一种中药,老百姓叫广东菜。春天刚长出不大,拿它包出的水饺,味道清香,也可肉炒做菜,发生瘟疫时,净洗根后,投入水缸中解毒。长白山区遍地是宝,任何植物都是中草药,这个我相信。但萧大哥说它叫广东菜,这么土的野草,有这么洋气的名字,似乎不相关,这件事情上,我不相信萧大哥。
下山回到延吉,第二天的下午,我向老中医的岳父请教,这味中药的名字。岳父不紧不慢地说:“它叫野鸡脖子,学名叫贯众。”两点都和萧大哥说得有出路,萧大哥说它学名叫“贯中”。野鸡脖子叫法准确,它和广东菜相差太大。岳父从书架上翻出中药手册,翻到其中一页。
一幅手绘的植物的平面图,和我在山中遇到的一模一样。《吉林省常见中药手册》是一本绿皮小书,巴掌一般大小,吉林省药品检验所革命委员会编著。不是正式书号,属于医疗系统内部发行,泛黄的纸页中保存那个时代的气息。历史和时间在书中相遇,将我推到遥远的过去。我一边翻书,想山野中的野鸡脖子,评论家叶立文在我的书序中说:
在这样一个无处不具象的历史时空中,倘若回忆者不能重返自我生命的历史现场,那么也就无从体悟个人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所存有的微妙关系。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它首先设定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具象,继而通过具象对人之存在的魅惑,渐次谋划了无数个人的命运之旅。这就是说,我们那些尘嚣危惧、歧路频频的生命轨迹,原来莫不与已经逝去的岁月流年息息相关。在此意义上去“散文”记忆,作品自然会超越怀乡散文的乡愁情愫,进而在叙写历史的生活具象中,为记忆赋予了一种可堪观瞻的生命意义。
文字记载的历史穿越时空,我们在纸上游走,感受不到在场的激情。触摸一段古老的城墙,体温和历史融合一起,发生质的变化。历史的真实,不是凭资料和想象出来的,评论家所说的“历史现场”,道出田野调查,对于写作者的重要性与必须性。
山中响起树枝折裂声,萧大哥前面开路,我们艰难地向上攀登。我只要停下,身上的汗马上被吹散,阴冷的风穿透衣服。一缕缕光线,从枝叶间筛落,一点声响传出很远。我不知道自己身处的位置,萧大哥是方位图,将一切托付他。
萧大哥突然说:“古城墙到了。”我茫然地看了一下四周,见不到想象中高大的城墙,只是乱草丛中,有一条明显的土棱,随山势向峰顶延伸。它保持原始性,任凭自然风雨的摧毁,自生自灭,附在其上的文化正消失,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我观察古长城的遗迹,目光浸在古老的城墙上。山岩和杂树间透出的野气,使人感受到清幽深邃。当年飘动的旗帜,走来走去的守卫士兵,壁垒森严的城墙,堵住入侵者,前进的脚步,他们葬身于墙外的大地上。现在除了风声,鸟鸣声都不见,这就是历史。萧大哥比我大十几岁,钻树林,爬山十分灵活,有一段墙沿着陡壁往山上伸展,他下到岩壁前,我小心递给他相机,并教他如何使用。萧大哥撞得树木直响,我替他安全担心,因为身后是陡斜的山坡,稍不注意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萧大哥将镜头对准古城墙的遗迹,我听到快门连拍的响动声。我扶着一棵小柞树,向双凤山顶望去,一抹阳光围住山尖上,映照草丛中的古城墙。
萧大哥说不好上,草丛密实无路可行,这样往上攀,再有两小时也上不够。我不好强求萧大哥了,他说冬天草枯叶落,这时最好上山。我将镜头对准双凤山,拍下珍贵的瞬间,也许有一天,我还要再登上山。
历史学家因而在他的心灵中重演过去,但在这种重演中,过去并没有变成现在或具有现实性。现实性是重演过去的历史学家现实的思想。历史思想的对象是现实的,其唯一的含义在于它被现实思考着。但这样并没有赋予它任何类型的现实性,将现实性吸纳到自身中,它仍然整个的是想象的。
一切历史蕴藏文化,是一部思想史,史学家不仅在文献上寻查,也用心灵和历史融合。
我听着林间的鸟叫,羡慕它们有一对翅膀,自由自在,任意地飞翔。林子里的光线暗了,夕阳变化色彩,上山的路不好走,下山也不易。我回过头去,再一次望着古城墙,它不是想象中的东西,而是刻在大地上的历史证人。
顺着来路下山,不时遇到碰断的树枝,露出新折断的茬口,过不了多长时间变干。我又回到小溪边,并不是急切地跨过,而是手伸进水中,掬起清凉的溪水,带着山野的气息渗进肌肤中。溪水顺山势往下流淌,完全凭借自然的形态,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我摘下一片干枯的野葡萄叶子,放进溪水中,看它被推向远方,沿着树木和草丛遮掩的溪水,很快消失。水中金黄的落叶,传递季节的信息,山中不需要语言,叶子的变化,一缕光线的明暗,一阵山风的大小表达一切,我记下那段难忘的田野调查:
这是最后一段古城墙
在山野中
它是一个耄耋的老人
孤独地眺望
它在等什么
回忆中浸满酸涩
风化的皮肤
留下斑斑的痕迹
我在古城墙上寻找
风中枯立的野草
仿佛丢失的音符
发出凄凉的声音
风雨洗去古城墙的颜色
它曾经围起一座城
盛满温馨的日子
而今一点点地消失
面对古城墙的遗址
掀开一页史书
我在书中
倾听历史的回声
很想扯开嗓子大声地叫喊,拉一下野葡萄藤,算是最好的告别。小心地踩溪水中的垫石,流淌的水绕过石边,清脆的水声印在心中,想起双凤山,就会响起溪水。拉扯路边的灌木枝,缓解下冲的惯性,免得被伸出的乱枝刺伤。溪水声听不见时,眼前一片明亮,我们走出林木包围的双凤山,又回到山脚下。我离开双凤山越来越远,登顶不成功,留下的遗憾,储存今后的日子里。古城墙是历史的记录,它和山上的植物不然,也许有一天全部毁灭,但它庞大的历史根茎,扎在岩石的深处。
在周家沟里走,路的坡度缓慢,不费太多的力气。鸟儿躲在草丛中不停地叫唤,我问萧大哥,这是什么鸟,他回答说这是野鸡。循声音的方向举起相机,镜头捕捉它们,想拍下嬉戏的情景。无奈草密实,林子遮掩一切,听着在不远处,却连影子无法抓住。
林子边上,有一棵长得粗壮的松树,蓬开的树桠,仿佛撑开的大伞。松树的背景是双凤山,我和它对视一会儿,拍下神气的样子。
夕阳在天边变幻色彩,一抹光线掉落双凤山上,古城墙又一次经受夜与昼的变化,时间不知不觉中走过。日落之后,双凤山归于黑暗,在长夜休息养生。双凤山怀抱古老的城墙,唱起悠远的歌,在风的摩挲下,夜的滋养中进入梦乡。
望着双凤山,心里生起遗憾,深秋的凉意,蓦然回首间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