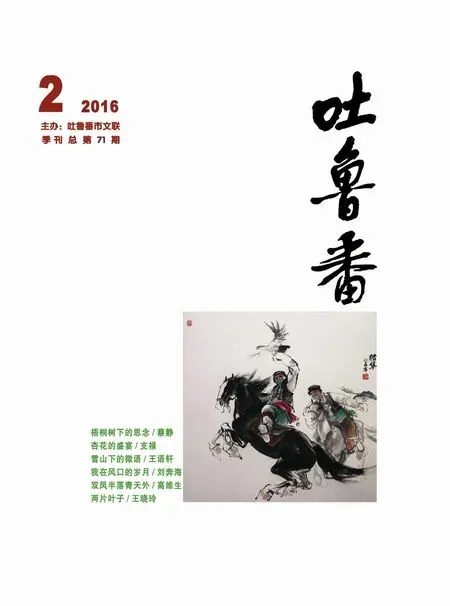姑娘亚茹
王新梅
姑娘亚茹
王新梅
有减肥的客人来得早,大婶子安顿了亚茹去早点。“哎——”亚茹答应着。咽下最后一口饭,利索地穿衣穿鞋,临出门抓了新手镯。手镯是银子的,婶子挂念她还是个孩子,上次进货的时候给她买的。上面有几个小铃铛,亚茹喜欢着呢。
手镯叮叮当当地,黑子抻直了头,定定地注视着她。亚茹喊,黑子。黑子就欢天喜地地摇着尾巴跑来了,欢快地跟着亚茹往路上走去。出了巷子左拐走上几百米就是城市了。虽几百米外就是城市大路,但这条路像还没进化好似的布满大坑小洼,却是亚茹最喜欢的一截路,两边有树,有自由飞着的蜻蜓蝴蝶,有各种样子的野花,野枸杞沙棘隐姓埋名深藏其中,两边还有大面积的农田,阳光还没来得及吸走的露珠,像植物晶晶亮的眼睛。下过雨后,某个草丛里还会有蘑菇的白脑袋冒出来——一切像老家村子的样子。还有一只跟在后面的小黑狗,亚茹的脚步每每会轻快起来。
“该上大路了,车多,不要跟了。”黑子乖乖地停下。“回去,晚上见。”亚茹摆着手,黑子眼睛里有委屈。亚茹抚摸了下它的头,从包里掏出半根火腿,掰成几小截放手里。看黑子乖乖地吃完,亚茹抬起胳膊指着来的方向,“回去回去。”黑子一步三回头跑远了,亚茹上了公路。
到了美容院,脱下手镯,开始干活。她先整理床铺,要洗的撂一堆,要铺的挑一色放好。再扫地拖地。完了把那些洗面奶按摩膏各类精油各就各位。熏烤仪推到一边,体重仪用脚推到柜子下,滑车都摆在床头。三年了,亚茹已经再不像开始那样眼里没活手足无措了。
小婶子起初也是嫌她有点小的。婶子们比她早到新疆,说话带着普通话的调。“亚茹你们舍得,我都舍不得,这么小,还这么瘦……”小婶子两只手怕冻着一样,互相握着放在膝上,腰是直的——和她妈妈不一样,妈妈的腰和背总像背了一筐子菜或者别的东西,习惯性地向前弓着。她停顿了下,又说:“不过,到我们那多吃点就能吃胖,新疆的饭菜养人,你看我现在都吃成啥样了。”她挺了下脊背,好像让人看她的腰身。亚茹听不出来婶子是想带她去呢还是不想。她是不想去学校了,学习差,被老师天天惦记着训。也不想辍学后跟村子有些女孩那样,在家里干上几年农活,早早地出嫁。她怯怯地望了下婶子。小婶子才比妈妈小几岁,倒好像小了好多岁一样。还像块香皂一样冒着香气,不像妈妈整天剌着头发身上总是汗味混合饭菜的味道,一点也不好闻。总之,像婶子那样就错不了。
反正我是不想去学校了,亚茹想说没敢说,但眼神大人们都看出来了。
就这样,三年前,十六岁的亚茹最终跟着婶子来了。
两个婶子十年前来新疆打工,认识了亚茹的两个叔叔。叔叔是农村的。不是那种偏远的山沟沟里的农村。村子紧挨着城市。半个村子都已经快被城市占领了,修了马路修了农家乐。快了,我们这马上也要被征了。啥叫征了?就是把我们的地、房子全部换成钱。叔叔家有一块地已经被征了,换了钱后,两个婶子开了这家美容院。
城里美容院很多,还是不够用。婶子们着急地赶紧征个好价钱,趁生意好,再开一家美容院。
用自家亲戚自然错不了。那些女孩子学会了手艺就能耐得不行跑了。吃不了苦,啥也干不成,大婶子在第二个美容师走后,总唠叨这句话解恨。人家又听不见。几天前,亚茹说,婶子,我哪也不去,就跟着你们干。婶子自那以后念叨的少了。干了五年的那个女孩说要自己开个美容院,到时候让亚茹过去,工资开得比现在高。她们有时候悄悄地叽叽咕咕,等她一走了,婶子就怕亚茹起了二心。
婶子们对她还是蛮好的,尤其是小婶子,让她出去学习新的美容手法。说了好几次要给亚茹涨工资,倒是大婶子摆出一堆理由阻挡着,但也买了些衣服鞋子还有手镯什么的东西哄着孩子。偶尔也说,亚茹长大点,技术再好点,再开店就让她当店长。亚茹年纪小,也没啥心。新疆再没有别的亲戚。亲戚总比别人可信吧。她也这样想。
减肥的刘姐起码五十岁了。就是六十岁,婶子们也喊刘姐,亚茹也喊。她们这里年龄最大的顾客六十八岁了。在老家把这么大岁数的人喊错辈分会被人家白眼的。这里,被喊的人也无觉不妥,个个心甘情愿地当着这个才十几岁小女孩的姐。刘姐赶时间,进了屋子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扒光了,赤条条趴到在床上。“刘姐,凉,别冻着了。”亚茹赶紧拿了毛巾被展开盖到刘姐身上。又利索地从架子上扒拉出刘姐的减肥套盒,亚茹不敢怠慢,客人着急,自己得表现出比她们还着急才行。她麻利地搓手,好让刚抓了凉水的手热一点。然后将调好的玫瑰和茉莉滴到刘姐背上,用两只手自下而上涂抹,开始第一道程序“展油”。
上午做了两个顾客,就到了中午。大婶子来得迟,带了饭来。亚茹和小婶子给客人敷了面膜后,洗了手赶紧扒拉两口饭。已经有几个客人打电话预约要来了。
张姐来了。张姐是老顾客,认识的人多,和旁边的顾客也熟悉,两人就聊起来。自然先是互问忙不忙。问完了也答完了,就又扯点眼下减肥的话。亚茹小,力气也小,但干活卖力不偷懒。一双细腿撑地,两只细胳膊左右开工,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她的力气越来越大了,趴着的张姐一百多斤的肉,亚茹双手往她的背上一推,她白花花的身子就窜出去半截。一推一收,张姐的声音就七上八下地不流畅起来:小关,身材那、么好、还、减啥、肥?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腰还不到、一尺七。小关三十多岁,主业是在一个清闲单位看报纸喝茶,副业给一家保险公司推销业务,反应自是又快又准,她不说自己减肥的事,先惊讶年轻时候的张姐,天哪,你咋那么细,我腰粗的就不好意思给你说呢——
玫瑰的茉莉的还有别的什么精油散发的香气弥漫在四周,粉红色的墙纸、粉红的纱幔还有乖顺的亚茹都有着让人完全放松下来的奇妙诱导,身体也罢,神经也是。美容床上躺着本是无聊和冗长的,如果旁边是一个会聊天的人,那就是另一番感觉了。谁心里没有个爱憎没有个好恶,它们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到这个世界呢。从减肥说到胸不够大屁股不够翘腰不够细,继而说到男人的审美,后来就又说到她们都认识的一个风骚女人。她们的话题越来越远,竟说起了女人的床上功夫。女人都对风骚女人没有好感,简直就是她们这类好女人的天敌。她们毫无顾忌地说起这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床上功夫怎么个好法呢?两人饶有兴趣,听说还会……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干杯的人,有着一拍即合的快乐和融洽。说得尽兴,忘了亚茹只是个十八岁的姑娘。
最后不知怎么说着,两人才想起来年龄还小的亚茹。话题就扯到亚茹。亚茹来了三年了,比起以前胆子大了,也会说话了,也比以前好看了。
亚茹的父母同意亚茹跟着婶子来这边后,亚茹还是高兴多一点。她不知道以后要迎接的新生活是什么样,但想到要脱离学校脱离课堂还有那个脾气大的老师还是怪兴奋的。临走,父母都犹豫未定,看她的眼神像以前把好吃的给了弟弟,过年没给她做新衣服那样,有些发窘。可这次亚茹真的没有怪他们。婶子说,先每个月给几百,等干熟练了能当个大人用了一千两千或者更多都有可能,看她自己了。说完这句话,婶子还有爸妈都把头扭过来看她。仿佛在打量她行不行。想着自己可以像村里那个在深圳打工的姐姐一样给家里过年过节寄点钱了,亚茹更加不再留恋学校的一切。她想起最好的小伙伴知道她走后惊讶的眼神。那怎么办?小莲,亚茹悄悄嘀咕了一句。她曾和小莲勾手永远不分开。他们一起上的小学一起上了中学,还进了同一个班。家离得也不远,早晨一起走下午一起回。来回十里路,有个月饼他们掰开一人一半,吃个雪糕也是你一口我一口,他们比姐妹还亲。有许多秘密只有对方知道。
小莲的成绩比亚茹好,她会耐心地辅导亚茹。亚茹怎么也做不来数学题,本子上的叉叉越来越多,像一根根无形的绳子要把她绑起来一样,让她没了信心。等后来学到物理化学了,她就更是一头雾水。
可亚茹学美容倒很快,这比两个婶子以为的要好。亚茹倒并不吃惊。除了一开始背那些陌生的身体穴位花了功夫,其他的,在她看来这都是力气活。出力流汗什么的,农村长大的孩子不嫌弃,比做数理化题好多了。婶子说对顾客要耐心要微笑,以及一些巧妙地向客人推销产品的技巧,亚茹做得都不错。也不全是出于功利和私心,她不就是个朴实和简单的女孩嘛。因了这个原因,有的客人还更相信她。当然也有客人问她深一点的技术问题,她回答不上来。那也没关系,人家就当她是个孩子不再问了。又不是在课堂上,几十双眼睛看着呢,羞得不行。没有学习的压力,亚茹觉得也蛮好。可前面那两个美容师不喜欢。她们都干了七八年了,到了该结婚成家的年龄了。人大了想的自然多啦。也许事实就是如此,可大婶子说这话时总带着嘲讽的意味。
张姐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今天打定要好好捯饬下自己。全套护理都做。旁边的听了嬉笑道,莫非明天要做新娘子去呢。张姐叹口气,十年没见了,别老得同学们认不出来了。同学聚会可就是情人聚会,是得好好收拾下,旁边那位继续开着玩笑。
张姐是老客户,每年消费都上万了。小婶子自是忙中偷闲亲自服务,她来给做完身体的张姐做脸护。亚茹洗了手不等婶子说,来给张姐做手护。
张姐的电话响了,是儿子打来的。张姐不好接电话,亚茹帮她拿着手机。张姐的儿子亚茹来的第一年就见过,和亚茹一样大,说起来,还比亚茹小了一个月。可人家是城里有钱家里长大的,吃的好喝的好,长得人高马大,唇红齿白,眉黑鼻高,比个女孩子还秀气。张姐也是知道孩子长的好看,别人一夸就咧了嘴得意。那年,张姐是来做减肥的吧,男孩一直窝在沙发上看书等。亚茹遵婶子的嘱咐给他倒了杯水,男孩也挺有礼貌,忙趄着身子接杯子。一给一接时,两人的脑袋给碰上了,两个孩子害羞而慌张地笑了。
美容院的顾客大多都是女人,年轻的女人年老的女人,胖女人瘦女人,除了偶尔等老婆的男人或者儿子,几乎不见男人。那个辞职去职专上学的美容师已经二十岁了,她说,一天到晚的窝在这里,咋可能碰到个对象。这女孩打算先拿个文凭,以后干别的什么去。干什么去呢,那女孩好像也没具体的打算,只是觉得自己初中文凭没啥用,先念了中专再说。
她记得最早她和小莲也有过打算的。能考上个好高中,然后考上大学就最好了。考不上大学的话,就和村子上那几个女孩一样,离开村子去广州上海那些大城市打工。她们一年或者两年回来一次,穿得像个城市女人一样新鲜亮眼,村子没出去的女人都羡慕呢。有的生了小孩就走了,回来后娃娃都大了,可娃娃的娘看上去好像更年轻漂亮了。
小莲来信说,她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男孩。可男孩不喜欢她。喜欢小莲的是其他班里的,是邻村一家的。小莲说,男孩告诉她,他是在放学路上留心了小莲的。小莲说,自亚茹走后,她好长时间都是一个人来回走。天冷,太阳落得早,半黑不明回到家里,有时还怪害怕的。
亚茹就想起了那条路。亚茹家在村子最里面,亚茹穿过整个村子才能走到这条路上。这条路两边都是村子,学校过了两个村子的庄稼地就到了。学校在那村子的山坡上。在村子里走都不怕,就是那一截路上人少。两边都是庄稼,没有房屋。冬天雪一下,到处白茫茫一片,看上去有点荒凉。可夏天看着多好看呀,树的高大不说,庄稼的茂盛也不说,光路边开的各种小花,五颜六色的散开去,啧啧,还有蝴蝶蜜蜂蜻蜓飞呀飞。放学回来,亚茹和小莲常常揪了路边能吃的各类野果子吃。下雨以后,还能采到大蘑菇。妈妈用小葱炒了好吃极了。母亲上次电话说,晒了一小袋,过不久就寄来。亚茹寄回去的钱越来越多了,母亲渐渐觉得当时的决定不算糟糕,嘱咐亚茹听婶子的话。亚茹似乎能看到母亲的脸。邻居二娘家女孩在深圳发廊上班,每年过年和八月十五寄了钱来,都会炒些瓜子到学校对面那去。那人多,瓜子散出去的时候,就把女儿寄钱来的消息也顺道散出去了。我家小娥说那好,以后要在那成家。二娘也不顾及灰旧的牙比平日里暴露的机会更多了。可是上次小莲来信说了,村子里的人都说二娘家那丫头被一个男人骗了后失了身子,现在在深圳干着不正经的职业。啧啧,亚茹这几年自是男女的事情知道的多了,还是吃了一惊。她记的小娥好看的眉眼,两条长腿。唉,她像个大人一样叹了口气。想不出个所以然,末了她想,怪不得这里来的女人总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接完了电话,旁边的要看张姐儿子的照片。嘟囔着儿子的贪玩,张姐擦了手翻手机找儿子的照片。婶子也赶紧凑过来看。啧啧,好长时间也没见了,孩子长成大小伙子了。英俊超出了预想,人家继续夸,这以后得多讨女孩喜欢呀,你们两个人就已经是人精了,可比你们两口子还好看。这怕是所有母亲都爱听的一句话。百听不厌。有次,村里的人也这样夸亚茹,母亲听了后眯着眼咧着嘴嗔怪人家。亚茹是好看的,有次张姐被按摩的舒服了,话赶话地和她的婶子开着玩笑,亚茹要是给我当媳妇也蛮好的。这丫头秀气,有眼色勤快,脾气还好。羞得亚茹脸都红了。她后来还被岁数大点有儿子的王姐李姐们开过玩笑,自然知道了那就是个玩笑,再听了就抿嘴一笑。
亚茹来的第二年,顾客里面有个校长。无意间知道了亚茹还小的很,数落了婶子两句,意思是孩子太小了,她这是雇佣童工,违法呢。婶子声音立即惊讶起来,我也这样说呢,可这孩子上不进去学了。我不带过来,也是辍学在家了。校长的脸在婶子的手下被按摩得看不出表情了,眼睛也不由自主地半闭着。可声音还是能听出是校长来:那可以上职专呀,女孩子家得上学,连十八岁都不到。紧接着说的话就又体现出她这个年龄的妇女的特点:不上学了,到时候自己当妈了,也不会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说着斜着瞄一眼亚茹。亚茹低着头,乖巧地用眼睛会意了下,咪咪笑的表情。意思是领了长辈的好意了。甜美温顺的表情,让校长立刻变回顾客的身份,唉,啥都是手艺,好在是跟着你学手艺呢。说着伸出两只手来交叉着做挤压掐捏的保健操。亚茹数了下,校长就是认真,做了五组,一组十下。不多不少。
小莲到了初三,越发努力了,她打算考个好成绩,考到市里那所好点的高中去。她已经想好了,考个师范学校,到时候回来当老师。她要当个不打人不笑话人的老师。这曾经是她们两个人的梦想。
其实,亚茹早已经不太恨那个班主任了。这世上,怕只有母亲不嫌弃自己笨,哪个人不是希望你更省心更利索呢。
亚茹也想当老师,可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也早在老师的挖苦中熄灭了。她现在才觉得自己太脆弱了,自己学习不好,还那么娇气。老师骂了就骂了呗,干嘛自己就受不了呢。因了这一丝不甘心,她真为小莲高兴。然后,她偶尔,有时,也会冒出个自己都吃惊的念头,要是这会她在教室坐着,会是啥情景。
一直到了傍晚,张姐所有的美容项目才做完。张姐左右对着镜子看着,满意地拍拍营养和水分都补足的脸,又整理着头发。张姐的老公和孩子在楼下等着,接张姐一块去看望个病了的长辈。有车,顺便把你们送回去,天也黑了。张姐极力邀请着。婶子刚才替她免费做了个卵巢保养,人家这是感谢呢。婶子客气地推辞了下就连连催亚茹快点。
下了楼,就看到了路灯下两个大个子。张姐的老公是市里一个单位的头头,有着这个年龄的中年人都有的肚子和微微少发的头顶。但看到他旁边的儿子就知道,他年轻时有多帅。刚才两个姐看照片的时候,亚茹也偷偷地瞄了一眼。两年不见了,亚茹看不见自己的变化,可人家已经变成一个相貌堂堂的大男孩了。男孩看到亚茹,也稍稍愣了下,想起什么,又一低头坐到了车前面。下楼来的三个女人就挤在了后面。亚茹在男孩后面坐着,只看到男孩的后脑勺,有好闻的洗发精的香气弥散开来。上路了,城市的路灯大大方方地燃起一路明亮。在每一处路灯最亮的光照下,男孩的头发一根根滤过黄色的光晕,唰,唰,唰,似乎灯光被这结实粗硬的头发一下一下切断了,碎了亚茹一身。他的肩膀也像个大男人的样子了。想起三年前见他时,他还有些害羞,现在已经知道表现自己的骄傲了。自己呢,也不再是当初那个傻乎乎的小孩了,婶子说,你已经快是大人了。想起这些,她听到自己叹了口气。
出了门走上一百米不到一拐弯就上了那条路。和城市漂亮的路灯充足的光照泾渭分明,这条路寂静黝黑,车灯向黑暗发出一道射线,刺破了寂静。路两边草丛中的青蛙、甲虫、潮虫、蜣螂的梦被惊醒了吧。婶子他们几个大人谈论着城市拆迁征地的事。亚茹不吭气,男孩也无话可说。两个人保持着沉默,倒好像是对大人们热衷的事情达成了相同的共识,在这沉默里,亚茹清晰地捕捉到了男孩的呼吸。
车停在婶子家门口。婶子弯着腰感谢,摆手说再见。
进了门,婶子在前面走着。黑子本来睡着了,听见镯子的叮当声又激动地跑来,在亚茹脚跟蹭来蹭去。和黑子玩了一会,亚茹让黑子回去了。黑子是邻居家的狗。黑暗中,亚茹对黑子说,明天早晨见。
婶子嘱咐亚茹关大门。关大门的时候,亚茹确认张姐他们一家已经从那条黑乎乎的路上驶出,在城市的公路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