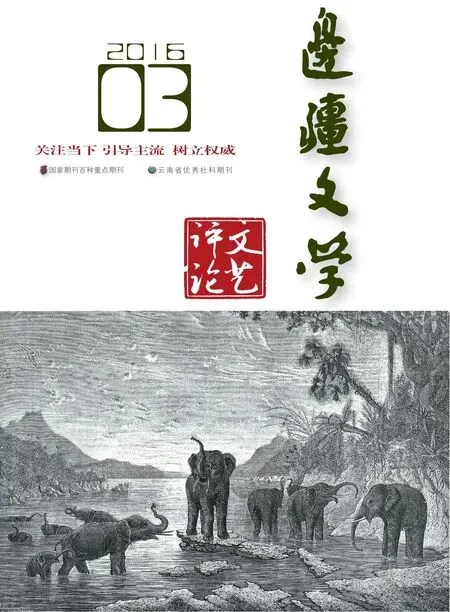论《卡门》的叙事策略
◎孙佳丽
论《卡门》的叙事策略
◎孙佳丽
梅里美在十九世纪文学大潮流中能有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那独特而又高超的写作技巧。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叙事技巧方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所以历来不乏有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入手来对其及作品进行研究。本文继续从叙事策略出发,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梅里美的风格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讨。从《卡门》的叙述视角转换、不可靠叙述、含混的评论与反讽等多个角度来研究梅里美在《卡门》中叙述策略的呈现方式,并且更进一步地探讨作者采用这一叙述策略的深层动机,弥补以往叙事研究方面的缺憾。本文试图将文本与作者粘合在一起,由外到内、由形式到内涵,顺利实现作品与作家之间的互动研究。
要全面探究《卡门》的叙事策略首先需要弄清楚“叙述视角”与声音的关系。因为任何一篇小说都是通过一定的“观察点”来描述故事,并且通过特定的声音让读者明白叙述者内心的感受和态度,高明的叙事策略往往也是通过变换叙述视角、调整声音距离等方面实现的。
在许多研究论著中,视角和声音一直被视为一体。虽然两者都是从叙述者角度出发,但并不等同。在热奈特那里,视角研究的是叙述者从什么角度看对象世界,声音则是研究叙述者如何通过叙述话语显示自己的存在,在大多数作品中,这两者是同一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二者是呈分离状态的。视角与声音之间是一种比较辩证的关系,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作用。
一方面,从视角的角度来看,无声的视角只有依靠声音来显示其存在,这样读者才能够得知叙述者眼中的世界及其心中的感受。另一方面,从声音的角度来看,叙述者的声音受制于他所在的视角。主要表现在,首先大多数叙述者在传达信息时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带有个人的情感色彩,因此,当声音是由不同的叙述者发出时,也就会传达不同的感受,从而造成词汇色彩的多样化;其次,特定叙述视角还限定了相对应的叙述内容,当视角仅落在某一人物身上时,声音就只能表达这一人物的感受和态度,而对于其他人物来说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总的来说,视角与声音之间是一种既依存又制约的关系。两者间的这种微妙关系造成了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更进一步地构成了整部作品在叙述话语上的多重性、在叙述空间上的留白性。而以上的这些论述正是笔者能获得对《卡门》某种形式上发现的理论依据。
一、《卡门》独特的“双重第一人称内视角”结构
热奈特对“观察点”进行了概念总结,用“聚焦”一词形容叙事的观察角度。他认为,叙事类作品的聚焦类型有三种:零度聚焦(非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零度聚焦指的是无所不知的观察视角。叙述者不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物的经历,甚至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在“非聚焦”叙述者面前,每个人就像是透明人那样毫无隐私可言,因此,这种视角也被称为“上帝的眼睛”。第二种内聚焦。在这种叙述视角中,故事是通过作品中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叙述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者)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测、臆断其思想感情”。第一人称叙述就是内聚焦的一种。最后一种是外聚焦。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向读者呈现正在发生的事,他只提供人物的外部行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内在动机和情感态度。而梅里美在《卡门》中则明显地使用了“双重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叙述策略。
《卡门》总篇分成四个部分(不包括序诗):第一、二部分的叙述者是以第一人称身份出现的考古学家。“我”要到“蒙蒂拉”做一次长途考古,在安达卢西亚结识了一位躲避官兵追捕的强盗,并帮助他逃脱追兵。为了得到一些关于古蒙达的有用资料,“我”在科尔多瓦“住了几天”,在这里邂逅了美丽的波希米亚女工卡门希达。被她身上独特的神秘气息吸引,“我”接受了她为我算命的邀请。在这期间,我的金怀表不知何时被她偷走。后来神父告诉“我”,强盗已经被抓住并要被处以绞刑。出于友情,“我”来到狱中探望这位即将离开世界的朋友。第三部分的叙述者是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的强盗唐·约瑟。由唐·约瑟的视角讲述了他与卡门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第四部分又回到第一人称叙述身份的考古学家。这部分可以说是作者提交给读者的一篇关于波西米亚人的研究性材料。在最后这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关于波希米亚人的人种性格以及历史发展的分析。从《卡门》的整个作品结构可以明显看出叙述者身份的转换:由一位来自法国的考古学家叙述逐渐过渡到一位经历不凡的强盗唐·约瑟的叙述。在这里,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唐·约瑟都是作为故事中人物出现的,并且他们都是以“我”的口吻来讲述各自经历。在此,笔者暂时把这种叙述视角命名为“双重第一人称内视角”。
首先,叙述者都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但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同。内视角是从作品中某个人物所处的位置来展示其所见所闻,所以,当考古学家以“我”的口吻来叙述他的经历时,读者就只能从考古学家的角度来一步一步进入故事(“我”因为考古工作需要收集一些材料来到安达卢西亚,在路途中遇到一个陌生人,通过进一步交流“我”得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强盗)。在叙述故事时,读者总是从“我”的眼光去观察、思考、判断,这样读者很容易把自己设置成考古学家这样的身份定位,其所达到的好处就是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当读者把自己设想成考古学家后,就会不自然地被考古学家的价值观念所牵引,而对有着“传统”文明意识的向导是一种鄙视和不满,从而不仅使故事在表层上有一个可信的叙事背景,就连深层的价值判断也会得到读者的认可。同时,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唐·约瑟、卡门希达)对于我们是神秘的、不可知的,我们有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保持着对其的好奇心。
当叙述视角转换成唐·约瑟之后,故事也就算是真正地开展了。随着他的叙述,卡门也登场了。他讲述了认识卡门的全过程,在这样的镜头推进过程中读者不可能置之度外,看着一个小伙子由高贵的出身逐渐堕落为一个走私贩、强盗,没有谁是不感到惋惜和同情的,带着这种同情来看卡门,她俨然就成了一朵“恶之花”。事实上,从唐·约瑟角度看到的卡门必然是非客观的、带有个人情绪的,这也形成了我们对卡门的一个片面的认识。
另外,双重第一人称内视角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探究。作者在唐·约瑟的告白中安排一个旁观者,让两个“我”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小说里,这种对话关系具体表现为作为考古学家的“我”对作为强盗的唐·约瑟为爱情放弃一切壮举的倾慕,被他那独特人生经历吸引,耐心听取并记录了关于他和她之间的爱情故事。对话的结果是“我”饶有兴味地听着、记录着这个关于“强盗与女巫”的故事,并对这个“神秘野蛮古朴”民族的语言、性格等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小说的第四部分)。虽然在第二部分我们只听见了唐·约瑟的声音,但是从叙述者对旁听者所造成的影响中可以窥探隐藏在听者冷静客观表面下内心欲望的喧嚣与骚动,即对卡门,这个恶魔似的、与众不同的女人无法自拔地迷恋。
二、唐·约瑟的“不可靠”叙述与“离间”效果
W·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不可靠叙述”这个概念。布斯把“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的这样一类叙述者称为“可信的”,反之称为“不可信的”。他在定义“不可靠叙述”的同时,也提出了“隐含的作者”的概念。“隐含的作者是作者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在他(作者)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通过以上布斯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不可靠叙述和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作者在创作时,通过叙述者将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是读者会发现作者不完全等同叙述者。可靠叙述者令读者信服,不可靠叙述往往使读者产生种种疑虑。
在《卡门》中主要有两个叙述者,由于第一个叙述者(考古学家)是作为故事边缘人物,扮演的是倾听的旁观者角色,因而他的态度、价值取向并不是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相比较而言,唐·约瑟的亲历者身份倒是决定了他的叙述会带有个人情感判断。由于他和卡门特殊的情人关系,使他在提到卡门,并讲起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时不能保持“冷漠客观”的“叙述风度”, 自然而然地就让唐·约瑟的叙述参杂了他个人情绪化成分。
从他的视角,我们知道他是在卷烟厂当门卫时遇见了卡门。“她穿着一条非常短的红裙子,露出满是破洞的白丝袜,一双小巧玲珑的摩洛哥式的红皮鞋,上面系着火红色的绸带。她撩开头纱,露出双肩,以及别在衬衣上的一束金合欢花,嘴角上还衔着另外一朵金合欢花。她扭着腰肢往前走,活像科尔多瓦养马厂里的一匹小母马。”这是唐·约瑟对卡门第一次出场的描述,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卡门的态度,“就像一个真正的波希米亚女人那样淫荡无耻。”而且,他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他的感觉,“起先,我并不喜欢她”。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把卡门与唐·约瑟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唐·约瑟走向堕落的开始。他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中邪”,称为卡门所做的一切为“蠢事”,而且当他爱卡门爱得越深他就越觉得她“是个魔鬼”。
总之,从唐·约瑟总体叙述中可以得出他对卡门又恨又爱的矛盾态度。如果把这种叙述中所包含的爱情情感因素去掉的话,所展现的卡门其实就是一个放荡、自私、让人堕落的邪恶魔鬼,这样的一个妇女是让人厌恶、不耻、嘲讽的。然而,隐含作者也是想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吗?对此读者是心存疑虑的。
事实上,作品中的叙述者并不等同于隐含作者,他们之间有时会出现“审美距离”。W·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到关于“距离”:“时空的距离、社会阶级或言谈服饰习惯的差异——这些和许多别的因素用来控制我们涉及审美对象时的感觉,就像某些现代戏剧非真实的舞台效果具有‘离间’作用一样。”“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隐含的作者。这种距离可以是道德上的,还可以是身体上的。”在《卡门》中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唐·约瑟是分离的,这种分离造成了唐·约瑟的道德价值判断与作者之间可能存在着距离。唐·约瑟不断地声称卡门是一个魔鬼,是诱使他道德堕落的荡妇,但隐含的作者对唐·约瑟所谓的“堕落”是一种默不作声的赞美。其实,唐·约瑟是一个表面上不可信而实际上可信的叙述者。
细细探究唐·约瑟的叙述会发现他总是在强调自我的不可控制性。“我看见那朵花就掉在我两脚之间的地上;我那时不知中了什么邪,竟趁着伙伴们不注意时把花捡了起来,飞快地把它当作宝贝似的藏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她老是说谎,我不知道在这姑娘的一生中有没有说过一句真话。可是,只要她开口说话我就不由自主地信以为真。”“总之,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开始说傻话,并开始准备干傻事了。”“先生,一个人变坏是不知不觉的。一个美丽的姑娘冲昏了我的头脑,我为她与人打架,闯了祸,不得不逃进山里,连想想也来不及就从走私贩子变成了强盗。”从他的这些表白中可以知道卡门身上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在吸引着唐·约瑟,这种魅力就像那朵金合欢花充满了神秘的野性与妖娆。正是被这种别样美的吸引才使得生活在文明规范之中的唐·约瑟不顾法律道德的制约最终拜倒在卡门的石榴裙下。
《卡门》的另外一位叙述者考古学家可以说是隐含作者的化身,他作为一个旁听者,在第三部分基本上没有直接态度。但是从整个作品来看,也可以隐隐窥探他对卡门的一个情感态度。
在第二部分里,“我”第一次偶遇了美丽的女工卡门,被她身上独特的女巫气息吸引“我”到她家,并让她给“我”算命,结果于无意之中被偷走了昂贵的金表,但是,作为“受害者”的“我”显得并不在意。“说实话,我宁愿失去我的表,也不愿去法官那儿作证,吊死一个可怜的家伙,尤其是因为……因为……”因为什么呢?重复的“因为”到底是为了显示“我”因为着急朋友而语无伦次,还是为内心羞赧的情感找一个大众化的借口?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个深思的空间。
考古学家不愿意要回昂贵的金表,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可怜的唐·约瑟作为其中之一原因已经说出来了,“尤其”显示了更重要的原因。面对神秘迷人的异域女子,或许考古学家也已经“中毒”了吧?,只是“中毒”程度不同而已。假设条件允许,考古学家或许大有步唐·约瑟后尘的可能,而作为读者,在阅读时,也不自觉地成了紧随唐·约瑟和考古学家之后,成了中卡门爱情之毒的“牺牲者”。
考古学家前往监狱看望唐·约瑟,出于友情之外,更为真正的意图是想进一步获得关于卡门的最后消息,以排遣自己对这个一见便难以忘怀的女人的难耐情思。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小说第四部分存在的缘由和意义:正是对这个姑娘的爱恋,引起了“我”对其整个独特种群的兴趣,并对这个民族进行细致研究。最终,以研究性结论的方式告诉来自文明世界的读者,波希米亚人是多么伟大的存在。事实上,作者是想通过这种宣言式的呐喊,以祛除“文明人”身上对“野蛮人”所固有的偏见与鄙视。唐何塞所说的“中邪”,不仅在考古学家身上再现了,就连读者也会被这种魔力牢牢控制住。
从以上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对于卡门这样既热情似火又美如天仙,既聪敏机灵又邪恶狡狯的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妖女,无论是唐·约瑟,还是考古学家,抑或是隐含作者对卡门这样的女子都有一种不自觉的、难以抵制的吸引力。所以所有的叙述者其实都是沉迷于这样的一种魅力之中,表面上对卡门的诅咒其实更加彰显了隐藏在他们内在对卡门的赞美与追求。
三、序诗的含混性与人物设置的反讽性
在胡亚敏《叙事学》一书中将“含混的评价”的特征归结为“叙述语言的歧义性和意义的多重性,它的主要形式是反讽。”在《卡门》中存在着一个比较为读者所忽略的部分:正文前面的序诗(“女人皆祸水,美妙仅两回,或是坠爱河,或是临终时。”)这是梅里美引用希腊作家帕拉达的一句名言,不管原文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在这里主要研究作者把它用来作《卡门》序诗的用意。
这句话有两种理解的角度。第一,即,所谓的“红颜祸水论”;第二种理解值得深究。作为一个“标示”,这首诗也寓意深厚。“标示”是傅修延提出的一个叙事学范畴,通过标示,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意图提炼出来,提醒读者。
结合《卡门》的表达内容,这首诗其实很好地展现了卡门的一生:“轰轰烈烈地爱、为争取自由义无反顾的死”,而作者用了两个字形容:“美妙”。虽然女人是祸水,她使男人失去理智,从而坠入爱情的深渊、陷进欲望的泥淖,但这也正是女人的魅力所在。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反讽。表面上说女人是祸水,然而当这种祸水真的来“祸害”人间时,作者却说她是美妙的;死亡是可怕的,但当一个人为了追求自由而拒绝被束缚地苟活时却又是美妙的。
作为序诗,这里面必然也隐含了作者对卡门的评价。正如上面所说的,卡门是一个聪明狡诈、漂亮妩媚的波希米亚女子,她轻佻、放荡,她让唐·约瑟这样原本老实本分、前途光明的男人最终堕落成一个走私贩、杀人犯,在这个方面来说,她无疑是祸水。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她对唐·约瑟没有爱情,她会正经地和他爱的人说“你知道吗,小伙子?我想我是有点爱上你了!”卡门是很自私的女人,他和男人们接近大多是为了利益,比如接近考古学家是为了金表,接近上校、军官是为了走私,然而她对唐·约瑟说,“你怎么这么蠢啊?你没看出我爱你吗,既然我从来没找你要过钱?”另一个方面,当卡门不爱唐·约瑟的时候是决绝的,她不愿意被爱情束缚,波希米亚人天生爱自由,所以她会最终选择被杀死也不愿被任何人束缚,“我跟你去死,但我不会跟你一起活下去。”“作为我的罗姆,你有权杀死你的罗密,但是卡门永远是自由的”。这可以说是卡门临终之前对自由的宣言。这样的卡门是悲壮的,是值得赞扬和讴歌的。
其实《卡门》中还隐藏了一个更大的反讽。由于唐·约瑟是叙述者,所以很容易从他的角度去评判卡门,读者的价值判断容易受到制约。现在,试着反过来,从卡门的角度来看作者设置唐·约瑟的目的。卡门对唐·约瑟的态度除了爱情之外,更多的是嘲笑、讽刺、反抗。
卡门想方设法地把一把锉刀送到监狱就是想让她的救命恩人逃出这个束缚人自由的鬼地方,结果唐·约瑟为了“当兵的荣誉感”宁愿老老实实服役,并忍气吞声地去当个站岗小兵。对待严于执行军令的唐·约瑟,她的态度是嘲笑“归队?难道你是个黑奴,听人随意摆布的?你真像只金丝雀,穿的衣服像,脾气也像,去吧,胆小鬼!”当唐·约瑟问他什么时候再见面的时候,她的回答是“当你不再傻的时候”。当唐约瑟痛苦时,她调侃道:“嗨!龙的眼泪!倒可以让我用来做媚药。”“你永远是个白痴!”
《卡门》的主人公无疑是卡门,唐·约瑟实际上是作为卡门的陪衬,他的世俗观念根深蒂固地嵌进他的灵魂,使他习惯于循着文明社会的种种规则,不敢有丝毫的违逆之举。他不敢用卡门送来的锉刀锉断狱栏逃跑,他对自由的欲望并不像卡门那样地强烈。对于他的堕落,并不是由于他渴望一种无拘束的生活,而仅仅是对卡门的爱情欲和占有欲使然。对此,他甚至责怪卡门是“魔鬼”。唐·约瑟觉得自己堕落的根源是来自卡门的“诱惑”,在他看来,自己当了强盗,去干走私、杀人这些傻事是自己为了追求一个“魔鬼”付出的代价,等价交换的资本主义商业原则使他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示着对卡门的占有权。一旦这种占有实现之后,他便渴望着救赎。他不追求自由,他只追求卡门,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独自一个人占有卡门。
从这些可以看出,世俗爱情生活中的对女性的统治欲和嫉妒恶习仍然支配着他的行动,文明社会中的道德伦理规范依然是他最终自我定位的尺度。卡门对于唐·约瑟愚蠢行为的嘲笑,实际上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制度下培养的无能懦弱小人物的嘲笑,她对唐·约瑟专制爱情的反抗,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下滋生的自私独霸意识的不满和控诉。
四、叙事策略中隐含作者的道德伦理倾向
历来对梅里美的研究总是离不开“客观叙述”、“不动声色”、“不动感情地冷漠叙述”等等这样的评价。确实,由于作者巧妙地设计了两个叙述者,并让他们之间展开对话,这种方式使作者本身很好地隐藏起来。然而正如布斯所言:“简而言之,作者的判断,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找的人来说总是存在的、总是明显的。它的个别形式是有害还是有益,这永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不能随便参照抽象规定来决定的问题。当我们现在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
小说《卡门》由叙述策略所造成的独特之处在于,读者直接面对的故事并非作者所要真正讲述的故事。《卡门》的表面上的故事,是作为第一个叙述者而存在的考古学家,在其关于地理学术研究的路途中,饶有兴味地“插叙”的一段往事。地理研究中的种种,显然不是作家真正要讲述的故事,小说的真正内核则是另外一个叙述者唐·约瑟叙述的关于卡门的故事,而从卡门故事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态度可以说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心。
詹姆逊将叙事定义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即将叙述话语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一种或赞同、或反抗的隐语与发泄。詹姆斯认为,作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作家采取的叙事手段。特别是作家表达一种对立的价值意识时,迫于统治意识的压力,往往会采取一种比较隐晦的伪装来保护自己。无疑梅里美选择的是伪装。结合梅里美的生活实际来看,1803年梅里美出生在巴黎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大学的教授,母亲也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在这个开明的资产阶级家庭里,梅里美自幼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青少年时期的梅里美就向往把自由与力量作为精神的栖息地,形成了对时代、对艺术异常敏感细腻的气质。但伴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来的并不是理想中的自由,而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疯狂的痴迷与追求,甚至沦为物质的奴隶,这时的人变得虚伪而又懦弱、自私而又狭隘。
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梅里美深感失望,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会有对来自西班牙贵族唐·约瑟的嘲讽与蔑视,对卡门那种不顾一切追求自由精神的赞美与宣扬。回归到原始初民们自由自在、直率坦然的生存状态,成为梅里美对抗18世纪末被技术革命现代化和深刻异化了的社会的宣言。鉴于梅里美秉持着这样一种伦理修养,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他作品里,那充满异域情调的话语,其实就是其在文学创作中躲避文明的实践。也读懂了像卡门这样充满野性、追求自由、对文明世界不屑与嘲讽,实质上都是作者在弥补对本土现代文明给心灵上所带来的一种幻灭感,也是作者在极力拯救已经碾碎在现代文明车轮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通过对《卡门》叙事策略的分析可以感受到,作者运用双重第一人称内视角的方式,一方面造成作者本人的直接引退,从而为表达一种与文明相悖的价值取向做了很好的遮蔽物。另一方面,视角的变化便于不同人物之间对话交流与情感上的一致性,从而为作者终极结论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证据。含混的话语模式显出作者创作上的自由,梅里美是一位高超的心理大师,他不直接告诉读者他自己认同什么,而是通过各种手法来悄无声息地“控制”读者,但这种控制并不是一种专制,无论是前面的序言,还是对卡门的故事,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个从历来对卡门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然而在梅里美的作品中,我们却无法否认那种自由的、粗犷的、带着原始野性的人物身上有着一种“文明人”所没有的“魔力”,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种魔力的积极性,但至少通过它,梅里美能找到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心灵栖息地!
[1] 梅里美.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精选[M].王虹等译.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2] 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 胡亚敏.叙事学[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贺秋帆.小说《卡门》的叙事研究[N].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 期.
[5] 黄茜.试论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D].·江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
[6] 张静.论梅里美创作的边缘意识[D]. 兰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
[7] 胡亚敏.论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N].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8] 李慧、张虹.浅析梅里美小说的叙事风格[N].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文艺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