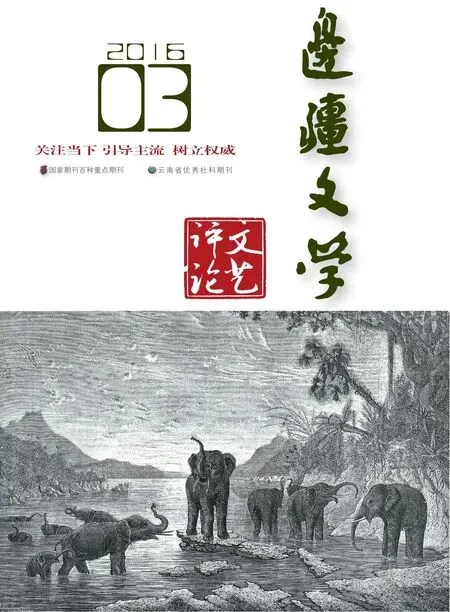歌唱的心的和声
——读张直心《晚钟集》
◎李 骅
歌唱的心的和声
——读张直心《晚钟集》
◎李 骅
标题借自著者挚爱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晚钟集》后记中著者自述曾于劫难中抄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以安魂。由心而歌,同声相和,这恰是我读《晚钟集》的核心感受与感动。文集那似曾相识的语感、气质牵引着往事,怦然而来的新见却又分明指向未来。
一、历史面具及精神图景
作为著者学术研究的重心,鲁迅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本书中获得了更深、更多的梳理和总结。在对众多作者、作品“精神谱系”般的整理和考掘中,不难发现:著者无意重构文学史,却以独辟蹊径的灼见,每每烛照作品的内核、作者的心地和时代的本源,从而无限逼近了文学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中诸多大事件的真相、小人物的真情。著者每每于历史的大起大落之间关注其起承转合,于“金光大道”之外关注歧路支流,于章节段落之余关注天头地角处的留白,如此望闻问切,见微知著。无论面对史料的冗杂吊诡,还是前论的“历史局限性”,著者心中和笔下始终是耐心且耐烦的,尽力克制隐忍,偶有峥嵘气象,也都是缘于读者期待的“史笔”的正气和学术的直言的迸发。
一个常识是:生活每天都是现场直播,历史无法排演,文学史亦然。于是,在作品和思潮的“前台大戏”之后,有关创作习惯、心理成因、艺术个性之类的“后台”景象往往更加诱人。显而易见,这应该是切入现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和心灵史的重要手段之一。
尤为动人的是,于此一途中,正如此节小标题所示,有意无意间,著者事实上已然剥去了文学史中的太多“面具”,然而,超越习见的意外在于,无论面对的是曾经的“铁面人”、“二皮脸”,抑或“鬼画符”,在真容呼之欲出之后,其并未刻意追索“面具”之下的“素颜”或大众意义上的“真相”,却转而关注其尽可能全面的精神图景和内中的价值逻辑。而这,岂不正是新时代下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突破困局的关键所在?
“史笔”之外,著者多用“简笔”和“伏笔”,在阐述中“留白”,在所谓“必然”中假设,在句号之余画下问号,在呼之欲出之际“打住”,在情感沉淀之后方抒情。文集一再提及“规范”意识,窃以为,这既是建立在学术坚守和学者情怀之上的精神洁癖,更是因着这一代人突出的家国意识和典型境遇带来的独具只眼。
其实,对作品、作者和研究者的研究,本是著者当行本色,然而,似这般的细腻、精到和绵密,以及水到渠成之后的豁然开朗,独辟蹊径之后的耳目一新,带给读者如此丰富的精神探险或促膝对谈之愉悦,却真心不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常见境界。
二、诗人之思与哲人之诗
一直以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尤其是云南文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始终是著者文化视野中的重要观照范畴和研究对象,此中创见多多,且多数都是在见人所习见的情况下言人所未言。究其功力,窃以为“功夫在诗外”。这诚然是以著者长期云南生活经历和边地文化浸染为基础的,源自多重文化视角辨析后获得的文化资源和理论力量;更是著者结合自身生命气质选择的文化皈依(著者坦言:“云南是我的精神原乡之一”)。想来是有心编排,文集首尾两篇俱是写云南的文章。云南各个时期的实力派作家、诗人或后起之秀,如汤世杰、黄尧、于坚、李钧龙、黄晓萍、先燕云、黎小鸣、张雷自在著者视阈中,而对李乔、李必雨、存文学、岳丁、景宜、董秀英、张焰铎、查拉独几、哥布、纳张元、黄雁、陈建华、亚笙、张仲全、毕然等少数民族作家更是倾心评点。
显而易见,作为书中关注的某个重点,以艾芜、沈从文等为代表的先驱,正是这一道路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于是,基于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续接,和前人相似,在著者的价值谱系中,民族文学及云南文学至少承载了三重寄托——“文化飞地”、“摄魂之地”和“精神圣地”。细加辨析,较之前人,著者的这一选择似更加自觉、全面和深刻。
正如著者当年知青岁月中擅长的插秧、犁地和剥笋一般,用力还需细心,以此从民族“文化史”、甚至“精神史”的高度出发,让笔下画幅缓缓舒展,同时揭示出相关作品文学意义上的“文本价值”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价值”。除却研究成果本身,这一学术姿态及方法本身,也包含着寓意丰富的暗示和多重的启迪。
基于“平视”立场和多维视角,著者在“作品”和“理论”之间驾轻就熟,行文逻辑丝丝入扣,多有数学推理般的思维快感和美感;理论激情奔涌如铁骑突袭,思辨深处刀剑齐鸣。而更多的也更可珍视的,则是还“边地”以本色,凭借天赋的艺术敏感和后天炼就的审美穿透力,珍视点滴细节,进而小中见大,曲径通幽,借助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学科的工具拓宽读者视野,进而敞亮彼此心域,真正把“魂”放到了民族历史、信仰和气质的内核之中。惟此,边地于著者而言的“精神的第二故乡”意义,也就因这样的贴近、渗透和融合,成就了近乎献祭般的虔诚;而被人追慕为至高姿态与境界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理解之同情”,也就在著者笔下显得如此的自然而然。
反观此道中不在少数的先入为主者的“自说自话”或虚妄张狂的“空口白话”,大都连基本的“民族观”都还东倒西歪着,遑论其他!
三、书斋立场和人间情怀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评论家以及人文学者普遍遇到的共同问题——“文学何为”、“学术何为”已然在当下社会、文坛、学界中深度发酵,渐次形成精神谜局、乃至危机。甚至衍生出“何谓文学”、“何谓学术”一类的困惑和忧虑。于是乎,或高台教化,一味端着;或顾影自怜,假作清高;或描眉画眼,刻意时尚。在连环套中饰演空城计,进退维谷,方寸大乱,反美其名曰“多元化”、“多样化”。如此这般,无论作为“知识分子”或“学者”而言,精神的拮据和境遇的尴尬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
溯其渊源,正如书稿中潜行不断的一条脉线所示,与世界同理,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当下,“书斋”或“广场”抉择中的典型人或事,以及由此派生的“启蒙”或“救亡”,“写什么”或“怎么写”,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对此,和前辈中那些才、学、识俱佳的学者一样,著者以自身的治学实践和实绩再次证明:任风声雨声裹挟家事国事,无论“载道” 、“言志”抑或“抒情”,有质感、有质地、有质量的思考和研究,均会因其坚卓的姿态、坚实的内核而外延深远,回响不绝!静观书稿:含情带血,真性情直通学理;眷注遥深,大情怀岂止文章。
正所谓太阳之下无新事,著者执着于自我精神之路的攀援,渐次从历史的循环中看出自由的上升,从思想的A货中炼出学问的正品,从偶然性的大海中寻出必然性的浮木,聚而成筏。然后,或者真的如鲁迅所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也许,正是在这一哲学高度上,“以史为鉴”四个字真正概括了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对当下芸芸众生的价值之所在。
书末“后记”在对治学历程的梳理中,预料之外然又情理之中,著者写下了“退守在书斋”的句子。窃以为,这绝非自谦,更不必刻意解读为东方民族特有的“以退为进”之类的柔术或遁词。质言之,守住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持续至深处,辐射至远方,能如此,则是否是“退”,是否在“书斋”,真的还重要么?无论是否非要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著者击石取火,以心成釜,继而聚精神柴薪,煮自己的肉。其所欲者,诚然有在思想承传之下,“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使命意识;更为当下深陷“历史终结迷幻”中的所谓“绝大多数”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真诚、深情,甚至略带焦灼地提醒其“精神胎记”和“文化基因”的所在,寄望我们若言及“我是谁或去哪儿”的时候,多少能够因为居然知道了“打哪儿来”而正本清源,然后晓得在面对诸等“新“模式,如“互联网+”之类时,问一声打哪儿“联”,“联”什么;“+”什么,怎么“+”?以便往后不至于依旧超大面积地荒腔走板,或者协力同心地自我催眠。
临了还想说的是,作为读者,我尊重并挚爱著者书末凸现的“晚钟悠扬”的意境与意向,并自认多少能够体味此中的神性和厚重,以及热忱中的理性,超脱中的坚持;但,却不能认同著者“行程过半”、“年华向晚”一类的感伤。一直的趣味在于——书的本身自有其生命,再说“一千个读者耳畔便有一千种‘晚钟’ 声”,许是慰藉,或成号角,换个角度听,晚钟,又岂知不是“晨钟”呢?正如先生笑谈的“书生老去”,试续四字——哲人自来!
(作者单位:昆明诺仕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