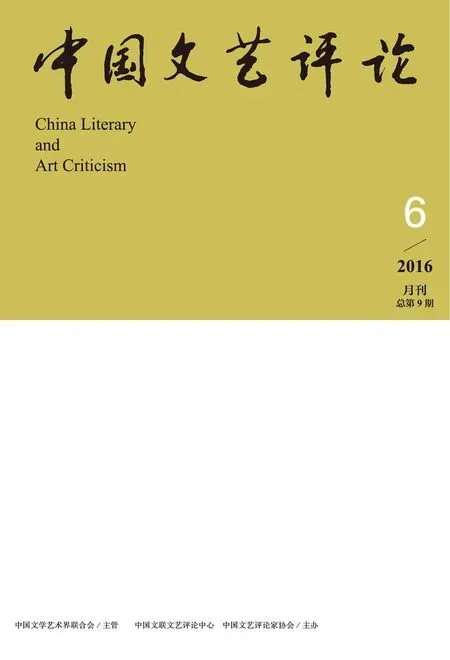张世英对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推进
毛宣国
张世英对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推进
毛宣国
张世英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也是对中国当代美学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他的美学思考推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研究,这种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哲学本体问题的关注,使张世英意识到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缺陷和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可贵,他以此为出发点的美学思考,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二、对西方现象学美学,特别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美学的接受,彰显了隐蔽对敞亮、不在场对于在场的艺术哲学的重要性。这种彰显有助于破除中国当代美学长期执著于“主客二分”、执著于“在场”,将美的问题抽象化、本质化的思维模式,突出了想象和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对人们思考中国古代美学重要理论问题如“隐秀”“意象”说等,有一定理论价值。三、“人生境界”说和“美的神圣性”的观点说明,对美的认识不应停留在知识和常识的意义上,而是应该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绝对的价值存在,走向高远的精神追求。这种认识提升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理论和精神层次,使美学更加贴近人生,更能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创造。张世英的美学思想,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著名美学家叶朗充分肯定了张世英的理论贡献,认为他的著作,如《天人之际》《进入澄明之境》《哲学导论》《境界与文化》等,“对于中西美学的沟通和融合,对于美学理论的建设,都有很大的推进作用”。[1]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笔者赞成叶先生的这一评价,拟从三个方面具体谈谈张世英对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贡献与推进。
一 、哲学本体的关注与中国传统美学价值的发现
张世英长期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他的美学思考,与他对哲学本体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张世英说,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主体性的讨论,使他意识到西方传统哲学对主体性理解的片面性,开始关注西方现代哲学,并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的批判中,体会到人对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有主客二分和主客不分两种,并进一步体会到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可贵。[1]张世英:《天人之际·序》,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与思维模式,在张世英看来,特别适合于美学。因为审美活动不是一种科学认识,而是一种体验。体验就是不问主客,不分主客,是人与物的交融,是“天人合一”。以此为出发点,张世英开始了他的美学思考和理论建构。
张世英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哲学与诗的脱离,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世界,对于这样的哲学必须加以超越。他明确指出:“哲学不能老停留于抽象概念,而应当重现实,不能老停留于思维和理论而应当重想象重实践,不能老停留于哲学本身,而应当与人生相结合,与诗和文学相结合。所以我在本书中提出并讨论了诸如思维与想象、诗与思、在场与不在场、隐蔽与显现、言与无言之类的新范畴。”[2]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页。他把这称之为“哲学的新方向”,认为它“超越哲学的旧传统,把哲学变成真正贴近于人、贴近于生活的有激情的东西”[3]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页。。张世英所说的“哲学的新方向”,不是从概念出发,不是将哲学看成是一种认识,看成只是与思维相关的关系,而是强调哲学的诗意,强调想象对于哲学思维的重要性。他认为,“哲学要现实化,就必须诗化,也就是把哲学变成诗的哲学、艺术的哲学”[4]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诗的哲学和艺术的哲学的目标不是知识和概念,而是提高人生境界。张世英认为,当把哲学界定为普遍规律之学,也就是将哲学界定为科学的时代终结以后,还应该有一门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学问,那就是以提高境界为目标的学问。哲学就是“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5]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以提高人生境界为目标的哲学决非抛弃普遍概念和普遍规律,决非抛弃知识,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6]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哲学应以建立在万物一体基础上的诗意境界和民胞物与的精神为目标,这种境界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7]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境界之学的提倡,在《哲学导论》中主要偏于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展开,而在2007年出版的《境界与文化》中,张世英则比较集中地思考了个人的人生境界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人生各种文化活动中、各种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中,“审美境界”又处于核心地位,它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不仅超越“欲求” “求实”,而且也超越“道德”的境界。人们只有在审美境界中,才超越了物与我之间的分隔与界限,达到了人与世界的融合为一。
对于张世英的“哲学的新方向”理论和“审美境界”的弘扬,学术界或许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与评价。笔者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张世英的这一理论尝试,是试图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哲学与美学,寻求一种新的哲学美学思考方向。这种哲学思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重新审视了西方传统哲学观念,而且也重新发掘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的价值。叶朗谈到中国近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将朱光潜作为中国现代美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认为他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了美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是反映了西方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趋势,一是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历史趋势。张世英的美学理论与研究,同样反映了这两个趋势。与朱光潜不同的是,张世英的美学思考更明显地表现出向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回归的趋势。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术语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不同以及与西方现代一些重要哲学思潮的相同相通,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1]张世英:《天人之际》,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不是主客二分,而是天人合一才能解释审美意识,所以中国哲学和美学必须告别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哲学和美学,走天人合一的道路。他还在西方现象学哲学思想的启发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超越在场”思维特征的意义,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重现实、重想象、重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优点”[2]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页。,有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的“不在场”的思维传统,而这些对于中国当代哲学美学的思维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张世英用“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概念来解释哲学与审美,提倡“境界”之学,这些概念都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张世英把他的哲学称为“万有相通的哲学”,认为“哲学之最高任务不是认识相同性,而是把握相通性”[3]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页。,这种认识也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启发。他说:“西方古典哲学家大多重认识论,把认识相同性视为哲学的重要任务,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重本体论(存在论),认为把握现实的东西之彼此相通的哲学的重要任务。”[4]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页。在他看来,只有中国哲学的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思想,才能突破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从宇宙整体的内部体验到一种物我(包括人和己)两忘的境界”[5]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页。,这正是最高的审美意义和价值所在。
张世英向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回归是一种哲学本体意义上的回归,也是充分认识到西方传统哲学弊端之后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意义,只要我们回顾一下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发展进程就不难明白。这种哲学本体意义上的回归并不始于张世英。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美学界就有人试图从中国传统形而上哲学本体思维的高度来思考美学问题。比如,方东美在《生命情调与美感》《哲学三慧》《中国人生哲学精义》等著作和演讲中,就试图用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思想来阐发中西审美、艺术、科学观念的不同。他认为,“生命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广生之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1]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台北成均出版社,1983年,第98页。——这是中国哲学基本精神之所在,所以中国古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多将生命寄于科学,而是寄于艺术,富有艺术和审美的生命情调。方东美还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思维的不同。他说,“从近代欧洲人看来,人和宇宙的关系则是二分法所产生的敌对系统,有时是二元对立,有时是多元分立”[2]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蒋国保、周亚洲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65页。,即主客二分和心物二元,而“从中国人看来,人与宇宙的关系则是彼此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中道”[3]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蒋国保、周亚洲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65页。,即天人合一、心物一体。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我们立足宇宙之中,与天地广大和谐,与人同情感应,与物物均调浃合,所以无一处不能顺此普遍生命,而与之全体同流”[4]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蒋国保、周亚洲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83页。。不过,这种哲学本体的关注,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中国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认为美学来自西方,只有西方美学才有系统的理论和哲学观念,只有西方美学才称得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所以中国美学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追赶西方美学潮流,用西方的思维和观念来看待中国美学。美学研究也就不再关注中国的哲学和形而上思想传统,而转向对中国具体的艺术理论和艺术经验的研究。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曾意识到追赶西方美学潮流的理论缺陷,并作出努力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缺乏新的哲学思想基础和对中西方哲学的系统反思,都未能使这一状况得到真正改变。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界少有的关注中国传统哲学和形而上学思想价值的美学家,写作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形上学》笔记便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形而上思想如天人关系等的深入思考。《笔记》还比较了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认为希腊哲学出发于宗教与哲学的对立,于是走向“纯逻辑”“纯数理”“纯科学化”的道路,无法将逻辑理性与生命价值统一起来。而中国哲学则不是将哲学与宗教对立起来,故对古代宗教仪式、礼乐保持敬仰的心态,于是将生命价值与理性统一以来。[5]《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但宗白华并没有对西方哲学的普遍价值产生怀疑,在理论上也接受了西方哲学美学特别是生命哲学美学的观点。他的美学也可以说是以“生命”为本体的美学,这一美学思想的来源除了中国传统美学之外,也深受叔本华、柏格森、歌德等人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在进行中西哲学美学思想的比较时,也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哲学思想的根本缺陷,于是将重点放在中西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的差异比较上。他认为西方美学长期将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美的哲学思考构成了对美学的基本规定。而中国传统美学更重视的是艺术审美实践,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应该紧密结合中国艺术实践展开。朱光潜也是如此,他对西方传统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美学的理论缺陷是有所认识的,但是由于缺乏新的哲学理论的支撑,所以也无法创建一种新的美学理论来突破西方认识论美学的局限。晚年,他对自己的美学研究进行了反思,意识到自己翻译和评介西方美学的那些著作和文字的理论局限,所以将《诗论》看成是自己最有价值、最有原创性的著作。不过,《诗论》只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重要论著,并非一部哲学美学著作,所以也无法提出关于中国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了一场美学大讨论,并形成了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流派。但实践美学并没有突破西方传统的哲学美学观念,同时也缺乏对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精神的认识,无法将中国美学特别是具有哲学本体关注的中国美学研究推向前进。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人们已意识到实践美学的缺陷,批评、质疑之声不断,出现了后实践美学一类的理论思潮。由于这一理论思潮主要还是运用西方近现代哲学武器批判实践美学,缺乏新的哲学本体支撑,缺乏对中国传统美学价值的发掘与认识,这样的批评质疑之声也缺乏力量,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美学仿佛一下失去了发展的方向:美学研究中的浅薄、实用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在许多人的眼中,美学应该被还原为具体的艺术经验和艺术理论的研究,而真正属于美学的哲学的、形而上的思想品格常常被人们弃之若敝。
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出张世英关于美的哲学思考以及向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回归的特殊意义所在。张世英美学研究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有一种哲学的本体的关注与自觉。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国美学界长期以来习惯用西方传统哲学美学观念看待美学的缺陷,所以竭力从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中汲取思想营养,用新的哲学美学观念来引领中国的美学研究。在中国当代美学家中,张世英是最早认识到西方传统哲学主体原则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缺陷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缺陷以及它对中国美学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中国美学研究寻求一个新的方向。张世英的美学研究,可以说体现了美学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美学离不开哲学。如果考虑到中国美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来理解美学,考虑到中国当代美学对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和形而上思想传统的忽视,张世英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发掘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万有相通”“民胞物与”等哲学观念,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乃至中国美学如何走向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美学要走向世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本体意识与关注,要重视中国哲学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思维成果,而不是将美学简单地还原为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经验的研究。
二 、现象学哲学美学的接受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意义
张世英向中国传统美学的回归,对中国传统美学价值的再发现,与他对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与接受有着密切的关系。张世英所确立的哲学新方向,不仅本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也是对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接受现象学哲学美学理论成果并予以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张世英所关注的西方现象学哲学美学代表人物主要有三个: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黑格尔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其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其“绝对精神”的哲学将同一性、永恒的、抽象的本质或普遍性的东西作为追求的目的,其实质应该是背离现象学的。在张世英的哲学理论中,也常常将黑格尔作为传统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加以批判。那么,他为什么要将黑格尔作为现象学哲学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所提出的“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命题中看到了其与胡塞尔所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口号之间的关系,看到了一种批判西方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黑格尔所描述的“实体自身转化为主体”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认识对象的意义,都不仅包含个人的认识在内,而且包含了整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内容,它是个人和全民族、全人类思想文化的结晶。黑格尔所谓当实体完全表明自己即是主体之时,精神现象学也就结束了。这个断语的深层内涵就是:当实体、对象在意识中活动之初,它没有任何意义,什么也不是,但到了精神现象学结束之时,它已经经历了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经验意识活动、发展的各个阶段,亦即个人认识和整个民族以及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这样,实体、对象的意义也就最充分地展示、显露出来了……例如一朵花的意义,对于我们今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今人来说,它就不仅是红红绿绿而已,也不仅是植物而已,而是具有道德含义、审美含义、宗教含义等等。”[1]张世英:《现象学口号“面向事情本身”的源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胡塞尔与黑格尔的一点对照》,《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而这些正是胡塞尔现象学哲学所缺乏的。他认为,胡塞尔只能说是通过“悬置”“还原”等现象学方法,从理论上抽象地说明了事物的真实意义在于把独立自在之物转化为意识的为我之物,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则通过富有历史感的描述,解释了“实体自身如何转化为主体”的问题,所以它成为以现象学观点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一个光辉的范例。[2]张世英:《现象学口号“面向事情本身”的源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胡塞尔与黑格尔的一点对照》,《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对于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美学的意义,张世英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专注于‘事物本身’,它要求达到事物在直观中出场的本来面貌,不允许别的事物闯入事物本身”[1]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9页。,已具有了反对旧形而上学的主客关系模式的意义。因为胡塞尔所讲的对象是意向性对象,对象就是它在意向性地出场中所呈现的那个样子,而没有什么不在意向中出场的所谓独立的存在,已表现了胡塞尔与那种崇尚抽象或自在的旧形而上学的分歧。但是,在张世英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始终缺乏一个历史的维度,缺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关怀。而这一局限性,在海德格尔那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他说:“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的观念以及对于欧洲文明危机、文化危机的关怀,表明他已意识到他的现象学缺乏文化意蕴、缺乏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关怀的局限性,但他终其一生,一直没有把他的现象学同人生、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以此为特点的有系统的哲学。而把哲学与人生紧密结合起来的这一特点,乃是由他的学生海德格尔所倡导、由海氏以后的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所陆续发展起来的。”[2]张世英:《现象学口号“面向事情本身”的源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胡塞尔与黑格尔的一点对照》,《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所以他特别重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美学思想,他对现象学哲学美学的接受与运用,也主要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为对象。
张世英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着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感性中的东西到理解中的东西”的追根问底的方式,这种追问是“以主体—客体关系的公式为前提”,“以形而上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或普遍性、同一性为根底”[3]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页。,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存在论的现象学哲学美学,“已不满足于这种追根问底的方式,不满足于追求旧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追求抽象的、永恒的本质,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4]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页。。这种哲学的追问“并不主张停留于当前在场的东西之中”,“而是要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这未出场的东西也和当前在场的东西一样是现实的事物,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本质或概念”[5]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页。。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包含着与海德格尔相似的“超越在场”的思想成分,因为“胡塞尔在很多地方谈到事物的‘明暗层次’的统一,谈到事物总要涉及到它所暗含的大视野。这实际上意味着,感性直观中出场(‘明’)的事物都是出现于由其他许多未出场 (‘暗’)的事物所构成的视域之中”[6]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页。。但是由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缺乏历史的维度与人生的内涵,所以这样的思想成分只是暗含、并不彰显的。海德格尔则不然。因为他是将“人生在世”作为其理论前提,认为人乃是融身在世界之中,依寓于世界之中,世界乃由于人的在此而对人揭示自己、展示自己,其关于隐蔽与显现的理论、关于“在手”与“上手”的理论、关于“此在”与“世界”相融合的理论,已清楚地意识到事物所隐蔽于其中或者说植根于其中的未出场的东西,不是旧形而上学所讲的抽象的本质或独立的自在世界,而是人生在世、现实的东西,是“作为隐蔽于在场的当前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然而又是现实的事物”[1]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页。,它的意义自然是丰富无限、不可穷尽的。
正是受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美学思想的启发与引导,张世英对审美和艺术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张世英认为,海德格尔的一大贡献就是“强调‘隐蔽’和不在场的东西对于‘敞亮’和在场的东西的极端重要性,正是‘隐蔽’和不在场的东西使得一个存在物之‘去蔽’和出场成为可能”。[2]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诗意或艺术品的审美意义就在于它能从在场中把握不在场,“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和抓住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中体会和抓住未说到的东西”[3]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比如,马致远的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如果执著于表面所写的那些东西,则毫无诗意,但若把表面所写的那些可见、可说的东西放回到它们的“隐蔽”处,则可以体会到这首小令所敞开的是一幅满目凄凉的景象和诗人的惆怅之情,就会觉得诗意无穷。
也正是从这种重视“隐蔽”和“不在场”哲学的观点出发,张世英强调了“想象”对于审美活动的重要性。他说:“诗意或艺术品的审美意义所隐蔽于其中的不可穷尽性和不在场性,乃是我们的想象得以驰骋的空间和余地。”[4]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3页。那么,什么是张世英所理解的“想象”呢?他认为,对于“想象”,西方哲学史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外在对象看成是原本,而意识中想象的东西不过是原本的摹彷或影像。对这种“想象”的理解他是否定的,认为它是旧形而上学的观点。另一种是从康德开始并由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发扬光大的想象概念,即想象“不是对一物之原本的摹彷或影像,而是把不同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能力,具体地说,是把出场的东西和未出场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5]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页。。这一意义的“想象”,可以使不同的东西——在场的与不在场的,显现的与隐蔽的,过去的与今天的——互相沟通、互相融合,所以要把握万物相通的现实整体,就需要这种想象。想象不仅使人回到现实,也让隐蔽的东西得以敞亮而显示事物的意义。想象不仅适合于艺术,不仅适合于历史研究,而且也适合于日常的语言交谈。因为语言、谈话总是在现实的、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这种情景是隐蔽在直接言谈背后的东西,“只有想象才能使我们体会到直接言谈的背后的意义,才能使谈话的一方进入到和参与到另一方的世界中去,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通’”[1]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页。。对想象的追求并不排斥对思维的追求,但是“思维以把握事物的相同性(同一性、普遍性)为己任;想象以把握不同事物间即在场的显现的事物与不在场的隐蔽的事物间的相通性为目标”[2]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9页。,所以想象超越了思维。想象与思维相比,更能代表哲学发展的方向。
从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的哲学美学观念出发并结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与“情景合一”的理论,张世英还对“审美意识”的本质以及“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认为,审美意识不属于主客关系,它也不是认识,而是一种情感、情绪、情调或体验,是“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和“情境”。比如,对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如果简单地把这首诗理解为描写三峡水流之急速,那就不过是按照主客关系模式对客体(三峡水流)的一种认识,这就太缺乏诗意、太缺乏审美意识了。这首诗的意境主要在于诗人借水流之急速表现了自己含冤流放、遇赦归来,顺江而下的畅快心情。这里,水流之急速与心情之畅快,“一气流通”,无有间隔,完全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根本没有什么主体与客体之别,也没有什么主体对客体的思维和认识。[3]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张世英不否定审美活动中可以包含认识,包含“思”,但他把这种认识、这种“思”称之为“思致”。“‘思致’是思想—认识在人心中沉积日久已经转化(超越)为感情和直接性的东西”[4]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所以它在本质上属于情感和存在论的范畴而非认识论意义上的“思”。“审美意识的本质在于人与世界的合一,人与存在的契合或者说人与万物的一体性”[5]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它在本质上是超越有限、超越道德意识的,因为“道德意识并未真正达到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6]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但是,审美意识不可能排除道德意识。这是因为,“人与万物一体的关系是精神性的统一体之内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人对人的责任感和帮助他人谋幸福的道德意识的理论根据。所以在万物一体的审美意识中应包含人对人的责任感和为他人谋幸福的道德意识。善是美的必然结论,善包括在美之中”[7]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从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统一的立场出发,张世英反对那种只从愉悦性来理解审美意识,将审美意识看成是不负道德责任的观点,而是认为审美意识中既有愉悦感,也有道德责任感,是愉悦感与道德责任感的统一。
张世英对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哲学美学的接受,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他特别强调要破除旧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而回到天人合一的立场,特别重视海氏强调隐蔽对敞亮、不在场对在场的重要性的哲学观念,即“显隐说”的意义,认为它与西方传统的那种重视在场而忽视不在场的艺术哲学,也就是“典型说”有着本质区别。他认为,“典型说”是以概念哲学为理论基础,“典型就是作为普遍性的本质概念,艺术品或诗就在于从特殊的感性事物中见出普遍性、见出本质概念”,它要求能说出某事物是“什么”。[1]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146页。而“显隐说”则突破了概念化的思维,“显隐说”的审美意识要求回复到人与万物一体之本然,在于说明事物“怎样”从隐蔽处显现自身,“也就是要显示事物是怎样从隐蔽中构成显现于当前的这个样子”[2]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所以“显隐说”代表着西方新的艺术哲学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要强调隐蔽对敞亮、不在场对在场的极端重要性。美的定义于是由普遍概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转向为不出场的事物在出场的事物中的显现”。[3]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张世英的上述思考对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设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它强调用“天人合一”而非“主客二分”、强调从在场的东西超越到不在场的东西,用“显隐说”而不是“典型说”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对于破除中国当代美学界长期执著于“主客二分”、执著于“在场”,将美的问题抽象化、本质化的思维方式有一定意义。虽然在中国当代美学界中,也出现了像朱光潜那样重视审美经验,像宗白华那样关注艺术与审美实践的美学家,但从总体上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将美学的问题抽象化、本质化,是脱离丰富的、活生生的美的现象去讲美,究其本质就在于“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影响,把寻求在场、寻求普遍性与抽象本质的东西作为美学研究的根本,而忽视了不在场、丰富的美的现象对于美学研究的意义。张世英的哲学美学思考,对破除这种“主客二分”的本质化的思维方式,让美学研究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回到活生生的现实的审美活动中,其意义是显见的。
第二,它以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交融相通的眼光看待艺术审美,突出了想象和情感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这对于破除长期以来在中国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认识论美学模式有一定意义。对美学的认识论模式,中国美学界也曾有过质疑与反思。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对将美的活动看成是一种认识活动的观点提出过质疑,认为这是唯心美学留下的一个须经重新审定的概念。[4]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0页。李泽厚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提出过艺术不是一种认识的观点。但是由于其哲学基本观念的缺陷,他们都未能从认识论的美学模式中走出来。比如,朱光潜将美定义为“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1]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2页。,李泽厚将美定义为“主观意识、情感和客观对象的统一”[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第82页。,就是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美学模式来看待美的问题。而张世英的哲学美学思考则不然,他不再用主客二分的模式看待问题,也不是把认识事物的真假、把握美的普遍本质作为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而是强调人在认识世界万物之先就已融身在世界之中。强调想象与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在他看来,想象包含了思维又突破了思维的极限,所以它具有超越思维、超越逻辑的意义,能代替西方传统哲学所讲的认识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审美意识则是人与世界融合的产物,是“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情境”,所以它根本不管什么外在于人的对象,根本不是认识,而是一种体验。这些看法,是从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中把握美,显然突破了认识论的美学观点和思维模式,更接近美的本体。
第三,张世英对现象学哲学美学观念的接受,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美学和艺术精神的阐发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接受有助于人们重新发现与认识中国古代美学的价值。比如,他以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为基础提出了“显隐说”,并与西方传统艺术哲学的“典型说”相比较,这种比较就让人们对中国古代美学中的“隐秀说”有了新的认识。张世英认为,中国古典诗在从显现中写出隐蔽方面,在运用无穷的想象力方面,可以与海德格尔所代表的西方艺术哲学新方向——“显隐说”互相辉映。刘勰《隐秀篇》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其实就是讲隐蔽与显现的关系。它的妙处就在于从“目前”的(在场的)东西中想象到“词外”的(不在场的)东西,令人感到“语少意足,有无穷意味”。但这词外之情、言外之意不是抽象的本质概念,它仍然是现实的,只不过这现实的东西隐蔽在词外、言外而未出场而已。以“显隐说”的观点去看待中国古代的“隐秀”说,看待中国古代“意在言外”的审美传统,并不是像有的理论家认为的那样,是从个别事物中看出普遍性,而是要冲破同类的界限,想象——玩味到根本不同类的事物。想象到的东西仍然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现实,而不是经过抽象化、普遍化的东西。所以它对艺术创造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古代美学为什么要提出“隐秀说”,重视词外之情、言外之意的原因所在[3]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6—159页。,也是中国传统美学重视“意象之美”的原因所在。张世英的这种解读,显然能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和探讨中国古代美学诗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及其价值。
三、“人生境界”和“美的神圣性”说的理论价值
张世英之所以重视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重视中国古代的“隐秀”(意象)说和“意在言外”的审美传统,重视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关于隐蔽与显现、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的论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认为在这些审美传统和观念表述中,包含着一种超越意识,有一种超越现实的高远的精神追求,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诗意美”和“境界美”。张世英的美学,也可以说是一种追求“诗意”和高扬人的“精神境界”的美学,“人生境界”问题的讨论与“美的神圣性”观点的提出,就是这种美学意识的鲜明体现。
人生境界的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在很多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追求有高品位的人生境界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在中国现代哲学家,特别是现代新儒学那里,人生境界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冯友兰的“境界”理论对于理解“人生境界”问题有着重要价值。冯友兰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动物不了解它所生活的世界,而人对于宇宙人生有“觉解”。人不但有觉解,而且能了解其觉解,所以人所追求的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人对于宇宙人生觉解的程度不同,宇宙人生对于他的意义也就不同。根据“觉解”程度的不同,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品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自然境界最低,天地境界最高。处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对人生有最高的觉解,不仅意识到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意识到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他的一切行为的目的是“知天”“事天”,在人与宇宙、人与天地的统一中实现其人生价值。[1]以上论述见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新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天地境界”在冯友兰那里被视为一种“哲学境界”,不过,许多人认为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只有作为审美境界才有可能。张世英的“人生境界”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冯友兰“境界”论也有某种相似。张世英与冯友兰一样,强调最高的人生境界是人与宇宙、人与天地的统一,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不了解它所生活的世界,而人则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觉解。比如,他用王阳明的“人心一点灵明”观点来说明“境界”,认为“正是这点‘灵明’构成了一个人的‘境界’,动物不能超越,故无境界之可言。‘境界’就是一个人的‘灵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有意义的世界。动物没有自己的世界”[2]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就是如此。他将“境界”分为“欲求”“求实”“道德”“审美”四个层次,与冯友兰的“境界”层次划分也有某种相似。不过,张世英对“人生境界”的理解,远超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的范畴,他将西方现代哲学的“超越在场” “生活世界”“时间场域”等概念范畴纳入其中,认为“境界”不仅仅是个人主观的“觉解”,也是天地万物的无穷关联,在这关联中包括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因素以及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具体遭遇,其内涵比起冯友兰的“境界”论丰富得多。
在张世英看来,“境界”可以看成是个体根据一定历史文化条件和处境的自由选择。他说:“境界乃是个人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一定的社会体制下、以至在某些个人的具体遭遇下所长期沉积、铸造起来的一种生活心态和生活方式,也可以说,境界是无穷的客观关联的内在化。这种内在化的东西又指引着一个人的各种社会行为的选择,包括其爱好的风格。一个人的行为选择是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但又是受他的生活心态和生活模式即境界所指引的。”[1]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4页。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人的精神境界对于民族文化的构成非常重要,“境界”也可以指个人的精神境界,“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族文化不过是空洞的名词”。[2]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同时他又认为,“个人的精神境界又是在他所属的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有某一种文化,就有某一种境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西方人的境界,包括他们的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中国的儒释道三大文化支柱,也各有其相应的精神境界,其中也包括他们各自的道德境界、审美境界等。凡此种种,都说明,要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是弘扬民族文化”[3]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1—282页。。
张世英对“人生境界”的这一理解,蕴含着双重意味。一方面,他看到了“境界”对于个体人生的重要性。他之所以提倡“境界”,追求诗意的美,就是看到了“境界”和诗意的生活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有重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他将“境界”看成是“浓缩和结合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而成的一种思维导向,也可以叫做‘思路’或‘路子’”[4]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有没有一种精神的导引和境界的追求是很不一样的。他说:“人生就是人的生活、人的实践,人生所首先面对的就是人所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但人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怎样生活、怎样实践,就要看他的那点‘灵明’怎样来照亮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要看他有什么样的境界。一个只有低级境界的人必然过着低级趣味的生活,一个有着诗意境界的人则过着诗意的生活。”[5]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另一方面,由于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在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所以弘扬民族文化,探索人生各种文化活动、各种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探索着一条有益的途径,又成为张世英“境界”说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方面,他特别重视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并试图将它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哲学结合起来,并参考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之处(如反对超感性和理性之上的观点,主张哲学与诗意人生相结合的观点),提倡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观。他认为,“此种意义的‘万物一体,乃真善美统一的总根源。此种‘万物一体’观乃是在当今国际思潮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观的一种新的诠释和发展”[6]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他之所以提倡万物一体的境界观,目的就是“希望人皆能以此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境界为最高追求,走上成人之道”[1]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与“人生境界”理论相关联,张世英还提出了“美的神圣性”的观点。他说:“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的境界,还缺乏基督教的那种令人敬畏的宗教感情。我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从西方的基督教那里吸取一点宗教情怀,对传统的‘万物一体’作出新的诠释,把它当做我们民族的‘上帝’而生死以之地加以崇拜,这个‘上帝’不在超验的彼岸,而就在此岸,就在我们的心中。这样,我们所讲的‘万物一体’的境界之美,就不仅具有超功利性和愉悦性,而且具有神圣性。”“具有神圣性的‘万物一体’的境界,是人生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是最高价值之所在,是美的根源。”[2]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4—245页。在张世英看来,“美的神圣性”,或者说“万物一体”的境界之美,不可能脱离人的自然感情,但它超越了自然感情,是对自然感情的升华。“美的神圣性”与人世痛苦密切相关,但又不同于痛苦本身,它是经受了痛苦而又从痛苦中超拔出来的一种深层的美的愉悦之感。“美的神圣性”是与道德紧密结合的,但是它又不等同于道德,它是超道德的。他说:“我所谓超越道德之美就是指这种高远境界之美,而非指单纯的感性事物之美、娱人耳目之美。一个仅仅拘泥于从道德上的‘应该’观念出发而行为的人,虽然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不一定有高远的境界和胸襟。而一个真正有高远境界的人,必然也是一个讲道德的人,美的境界包含道德而又超越之。”[3]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5页。
张世英之所以提倡“美的神圣性”,是因为他看到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人们普遍追求好看好听的声色之美,而忽视了声色之美背后的心灵之美的支撑。或者说,缺乏一种超越现实的高远的精神境界。他提出“美的神圣性”命题,虽然追溯到西方基督教审美传统,强调基督教审美传统中关于美与心灵、美与对上帝的信仰、“艺术之美体现神性”等观念对于形成“美的神圣性”思想的重要性,但主要目的却是为了回归到现实,解决现实生活中诗意、神圣性缺乏的问题。他说:“美不限于感官形象,而是超越了感官形象,是上帝的光辉。这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观点的核心。批判其人格神的意义之后,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我以为我们的美学应当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之上:美,除了应讲究感性形象和形式之外,还必须具备更深层的内蕴,这内蕴的根本在于显示人生的最高意义和价值。”[4]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2—233页。在这里,“美的神圣性”已从基督教的上帝和宗教神坛走向了人间,走向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正因为此,他特别欣赏海德格尔关于“澄明之境”是“神圣性”的思想:“‘澄明将每一事物都保持在宁静和完整之中,澄明是神圣的。对诗人来说,最高者与神圣是同一个东西,即澄明。’‘神圣的’一词,是相对于日常现实生活的功用性而言的。日常现实生活,特别是现代技术化,把任何事物包括人都加以‘对象化’,都变成使用的对象,人的世界从而变得千篇一律,现代人生活的‘白天’变成了扼杀人的自由的‘黑夜’。这样的世界是‘不神圣的’。而艺术和诗,却使人‘突然地’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神圣的领域’。此种‘神圣之光’照耀出万物之本然,一切都自由自在。西方美学思想中的美的神圣性和自由,从此便由传统的抽象性转向具体性了。我认为西方思想文化史上,对美感的神圣性和自由的认识,至此可算达到了顶峰。”[1]张世英:《美感的神圣性》,《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这种欣赏的目的也就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解决现实生活中美的神圣性和诗意的匮乏的问题。他说:“我们讲美的神圣性,决不是要脱离现实性,脱离现实的生活。例如饮茶,就可以有单纯的现实境界,又可以同时有诗意的审美境界。一个没有审美境界的人,饮茶就是解渴而已。一个有诗意的人,一方面还能品出茶的诗意来。既有现实性,又有神圣性;既有了低级欲求的满足,又有了审美的享受。”[2]张世英:《美感的神圣性》,《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美的神圣性”变成了与现实人生亲密相处的东西,落实到人的生活最平常的领域中。这种神圣性与西方传统文化中那种以宗教意识和信仰为核心的神圣性,显然是有着重要的区别的。
张世英关于“人生境界”和“美的神圣性”的阐述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意义何在呢?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提升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理论和精神层次。在中国美学界,对美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观点,那就是将美看成是一种认识,一种知识形态的东西,或者将美学意义上的美与常识意义上的美,与一般人用日常眼光进行审美判断的活动和能力等同起来,而忽视了人们之所以从事审美活动,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丰富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上世纪50年代,朱光潜曾提出“美学意义的美”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美学意义的美”主要是指经过人们认识和体会过的艺术美,基本上还是属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2页。而张世英对“美”的认识,则完全超越了常识和认识的范畴。他说:“我们的美学不能只讲感性事物之漂亮、美丽,而应以提高人的审美境界为最高目标。”[4]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4页。在张世英看来,审美不再是一种认识,也不是一种日常意义上的美与漂亮,而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是人的精神和心灵境界的提升。但是这种提升又不是绝缘于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他在“人生境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美的神圣性”命题,意义也在于此。张世英所提倡的“美的神圣性”,与西方传统文化以宗教意识和信仰为核心的神圣性不一样,它不是指向上帝,而是指向人世。他看到了现实人生包含着无限的生机和美,有一种神圣性和永恒性的价值存在,所以只有赋予人世以“美的神圣性”,才能真正突出超越日常生活的声色之美和感性事物之美,指向高远的人生境界,使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对于张世英“美的神圣性”命题对于中国美学的意义,我们可以用叶朗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以作为本文的结束,它也可以看成是张世英这样执著于高远的境界之美、执著于诗意人生的学者的精神写照:
“一个有着高远的精神追求的人,必然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绝对的价值存在。他们追求人生的这种神圣的价值,并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分享这种神圣性。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在当代中国寻求这种具有精神性、神圣性的美,需要有一大批具有文化责任感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积累,做出能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的创造。”[1]叶朗、顾春芳:《人生终极意义的神圣体验》,《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毛宣国: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