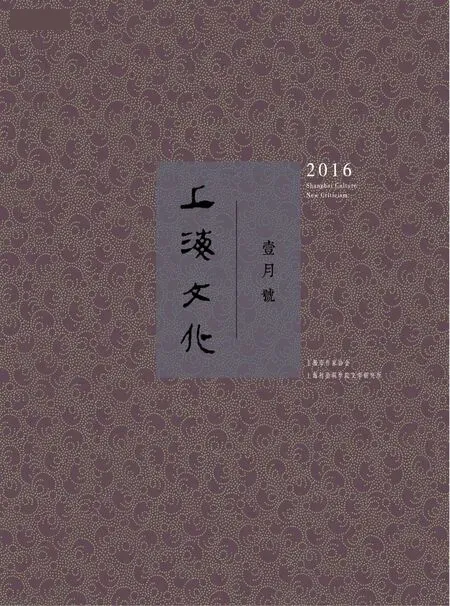黎明的时候《圣经》二题
张闳
黎明的时候《圣经》二题
张闳
书写与救赎,或月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往橄榄山去。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她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
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他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
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
耶稣挺起身来,问她:“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约8:1-11)
黎明的时候
这是一个特殊的早晨。这是一个不祥的早晨。这是一个要出事的早晨。然而,这是一个满有恩典的早晨。
起初,它看上去像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耶稣像往常那样,坐在圣殿门口向门徒和众人讲道。但危险的雾霾已经悄然聚拢过来。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经学家①和法利赛人——捉住了一位犯罪的妇人。他们把她带到了耶稣面前,要挑战耶稣的道,并且寻找陷害他的藉口。
耶稣与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自耶稣传道之日起,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不停地对他加以诘难和试探。以往耶稣与犹太人发生冲突,一般都是因为耶稣所传讲的真理跟犹太人所理解的真理有所不同,或是因为耶稣本人涉嫌违背律法,如在安息日医病赶鬼,等等。每一次耶稣都毫不犹豫地通过自己勇敢的行为和智慧的言辞予以反击,而且每一次,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都跌落进自己凭狡诈所设的陷阱当中。
但这一回情况有所不同。耶稣所面对的是一桩无可辩驳的罪,是摩西律法上明确无误地记载着的罪,而且,他必须要当即做出论断,无可回避,没有商量的余地。四周的人都拿起了石头。耶稣所要面对的情况是:他要是一确认这位妇人的罪,她就会被石头打死。或者,他要是否认这位妇人的行为有罪,那他本人也将会一道被石头打死。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危机时刻。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向三一神发起了挑战,考验他的神性,也考验他的人性。
这事发生在圣殿门口。
却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写字
然而,在此危机时刻,耶稣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选择了“书写”,以应对这场危机。这是一个奇异的选择,几乎是不可理喻的。
此刻,我们看到,耶稣“弯下身去”,俯身面向这片土地,这片沾满了罪恶的土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是选择了一个谦卑的姿态。这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
无论如何,耶稣选择了一个书写姿态来应对危机,如果这是一次写作行为的话,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写作状态。首先,他没有写作工具。既没有笔,也没有纸。要完成一次写作行为的基本物质条件都不具备。其次,周边环境也不适合写作。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而且是一群居心叵测的人,心怀恶意,急迫地等待他对问题的回应。这种环境,更像是一个战场,一个需要通过唇枪舌剑来搏击的论辩战场。可是,耶稣却选择了书写。这位本应在天上书写真理的经卷和世人罪行判决书的神,他在“地上”的书写却是“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并且,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
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经典的书写姿态。写作者总是低头俯身,单独面对一张白纸所显明出来的世界的“虚空性”。这在另一重意义上,也标榜了写作的真理性的特质——谦卑性。
然而,耶稣选择书写的姿态来应对危机,还有另一重意义。耶稣的行动,揭示了写作的另一功能或使命——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活动,将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和方式,处理写作者个人与世界(环境)的关系。我们看到,耶稣弯下腰,低下头,垂下眼睛,定睛在一个世人所看不见的事物上。他不注目环境和他人。这一姿态,写作者首先将自己转化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写作是写作者个人面对一个尚未形成的“文本”空间而要采取的行动。这个孤单的行动。写作者置身于孤单的处境当中,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与众人、环境和世界暂时隔离开来。他只定睛在他所要看到的。尽管书写在文字文本完成之后,最终必须交付读者阅读,或写作者会假想有某个潜在的读者的存在,但书写行为本身却不直接与他人交流。它是写作者的一次孤单的行动。而事实上,即便有众多的旁观者在现场,却并没有人试图进入耶稣写作的文本空间里而成为他的读者。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写了什么。
在地上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无非是天上的写作的摹本而已
耶稣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充满了敌意和仇恨的环境,一个充满了罪的环境,到处都是争竞、论断和指控。耶稣则要通过书写,营造一个属灵的环境,将他眼前围绕着他的那个空间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所在。因为,他需要一个与父神独处的环境,单独面对父神,默默与父神沟通。在法利赛人提出律法问题为难耶稣的情况下,耶稣必须重新回到父神的律法当中。他面对那一片空白的土地,如同摩西面对面前尚未书写的石板。他要回到律法被书写之初的状态。
可是,耶稣所书写的看上去却是一个乌有的文本,一部不存在的书,至少可以说,是一部未经阅读的书,而且,它的脆弱的存在,使之显得仿佛一片“空无”。它随时可能被世上行走的脚步所践踏并轻而易举地擦除。他是在书写“虚空”吗?哦,“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传1:2)!正因为如此,一般解经家认为,耶稣并未完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没有写下任何有意义的文字,只是在消磨时间,把围观的人耗走。②但是,看客从来不会被无聊所耗走,因为他们就是无聊本身。无意义的举动并不能抵抗和消除无意义,相反,它将与其所要克服的对象一起沉沦。③如此这般的“虚无”的书写,恰恰是要昭示出更高意义上的书写。任何人为的写作,“都是捕风”,如果它不能够指向终极书写的话。
事实上,在地上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无非是天上的写作的摹本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临摹”属性,才给地上的写作带来终极意义。或者说,地上的写作才找到了意义的源头。
关于罪与罚的写作,已经在地上临摹过了。那就是摩西从神那里临摹而来的律法——“十诫”。摩西在西奈山上,同神一起在石板上书写“十诫”,这大概是《旧约》中所明确记载的唯一的书写行为。而且,首先是神在书写。《福音书》中的书写行为的记载,则是耶稣的这一次。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他不会是为了打发时间随随便便写着玩的。当耶稣在写字的时候,可以想见周围的环境,那里早已是群情激愤。众人手里都拿着石头,随时准备砸向那个妇人,甚至砸向耶稣本人。而且“他们不住地问”,咄咄逼人。而耶稣则用书写来回应这种逼问。
经上特别写到,耶稣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当初,神在石板上写下“十诫”的时候,经书上也明明白白地记录了他的写作方式。“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与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版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版”(出31:18)。这里强调了神是用“指头”写作。可见,用“指头”书写,是圣父和圣子共有的写作习惯。他们没有使用人造的书写器具,乃是使用自己的肢体,与大地接触,在地上刻画,就好像神最初抟土造人一样。器具的中介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阻隔神要表达和要改变的。
耶稣的写作保持了与父神的完全一致。他在地上所做的,完全是父神在天上所做的,决非为了应付环境而采取的消极措施。因为,“子靠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只能作他看见父所作的;因为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约5:19)。耶稣面对与律法有关的质疑时,选择了与父神一致的书写。耶稣要写的,当然是要写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因为这正是基督第一次降临世上的使命,他所做的就是“在地如在天”。
除了这一次“写字”之外,没有证据表明耶稣曾经有过其他的写作经历。事实上不仅耶稣,人类文明史之初的那些伟大的原典性的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都鲜有写作活动。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能言善辩,却也不写作,正如尼采所说——“苏格拉底,从不执笔。”释迦牟尼也偏爱发表演讲。他们的言论,被他们的门徒和追随者笔录下来,传之于世。耶稣之前的犹太先知们也是如此。可见,在通常情况下,在真理的表达方面,口说言辞具有优先性,而写作则是一个次级行为。亚里士多德指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④德里达也看出了古典时代语言观的这一特点——“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关系。”⑤但他认为这是古典时代所谓“言语中心主义”的偏至所在。此外,言说行为在言说者与听众之间构成一个直接的交流场域,与之相关的不仅是语词和句段的意义,还有声音、语调、语速、表情、节奏,乃至其间的停顿和静默,都成为其交流的影响性的因素,甚至它可能还会被打断,有人插话、提问、质疑,乃至争辩。这一切,在耶稣的传道过程中都经历过。而书写行为是排他性的,它并不接受旁观,而且,它本身是一次单独而又完整的行为,不接受打断和割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显明了律法本身的完整性。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强调了律法的书写性,他在另一处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太5:18)。律法不只是一言一语,更重要的,它是“一点一画”,是被书写出来的条文。
而且他在这一事件中,两次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书写成为一种强调和重申。事实上,“十诫”的书写也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摩西带着神写下诫命的石板从西奈山下来,发现以色列民在他上山的期间,在山下拜偶像,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盛怒之下,将石板摔碎在地上。之后,他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山上,跟神重新立约。“摩西在那里与耶和华在一起共四十昼夜,不吃饭,也不喝水。他把这约的话写在两块版上,这就是十诫”(出34:28)。
律法一再地通过书写而被强调,表明它并不随着外部环境和人群的心理状态而改变。书写通过强调符号之间的“差异”来界定意义的边界,使律法成之为律法。它用文字符号被“一点一画”记下来,铭刻在记忆的心版上,如卢梭所说的“上帝将字写在人的心中”。它不接受提问,也不接受补充和纠正,而且也不会随着言说者的声音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律法是不可更改的绝对命令。耶稣之后,尤其是在使徒保罗那里,圣经才真正由“口述时代”进入“书写时代”。保罗通过书信的方式来释经传道。
现在,在这个特殊的早晨,我们看到,基督的“指头”触及地面,这地就要被翻转,被改变。环境就要被洁净,被祝福。
人类文明史之初的那些伟大的原典性的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都鲜有写作活动
谁是没有罪的
终于,耶稣“挺起身来”,回到世界环境中,重新面对世人,并开口说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他没有回避“罪”,也没有回避“律法”,而是要告诉世人,律法并非外在于人的律令条文,并非人用来论断他人的戒条,乃是使罪彰显,而且不只是他人的罪,而是每一个人的罪。
律法并非外在于人的律令条文,并非人用来论断他人的戒条,乃是使罪彰显
法利赛人怀疑耶稣的道,怀疑耶稣的恩典和救赎,他们要用律法来捆绑和限制、考验耶稣。他们不知道,此刻,这律法的制定者就在他们眼前。现在,法利赛人却要以律法的捍卫者的身份,用神的律法来定神子的罪。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荒谬处境,也是存在的荒谬性所在。更为可悲的是法利赛人,他们天天在盼望中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而弥赛亚就在眼前,他们却不认识。这是法利赛人生命中的最深刻的悲剧。
对于耶稣来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恶意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们通常对种种罪恨之入骨,喜欢给人定罪,但这一回他们其实真正感兴趣的并非“淫乱之罪”。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决意要来成全律法的,而是蓄意要来挑衅耶稣。许多解经家都注意到,法利赛人只抓来了行淫的妇人。倘若有行淫,必有一对男女两个罪人。现在,带到耶稣面前的,却只有一个女人。那个男人却不知所终。而这一群男人将这位犯罪的女人带来,事实上已经预先为那个男人开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在为自己可能的罪开脱了。可是,耶和华是公义的神,法利赛人却并未真正实现律法的公义。
然而,这尚且不是重点所在。法利赛人恪守律法,他们甘愿活在律法的辖制中。可是,律法所要求的是“完美”。因此,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犹太人,在恪守律法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完美。法利赛人的恪守可谓艰苦卓绝,却永远不可能成就律法。正如保罗所说的:“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神吗”(罗2:21-23)?
耶稣是来成就律法的。耶稣的行为显明了律法本身的完整性。神的律法要求的是整全的,而不能限于一二条相互割裂的条文。守律法,就必须是整全的律法,尤其是其中的“总纲”,诫命中最大的——“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10:27)。法利赛人自己并不能恪守律法的整全性,甚至偏离了律法的总纲,而是选择性地援引律法的部分条文,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并将之作为指控耶稣的依据,这乃是对律法的最大的毁坏。
但是,成为义人不是靠着人自身,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和克己的努力,乃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这就是保罗所谓“因信称义”。成义若是靠着人的恪守律法的行为,那就等于是忽略了神的作为,取消了神的恩典。在行为不可能完满的情况下,“称义”就必然会陷于伪善。所以,耶稣曾在另一处斥责他们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太23:13)!正因为如此,耶稣从不呼召这些自称为义的善人,乃是呼召了那些边缘人群,乃至通常所认为的“罪人”,成为传他的福音的使徒。耶稣明确地表示:“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悔改”(路5:32)。因着悔改和信,才有得救的盼望。
都离开了
耶稣说完那些话,又重新回到沉默中,回到书写的孤单当中。
在此特定场合,回到写作状态还有一重含义——提醒人们的羞耻心。当耶稣开口说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的时候,神的大能就震动环境,也震动了法利赛人坚硬的心,让他们感到羞耻。
耶稣的写作跟羞耻心有关,这一点是容易被忽略的。耶稣尚且只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而且不曾婚娶。法利赛人却擒来一位行淫的妇人推到耶稣的面前。衣衫不整的妇人面前,耶稣选择了低下头来写字,避免了彼此的尴尬。另一方面,也是尊重了女性的羞耻心。尽管这妇人犯了可耻的罪,但耶稣仍愿意尊重她的羞耻心。这就彰显了耶稣基督诚挚怜悯的心肠。
但是,公正地说,法利赛人尚且是知廉耻的一群。他们在面对自身罪性的逼问下,自知羞惭,悄然离开。事实上,在这个布满罪的世上,生活的时间越长,罪就越多。如果没有神的赦免的话,任何人都难以脱离罪的沾染。所以,年长的就先离开。法利赛人尚能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和罪性。
羞耻心是世俗道德的根源。即便法利赛人,也没有完全丧失羞耻心。就算不从信仰的层面谈,从一般意义上的世俗道德方面,法利赛人也察觉了自身的亏欠。当他们被耶稣指出其可能的罪性的时候,一个个羞愧而退。但是,羞耻心所指向的乃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律令,而不是得救的恩典。如果要审判的话,谁有权力来完成这一审判呢?既然人人都有罪,又有谁可以成为公义的审判官呢?审判的权柄只在公义的神、全然无罪的神的羔羊那里。耶稣问道:“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当然没有。因为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罗3:10)。
律法成就之际,都是每一个人单独面对救主的那一刻
不定你的罪
我们看到,当耶稣的书写终止之际,律法就成就了。
律法成就之际,都是每一个人单独面对救主的那一刻。那个曾经喧嚣一时的世界,现在只留下一个全然无罪的救主和一个罪已被全然彰显的罪人。救恩就发生在这一时刻。法利赛人终究只是谨守克己的道德家,他们令人惋惜地离开了与主同在、向主悔改的现场,错过了从主而来的救恩。
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太5:17)。耶稣在这一事件上彰显了他所称的“完成”。完成,既是终结,又是实现。因着耶稣的降临,凭着他赦罪的权柄,他带来了救赎。信他的人从此不再活在“罪”中,也不再活着“律法”中,乃是活在救恩中。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世人灵魂,为世人赎罪的。法利赛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依然活在律法中。所以,他们要试探耶稣,要求他审判世人的罪,认为如果他是基督,就应该这样做。
耶稣成就律法,彰显救恩,在世上的罪人都如同这位犯罪的妇人一样,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担当,便站在主的恩典里,而不再在罪里了。基督的恩典是白白给与的。但并非放任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从此脱离罪的辖制,悔改,而归向主。“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没有隐藏我的罪孽;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诗32:5)。
自由的言说及其枷锁,或出埃及记第四章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以前不是,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因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
摩西说:“主啊,请你差派你愿意差派的人。”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他现在出来要迎接你。他看见了你,心里就快乐。你要对他说话,把你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口里;我必与你的口同在,也与他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向人民说话,他要作你的口,你要作他的神。这手杖你要拿在手里,用来行神迹。”
(出4:10-17)
为什么是我?
带领二百多万人民出走埃及,穿越旷野,去到神应许给他们的祖先之地。这是一群奴隶,一群四百多年奴隶的人民。这样的带领绝非凡人所能担当,他应该是一位空前绝后的英雄。神拣选了摩西。
摩西的困惑是——为什么是我?
为奴四百年,以色列人无所事事。他们除了为法老做工,就是繁衍后代。浑浑噩噩的四百年,一个几百人的家族增长了一万倍,成为几百万人的民族。可是,他们忘记了神,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忘记了神对他们的祖先的应许之地。他们好像也被神所遗忘,四百年里未显任何神迹。直到有一天,一个人来唤醒这一切。
这两百多万人中,只有一人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不仅是自由人,而是王子,是主人。他就是摩西。只有他一人曾经经验过自由,尝过自由的滋味。确实,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越过红海而获救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有在水中被拯救的经验,婴儿时期就有了。
奴隶虽然渴望自由,但并不懂得自由,不知道人在自由状态下应该怎么做。人若没有准备好成为自由人,当自由来临的时候,他们并不能承受。因为他们习惯了被奴役的状态,习惯了用奴隶的思维来理解一切。奴隶意识已经成为他们的“自我意识”的核心。他们只能想象奴役状态的生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
在奴隶意识的捆绑中,人没有能力理解神,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神,他们甚至只能羡慕、模仿和膜拜他们的主人及主人的神。他们从埃及人那里所攫取而来的金银,却用来铸造埃及的神。连亚伦也无法挣脱这种捆绑。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崇拜活着的人和属世的物有什么意义?!那些就是他们被奴役的根源。他们曾经在埃及地亲手用泥塑和石雕过这样的神像,但这些神非但不带领他们摆脱奴隶地位,反而将他们更加牢固地捆绑在苦难当中。那些不是他们的神,而是他们的主子的神。甚至,那些根本就不是神,而是主子们为了奴役他们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偶像。
因此,耶和华神并没有允许以色列人立即进入应许之地,而是让他们在旷野中流浪了四十年。四十年,那些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人,也就是“奴隶的一代”都离开人世了,除了约书亚和迦勒,剩下来进入应许之地的是旷野之子,是“自由的一代”。神不允许将奴隶意识带进应许之地。连带领人们出埃及的领袖摩西也都未能进入。
而摩西是唯一挣脱了“奴隶意识”的人。“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33:11)。神将他当作朋友看待,因为只有他,才真正明白神赋予他们自由意志的心意。
可是,摩西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言说就是生命
埃及神是僵死的偶像,而以色列人的神却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会说话。他向摩西显现,对摩西说话。
言说,是生命的重要表征。这也是又真又活的真神有别于诸假神、偶像的根本性的标志。另一方面,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就是一个用语言来创造的神。世界之初生,就是因着神的话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而当摩西与以色列的神相遇时,神就开口对他说话。摩西明白,他所遇见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有别于他在埃及地所见过的诸神。也正因为如此,摩西告诫以色列民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8:3)。后来,耶稣重申了这一点(太4:4)。
可是,摩西却拒绝了神的呼召。他找了各种理由推辞,强调了各种难处,但神都一一为他排除。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缺陷——言语障碍。摩西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缺陷,他因着自我认知,以自己所能理解的准则衡量自己的能力,自忖难以完成神的使命。他有自知之明。这在人,是何等宝贵的品德!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以前不是,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因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然而,在神看来,所谓“自知之明”,乃是弃绝了与神的连结,是对神的不信任。耶和华是以勒的神,是全然预备的神。神的拣选和呼召,他为受召者必有预备。这一次,他为摩西预备了亚伦。
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当他听到要用以撒献祭的命令时,他虽然不理解,也难以接受,但他依然凭着信,顺从神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以勒的神,必有完全的预备。耶稣在呼召彼得和马太等门徒的时候,也并未向他们解释“为何需要听命”的道理,他们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跟随耶稣。与之相反的是,有人说:主啊,让我回家去埋葬了父亲,再来跟随你吧。这人就因不信任主的预备,选择自己决定办事,而失去了与神连结的机会。
摩西因为自己的口拙,而自认为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然而,神掌管他的生命,也掌管他的头脑和舌头。
除了约书亚和迦勒,剩下来进入应许之地的是旷野之子,是“自由的一代”。神不允许将奴隶意识带进应许之地
口吃病案
摩西自知有拙于言辞,用他自己的表达,是“拙口笨舌”。这其实就是“口吃”的委婉表达。弗洛伊德就将其表达为“口吃”(参阅佛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然而,摩西的言语障碍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摩西的口吃,显然不能归咎于先天性的家族遗传。他出身利未支派。这个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素养最好的,正因为如此,日后他们成为专职的祭司家族。而且,摩西的哥哥亚伦就是一个口齿伶俐的人,他的姐姐米利暗也不逊色,她竟是一位女先知。可见,他的原生家庭有着非同一般的智慧遗传。
那么,摩西的口吃只能是后天性的。可是,以他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照理应该比他的兄长们更加能言善辩。他从婴儿时期起,就在埃及王宫长大,并且。在名义上是法老的外孙。作为王孙的摩西,应该受到了最良好的教育。
摩西的双重身份的冲突令人关注。作为自由人,他却又是一个特殊的自由人。在他身上,有着主人和奴隶的双重身份。从血统上说,他是奴隶之子;从社会身份上说,他是王子。作为王子,相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熟悉埃及王室文化、礼仪、语言,及其信仰体系。
另一方面,他却又由以色列妇人(实际上是其生母)哺育成人。相信其作为乳母的生母,恐怕也没少向他灌输其原生家庭的文化及信仰。在母爱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乳母影响的重要性不可轻视,有时甚至大过生母。这一点,在亚历山大·普希金身上有过充分的体现。何况摩西的乳母实际上正是其生母。
我们不知道摩西的童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在埃及宫廷的生存环境中,他的身份的特殊性,无疑会给他构成极大的压力。一旦他模糊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时,恐惧、悲观、消极、自卑等心理征候,随时都可能成为他的灵里的压伤。临床医学证据表明,儿童在被歧视的环境中,精神压力过大,过度自卑,容易因为精神紧张,而导致口吃。或者同时学习两种以上的语言时,由于无法协调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在发音、语义,及逻辑等方面的差异,亦容易导致口吃。这些情况,在摩西身上都同时存在。而且还不仅如此,摩西所习得的两种语言还不仅是语音学上的冲突,也不仅仅是语义学上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包含的属灵的价值层面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在摩西的大脑中,自童年时代起,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语言中枢,也可以说,他有两个属灵的中枢,而且是两个相互对抗的中枢。其作为乳母的生母所教导的语言与信仰,以及无意识深处的种族本能,在反抗其现在的外在身份。等他成年之后,被压抑下去的族群意识终于占据了上风——他挺身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身份。然而,其在宫廷教育中所习得的价值观和语言,依然会占据压倒性的地位。如此一来,他甚至也很难获得本族群成员的认同。带着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他必须完全自我放逐,彻底脱离那两种难以融入的社会:主人的社会和奴隶的时候。他独自来到旷野,成为牧羊人。在那里,他独处,努力成为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一个独自面对自我的个体,学习认识自我,并学习牧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遇见神,与神面对面,并被神所拣选。
但他首先要学会倾听神的话。
摩西的先祖们也与神耶和华有过面对面的经历,但一般他们都是倾听神的话,并照着去做。挪亚是这样,亚伯兰是这样,以撒和雅各也是这样。或者,充其量单独与神进行一些就事论事的交谈。而现在,摩西不仅要听,而且要做出回应,更重要的是,他还得将神的话转告众以色列人。他必须将神的话翻译成人的语言,并且,还得让那些完全缺乏启蒙教养的奴隶们听懂。
如是一来,摩西就始终面临着双重的语言冲突。一种是埃及语与希伯来语的冲突。一种是神的语言与人的语言的冲突。前者是主人的语言与奴隶的语言的冲突。后者是灵里的语言与肉身的语言的冲突。摩西显然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双语教导者。
这一系列的冲突,既是摩西语言障碍的后果,也是其语言障碍的根源。
话语革命
当摩西面对耶和华的时候,人类的语言必要摈弃,而神的语言又尚未习得。他的口吃必将更加严重。耶和华为摩西预备了亚伦成为他的帮手。可是,亚伦虽然能言善辩,言辞流畅,但他并不能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和宣谕诫命,他只不过是一位“传话人”而已。在地上,亚伦不过是好用的话语工具,摩西才是言说的主体。
太初有道,而人类要习得这太初的道(语言),是何等的艰难。摩西的这种结结巴巴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在灵性发育之初的状态。仿佛神的语言的“草稿”,打在以色列族群的心版上,打在他们尚未开蒙的主体意识的“白板”上。这就是“道”的童年状态,也可以说是理性、智慧和灵性的童年状态。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摩西开启了“书写时代”。他要将神的话记录下来,刻在石板上,让人类牢记,而且不可更改。童年的人类,若不以行为规范来教导他们,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天性中的恶和根本上的罪性,会让他们偏离神的道。即便有亚伦的代言,依然是不可靠的。因为亚伦就是不可靠的,他口齿伶俐,却不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在摩西离开众人去到西奈山上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亚伦却与以色列民众一起,重新回到偶像崇拜的旧恶当中。以致让摩西在愤怒中摔碎了刚刚写好十诫的石板。神的诫命不得不再一次被书写。摩西重返西奈山,重新回到神那里,记录神的律法。二次书写,进一步强化了书写的重要性。
以书写替代言说,是摩西在以色列的一次话语革命。书写在逻辑上的严密性和存在形态上的稳固性,让神的话语具有了永恒不易的性质,带给以色列人恒久不变的精神内核。这个神所拣选的族群,开始从幼稚状态走向了学龄时期,直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临人世,他们终于得以长大成人。
以书写替代言说,是摩西在以色列的一次话语革命
❶“经学家”,圣经和合本译作“文士”。本文据环球圣经公会圣经新译本1992年版译名。本文所引经文亦据新译本。
❷如巴克莱(William Barclay)等著《每日研经丛书》,贾玉铭著《圣经要义》,黄迦勒著《圣经注解》,摩根(Campbell Morgan)著《摩根解经丛书》等著名解经著作,都倾向于这一解释。
❸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不乏以“虚空”抵抗“虚空”、以“无意义”克服“无意义”的例子。典型如鲁迅《野草》中的《复仇》一篇,即以无意义的姿态实现对无聊看客的复仇。进而,他在《复仇(其二)》中还套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将耶稣改造为他所预设的以自我虚无化来反抗世界虚无化的英雄。但这一切乃是基于“仇恨”的生存论的结果。关于这个论题,容另文专论。
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第55页,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❺[法]德里达:《论文字学》,第14页,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