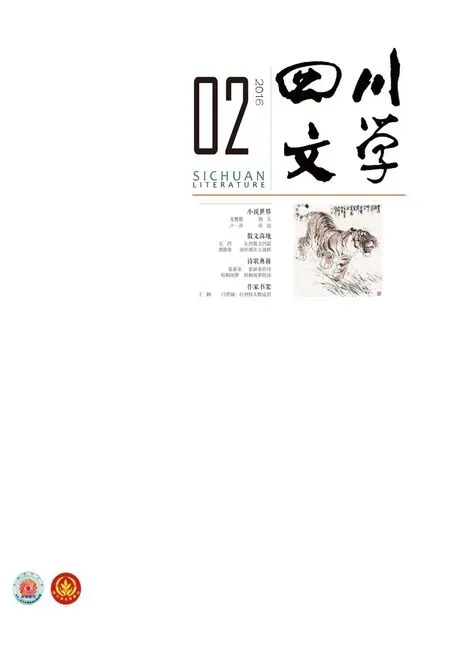文字先贤
吕虎平
文字先贤
吕虎平
一
家乡有座古台,是仓颉造字台。儿时和玩伴围着它转,误以为是造纸台。这种误会来自于临村的造纸作坊。后来,知道了仓颉与汉文字的关系,自然对它生出几许敬重。
邻村叫北张村,是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地方。北张村有一座庙,供奉着“纸圣蔡伦祖师”的牌位和泥身金面塑像。有一首民谣:“仓颉字,雷公碗,沣出纸,水漂帘。”说的是村子周边与造字、造碗、造纸、造帘有关的几处古迹。北张村的手工造纸,十分辛苦。有一年暑假去同学家玩,后半夜,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以为刮风,再听,又不像,扒着窗户看,只见男男女女站在山墙边,借着月亮的微光,将抄出的纸,一张一张贴在墙上。此时,月亮的微光,已超出文字本身的意义,折射于我的视线,成为一幅黑白默片。同学说,这是老活计,无论酷暑炎夏,寒冬腊月从不间断。当地有句顺口溜“有女不嫁北张村,半夜起来糊墙跟”,就是明证。雷公碗是雷公村一座古窑,小时候去,还帮着师傅和烧泥,后来,古窑坍塌,废弃,被夷为平地。紧邻北张村,是西周的灵沼、灵台、灵囿的“三灵遗址,是周王祭灵之地。遗址至今尚存,建有庙宇数座常年香火不断。
我喜欢在家乡的田间闲走,与其说是漫步于乡野,不如说是游弋于自己的过往。家在长安,但并非历史意义上颇负盛名的古都长安,而是唐时的京兆邑,后置县长安,成为都城长安的后花园。从地缘大势看,长安起笔高峻,泼墨而来,挥毫而去。南有秦岭屏障高耸,东有浐灞两河汤汤北流,西有涝河浇灌沃野田畴。整个长安,地处八百里秦川的核心,身姿绰约,如丰腴的贵夫人。一条名为沣水的河流在核心的核心,拐了好大一个弯,弯出一河碧波、两岸诗意,弯成一幅巨大的乾坤八卦图。灵台为乾卦坐于西岸,造字台为坤相坐于东岸。两台隔岸相望,使悠悠沣水,如时光的隧道,穿越千年。
世界上,大凡奇迹的诞生,都离不开独特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人文精神的烛照。这一地界,还有许多史实和传说,与乾坤八卦密切关联。在这里,你随时能触摸到历史的气息,听到先人的心跳。造字台西邻,是西汉周亚夫屯兵的细柳大营,留下周将军严明军纪的千古佳话。长安四中建在大营旧址上,许多路基还是当年的青砖条石。在此读书时,我每天从上面踩过,不知道哪一脚与汉文帝踩在同一块砖石上。北邻,是周穆王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游牧的穆王》,对此曾有介绍。此文曾得《当代》杂志原主编何启治先生的高度认可,认为开了游记散文新风气。我生活的周边,只要平地凸起,往往是一座帝王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陕西兴起盗墓狂潮,周穆王墓冢被撕开一个小口。一个小口,撕开了埋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野心。
灵台南临,是草堂寺,前秦王符坚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入住于此翻译佛经。高僧圆寂后,他的舌骨焚烧不化,人称“三寸不烂之舍”。又因其舌骨舍利埋葬之处生出一朵白莲,又有了“口吐莲花”之说。这两句成语原本是称赞鸠氏译经的精准达雅,但历经千年,却演绎为对一个人能言善辩的评价。草堂寺往南是清凉山,是老子驾鹿西行楼观台,撰写《道德经》的发祥地。这里山高坡陡,林木高挺,我曾去清凉山避暑,酷热夏天,穿行茂林修竹间,但闻泉水叮咚,鸟雀唧唧,禅意顿生。
二
仓颉到达三会寺的时候,已是十月。从都邑长安到三会寺,也就十余里路程,仓颉却走了两天两夜。当地人喜欢酿酒,一种粮食发酵后的米酒。他们以兽头米酒当祭物,在三会寺道场聚集,欢呼,以庄严、盛大的仪式,祭祀天神,祈祷丰收。季节已进入深秋,但燠热尚未散尽,阳光依然朗照。仓颉走一阵,看一阵,走走停停,把一个多时辰的路,走了两天两夜。他一边嘴里咕哝着,一边用树枝在地上描描画画。有时挠头,有时抓耳,有时捶胸,有时击掌欢呼。
仓颉在黄帝手下做官。黄帝分派他管理性口数目和屯里粮食的多少。仓颉这人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无论是牲口圈,还是粮仓,都能管得井井有条,不出差错。随着牲口、食物的增加,光凭脑袋记忆已经很不现实。于是,他便想出结绳记事的办法,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牲口和食物。用绳子打结,代表数目的增加,解掉绳结,代表数目的减少。然而,都邑的财力物力不断壮大,结绳记事难以满足现实需要,仓颉又想出一招,用贝壳记事。这办法的确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黄帝见仓颉能干,封他为史官,将祭祀、狩猎、部落人口增减以及天灾人祸,天干地支,统统归他管。毕竟事情繁杂,名物繁多,贝壳记事又不靠谱了。一次南巡途中,仓颉以“羊马蹄印”为源引发造字灵感。他看尽星宿分布、山川脉络、鸟兽痕迹、草木器具,依据其形描摹绘写,造了种种不同记事符号,并记录下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仓颉把这种符号叫做“字”。
初来乍到,万事无着,仓颉未免心有些烦乱。人们知道,他是黄帝的史官。一个史官跑到民间,疯疯癫癫,痴痴狂狂,当地人对他既提防,也疑虑。连日来,他画出“鸟”,教给路人甲:“这是鸟。”路人甲白他一眼,笑他愚痴。他画出“云”,教给路人乙:“这是云。”路人乙睬都不睬,笑他呆傻。仓颉急啊,他爬上道场祭祀用的土桩台,双臂下垂,双腿岔开,大声喊“人”。他又将双臂伸展,大声喊“大”,即使他呼干了唇舌,喊哑了嗓子,还是没人理睬。但仓颉不厌其烦,苦口婆心教给每一个人。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这个人虽然有些痴狂,但举止间真诚,对他也就不再心存芥蒂。有一天,有人终于学他发出了“人”字的读音。他撩起衣襟,擦擦汗,开心地笑了。
很快,仓颉和当地人做了朋友,很多人愿意和他说心话,跟他学字,而他看起来也乐于倾听,乐于教授。在三会寺,仓颉有了很好的名声,到了后来,只要说到仓颉,当地人会用敬重而又亲切的口气,仿佛说的是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有一天,一老者问他是不是将“重”和“出”造反了。千里之远应为“重”,两山重叠应为“出”。仓颉恍然大悟,是自己把这两个字教反了。他已传授给更多的人,现在纠正为时已晚。此后,仓颉造字、教字更加细心,丝毫不敢含糊。
两年过去了,仓颉依然漫步于乡野田间。他有时低头沉思,有时匆匆急行,有时,爬上土桩台,仰望苍穹。夕阳西下,残阳染红了西天。仓颉颔首微笑,对他而言,那天象,必是吉兆。
夜已深,忙碌了一天的仓颉,依然没有睡意。他无暇顾及衣服上沾的草屑和尘灰是否与他的史官身份相符。他坐在篝火旁,一遍一遍将多年来所造的字,抄录在竹简上。明日,黄帝即将颁昭,汉文字,将以文告形式昭示天下。文字一出,人类从此由蛮荒岁月转向文明生活。
三会寺祭祀的土桩台,从此被称作仓颉造字台。
三
历史因文字而得以存续。
据《长安县志》载:历史上的三会道场,曾经亭台楼榭遍布四周,集市贸易相当繁荣,汉唐时期达到鼎盛。随着历史的变迁,这里渐渐萧条了,只能从周围出土的瓦当残片想像当年的盛况。“释子谈经处,轩臣刻字留。”这两句诗是唐景龙年间,中宗皇帝驾幸造字台上官婉儿的一首应制之诗。诗歌大气恢弘,很难看出其出自一个女子之手。在遣词造句上,每一句都一字定音,读来让人心中坦荡舒畅。从 “释子谈经处”便能看出,婉儿对三会寺的历史了如指掌。三会寺原本是高僧谈论经书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洗涤,如今已是无人问津,寂寞萧条。而“轩臣刻字留”的轩臣,指的就是仓颉。
突然想到了造字台,想到了它的高度,这个高度也可以理解为断崖。人世间的断崖无处不在,文字的断崖更是岌岌可危。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清朝的文字狱,是对文化极大的戕害。先秦以前的历史与文明,由于焚书坑儒而使整个华夏文明基本失忆。秦始皇兵马俑因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座世界八大奇迹的故事,只能由后人猜想。清朝,文字狱异常酷烈,明史案、清风案、黄培诗案、南山集、徐转案、吕留良案,一桩桩血案,沾满血醒。著名的“清风”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徐骏的父亲徐乾学在康熙朝任刑部尚书,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是大清开国鸿儒,他因反清复明败露而逃亡,下狱,在文人学士的保举下被赦免。顾炎武感到反清无望,只好潜心学文,成为一代鸿儒,著作等身。他的甥孙徐骏却没那么幸运。徐乾学在朝为官过于强势,遭人嫉恨。有人想报复他,苦于找不到破绽,只好对他儿子下手,揭发徐骏诗文集内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和“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被下大牢。又有人查出他曾在奏章中,将“陛下”写成“狴下”,雍正大怒,下诏斩立决。另一种说法在《清稗类钞》有记载:雍正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一书生见状顺口吟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中国人喜欢咬文嚼字,有关文字狱的记载,历史上比比皆是。金朝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受害者是翰林学士张钧,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萧肄这个伪君子,反而获得皇帝赐赏通天犀带。元朝英宗年间,身为高僧的宋恭帝赵㬎因怀念宋朝,写下“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诗句,被认为是“讽动江南人心”,赐死河西。明太祖朱元璋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又当过和尚,对“贼、寇、光、秃、僧”这些字眼非常敏感。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赞美他,他却牵强附会,认为光是指光头,生就是僧,则与贼近音下令把徐一夔杀了。
文字像一枚双面币,一面是文明,另一面是邪恶。当文明的大河向前奔涌的时候,邪恶的潜流,总是隐藏其间。神是忌邪的神。历史拒斥虚假邪恶而又不得不遵循某种神谕,在文字的世界刀削斧凿。我仿佛看到文字的屠刀,寒光森森,亮出白刃。
四
我曾做过考证,关于仓颉的记录,最早见于战国时的荀卿,之后见《吕氏春秋》和《韩非子》。荀子说:“故作书者众,仓颉而独传者。”往后,《淮南子》、《论衡以及《史记》,已将仓颉从“作书”而引申为造字的先驱传其四目双瞳,这是上古时代 “四目神”最早的原型。
四目神的形象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仓颉,一说是鲁班。很小的时候,听说仓颉是四目双瞳,实在难以理解,有心想看一看。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卖年画的老妪,她的年画很有趣,有舞大刀的关云长、门神秦琼敬德和捉鬼的钟馗。我问她,有没有仓颉。老妪的回答让我很失望:拿回家,有啥用呀?四只眼,怪怕人的。我说,四只眼是文化人。老妪一时没弄明白,挥了挥手说,去去去,不跟你这娃儿说了。谁知,第二天,老妪带来一张仓颉画像,四目并行,看一眼头有些晕眩,心下生出凉气、森气。我想,那可能是神气、仙气。大凡圣人都该有这样的气韵吧。
《吕氏春秋》载:仓颉原本姓侯刚,名颉,因他造字有功,黄帝赐予“倉”姓,即人下一君,君上一人。玉皇大帝也因仓颉造字赐予人间谷子雨,以慰圣功,这也有了谷雨的来历。
说到仓颉,鸟迹书碑是绕不开的。仓颉生于陕西渭南白水县鸟羽山,造字石楼沟。关于鸟迹书碑有一段传说。据说仓颉造字二卷,从中选其最满意的28字刻于石楼沟山石上。秦朝末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辅助公子扶苏到上郡筑长城,驻军设防,抵御匈奴。蒙恬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儒将,好读书写字,当他和扶苏领兵由咸阳北上时,选择了白水这一条路,为的是顺道拜仰先贤庙。当他听当地人介绍石楼沟尚有仓颉造的鸟迹书时,十分高兴,前往已是荒草遍地、乱石满沟的石楼沟,观看依稀尚存的鸟迹书遗迹。他深感仓颉造字的神奇,更为字迹的破损而惋惜,将字迹临摹下来,刻成石碑,放置于仓颉庙内。蒙恬的鸟迹书碑,在仓颉庙存留了1000多年,唐代,被朝廷拓裱成轴,存于宫廷或内府。北宋时期,编入《淳氏阁帖》。到了元朝,蒙古铁骑南侵,兵祸连年,庙宇被毁,鸟迹书碑也失去了踪影。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梁善长主政白水,整修仓颉庙,不惜重金购得《淳化阁帖》,选精石,请巧匠,邀名流,潜心仿制,终使仓颉鸟迹书碑重见天日。
历史需要靠文字记忆,如果没有文字,历史就变成了传说。仓颉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价值,是他让历史记录有了可以凭据的载体。在中国人物传播史上,他是个伟大的奇迹。从古代史籍的只言片语中,仓颉被挖掘出来,并借助强大的民间叙事话语,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有人说,文字的创造来自于民间,仓颉,作为黄帝的史官,他只是将民间的创造收集整理,充其量,也就是文字的整理者。无论哪种情况,仓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无可比拟。
五
重登造字台,是在秋天。秋天登临,是一种幸福,本草丰盈,色彩斑斓,浓重的秋色,仿佛要将人溺死一般。坐在台基上,仰望天空飞过的鸟雀从视野消失,俯瞰袅袅炊烟,扑面而来,这是一种绝对的惊艳。我突然生出一种特殊的感觉,在造字台和我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先天的亲缘关系,尤其在这深秋,一股潜流在血管里鼓荡。
迷恋造字台,是因为它接近蓝天的高度,还有星夜的深邃。那天,我从一条乡间小道绕过去。这条道很少有人走,这是我儿时常走的小道。偶尔有几个农人,扛着锄头,哼着秦腔,渐渐消失在玉米地里。我所置身的空间,纯净、明澈、悠远,飞翔的鸟雀在蓝天白云间,清楚地写出无拘的自由。深邃的天穹笼罩在头顶,低垂的天幕,伸向莽莽苍苍的秦岭犬牙似的山峰之外。我觉得自己似乎穿越到远古时代的某个端点,与仓颉对谈。
不知是秋风过高,还是什么原因,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迷糊中,一老翁缓缓走来,清癯的脸,笑吟吟地,他要送我什么,我没有伸手。我不习惯接受别人的东西,何况陌生人。问他是谁,他不答,只是用手指了指脑门。我觉着没有什么呀,忽然,他的脑门露出一只眼,我一惊,老翁背手走了。我发现他的后脑还有一只眼。我倒吸一口凉气: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仓圣人?我急忙去追,被一块石头磕绊了一下,摔下深渊。我惊醒了,身子轻飘飘的,没有力气。人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想不单单是这些,也许,这是仓圣人的神气不散。
去年春天回西安,朋友邀约拜谒先贤。到了造字台,却无法入内,这里已用作警犬队训练场。一道铁栅门,孤傲、冷漠。几十条警犬,瞠目而视,长毛竖起,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和朋友绕道附近的小食街,专门吃一种鲜美无比的杂肝汤。这是西汉时就已流行的民间小吃。吃着吃着就产生联想:这个曾经让人类迈出蛮荒的古台,历经数千年,反而失却了往昔的繁华。过去与现在,唯一能连接的,也许只剩下这碗杂肝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