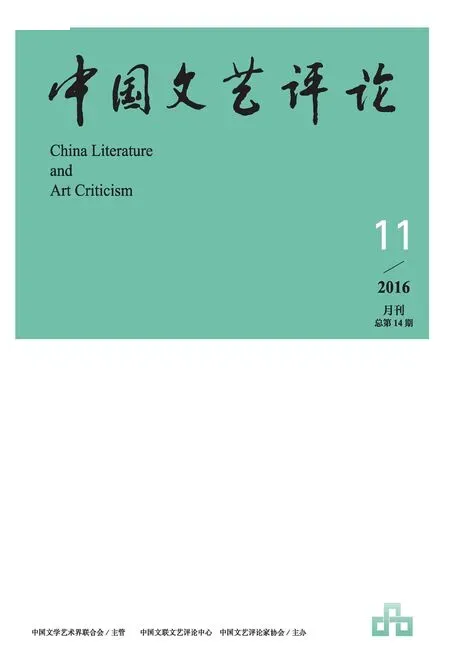莫让经典陷沉默—汤显祖作品传播得失谈
赵建新
莫让经典陷沉默—汤显祖作品传播得失谈
赵建新
2016年,适逢东西方两位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离世400周年,中英两国都以此为契机,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演出。中国的纪念演出在7月16日至19日达到了高潮。在这四天中,上海昆剧团首次集中上演汤显祖全本“临川四梦”,一时成为京城盛事,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以往国内外著名话剧团上演经典话剧时才能见到的演出盛况,在上昆精心打造的“临川四梦”中得以再现,这让人不得不感叹传统戏曲经典在一流剧团的演绎下所焕发出的勃然生机。
但是,如果我们的视野超越此次纪念演出,而把其放到全球纪念莎翁茧翁(汤显祖晚年曾以此自号)的系列演出活动中,把纪念茧翁的演出与纪念莎翁的演出相比较,再进而言之,如果我们把茧翁与莎翁的作品放置于全球化戏剧经典的演出传播进程中,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无论艺术形式的丰富性,还是作品被再度阐释和改编的多样性,莎士比亚的戏剧远比汤显祖的戏剧走得更远,影响更大。在热闹的纪念活动之余,戏剧工作者理应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竭力寻找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方为传统戏曲艺术走出国门、融入和参与世界文化的应有之义。
从字面上看,织物纵线称为“经”,册在架上名为“典”,经典便由此引申为“典范”“标准”“规则”之意等。古今中外那些被认定为“经典”的作品,正是大师们扎根于其所处的时代氛围和文化传统中,以其极具个性的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塑造形象,从而参与、影响人类的精神和文明的构建进程。这些经典一旦形成,便呈现出一种“有始无终”的状态,它们创作的原点是大师们的个体情感,但最终的审美指向却超越时空,抵达全人类的共同情感,所以人们在认定一部作品是否为“经典”时,除了从“内涵的丰富”“实质的创造”这两方面来衡量,也要看它们是否具有“时空的超越”和“阐释的无限”这两种特质。所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不但是指莎士比亚经典作品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让人们在理论研究中“说不尽”,同样也指因其提供了巨大的超越性和无限性的审美空间,而让后世在舞台上“演不尽”。这里的“演不尽”,
不仅指人们在几百年间不断搬演莎士比亚的原作,还指后世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遭际和现实境遇,不断改编和移植莎士比亚经典剧作中原型故事和人物。这种改编和移植,一方面让经典中的原型故事和人物与改编者的当下境遇相结合,从而使其具有现实意义和当下指向,赋予经典鲜活的时代生命;另一方面,这些依据经典原型再造和重生的人物,当面对类似的人生境遇和现实问题时,依旧对原型人物所叩问的人性之隐秘和人生之忧思发出超越时空的回应,从而更加彰显经典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
单就2016年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的活动而言,上述此类“演不尽的莎士比亚”举不胜举。例如,由英国文化协会等共同发起的“永恒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中,不但有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携莎剧经典《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威尼斯商人》登陆中国各大城市,还有英国国家剧院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让全球观众在电影院中欣赏莎士比亚戏剧。2016年4月23日,“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英剧《神探夏洛克》扮演者)主演的《哈姆雷特》以及阿德里安·莱斯特主演的《奥赛罗》等一系列莎士比亚戏剧在北京和上海相继举办放映活动,中国观众得以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欣赏莎翁经典戏剧。
在纪念莎翁的演出中,不但其故乡英国举办的纪念活动如此丰富,即便中国也不甘落后,在国家大剧院推出的“东西对话·戏剧传奇”的演出板块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年上演的12台剧目40场演出中,除了传统的戏剧,还有多明戈、丹尼尔·欧伦、乌戈·德·安纳等演员打造的全新版歌剧《麦克白》,由摩纳哥蒙特卡洛芭蕾舞团、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分别带来的芭蕾舞剧《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甚至还有中国原创的爱情音乐剧《莎翁的情书》等。可以说,无论东方西方、中国英国,根据莎翁戏剧经典改编的姊妹艺术也是举不胜举。
而当代人根据莎剧经典改编和移植的作品也花样百出,如今年由曼彻斯特皇家交易所推出的剧场版《哈姆雷特》,由女演员玛辛·佩克主演。此版《哈姆雷特》从女性视角诠释哈姆雷特内心世界,打破了人们欣赏《哈姆雷特》的惯常思维,意在挑战人们的性别偏见,推动性别平等;格里伊剧团和孟加拉国达卡剧团新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通过残疾人长期培训计划实施完成;跨文化表演团体特拉诺剧团将在贝尔法斯特的泰坦尼克号码头上演《贝尔法斯特暴风雨》,演员来自世界各地,演出阵容超过200人。此外,由英国新锐艺术家领衔制作的莎剧经典情节短片也在今年向全球推广,旨在启发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探索莎翁作品内涵并激励他们制作短片参加网上竞赛,展现自己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
如果我们跳出2016年相关纪念活动的圈子,放眼四百多年来的莎剧演出,就会更加感叹莎剧经典的传播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改编移植的丰富性,其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无可匹敌。就中国传统戏曲而言,从1914年四川雅安川剧团王国仁把《哈姆雷特》改编为川剧《杀兄夺嫂》开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驯悍记》《无事生非》《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仲夏夜之梦》《温莎的风流娘们儿》等12部莎剧经典先后改编成了川
剧、粤剧、越剧、京剧、昆剧、黄梅戏、豫剧、云南花灯戏、汉剧、吉剧、潮剧等11个戏曲剧种,这还不算众多的话剧版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莎士比亚经典剧作作为人类永恒的精神宝藏,说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非言过其实。当然,几百年来,世界各国对莎剧经典的改编和移植不乏“六经注我”式的有意无意的误读、曲解和解构,但所有这些,倒更能证明莎剧经典跨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而这,正是经典之为经典的魅力所在。
单就剧目和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言,与纪念莎翁的演出相比,我们纪念茧翁的演出不能不说令人汗颜。从年初截至到目前,大规模的集中演出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上昆四场演出,还有北方昆曲剧院、苏州昆剧院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三个昆剧院团演出的《牡丹亭》和《南柯梦记》等,它们同是“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的演出剧目。除此之外,还有两次规模不大的演出,一是2016 年4月22日,江西抚州在英国斯特拉福德上演的抚州采茶折子戏《牡丹亭·游园惊梦》,一是2016年7月,江西省文化厅主办的“汤显祖四百年梦回滕王阁”之赣剧专场演出,这次专场演出上演了《牡丹亭·游园惊梦》《紫钗记·怨撒金钱》《邯郸记·生寤》三出赣剧折子戏。
除了戏曲,还有两次话剧纪念演出最近也见诸媒体,一是英国利兹大学和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的师生合作,从《仲夏夜之梦》和《南柯梦记》取材,改编成一出名为《仲夏夜梦南柯》的戏,于7月27日在英国利兹大学上演,此后又于9月16日在莎士比亚国际戏剧节上演出;二是英国壁虎剧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根据“临川四梦”和《仲夏夜之梦》改编的话剧《梦境》,将于10月在上海上演。
以上便是笔者了解到的国内纪念汤显祖的大致演出情况。与纪念莎翁的演出相比,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区别:
第一,从国家和地域看,纪念莎翁的活动从英国到中国,几乎覆盖全球;而我们纪念茧翁的活动,主要是国家的文化主管部门和茧翁的故乡江西,此外还有历史上汤显祖曾任知县的浙江遂昌。诸如上昆、苏昆等专业院团的演出,也多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所主导和组织。实际上,此类演出需要政府组织,也更需要民间的自觉自为。
第二,从演出的艺术形式看,纪念莎翁的演出涵盖了戏剧、影视、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而我们的纪念主要是戏曲,戏曲中主要是昆剧,赣剧、采茶戏和话剧之类只是点缀。所以,在红红火火的纪念展演中,一度会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这是在纪念汤显祖还是在纪念昆剧?通过纪念活动,我们是在提升汤显祖作为世界级大戏剧家的文化地位,还是彰显昆曲艺术保护传承的最新成就?当然,在整个纪念活动中,“临川四梦”无法和昆曲割裂,伟大的“临川四梦”在历史上几乎就是通过昆曲艺术来传承和接续的。但时至今日,在世界文化交流日趋密切的当下,如果还把某个经典的大师之作固定限制在某一类艺术形式中,其不利于沟通和传播的弊端,必将日益显现。毕竟,在当下时代,“临川四梦”并不一定要用昆剧这种戏曲形式表现不可。
1980年代末,中央戏剧学院就曾把“临川四梦”中的《南柯记》改编成话剧。据时任中戏
戏文系主任的谭霈生先生回忆,此剧改编比较成功,排练效果也很好,只是由于特殊原因,这出戏并没有正式出现在舞台上,成为一时之憾。
第三,从规模范围看,纪念莎翁的活动遍及政治、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基本上是依靠社会文化机构在运行;而我们纪念茧翁的活动大多集中在戏曲界,多是政府组织的剧团演出,社会响应度并不高。
毫无疑问,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等世界级戏剧大师相提并论,丝毫不会让我们感到些许惭愧。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英两国的纪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传播的“逆差”,又有目共睹。莎翁经典近几十年来,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其艺术传播方式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当今世界所有新兴艺术媒介几乎都赋予了莎翁经典以多样的艺术形态,仅凭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来展现莎剧经典,早已显得拘泥和落伍。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和探索,莎翁经典也的的确确走进了中国,而且走得畅通无阻、扎实稳健;而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我们要让大戏剧家汤显祖与世界接轨,让全球接受,如果还局限于以一种艺术形态为主演绎大师之作,就会显得不合时宜,更不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文化新形象。
其实,多年来我们已有很多文化工作者深耕于此领域,尝试把传统文化艺术以各样的形态传播到世界各地。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例,先后就有中央芭蕾舞团创作的同名芭蕾舞剧,著名华人音乐家谭盾、昆曲演员张军和舞蹈家黄豆豆联手创作的同名实景园林昆曲,苏昆和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合作的同名昆曲等,其中尤以芭蕾舞版《牡丹亭》最成功,影响也最大。芭蕾舞版《牡丹亭》以现代美学视角关照杜丽娘这一形象,在人物塑造上把其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在同一个舞台空间上同时出现三个不同的杜丽娘,从不同情感侧面揭示杜丽娘的复杂形象,使之更加丰富立体。芭蕾舞剧《牡丹亭》既保留了昆曲的传统音乐元素,又与现代音乐和舞蹈相结合,在芭蕾舞足尖的千回百转中实现了传统昆曲艺术淋漓尽致的现代表达,已成为中芭的新经典演遍世界各地。它既实现了对芭蕾舞本土化的深层次探索,又在多样态传播中国戏曲经典方面做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其成功的经验理应得到推广。
经典的传播往往伴随着自身不断被改编移植的再创造过程,传统戏曲经典在这方面不乏成功先例。众所周知,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历史上除了被中国人改编为京剧、秦腔、川剧等十几种戏曲形式,18世纪还曾经被法国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欧洲上演。到了当代,国内改编移植的版本有话剧、越剧、黄梅戏,也有汉剧《失子记》、小剧场戏曲《程妻》等,在国外有2012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和韩国明洞版的同名话剧等,所有这些,无不是改编者对经典做出了既具个体化也极具时代意义的解读,赋予了经典以新的生命和当代诉求。正是由于几百年来被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不断地创造性阐释,《赵氏孤儿》所呈现出的忠诚与背叛、复仇与放弃、牺牲与私欲等价值观被各个时代的艺术家们所淘洗、提炼、扬弃,其撼动人心的事关生命和大义的永恒价值将在世界范围内被传诵和铭记,由此,经典方得以深入人心,实现真正
的“走出去”。
既然关汉卿的《赵氏孤儿》能做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为什么不能?从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主旨来看,“临川四梦”是汤显祖对人的欲望的戏剧化表达:《紫钗记》和《牡丹亭》事关“情欲”,《南柯记》和《邯郸记》皆为“权欲”。汤显祖对人性中的情欲和权欲寻幽抉微,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其笔下以戏剧化的形式展现殆尽。例如杜丽娘这个人物,历来我们都会强调她的反封建反礼教的色彩,但她死后与柳梦梅的幽媾也是对人性的顺从,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显示这个古代女子的复杂性,只有到了还魂之后,重获生命的杜丽娘竟对柳梦梅说出了“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话,要后者还需按部就班地遵从规矩,“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游走在阴阳两世的杜丽娘此时才显示出巨大的心理情感空间,人与鬼之间,“想出来的事”和“做出来的事”之间,还隔着一道鸿沟,杜丽娘此时面对的伦理选择将更富有戏剧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心者若由此切入,难保不会编排出一出令人震动的新戏。再如《邯郸记》中的卢生,一生永不满足,追求不息,似乎欲望无始无终,在阅读文本时会让人或多或少产生这种感觉:作者好像急于把人物不断推到人生不同的巅峰状态,为此不惜牺牲某些情节的合理性,而在舞台演出中,由于情节进展过快使整出戏的节奏更显局促。按说《邯郸记》是“四梦”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此时的汤显祖创作起来必定是更加得心应手,但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完美之处?深入了解这部作品,我们也许会体察茧翁的用意,他这样写的目的就是要为笔下人物提供一个欲望的试金石,他不停地为人物设置凿石开河、御边大捷、死窜充边、得志纵欲等戏剧情境,让卢生出将入相,体验生死荣辱,最后猛然醒来,不过黄粱一梦。类似的这种欲望主题,在中外戏剧史上比比皆是,每当看到《邯郸记》时,总能让笔者联想到易卜生的名剧《培尔·金特》。培尔·金特代表着人世间的种种意愿、憧憬和欲望,穷尽一生追名逐利,最后得到了整个世界,却丢了自我。两人相比,何其相似!《培尔·金特》至今被世界各国剧团演出,格里格创作的同名音乐组曲更为世人所熟知,其中的《索尔维格之歌》更是世界名曲。相比之下,创作时间早于《培尔·金特》近300年的《邯郸记》却一直是沉默中的经典,少有其他艺术形式对其加以改编和再造。
其实,即便是在国门之内,我们对经典的态度也往往是敬而远之,始终让它们局限在一种艺术形式中,据江西南昌老艺人回忆,当年《牡丹亭》在南昌剧场以赣剧演出,座无虚席,名旦潘凤霞的表演“秀美娇甜”,对杜丽娘的演绎出神入化,而活跃于各地的乱弹、徽戏等戏曲和鼓角、西调等曲艺也都改编、演出过“临川四梦”。今天的舞台上却多是昆曲的杜丽娘。当然,唱昆曲的杜丽娘也自有其韵味和风采,但在艺术媒介和传播方式日趋丰富和多元的今天,在绚丽多姿的国际文化潮流中未免显得有些孤单和落寞。
赵建新: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艺术》编审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