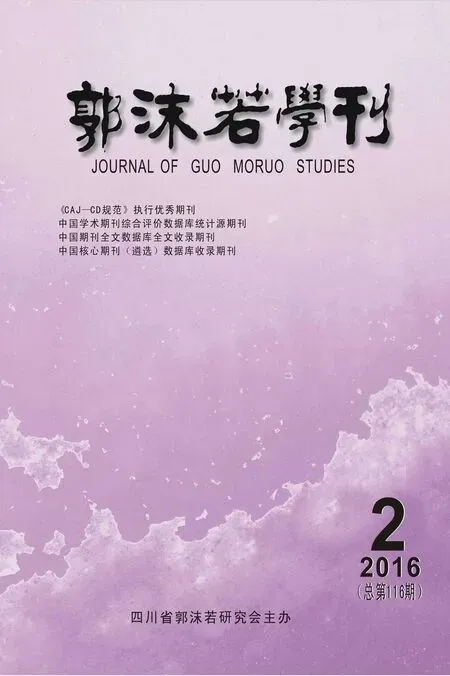俄文版《中国诗歌选·序》
郭沫若
俄文版《中国诗歌选·序》
郭沫若
中国诗歌,严格地说,汉族诗歌,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
三千年前记录的诗歌是抒情诗,这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主流。其他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几乎都有鸿篇巨制的庄重作品,或者说有史诗;这却是汉族诗歌所缺乏的。
中国古代的神话和传说未曾以诗歌的形式保存下来,尽管在屈原的长诗《天问》中包含了神话和传说的因素,但是它们却没有成为这部作品的主干,没有得到诗人的提炼加工。在这部长诗中常常提及神话和传说,但只是为了表达诗人对其真实性的怀疑。《天问》终究是抒情性作品,而不是史诗性作品。
事实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实,就难以解释了。或许,在远古时代,中国本来有史诗,它们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了;或许本来就不曾有过史诗。这两种说法都是很难证实的。第一种说法的支持者归罪于以孔子为首的儒生。孔子不喜欢神话,所以他“删诗”,也就是说不让古代的史诗性作品进入《诗经》。但是,周秦时代那些与儒家相对立的学者为什么不保存史诗性作品呢?从周秦时代的学者们引用的某些“亡佚之诗”(即被孔子从《诗经》中剔除的作品)来看,其语言和风格也与《诗经》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古代的史诗性作品被儒生们删去了的假设是难以得到证实的。
既然如此,或许不曾有过古代史诗?这也难以证实。从逻辑上推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书面的典籍出现之前,应该有口头传播的史诗性的叙事作品;既然如此,这样的史诗性的作品没有流传到现在,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
在古代,汉族就形成了诗歌和散文的严格区分。在诗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抒情诗,在散文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性叙述。《诗经》和《尚书》就体现了这种严格的区分。历史叙述巨匠左丘明,没有采用诗歌的表达形式,而是创造了叙述春秋时代各国历史的纪实文体。司马迁也同样如此,他没有采用诗歌做媒介,他掌握了极高的叙述技巧,对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历史作了记载。左丘明和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的散文大师。他们应该都掌握了诗歌技巧(司马迁有带韵的赋传世,虽然其著作权尚存异议),但他们在自己的叙述性作品中都回避采用诗歌手法。
在周秦时代学者的著作中,有不少带韵律的哲学经典和带韵律的对话文体。《庄子》中就有很多带韵律的对话。在汉代及以后,这种体裁继续发展,进而变为赋,赋是一种篇幅大小不一的散文体诗歌。以欧洲的文学观念来看,赋这一类作品也不妨当成诗。但是在中国,这种以叙述或对话为形式的带韵律的作品被称为“韵文”。这种带韵律的散文与具有特殊诗律的诗是有区别的。
在东汉以后,突然产生了叙述性的诗歌作品,如《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诗》)。但是在诗歌史上这类作品从来没有都成为主流。在唐代出现了“变文”,这是一种在敦煌的洞窟中发现的大量的作品。在金代以后出现了“弹词”这样的作品,这是有音乐伴奏的歌唱性的作品,这大概可以算做是叙事性诗篇。元代的“杂曲”,明清的“传奇”可以称为戏剧性诗篇。不管怎么说,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作品与诗歌是有区别的。
正因为如此,尽管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中国诗歌基本上是抒情诗歌。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特点。
以抒情性为特点的中国诗歌又是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它的语言是自然的,凝练的。在中国鸿篇巨制的诗作是很少的,像屈原的长诗《离骚》,通常认为是长篇诗作,它也只有三百七十几行。尽管长诗《离骚》中包含了不少现实之外的因素,但它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
中国传统诗歌作品的特点是抒情性,富有现实主义精神,语言自然,形式凝练。
正因为具有这些特点,中国诗歌具有特殊的魅力;在历朝历代的诗歌作品中,有不少令人惊叹的精品,它们仿佛是从美玉宝石中提炼出来的。尽管这样,不能否认,中国诗歌缺乏悲剧性崇高。
许多中国当代诗人致力于创作大型的叙事作品;期望这种新的尝试可以弥补不足,取得成就。
1956年6月27日于北京
(俄文原文载《中国诗歌选》,莫斯科: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57年,第一卷,第3—6页。
Антологиякитайскойпоэзии.Под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иГомо-жоиН.Т.Федорен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7.Т.1.)
(刘亚丁译)
(责任编辑:王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