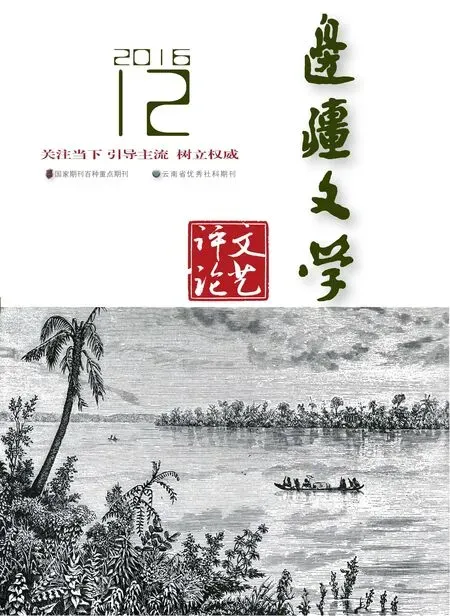素心相对如秋水
——评黄玲散文集《从故乡启程》
◎黄凤玲
素心相对如秋水
——评黄玲散文集《从故乡启程》
◎黄凤玲
散文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具包容性的文体。既可以链接历史,缅怀和追思;也能够指涉日常,会悟和备忘。甚至接纳和伸展人们内心最为隐秘或最难放置和类别的情感,故而,散文当是心灵最亲密的盟友。
新世纪以来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新媒体散文”,可谓是喧嚣热闹的大众写作,其中被评论者称为“调皮的”、“可爱的撒娇”的“小女人散文”以女性作家群体写作的姿态亮相。这是一些“当窗贴花红”的梳妆派散文,她们的语言精巧、圆腻,洋溢着诗意的优雅和轻盈的喟叹。一些女作家力图规避“女性写作”的焦点徽号,希翼穿越性别之门重归传统,回到生活和写作的内部。
云南作家黄玲就是一位对生活和写作有着深刻洞察力的作家。2015年12月出版的散文集《从故乡启程》,值得文坛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新世纪的女性散文写作。
一
在无数春秋中磨砺而日益通达的黄玲对于生活有清晰而坚定的认识:不要执著地试图从生活中赶走悲剧,喜悦和苦难原本是生活的存在方式,生命的感悟不仅来自偶然的惊奇或叹息,更来自寻常日子的平淡和平凡。故而,在貌似酷烈伟岸的历史浪潮里,她并未竭力赞颂那些高居神龛的孤独与喧闹或者黑铁般冰冷坚硬的规律,她始终关注的是那个熙熙攘攘甚至浑浑噩噩的凡尘世界。在她看来,那每一处欢笑,忧伤,狡黠或迷糊都是这尘土飞扬的俗世导向存在的一个隐秘通口。真正惊心动魄的生活,不是把自己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悲壮,也非擂响震耳欲聋的羊皮鼓的决绝,而是行走在庸常日子不卑不亢的坦然接纳和耐心等待。“平庸琐碎的日子像一张网,铺天盖地,无处逃遁。生命存在有千百种方式,莺飞草长、鸟语花香是存在,在尘世的奔波努力、精神的挣扎煎熬又何尝不是更真实的存在。”[1]
黄玲的散文,也涉及大话语模式的理想构筑,有史学厚度和精神力度,但并未沾染上所谓“文化大散文”一般写作者的虚空和伪饰习气。在《大美云南》里,有“我们的祖先元谋人”,有云南历史上可考的最早统治者“滇王”,有民国“云南王龙云”,作者在叙述中,既没有一味坠入历史事件的泥淖,用那些冰冷僵硬的数据和史料将阅读者攻陷,也并非完全摒弃历史的记忆,任由思想如柳絮般四处纷散。而是以历史为经纬,在作者沉实简洁的叙述中,阅读者不断地发现历史烟尘中的伟大人性和精神光晕。
《云南王皮逻阁》一文,作者首先以一个类似戏
曲主人公“亮相”的方式开场“为首的是一个高鼻大眼、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他身披黑色披风,腰挎长剑,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座庄严华丽的帝王之都。他就是来自遥远的西南地区南诏国的第四代王——皮逻阁。”接着辅之以史实和传说,在对皮逻阁的文治武功的敬仰之余,也对英雄建功立业中难以遮蔽的杀戮和惨烈予以甄显,让阅读者感受到历史之火的炙热和文学之血的感伤。
云南历史深远悠长,这片神奇的土地历代上演着丰腴纷繁的文史掌故。黄玲的目光不仅凝视着那些伟岸、壮阔的身姿和功业,还以一腔深情和知识分子的敏感融入那些沉潜在民间的历史碎片和生活的独特段落,将人物的精神信息从凡俗市井中剥离,让人心的温度在晦暗的时间之沙中光亮。
同是云南历史上的布衣名士,明代的兰茂和清朝的孙髯翁都有颇具传奇的经历。如何撰写他们各自镌刻汗青的独秀人生呢?这是对作家的深刻考验。以学者内涵入主作家身份的黄玲,并没有试图去“纠正历史”或“历史正解”,表现出了有别于历史学家的细致的诗情。《布衣奇才兰茂》行云流水般讲述兰茂一生在医药、音韵、文学、教育方面的成就,文言跳脱,语气轻捷松弛,对兰茂这位民间传说中被点化成仙的奇士的生平,可谓是面面俱到又点到为止,毫无赘文。
人们相对熟知的《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翁,作家将“联圣”生活的窘迫与精神的孤傲在《一代名士孙髯翁》一文中铺陈开来,以同为文化人的心性气质感同身受,孙髯翁“睁了眼看世间”的清醒和“布衣终生心怀天下”的尊严,作家行文相对沉缓,节奏控制均衡,再现了“蛟台老人”存在旅程和精神印记。更具宏阔、深沉的文化散文特质。
当然,如若以鲁迅先生的“史识”观要求,在独具个人眼光和精神敏感的“历史理解”方面,黄玲散文的自觉程度尚有提升空间,对于兰茂和孙髯翁的评析还是多受制于公共层面的历史结论。如此,不仅缩小了作者情感张弛的弹性,也使作品的精神指向性过于单一。
而《状元和状元府》跃出了历史浩渺的樊窠,打破时空和事件的桎梏,以现时人的不断重叠的视角去打量那些细碎的史料,用心底溢出的情愫去擦洗时光的阴翳,寻找到历史本初的意义。在亲历者李乔的脸上,我们看到作家沉思的表情“但只要闭上眼睛,屏退世俗的喧哗,便似乎可以让思维穿越时空。”此刻此景,阅读者与作家、亲历者、人物化身为一人,“所谓精神的传承,其实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它会一代代地继续下去。”作家以“借景移情”的方式,将游弋于苍茫流光里历时性的人的心灵品质和精神追求聚集起来,让阅读者在文字中触摸到了历史远处的余温。开创了散文写作中视角构筑一种新的发现方式。
二
在文学中,诗歌和散文,最能呈露作家的心境、才情,因为写作者将自己的心绪、个性、人格,甚至生命直接凝练成了作品,可以说是言心合一,身灵皆融。在这样的文字中,映射到阅读者心里的,既有美的迷醉,情的动荡,更有真的喜悦。应用在人生上,是物来顺应,斟理酌情,不落偏见的悟会。当然,这样的写作对于作家确是一种真实的考验。
作为一个对美有着异常感受力的作家,黄玲懂得,最好的事物并不来自美学理论家们喋喋不休的争论和阐述——它不会隐藏——值得珍视的是人们普遍可以看见的美,它坦现在日光之下,无需证明和解释。
在《故乡在远方》如江河般畅流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叫做米田块的小小地方的似水流年,而是以“故乡”为绸带的舞者,于历史敞亮奔流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或沉郁或飞翚的呈现。在这个日趋匿名化、表面化和短暂化的城市社会关系中,故乡成为承载黄玲精神密度最大的无形符号。在她由心而生,以情入笔的文化记忆和历史想象的双重复沓之下,人格印记的城市和乡村传递着作家流动疏离又富足融合的生活迹象和文化模式。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是另一个我的存在。
笔者认为,作家的价值在于:一直向前走,并适时与读者分享自己新近的印象。黄玲的行走是一生的,从故乡米田块启程,镇雄、昭通、玉溪、昆明、北京、首尔……“只有心知道,漂泊是为了更好地回望,远行是为了思念的绵长。”[2]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地一
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没有这底子,飞扬也只能是浮沫。”[3]对此,黄玲的体验是真切又富有新意的。
作家在不断的行走中,对于人生世相始终保有一种独到的新鲜观感,进而以一种别致的形式将观感表现出来。这样,予读者来说,便是由探趣而生欣喜的阅读历程了。正是因了这心意相通的密切关系,让阅读者不再莽撞轻佻地嬉戏消遣文字,而是将精神凝注于作品的幽深密道,细细品悟作家笔下最具生命力的“灵韵”。 总让人想起易卜生的话:“我写作不是给男女演员提供角色,我写作是描绘人间肖像”。
黄玲不想让伪装和虚荣搁浅了让心灵返乡的诉求,那片生育她的土地是她的喜悦和痛苦,也是她信仰不熄的所在。在这个物质不断挤压心灵,游移成为现代生活常态的当下,无处安放的乡愁也在故事的叙述中自然弥散开来。她率性而又节制的语言,包含着智慧的张力和生存的敏感,揭开经验的暗处,舒展出一个抵达内心而又照亮存在的视野。
在《舷窗人影》中,黄玲并不打算穿着由崇高的词语织就的朱罗衣,以一种形而上学论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作出一副漂亮美观的象征姿态,化身佯装掌控“真理”的哲学家。黄玲的家乡风硬草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勤俭辛劳。然而,嘈杂简陋的日子并没有消解她对岁月和希望的虔敬。她享受着一种平等地行走在人群之中的安静,但也不惧怕以自己的名义发言:“只是历史的碑石上只刻下高原汉子的雄姿和豪饮,女人则被挤压成小小的符号和斑点,如明月旁边的星星,永远闪着微弱而沉默的光,衬托着广袤的天空。”[4]
他们这一代人是有着“良心”信仰的自觉者,他们愿意俯身倾听人们的话语,但并不戴着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面具出现,因为她深谙莱蒙托夫诗歌中的那个世界:看一看你的周围:人群在日常的路上欢快地走动/在他们那节日般的脸上忧虑的痕迹隐隐/却没有一丁点儿眼泪来大煞风景/但在他们当中未必有这么一个人/不曾被严厉的拷打折磨/在皱纹过早爬上脸上之前,不曾有被损,也没犯过罪行。
在《人生屐痕》里,作家很清晰地懂得,个体要在人群中方能找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伶仃一人,缺乏同情与互感,生命便无所发现和寄托,必然会颓顿枯灭。文章中,叙述者身处人群之中,心像安恬,精神平帖。她不哀叹、不怨忿、不疏离,也不恐惧或对抗众人,她在欢笑或者沉默,坦率纯真,洒落隽逸。在从容清缓的叙述中,你会感觉空气变得干净,呼吸更加有力,胸腔充盈着源源不断的真气,这样的文字是健康的,洋溢着阳光的暖意和月华的深邃。
三
我们身婴世网,物质世界在不断捆缚和挤压我们的灵魂,流水线使城市僵化,机械无情至生活窒息。自我与他人之间,愈是隔杂疏离。在人们游离自然太久之后,便少有自在舒适之感,因为困顿和苦痛,时有叹声和哀吟。其实种种,皆是违离自然之心生出的文化病之故。中国古之自给农耕文化,易自足于圆融安然美观,多忽略奋然向前的活动之美。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和安定,它能给予那些奔赴城市,紧张、血气、忍耐、挣扎的生命以养息精力的补救,记忆中的长林丰草将渐渐恢复他们的意志和气魄,进而重返活动的城市。
读《大美云之南》时的感觉最能疗救此种文化病:从“我们的祖先元谋人”之首,阅读者便开启了云南浩如烟海的的尘封历史之旅,出发在即,海上却是重重密密的云气,不免替船长暗暗忧心。但随着风帆高扬,船上的游客时时发出惊呼,茫茫大海上的雾霭渐渐消散了,眼前越来越清晰,猛地发现,眼前耸立着一座岛屿,哦,不,是不断闪现的岛屿,它就在那里,轮廓分明,稳固如山,让人不由正襟危坐,心生敬意。待得胸中热浪稍减,已是轻舟万重山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空气中若有若无的浊酒沁馨,耳边隐隐传来雪山恋人的情歌……
黄玲良好的道德感和伦理精神,带着知识女性的柔情和祝福,世间的人,在她,都应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对象,所以,她并未将笔触滞留在表面化的忧愤和感伤,于是她绵密从容的叙述里自然彰显出一种张弛有节的优雅风度。
“莫名其妙地喜欢车站的气氛,这是人生的一个中转站,人们在这里暂时停留,然后各奔东西。……
‘在路上’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无法逃避的宿命。它意味着心灵永无居所,故乡永远在远方。”[5]这样的文字让我们在黄玲的散文中常常能够发现她对人类的普遍忧思,带着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坚韧和悲悯,在对生命和大地的敬畏与尊重里,书写着一个文化学者的哲思追求,在她恳切与热忱的个人化情愫的流淌过程中,坚执着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气质。
黄玲的散文中确有一种“人性的温情”,不过,这样的温情并不是刻意过滤了生活的恶劣和人生的严酷的,她也并不把流逝的光景和孤僻的乡野当作规避世俗的田园净土,故而,即便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在她充盈着善意和温情的叙述中,自有一种冷峻的沉思表情面对现实的困境展开精神的追问。“心灵的救赎无人能够援手,只有依靠自身的挣扎前行。……当我们在树林间穿行的夜晚,如果用心倾听,一定能听到被风雨摧残、被刀剑损伤的伤口发出的呻吟。”[6]她时而将自我“准客体化”,将自我置于主体意识所观照的对象之位,让寂寞打开心灵深处的眼睛,赤裸的世界在和作家对话,平凡的生命放射出神秘的光:
“远处有几声虫鸣唧唧,丝丝凉意从草丛上掠过,月亮似一冰轮高悬蓝空。升得高了便变得更加清明一些,环绕的云却又让它往朦胧的方向靠近一些。在异国他乡,竟然会有这样的奢侈,一个人独享一个空寂的校园,独拥一轮高悬的明月。天地间只有我和月相对,校园白日的喧哗都随风而去,剩下一片空空的静。”[7]此中空无所有的心境最是难得,也最为广大,最是真切。
四
在笔者看来,好的作家,即使外像冷烈清嘉,内里则应是丝绵着了胭脂般,易渗化开去的。黄玲便是这样的作家:学者的克制和冷静让她保持着理性和思辨的头脑,柔软温润的心灵则让她的文字不被市侩裹挟,潜藏的激情为阅读者创造了一个充满了骨血的抒情世界。
黄玲的散文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出发,自给自足又诚实内省,素颜布衣的文字空间时时隐隐闪现人性内在维度。婉约恬淡中自会建构生命的高度。当然,我们时而也会不经意中触及到一颗因悲伤而沉思默想的灵魂,在《亲情如水》系列文章中,作家纤巧如丝的情绪显得特别敏感,仿佛一张精致古雅的瑶琴,轻柔悠缓的怜爱拂过弦梢,那么细腻诚挚又精妙绝伦,既朴实无华,又异常动人。
在这组文章中,黄玲不仅仰脸抒情感怀,更多的时候是俯首注视脚下的大地,用文字去抚摸故乡的每一棵草,每一粒石子。沉着的情感像水一般缓缓渗入那片现实的土地。此刻的黄玲是最为坦然和自信的。因为她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和厚实的亲情,以及那些在时代的隙缝里艰难生存的挣扎痕迹。在这样的散文中,黄玲表现出了作为小说家的优势——散文中有人物。《外婆的村庄》的外婆,豁达仁慈,“喜欢穿一身阴丹蓝长衫,包一块青丝帕子”,“用一只磨得锃亮的铜水烟袋,咕咕咕地喷吐烟雾”;隐忍坚强的母亲,“独自一个人进城去医院生孩子”,“用微薄的退职金在村里建了一栋草屋顶的房子”。最真切的“人物”便是“外婆的村庄”,这是一个彝族村庄,这里的人们“皮肤要黑一点,鼻子要高一些”,这里请毕摩“转嘎”,这里彝人的姑娘“出嫁了也是自己的姑娘,过年是要叫兄弟牵着马接回来过年的。”黄玲的叙述是朴素安稳的,没有惊天泣地的故事,没有浪漫感伤的情结,但那份深沉内敛的情感在作家贴心蕴藉的文字里,像晨雾中的莲花,静谧却又动人心魄。
《舅舅·舅母》里,大舅舅“不多言,不多语”,但孝顺善良,让晚年的外婆“有了一份相对安稳的生活”,尽享天伦之乐;而对罹患“肺结核”奄奄一息的女儿竭心尽力的救助,以及对五个儿女公正与怜悯实难平衡的煎熬,凸显出大舅舅父爱的博大与深沉,思之令人动容。还有整组文章中“母亲”的形象,忙碌的母亲,絮叨的母亲,无奈的母亲,衰弱的母亲,倔强的母亲,委屈的母亲,达观的母亲……伟大却不无悲剧意味的母亲,来自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当我们凝神回望时,渐行渐远的“母亲”便仿佛迷蒙的烟雨翠湖,“它是一只眼睛,一只令我肝肠寸断的眼睛,照着心灵的角落,让我不得安宁”,空留怅惘和无声的叹息。这样的散文身体是在场的,正因为身体的在场,它才能使作家心灵的律动成为真实,
进而支撑起散文内部一以贯之激情流动的河床和精神发现的天空。
好的散文,让阅读者放下书卷,仍然会有惦念的感觉。黄玲的散文,让我心生惦念,而不想张扬。这不可言说之境,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体味吧。
五
黄玲的散文语言没有丝毫的乖戾气,文章始末都保持着她所特有的那种透视力和平衡感,坚定明敏,带着作家自己的温度和气息,宛若清冽的溪水般的珍贵品质,像极了一位技艺臻于化境的古琴高手,她的文字里高山流水,云卷云舒,早已是目送归鸿,景近心远了。
作为高校教授的黄玲恰如古时得科第之士人,生活无忧无迫,人事宽驰。故能于闲定生活中收拾精神,既不耽于道家空寂和放纵之弊,也不致似墨家因太过艰窘而计较功利,总是行走在人生笃实中和儒家正脉之道,沉实淡宕的艺术人生几可达朱子所说的“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的敬静之境了。如此安闲、平易的心态最适宜散文写作。
《旅韩日记·摘录》是类于闲笔式的散文,这类散文欢迎阅读,可以品味,但却并不适合阐释的。然而,往往正是这类文章最得散文精髓。没有摆出作文的故意姿态,也不在结构上用力过度。看似随意,但却并非信马由缰,漫无边际;长长短短,当行则行,当止则止。《韩国校园的吃》、《去教堂,看别人信教》、《一个人的中秋》、《参观韩屋》,一扫所谓“为远方写作”的空洞和平庸之风,将目光收回,关心“粮食和蔬菜”的日常,从生活的细节中去关注个体经验和精神发现,淡定的情理中不乏有深度的哲思。
散淡而不纷乱,自在而不芜杂。这样的文字既是作家叙事的话语表情,也是心灵风度的外化。读来舒适自然,却能让阅读者兴味盎然。见修养,也见性情,这便是很好的散文。
写作散文最为可贵的是心灵的真实和朴素,切忌矫饰装腔。那些恢弘的感叹和过度升华只会让散文陷入空乏、酸腐的陷阱,从而丧失散文“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的本性。黄玲笔下的生活,并非张爱玲欢喜的“像钧窑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么滞缓,带着悠悠的模糊的幸福。是清楚明晰的,但也不是雪白十字布上的挑花,那么娇靥醒目。倒像是赵延年先生的木刻画,有一种昏濛的愉快和屋瓦上白霜样的清爽。
我想,这本书如果以颜色来作比,那应该是蓝色的吧,深深浅浅,明明暗暗的蓝。明亮的蓝像地中海般的晴朗和庄严;幽深的蓝则似星空的夜,静谧深邃。
【注释】
[1]、[2]、[4]、[5]、[6]、[7],黄玲,《从故乡启程》,2015年12月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3]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1992年6月第一版,浙江文艺出版社,112页。
(作者系昭通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