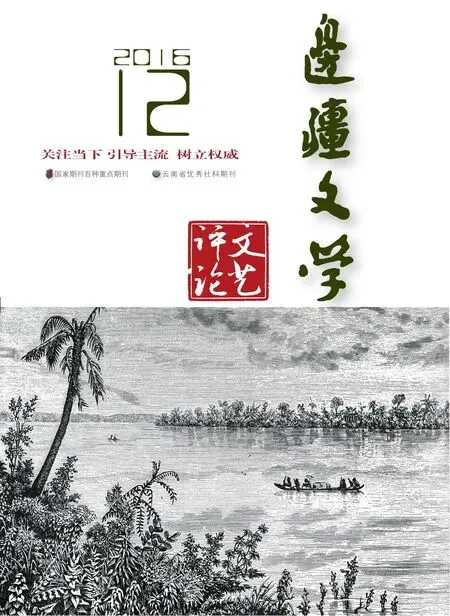站在女人的立场想象历史
——关于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的对谈
◎赵 玫 张 莉
站在女人的立场想象历史
——关于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的对谈
◎赵 玫 张 莉
赵玫: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我们家族的女人》《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等。
张莉:文学批评家,主要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魅力所在》《姐妹镜像》等。
争鸣广场
主持人语:如何走进一部作品,去解读作品,洞悉背后的故事,以及了解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创作轨迹,与作家进行深度访谈与平等对话,无疑是一种有效方式。我们经常见到某些访谈,或浮皮潦草,云里雾里;或仰视吹捧,盲目崇拜。究其原因,这里可能牵涉两个问题:一是受访者值不值得访谈,二是访问者会不会访谈。关于受访者的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并不困难。而访问者的自身学识、案头准备、访谈技巧、写作态度等等,可能更为重要。这里发表一个访谈文本,仅供喜欢这种文体的读者参考。(冉隆中)
“我自己心里有很独立的空间”
张莉:我对您的一篇散文《爱的交换》印象特别深刻,上课时还和学生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们讲到伤痕文学,讲到当时孩子去检举父母的故事,这些在当时不是很正常的吗?后来我们一起读了这篇文章,在那里,那种检举并不存在。父亲为了你的前途,签字承认自己的“反动”,去下放,还主动写信给你,要你去分配办揭发自己,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牵连你,希望你有好的前途。但是,你拒绝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像你那样的决定,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亲情,另一方面孩子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样的选择和当时主流价值观太不一样了。
赵玫:和我父亲的那个,对我本身来说特别重要,它是人性本身特别强烈的东西。比如说我爸是比较耿介的一个人,对于他来说,你应经被打倒了,到乡下了,被开除党籍了,让他签字,我爸始终不签这个字。但他为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去签字。这里有深刻的人性的东西,后来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就特别难过,就是说他为了我可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张莉:你在那篇文章里说,你和父亲之间,原谅这个词根本不存在。“这是亲人之间最可悲也是最残
酷的一件事。何以要让父亲在女儿面前批判自己?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宁可不留在城里,宁可上山下乡,也要让父亲回家。”那时候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这样做。后来你初中上了一年没去下乡,直接去钢厂了,那段经历对你写作经验有帮助吗?
赵玫:那一年我没下乡,因为我们全体都要留在城市,城市已经没工人了。那时候我16岁。在那个时代,得生存,我觉得自己是个很努力的人,和从小的教育培养有关,总是想成为好的人。到钢厂一开始我在氧气站,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跑到很远的地方三班倒。我的家庭背景不行,所以我特别努力,一直在追求进步的东西。后来因为爱写,又到厂部,到了宣传科。但我一直没能上学,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那段时间我一直和工人在一起,就这样度过了艰辛的八年。但我一点都不痛苦,挺快乐的。钢厂的人都说天津话,但我不会说天津话,我整天在剧院里,说话都是最正确的普通话发音。人家都说像“大孙犁”,其实也不接受我们的。当然,我和他们都很友好,但我自己心里有很独立的空间。
张莉:“大孙犁”?意思是你的表达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的不同吧。我看孙犁自己有个文章说,报社的人打扑克,打趣那个输家:你怎么能像孙犁搬家呢?这句歇后语的后面是——总是输(书)。孙犁对这句话应该很敏感,他可能意识到那种被排斥的感觉。我最近两年为什么做孙犁研究,因为我想知道他是怎样融入天津这样一个陌生城市的。后来发现他没有,他从来没有融入过,但这反而成就了他。
赵玫:我爸爸很早就认识孙犁,孙犁在当编辑的时候还给我爸发过很多文章。他那时要弄一个《芦花荡》的剧本,还和我爸他们一块去白洋淀。那时我爸每到春节都会去看他。后来我说想写孙犁,他说好,告诉我他怎么吃煎饼果子什么的,就写了那篇孙犁的印象记。当时这篇文章在全国挺有影响,说这个人的文字怎么那么老道。
张莉:我发现孙犁扶持天津本地作家很少,都是外地的。大概是他没有把自己当做天津人。当时他在天津很有影响力吗?
赵玫:作为后辈我们很敬仰他。他很有风骨,不同流合污。一个人能写好东西他一定没有很多朋友圈和江湖气。我知道孙犁到后来身体很不好了,他去世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去了,我认为他是很令人敬重的人。真正的大师永远是大师。
张莉:作为作家,他的文字是可以超越时代的。他晚年写评论也很有成绩,他给莫言、贾平凹、铁凝写评论鼓励他们,这成就了另外一个孙犁。我写过篇《晚年孙犁——追步最好的读书人》,讲到他晚年嗜读古书,他是以返回古代的方式表示自己不与当代同流合污,那是他的生活态度。
赵玫:那次开孙犁的纪念会,郑法清说,孙犁说谁好谁就会好。孙犁眼光很准。孙犁先生是很有风骨的,他看不上,谁写得不好他也会说出来。他的小说《铁木前传》都翻译到国外去了。他语言的感觉到后期更劲道。孙犁生活在天津,是天津的幸运。
张莉:是啊。我们回过头来说工厂生活。我没读过你写工厂生活的小说。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你去过工厂那么多年。因为实在不能想象你和工厂有关系,而且呆了八年。
赵玫:我写过,但那是很早的事了。但我没有融入工厂。我和工友很好,到现在他们有时候还会来找我,我基本走到哪都会和大家友好相处。当然,这是某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但我就永远也写不到那个地方。可是,我回老家的时间并不长,却写了很多关于农村的作品,只有农村大自然的这种东西会给我很多感觉。16岁一到工厂就去拉练,去了河北的玉田县,我们好多女孩住一个屋。旁边住了一个妈妈和女儿,她们特别喜欢我,偷偷地把我喊过去吃饭。这些东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后来写《漫随流水》农村的那一部分,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好的。比如那种感觉,金色朝阳、棉花地啊,这些都是最美丽的。
张莉:一次有个上海朋友来天津,我陪他逛意式风情区,吃饭时他很感慨地跟我说,天津特别像上海,是以前的安静的上海,很洋派。他说洋派这个词我觉得很有趣,这在你的作品里其实是有的,比如《朗园》,是那种西洋的或城市的气息吧。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一些建筑带给了你这种想象?
赵玫:对。比如说那个墓地,还有我出生在妇产科医院。我刚刚写了一个关于教堂的,那个教堂的牧师是我爸爸上中学的老师,包括我小时候在实验小学上学,那些干部的子弟全都住在老资本家的房子里。这些东西浸润着我,虽然我没住在那些房子里,我是住在剧院这边,但我好多同学都住那,有时候下学就会去那玩。去那玩的时候没意识,等你要写的时候那
些东西就都来了。
张莉:每个作家笔下的天津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吸取的养料是不一样的,和作家内在的血液有关系。
赵玫:小时候的东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比如墓地啊,俱乐部啊,那时我爸有一张卡,一到周末就带我们去。那俱乐部原来是英国人的跑马场,最早的游泳池都在那。我爸是53年来到天津,我们住的剧院的地方离那特别近,每周我爸妈都会带我去。还有教堂,所以,我想到那教堂被拆毁,就有那种特别深刻的难过的感觉。
张莉:我知道你是1986年开始写作的,一开始是写作家的印象记。
赵玫:对,还写了一些理论的文章。我当时给张洁、刘索拉、铁凝等写过,那时候大学毕业,没有立刻进入小说,等于是开始当编辑了。1985年《文学自由谈》创刊,然后就有了机会,我写了很多理论文章。当编辑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作家,觉得纯粹的理论不能完成我当时真正想要做的,再加上我父亲本身对古典文学这方面比较熟悉,他是剧作家,导演。剧院这样的环境中,像我们家有那么多书的都不多。所以,从小家庭中,所谓书香的这种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进入的这个领域虽然跟戏剧没有特别多的关联,但还是会有场景化的某种东西。
张莉:后来是什么契机让你突然写小说了呢,我对这个转变特别感兴趣。
赵玫:其实我始终想写小说。在南开大学上学的时候,当时读了张洁《沉重的翅膀》,张承志《北方的河》那一批东西,那些作品对我们来说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我之前也尝试过写小说,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上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这种方式对我就不行。我只要是用这种东西写作就肯定写不好。大学毕业后,20世纪的现代文学被翻译过来,突然在那时候就做了一些恶补,比如读法国小说,包括读美国的福克纳,杜拉斯,伍尔夫等从他们的小说当中我突然觉得我会写小说了。因为在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位置上没有我的发展,我也不会写那一类的小说。但是当这些作品进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可以了。我认为我重要的小说比较早的就是《河东寨》,《河东寨》当时也是用一种很新意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了,我就按照这种所谓比较现代的方式写了一大批小说。
我们家族的女人
张莉:那当时80年代有很多西方的作品涌过来,催生了中国的先锋写作。比如刘索拉《你别无择》,你应该是那个潮流里的一个作家,而且一直坚持这样写作。《我们家族的女人》是很著名的。是什么契机,使你意识到自己是满族人,要去追溯家族?我觉得这个意识特别重要。
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是我写作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送到乡下,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到十三、四岁的样子。我老家是河北省乐亭县,你看,我们两个都是河北人。在我们这个家族呢,有人在京城做官,但这个大的家族就被跑马占圈占住这个地了。我喜欢老家,所以,乡下在我笔下完全是不一样的,像现在只要是我写到的关于乡下的永远是最美好的一个部分。在老家的时候,我慢慢地知道了关于整个家族的历史,我们家族的女人有很多不幸的,有很多离婚的,我慢慢地就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了,觉得这是一个家族女人的历史。这些满族女人身上有特别坚韧的一种精神。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还是用了一种比较现代的写作方式,中间还穿插着当代的故事,但我觉得那种家族的血、满族女人的那种坚韧都是从我自己的姑妈、奶奶等身上发掘的,都是真实的。后来我查家族族谱的时候,我们这个“赵”叫叶尔根觉罗·维,我是叶尔根觉罗·什么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家族的长相,比如我爷爷那张瘦长的脸,就完全像康熙那样的。这种家族和血液的东西很强大,有时候你没意识到罢了,其实它还是在你血液当中。
张莉:很多民族身份我们能意识到,因为衣服以及饮食习惯等。满族现在同化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意识到自己是个满族人,你得是在某个时刻醒过来,突然认识到自己是少数民族才对。不过,你作为少数民族写作者的身份没那么清晰,意识也没那么清晰,你不是特别敏感。
赵玫:对,没那么清晰,但有人还是能看出来。虽然表面上没什么,骨子里还是有的,比如我父亲身上的那种坚韧啊。但人和人都不一样,家在北京的和家在外省的满族人也不一样,虽然都是满族。还有样子上也有差别,比如有的长得胖胖的样子,并不是所
有满族都是那种细细的。我比较像满族,好多搞民族研究的人一看见我就说:“你是满族吧?”你说得对,虽然我是满族,但我不是特别愿意强调。因为我觉得我有可以不去强调这个的能力。
张莉:阿来有个文章,他说,一方面他愿意用藏族身份去写作,去思考,但他也意识到,单独强调这个人是藏族,可能还有另外的意思在。有时候他也觉得那种普遍性很重要。所以他说,“我借用异域、异族题材所要追求和表现的,无非就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认同,即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
赵玫:民族身份对于我来说也有好的部分,比如我最早的关于那种民族异化的感觉,还是从美国得来的。我参加国际访问计划,当时我们去了三塔菲,那里纯粹是印第安人,那一次在那个高原地区么不是,它是墨西哥州,在山脉上面,就去看了那些部落。他们讲了好多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对于世界的认知。我觉得很多的民族有自己的东西,意识到这些东西很重要。它会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眼光。我虽然不是特别强化关于民族这一部分,但我觉得这个民族身份一定能给人们带来好多不一样的东西。
张莉: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一个老师用一堂课给我们讲族群问题,她说少数民族本身这个提法就是有问题的,民族和民族之间不能以多数和少数来衡量,很有启发性。当一位作家以满族的身份发声的时候,其实和汉族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她是少数才要关注,才要特别照顾。现在关于族群写作在全球化都是很重要的,而且目前来说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潮流。我觉得关于家族和民族的作品可以再写下去,那是属于你的宝藏。回过头,我想说说朗园。我特别小的时候读你的那部作品《朗园》,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布老虎丛书,当时还有铁凝的《无雨之城》,我很喜欢。你是怎么想起要写这个小说的?
赵玫:当时说《朗园》卖了四五十万,据说当时整个中央电视台的人都在读《朗园》。当时写《朗园》之前我已经写过很多作品了,包括《我们家族的女人》。然后布老虎丛书就说让我们写这个东西。一开始有铁凝,洪峰,还有我,我们一块开会,还有马原,但马原没写,还有莫言,他也没写。那时候我已经很在意天津的文化了,之前我还写过和平区,那个就是关于《朗园》的。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在剧院嘛,剧院都是特别偏远的地方,当时河对面就是法国公墓,那个公墓都是我们小时候玩儿的地方。就在八里台那边,那里有法国公墓,有小石头的椅子,还有破破烂烂的喷泉,都是当年的东西。后来在六几年的时候这些公墓就被平了,就变成了个将军楼,就在月盛楼的那个部分。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那玩儿,而且我爸妈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带我去俱乐部,俱乐部就是英国的那个。我对天津城市文化有特别亲和的感觉。虽然我爸妈是从外地进来的,但我是出生在天津的,所以我对于法国公墓、俱乐部啊那种儿时的记忆,不仅仅是景观的东西,而且也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上实验小学么,实验小学大多都是领导干部的孩子。我就发现,在一个老房子里,既有很老的民族资本家,同时党的干部进了他们家,就把他们从二楼撵到一楼。然后再到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些工人进到房子里来,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小说结构。我自己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然后就一直写,但始终没有想起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因为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一个房子里的事,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名字:“朗园”。
站在女人的立场想象历史
赵玫:写《朗园》的时候,还是文学很繁荣的一个状态,大家都特别积极地写,又是很高的稿酬。我记得当时有两件事:一个是《朗园》得了好多的钱,一个是当时张艺谋要拍《武则天》。这两部作品几乎前后完成。跟布老虎丛书签约,跟张艺谋的签约,然后就是94年去美国。他们一开始说让我去爱德华写作中心,后来又说愿意给我一个更好的项目,就是那个国际访问者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走美国,然后本来有30天,但最后让我呆了40天。这三件事在九十年代初对我都特别重要。当时那个项目一个是关于女性,一个是关于写作,在美国走了很多城市。我是这个计划中第一个去的,后来铁凝、方方啊也都去过。现在想起来,《朗园》和布老虎的合作当时是很成功也很辉煌的。
张莉:我那时刚上大学,看过《朗园》的新闻,声势很大,发行量也大,它也算比较早的商业化、市场营销的成功案例。去美国是什么样的经历,影响了你后来的写作吗?
赵玫:这是一个国际访问者计划,到那后我知道我的项目一个是关于女性的,一个是关于写作的。他提前给你做好一个日程。从头到尾会有一个翻译跟随,后来我和翻译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来了以后她和我说你可以去费城去哪的,都给我安排好了,后来翻译说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来。我说我要去南方,我要去福克纳的家。因为当时我已经看过《喧哗与骚动》了,而且我和翻译界有着特别好的关系,包括像李文俊、陶洁老师等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来之前我就看了好多外国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要去看福克纳的家。他们特别好,就重新给我安排,从曼菲斯沿着整个南方一直到新奥尔良,包括住在农村的庄园、黑人家庭,还有去福克纳的家。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每到一个城市你都会和这个城市的人去交流。所以这对于我有双重意义,一个就是我会知道美国人的写作是什么样的,跟他们的作家也交流的特别多;同时,对于女性生存,我有特别强烈的感知,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女性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很不敏感的,当时的国人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女性权利意识。当然,也不能说没有理论,但它基本上是束之高阁,人们把它作为某种学问。可当你真正地你去跟那些美国女性接触的时候会发现,她们都明白自己的权利是什么,我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
张莉:而且,当时也有个契机,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对你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应该是一个刺激。
赵玫:对,我从美国回来正好是一九九五年,是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然后我们有专门的NGO论坛,跟北大的陶洁老师、朱虹、包括冰心的女儿吴青这些人,一起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这个论坛是天津社科院搞的,所以有好多天津的人,还有北京的,北大的这些。这个世界妇女大会,一个是我从美国意识到了很多女性的东西,但同时回来又在这开这个妇女大会。而且在国际访问者计划当中,我还认识一个老太太,叫什么记不太清了。这个人是美国妇女界的重要人物,因为我去了美国,然后这个美国老太太又来到我们国家进行交流。我当时就有一种意识要为女性写作,虽然不是特别明确。我回来后就写完了《武则天》,好多人就说我是女性主义,是女权主义,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武则天本身就有权力,所以你写她,就必须要写她的权力意识。所以对于女性意识呢,我当然有,但不偏执。
张莉:《朗园》之后,你开始写唐宫系列。是张艺谋导演邀请的。我印象中他请了当时最先锋的青年作家加入,你,格非、苏童、须兰等。每个人都写了一篇关于武则天的小说。回过头看,那个电影儿虽然没拍成,但对你来说受益很大,这开启了你的一个创作系列。
赵玫: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写了《天国的恋人》、《世纪末的情人》、《我们家族的女人》也算是三部曲。后来他们让我签约《武则天》的时候,他们给我一周时间考虑,我在想我写还是不写。我的顾虑是我对于历史从来没写过,但我得益于什么呢,我们家里新唐书、旧唐书都有,所以我就立刻看。看武则天,看《资治通鉴》什么的,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我觉得我应该写,而且觉得我应该有变化。我是一个特别希望有变化的一个人,比如说一种题材一种感觉你写完再写一遍,一点意思也没有。但你的变化成功不成功也不知道,但我愿意有变化。所以我愿意,就跟他签了,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一开始那些资料我看得昏天黑地,你想,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什么标点,这个就得益于上大学了,如果没有上大学,肯定不行。
张莉: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你写《武则天》之前,带着女儿去走了当年武则天走的那个线,洛阳啊,长安呀。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想,你一定感触深刻,有强烈的动笔欲望。
赵玫:是我爸提醒我说:“你看的差不多了吧,你应该走出去。”我觉得这说的特别对,那时刚好是夏天嘛,我女儿正好放假,我们就安排好一路走出去。在走的过程中,因为一开始把资料全看完之后其实心里已经有数了,但如果没有真的到那个山川、那个地貌当中,还是没有感觉。所以这一路就是从洛阳,这样走的,人家是那样来的。从洛阳一直到长安,你看那个白马寺,武则天到洛阳后她有宫殿,我就让当地的朋友陪着我,就说你帮我找原来那个旧址和现在这个白马寺,这个路你让我自己走一遍。最后真的是在朋友的带领下走了一遍。路实际上也不是很长,包括到后来看到洛河啊、武则天登基的地方,到今天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真的那个山川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原来的。
张莉:山川的样貌肯定是不变。我的感觉是,走出去对于当时的你写作《武则天》意义重大。你站在那看,会感觉到武则天她当年看到的全是这样的。那种感觉很实际。在屋里的时候想象一个女人怎样进行
皇权争夺和你走到山川之间感受是两回事,后者会让人感受到她的气魄有多大,那些山川和自然风景如何刺激她的斗争欲望。
赵玫:对,就是看着那种感觉,包括到咸阳,到陕西也是朋友都陪着我。然后看着一切你就立刻有了文字的感觉了。走的这一部分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那种地理风貌,那种感觉,还有所有的博物馆,而且还有那种浩大的屋檐。当时我还到了法门寺,给我一种印象是特别特别安静,安静极了!有一些小花,在屋檐上有玉石的风铃,在那叮叮当当地响,就这些所有的东西对我的写作都非常有帮助。
张莉:我们看到的天和她看到的天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法门寺和小花也是一样的,以及风铃。这是一种历史认知,《武则天》的电影虽然没有拍,但后来关于武则天的各种电视剧出来很多。老实说,你的小说对后面这些拍影视的人帮助很大,你是最早对作为女性的武则天的心理世界进行探讨的作家。
赵玫:对。我写武则天之前,看的那些史书全部是男性写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真的是有了一种女性的意识。我觉得我是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在写一个女人。比如说史书上说她杀了自己的儿子,可据我看来,即便是她杀了,那么,她为什么这么做,内心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厉害啊,她做所有的事永远是一击即中,一击即了,通过这些我就觉得武则天这个人真是太了不起了。
张莉:她和那么多男人,那么多擅长玩权术的人一起玩,自己还没有被玩死,她到晚年也算是善终。有人在她童年时代预测她未来要成皇帝这个事是真的吗?我很怀疑,哪个算命的敢在一个人小的时候预测她是皇帝呢,这是犯忌的事情,也是超出想象力的事情。很可能是必须要造这样一个理由,因为她要当皇帝,所以要制造这样一个理由。如果传说是真的,她根本进不了宫。李世民就不会让她进宫。
赵玫:这个事情要是从现实层面上来说可能这不是真的,但那个年代迷信这个。我觉得是后来人附会的这些东西。而且,她后来成功也是依托于宗教。后来张艺谋也说我那个小说写得好,我可能也是这些人中写得最认真的,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本来说只写到登基,当时他们当时打算就排到巩俐的登基,就六十多岁的时候。但我后来还写了武则天和薛怀义的私生活,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要不写就可惜了,就不完整了。最后我把《武则天》变成四十万字,原来打算是三十万字。
张莉:你面对的东西特别少,合起来肯定也不够一万字,很有挑战性。然后你之后就写了《上官婉儿》和《高阳公主》。《高阳公主》你其实在给她翻案,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比如说武则天,之前就有人认为她很有魄力,但高阳公主算是一个创新。
赵玫:先写的《高阳公主》,因为高阳公主是我在写武则天的时候发现的。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这三个作品里最轻盈、文字最好的就是《高阳公主》。所以到后来我一看见这个就特别兴奋,不想写武则天就直接去写高阳公主。有人写过武则天,有人写过上官婉儿,但唯一的高阳公主是只有我一个人写过的。其实是她的故事好,就这么几行的东西。
张莉:字少也意味着给你的空间很大。因为当时很多人说这样一个女人的所作所为是有伤风化,但你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和认知。我觉得《高阳公主》在这三个部分中对你是很重要的。
赵玫:对,但同时我有一点好的地方,就是这三个人物基本上是在一个时期当中,这很重要。互文谁都知道谁是怎么着的。特别有意思的是,《高阳公主》写完后,长江文艺出版社找我说,你怎么不写写上官婉儿呢?我说太累了,他说你得写。后来我为什么要写呢?特别奇怪,我写《武则天》的时候一个字都没写上官婉儿,特别奇怪。然后又竟然写了四十万字的《上官婉儿》。这里面倒是有很多武则天了。
张莉:因为之前已经有了《武则天》和《高阳公主》,所以你在讲上官婉儿的时候更自如了。我的直觉,上官婉儿是一个特别有戏、有意思的人。有些人读你的小说,可能会问,上官婉儿怎么会这样呢?但为什么不能?这是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对人的想象不拘泥。去年有过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上官婉儿的墓被发现了,我们看到了她的墓志铭,这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的。墓志铭里讲述的她,今天看起来和武则天的经历真是很相似。她被封过唐高宗的才人,做过唐中宗的昭容。提到了她和武三思的私通,还和武则天的男宠闹过绯闻。我看那个新闻,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上官婉儿曾经强烈反对立安乐公主当“皇太女”,四次向唐中宗进谏,从检举揭发到辞官不做再到削发为尼,最终以喝毒药这样激烈的方式以死相谏。唐中宗“惜其才用、慜以坚贞”,广求名医,终于将处于死亡边缘的上官
婉儿救活。最终唐中宗答应了上官婉儿的要求,但将她从昭容降为婕妤。安乐公主的“皇太女”之梦破产了。从这些讲述中可以看到,上官跟很多男人有暧昧,她那倔强和彪悍的性格都太戏剧性了,和你小说的讲述是很相近的。这个太重要了。只有一个女性站在女性角度去想象历史才可以做到,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想象不到上官婉儿居然是这样的女人,完全不会想象到这个事情。包括历史学家也不能推测出来,因为这是超越平常人对历史的理解的,可能也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你写的关于这个女人的书里有了,后来发掘的墓志铭就是一个证明。
赵玫:是的,那个新闻我知道,后来他们好多人拿过来让我看,我说这些我的书里全都有的,全都有。都是我想象出来的。
张莉:恐怕当时大家觉得你的小说就是对历史的一个想象嘛,没有人以为是真的。因为很多人理解上官婉儿会有定式,你是从一个女性,也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她。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马上想到了你的女性意识与历史写作的关系。这种站在女性立场上对历史的想象和书写是重要的,它对我们书写和想象历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赵玫:还有最后她的死,那个当然也是真实的,等于是唐明皇要杀她嘛。她走出来,秉烛,让他们杀。非常了不得的,这个女人,上官婉儿。
张莉:可能宫廷里的政治已经使她意识到自己活不了了,所以她走出来。这真的是一场政治,杀了她,又死后哀荣。一般的历史小说都是讲故事一样,情景再现。但你的是心理,是情感,不一定是那种栩栩如生的场景。这是刻意为之还是你觉得这样表达很舒服?
赵玫:写长篇不能太现代,但又不是去做太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写的时候是把历史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融合起来,这尤其体现在《高阳公主》上。它虽然是历史小说,但基本上看不出章回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说这三部作品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的写作很对。台湾人不也喜欢历史小说嘛,我们有次在一起研讨,他们也觉得我的小说在历史小说中是很另类的。
张莉:有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你是用当代人的眼光重新回到历史。当时你写作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叫新历史主义写作,我想,张艺谋请你们写的时候是有考虑的,他们挑选的这几个人都是有先锋色彩的作家,他很可能也是希望用现代的眼光来重新演绎历史。我觉得这三部作品很完整地呈现了一个现代女性怎么去看古代的女性,那些古代的女性呢,因为这样一种关照重新活过来。
赵玫:这三本书加起来前前后后写了十年,有一百万字,已经第七次在印了。永远在印。有长江文艺、天津人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还有台湾的,整整到现在是第七版。但之后再没写过。有人说你再写写这个那个,我说不写了。是这样的,在你年轻的时候,有体力的时候,完成了大部头的东西,这个是你未来想写都写不了的。
“我喜欢不做实的写作”
张莉:好多研究者都提到关于“性”,你里面有很多关于“性”的感受,你小说里不会去写行动,也没有场景,只有感受。这种书写性的方式在整个中国女性写作里面不是那么普遍,它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拒绝观看的,同时又是愿意表达那种女性感受的,是对一种精神感受的分享。你是有意识这样处理的吗?
赵玫:首先,“性”本身就是生命,跟一个人是离不开的。我觉得在新时期当中,它是一个一个突破禁区,包括写作,一点点往前走。一直走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所谓“性”的概念。对于“性”,我们一开始是讳莫如深,但慢慢地就知道“性”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小说跟着这社会往前走就有了这样的一些描写。
张莉:那你是看别人的东西感受到的还是自己慢慢意识到的?
赵玫:是自己意识的,因为我慢慢感觉到“性”和生命有特别重要的关联,如果你不写“性”,你的生命不是完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一部分是不可少的。后来很多人说我的作品中有“性”,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和人写“性”是不一样的,他们说我写的“性”是比较美好的,是真的“性”,不肮脏。包括我的《冬天死于秋季》也有很多“性”的成长,但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不能离开的。至今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依然会有这些东西存在,但我觉得是必须的。
张莉:在整个当代文学中,作为读者你会看到不同作家写“性”,也会看到性书写在中国文学中的发展过程。现在一些青年的写作可能会把这个不当回事,
就是很自然地随时可以出现。你小说里边有内敛的精神性的东西。但现在小说跟以前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可能代表了作家对人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认为人本身就是动物,另外一些作家认为“性”是情感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比如像卫慧她们,也写“性”,也算是一个冲击。她会写和外国人那种很有场面感的东西,一时成为噱头。
赵玫:我喜欢棉棉。现在的这一代写“性“和我们那一代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性”很自由,很随便,所以很轻。我们那个年代呢,虽然我们也生长,也来到这个年代,但对于“性”的理解肯定不一样。我应舒婷邀请参加过韩国的一个论坛,有一个篇章读小说,韩国人读中国的,中国人读韩国的。我在《铜雀春深》的最后一章也写了很多的“性”。然后一位韩国女性读这个,她说又不好读,但是又很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有时候读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张莉:你的作品里经常会有男人和女人,没有名字,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有意思。你说男人和女人,你不愿意特定指。可以是两个人,也可以是一种普遍性。当时处理的时候是有这种想法吗?
赵玫:在我的小说中,经常是一个人有名字,另外一个几个人没名字,我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我不愿意让一个小说里全有名字,当然也和篇幅有关,就是“他”和“她”让我有一种广义在里面,有的时候我是希望用这些的,不喜欢做实的某种东西。就是在你不做实的时候能稍微有普遍性的东西。
张莉: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之后,写实主义出现一直到今天,其实写实主义是大受读者欢迎的。你刚才强调你喜欢做实,实的作品一直不是写实的。而且你很排斥那种写法,一直要和它保持距离。如果有一天你写一个写实主义的小说,读者可能会更多。但你会尝试吗?
赵玫:他们有人说我是心理现实主义,我不喜欢现实主义这个词。我觉得自己肯定写不好这样的小说。每个人都必须取各自之长,我根本就写不好,所以不会去写,不去尝试。每个作家的感知点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物体,有人喜欢描写这一部分,另外的人可能喜欢描写其他的部分。
张莉:我喜欢你这个答案。有的人一上来就喜欢写复杂的人物关系,他脑子里有这个。但有些人眼里是没这些的。这种独特的写作方法是从上大学开始,还是从接触西方文学开始,还是像你说的杜拉斯和伍尔夫对你的影响?
赵玫:还有福克纳。我觉得西方文学的影响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好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受西方影响,但我不会写写实主义,不会写浪漫主义,他们的作品对我就像是救命稻草一样。我对外国的作家也是有选择的,比如一部分是我要知道他,但我真正亲和的、最爱的就这三个作家就是福克纳、伍尔夫和杜拉斯。他们的出现对我很重要。
张莉:伍尔夫和你有很相近的地方,比如她写评论。我特别喜欢她的《普通读者》,随时随地都会带着。
赵玫:在女性里我最早是喜欢杜拉斯,前两天我们还到北京参加了一个纪念她百年的活动。我最幸运的是我没有第一个看《情人》,我最早看的是《琴声如诉》。八十年代初刚写小说的时候他们建议我读杜拉斯,说我的风格和她很像,我幸运我读的最早的作品是杜拉斯最先锋的作品。那个时代是一个最先锋的时代,比《情人》还早的是法国新小说派最实验性的作品,所以我最早接触的是这个。但比杜拉斯更早的是有一年我们全家去北戴河度假,那有一个小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伍尔夫讲真正的现实主义的那个观念,那些观念就像纷纷的碎片一样。所以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是她所谓的意识流是真实的,而我们在大脑被重新整合的东西反而是虚假的。当时我对这些概念特别感兴趣,那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24岁上大学,28岁毕业,大概就30多岁。那时候刚开始写小说。
张莉:所以说那本书是恰逢其时,等于说把你唤醒了。
赵玫:对,让我学到很多。还有一个叫做《弗兰德公路》的作品,还有乔伊斯的小说,他的那种行进感,我当时特别认真地学。我印象特别深,讲那个墓地,一点一点往前走,就有了一种行进的感觉。我看《弗兰德公路》有一个场景,前面有一个公路,然后是跑马场,跑马的时候要跃起来,他用树林、马头什么的这样一种行进的感觉。诸如此类的写作对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就知道该怎么表现这些东西了。我读了《情人》等作品喜欢了杜拉斯,但我慢慢觉得杜拉斯可能太性感了,她是特别性感的一个人。伍尔夫是我更加应该学习的,因为她可以创作她所谓的意识流,把整个世界都颠倒了。
张莉:很同意你对伍尔夫的理解。我视伍尔夫为学习榜样。她有很理性的思考和很整体的看法,但她又用很感性的方式来表达。她没有学究气,还有那么多真知灼见,今天,无论是对我们创作也好,批评也罢,都很有帮助。我个人认为她比杜拉斯要厉害的多。杜拉斯属于比较好的女作家,有独特性,但伍尔夫是开门人。
赵玫:而且她有些概念特别重要。比如有些作家会说,我为什么是女性作家,我们应该是平等的,但伍尔夫不是这样认为的。她认为女性只有做到最好做到极致才是真正灿烂的。她不是浅薄的女性主义。
张莉:对,她不是从感性上去理解,伍尔夫的著名的文章是《一个人的房间》。里面有一段话我特别喜欢,“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我们要独立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重要联系,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她一方面意识到女性本身的地位决定她写作局限,另一方面她不把女性写的不好当做一个借口。她是从整体上来理解男性和女性的差距,非常冷静。她也承认女性本身的东西有可能是不足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可以克服的,好的女性写作就是怎么要把女性的优长发挥到极致。
赵玫:所以我讨厌说为什么把我当女作家,我不介意别人叫我女作家或女性作家这些。我觉得性别本身就在那。
张莉:伍尔夫的语言一方面和翻译有关,但她那种语感、排列的方式还是很独特的。比如一句话里面有一个中心,但她绕着说,同时有比喻、有排比,这个完全是属于女性的。
赵玫:实际上我是比较早不用引号的人。我觉得在语言的感觉中,尤其在比较先锋的时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光说一句话,这一句话中又有语气,又有内容,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不能用引号的。
张莉:伍尔夫用了一种女性的表达方式,她在刻意寻找这种方式。当她写一个论文,比如《一个人的房间》,她也是用那种讲故事、娓娓道来的方式,这是女性的特点。而不是板着脸孔说我是一个长者,这也是女性特点的一部分,她是协商的语气,而不是高高在上,她在强调女性写作的特点时,也强调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刚才你说你写作没有引号也是一种尝试和探索。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你写作的标识性在于,你的语言是繁复的,凝滞的,不是那种很轻快的,而且,你也不考虑取悦读者,你只是回视自己的情感和内心。这是你一开始就有的还是按着习惯走的?
赵玫:这是很自然的。现在我觉得语言本身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感觉上语言比故事更重要,这只是对我来说。因为有些人更喜欢用语言讲故事,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更在意语言的雕琢,但也可能这是一种错误。
张莉:这不能说错误。作家永远都应该对语言保持敏感性。事实上,我觉得语言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就是写作政治的一部分。比如什么身份的人说什么样的语言。前一阵看莫言的资料,他讲到徐怀中跟他们讲,语言就是一个作家内分泌。特别好,这是一个作家、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才可以总结出来的。你有一本书《她说她有她的追求》,里面你使用了三个“她”,其中包含有强烈的女性精神,独立,有精神追求。我喜欢这句话,这不只是一个朗朗上口的书名,也是一个态度。——当你用粘稠繁复的语言讲述的时候,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写作态度。当然,每个人的写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我觉得你最近的写作也在寻找让自己写作更完善的路。
赵玫:对,首先我和那种写实创作是很分离的,我跟它有距离。当然,近几年我实际也是在发生变化。其实每个作家都不可能一直都是那样,不同时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也一样。
(本文作者:赵玫系天津市作协主席;张莉系天津师大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