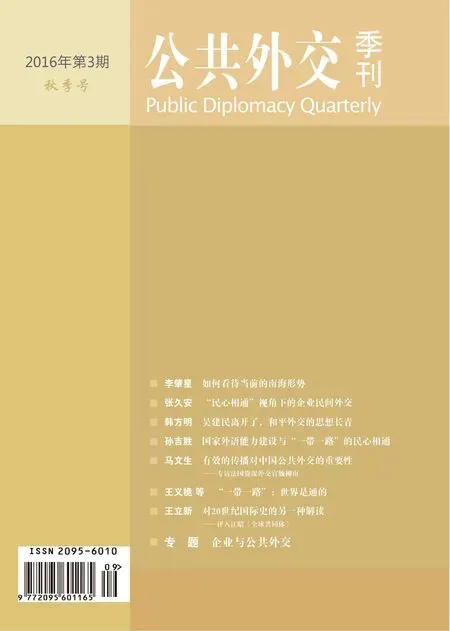有效的传播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性
——专访法国资深外交官魏柳南(Lionel Vairon)
马文生
有效的传播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性
——专访法国资深外交官魏柳南(Lionel Vairon)
马文生
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世界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然而,当我们的政府、企业以及民间团体在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一个又一个进步和成功的同时,却也不断伴随着部分国家、部分地区人民流露出的不解、警惕、甚至是误会。如何有效地传播中国形象,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本刊编辑部专访了法国资深外交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魏柳南博士,希望通过学习借鉴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有所启迪。
“中国威胁论”的来源与去向
马文生:魏博士,您好!感谢您接受专访。您在2009年的时候出版了《中国的威胁》这本书,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做了介绍,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善意。我们想知道,在传统的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形象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国外一直有“威胁论”这个说法,我们到底会威胁他们什么?
魏柳南:我觉得这方面我可以做一些说明,一部分基于我的工作经验,一部分基于我的研究经验。“威胁论”正式开始是在1993年的时候,是从日本开始的,之后才蔓延到欧洲、美国。曾经在很长时期,全世界的文化、宗教、政治战略等都是由美国和欧洲为主的西方控制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对西方控制世界的情况开始产生影响。以我的经验来看,是因为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写好决议,美国、法国、英国——有的时候是苏联——会来让中国签字。不是谈,不是交流,只是签字。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要求跟联合国进行谈判,说“这一部分、那一部分我们想谈谈,我们不太同意”,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比较新的情况。
马文生:以前一直都是用威权直接告诉你:你签字就好了。
魏柳南:对,西方国家决定,中国代表签字,大部分就是这种比较简单的做法。特别是对世界性的问题,比如说关于非洲、南美的问题,都不想听中国的意见。
九十年代以来,因为经济的崛起,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这对西方国家有一定的触动,就是觉得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欧洲外交官的感觉不太舒服,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跟中方交流的经验。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威胁还是机会。早于80年代,欧洲国家或美国大概也是这样,都觉得这还是机会,因为那时欧美的企业可以来中国投资了,而且开放的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大家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还没有想到会有政治战略的影响:政治方面一直都是西方主导话语权,但中国开始要求共享。
马文生:这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那么对外国社会及其普通民众的影响是怎样的,他们怎么看?
魏柳南:最近十年,中国越来越开放了以后,中国人出国越来越多,不管是学生、驴友、企业、商人等很多,这个在中国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外国人来说却是很重要的现象。包括大学教授、学校老师在内的普通民众,他们看到满大街都是他们不了解的中国人,但又缺乏跟中国人交流的经验,加之中外文化本身的差异,导致相互的不理解甚至误解和猜测。
马文生:因为不了解,所以感到害怕,感觉中国乃至中国人是个威胁——是这样吗?
魏柳南:是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不良影响
马文生:除了政府和民众之外,前面您也有提到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他们对国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魏柳南: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多积极意义,但问题也不少,首先一个问题是针对外出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做得不到位。中国企业的大部分员工,不管是工人或者是工程师,他们大多不了解当地的文化,所以他们在当地人的眼中形象很不好。比如说,对当地的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都不客气,不够礼貌,让人家内心感觉到一种压迫感。也许中国来的员工觉得这些非洲人是个落后的国家出来的,素质普遍低下,但是这些部长、总统都曾在法国或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虽然他们的国家经济落后,但他们自己是有文化的。其次,大概因为中国跟其他国家的企业性质不同吧,如果是芬兰的诺基亚公司有问题,媒体只会说是诺基亚,不会说是芬兰;但如果是中国公司有问题,他们就会说是中国政府的问题,他们往往从中国企业推断中国的态度,不是一个个人或一个企业的态度。
语言文化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马文生:中国人说汉语,外国人说外语,但是外交不可避免地要使两种甚至多种语言发生碰撞。实际上,自古以来语言交流一直是中外交流沟通的障碍。但文字可以打破这种障碍,虽然我们不会说英语但是能看得懂英文,外国人的思想也能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关于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魏柳南:我想说,在对外传播方面,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不是中文文章,而是纯正的法语文章、英语文章、西班牙语的文章。外国人的表达方式,有它独特的语言环境,外国一般的民众都能认可。大多数的英国人、法国人自己写文章,可以加入自己主观的一些看法,更切合老百姓阅读理解的习惯。
马文生:因为语言它是文化范畴的,公共外交也绕不过文化,但是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的载体就是语言、文字,没有这个东西很难。在不同语言的对话和交流中,翻译似乎是个大问题?
魏柳南:欧洲人特别重视翻译,但中国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有一次我陪同一家国有企业的几位领导去几内亚洽谈业务,他们带了一个年轻的翻译员随行。当几内亚的一位部长与我们在酒店谈判的时候,就是这位翻译员担任翻译。然而,这位翻译员完全不能准确地翻译公司想要表达的意思,仅仅五分钟,这位部长就站起来说:“你们可以回国了,跟你们谈业务我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解释是因为翻译出了问题,并自己担当翻译工作,所以他又回来了……由此可见,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语言也是公共外交,我们必须要明白语言翻译的重要性。
中国面临的新的外交局面
马文生:您在2015年接受《中国日报》采访的时候提到当时的中国应对外来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强。我觉得中国现在因为经济基础已经相当雄厚了,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多地拥有了话语权,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可以去说几句强硬的话,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是没有的……
魏柳南:我现在还是特别赞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这个观念,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实力还没达到可以有比较强硬说法或态度的这个水平。大概还需要有几十年的过程,现在只是发展了三十年,是不够的。如果中国的这方面做得太快,就会有负面的反馈和影响。
马文生:就是不能太急于求成?
魏柳南:是的,我觉得现在最好的例子就是南海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反应不是美国的,而是其他周边国家的反应。事实上这个南海的问题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问题,不是跟菲律宾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问题。美国就是要利用中国的外交政策来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在东南亚加强他们的影响。因此美国的传媒总说,中国崛起搞的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军事主义,对世界都是威胁。
马文生:是要鼓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一起对付中国吗?
魏柳南:因为经济的影响,十年前所有的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们跟中国有比较好的关系,特别是1997年经济危机以后他们对中国有好感,觉得中国还是支持他们的。但是突然发生的南海问题,让他们觉得事实上最好是有比较远的朋友,比如美国。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马文生: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全世界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当然我们可能就说我们提供了很多“中国制造”,除此之外,您认为还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魏柳南:我认为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对外投资,近年来,中国不论是援助或者是在外建设企业,都是对外投资,在如今欧洲的投资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中国在这方面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
因为有了投资,很多欧洲的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了,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又能够继续工作了。但也还是有不好的影响。特别是高新技术方面,中国收购了很多高尖端的技术,所以现在也引起了西方的反抗、反对,开始限制一些领域的投资机会,说明他们对中国有一种隐忧。
马文生:他们担忧这样下去,会把欧洲变成中国人的欧洲吗?
魏柳南:眼下就是这样,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好多领域现在都是中国在做的,德国还好一些,他们觉得经济方面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事实上存在矛盾心理:外国企业卖给中国企业是因为他们自己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没有人投资,企业就不能继续存在。所以舆论在这方面也是常有比较矛盾的感觉,一方面很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工作,保护他们的工作,但是另一面对中国人的这种投资又表示反感和担忧。
曾经有一些欧洲公司来找我,请我帮助寻找投资人。当我告诉老板:“没有问题,我知道在中国去找谁。”老板却说:“中国不可以,我不要中国投资。”
马文生:难道宁肯解散也不要中国投资?
魏柳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应该找到一个办法来解释为什么出现我们谈到的这个情况。我看到中国企业在法国已经发生过的失败案例,来了两年后就关门,因为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文化。投资外国,收购外国企业,这应该是个好事。但一定要让当地老百姓明白:“我收购它只是因为我想赚钱,中国企业收购只是单纯的经济目的,而没有其它目的”,这个要说清楚。
马文生:是不是借用法国人的笔来给法国人讲,借用欧洲人的笔来给欧洲人讲为好?中国企业常常做一些宣传手册,大都是展示其在国内多么先进、多么发达,多么有实力,将“增加多少就业”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这些或许是他们不感兴趣的。
魏柳南:对,不感兴趣。我觉得这种公共外交应该是长期的,你不能指望做六个月或一两年就放弃,而应该是持续五年、十年、十五年地工作,你才可以期待收到良好的效果。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马文生:想要改变国外对中国的偏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人来把我们的善意带给世界,但好像总是好事不出门……
魏柳南:这方面我要批评我们的汉学家,比如在法国,他们大部分都是批评中国,就是每次写文章、写一本书,或者在媒体、在电视节目里都是批评。去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汉学家,当记者问他:“你觉得华人在国外对当地国家是不是一个威胁?”他说:“一定是。”我认为汉学家不能这样说,因为汉学家的工作不是批评中国,而是解释中国具体的情况。
马文生:这似乎有一个误区:汉学家越能骂、越能说反面的、负面的话就会感觉到他这个人更敢说,说得更像个真话。
魏柳南:对,因为他是主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应该了解:非洲和中东地区很大的一部分,至少他们现在受到的影响大都是来自西方媒体。为什么?因为比方说你在非洲,或是在中东,他们当地人大部分不看当地的报纸,他们大多数会去看BBC、美国的CNN,或是看法国的报纸、媒体。所以在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是西方的媒体,而不是非洲本地的。
因此,要产生影响的话,最大的努力就是对西方媒体有影响,才可以进而跟非洲、中东、南美沟通。因为你要影响的人是他们的社会精英。领导、学者、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受西方媒体影响的。
马文生:所以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或对外传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清晰的目标:最重要影响什么人、达到怎样的预期目标。
魏柳南:是的。当你要在整个欧洲有影响,你会怎样选择?当然你会考虑他们对整个欧洲的文化或是政治的影响。去瑞士没有用,或是意大利大概也没有用。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是谁?是德国、法国、英国——事实上我觉得德国和法国现在比英国影响更大一些。所以你应该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媒体、学者,才可以成功。用中国话讲,应该叫做“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魏柳南:法国资深外交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马文生:本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