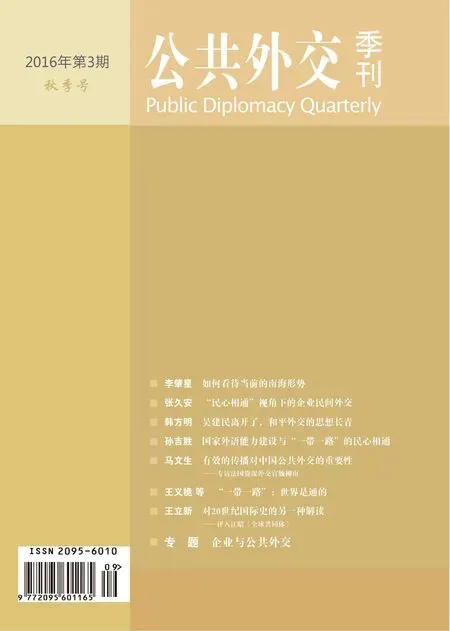中国佛教公共外交研究述评
张 波 刘佳佳
中国佛教公共外交研究述评
张 波 刘佳佳
学界对佛教公共外交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佛教公共外交历史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也存在着历史研究和对策研究不平衡、地区研究不平衡等不足。随着中国佛教在国际交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佛教与公共外交关系研究也得到学界和宗教界的重视,特别是在佛教公共外交历史、佛教公共外交当代实践等方面出现了不少成果。本文主要就近年来这些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
佛教公共外交历史研究
以史为鉴,总结历史上中国佛教在公共外交方面发挥的作用,能够为当下的国际关系走向良性发展提供崭新思路,更好地指导当前的实践。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中日佛教公共外交史研究
鉴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有关他的研究较多,其中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加以探讨的有周一良《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文物》1963年第9期)、孙蔚民《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作用》(《扬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李尚全《鉴真精神:当代中日友好交流的黄金纽带》(《扬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等。此外,马堪温与黄楷《鉴真在中日医药交流上的杰出贡献》(《中药通报》1982年第2期)、张厚宝《唐鉴真东渡与中日医药学交流》(《中国中药杂志》1989年第5期)等具体探讨了鉴真对中日医药学交流的贡献。葛继勇《〈续日本纪〉所载赴日唐人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则以《续日本纪》为中心,对赴日唐僧有整体的研究。
关于日本来华僧人方面的研究有半田晴久《日本入宋僧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郝祥满《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贺金林《清末日僧来华与中日交涉》(《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张兴华《遣唐使中的留学僧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包含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研究范围从唐宋一直延伸到近代,既有整体研究,亦有个案研究,从多个层面展示了来华日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
此外,黄咪咪《扬州—奈良佛教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则从扬州、奈良两座城市之间的佛教交流角度展开研究,显示了当前研究的新进展。
中朝佛教公共外交史研究
何劲松著《韩国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初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再版)中对中韩佛教交流有较多阐述,但限于体例,未能对佛教公共外交进行专门论述。有关中朝佛教公共外交史的研究可以参看黄夏年《中日两国的韩国佛教研究》(《佛学研究》1993年第2期)、敖英《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韩国佛教研究及今后的研究主题》(《当代韩国》2015年第4期)等文。
关于中朝佛教公共外交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朝鲜入华僧的研究方面,可大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考察中国的佛教宗派如何通过这些入华僧人传播到朝鲜半岛,如陈景富《朝鲜入华学僧对玄奘唯识学的研习与传播》(《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2期)、张德宗《玄奘法相唯识学说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与发展》(《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等。二是探求这些入华僧人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如刘素琴《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的贡献》(《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王德朋《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等。三是对入华僧人行迹的考证,如张子开《唐朝来蜀的新罗国僧金和尚事迹考》(《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李成国《新罗入唐僧侣考略》(延边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在这些求法僧中,新罗时期的金乔觉和高丽时期的义天和知讷等高僧最受关注。关于金乔觉,有李岩《“地藏菩萨”金乔觉及其九华山垂迹考》(《延边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等20余篇论文;关于义天,则有崔凤春《海东高僧义天研究》(浙江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10余篇论文;关于知讷,有李海涛《知讷真心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论文,都显示了较高的水平。
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佛教公共外交史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是陆路,一是海路。因此,中国佛教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佛教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索毕德(sobhitha)《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以佛教文化为中心》(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指出,在中、斯文化友好交流中,僧尼以及佛教艺术、典籍、佛牙等重要载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魏郭辉《唐五代宋初中印僧侣交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兰州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通过敦煌文书与传世文献探讨了中印僧侣来往路线的变化及赴印僧侣对印度、南海诸国佛教的考察。李庆新《唐代南海交通与佛教交流》(《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指出唐代“广州通海夷道”,是东西方佛教交流的最重要孔道,不少高僧大德循海陆两路往来于中土、天竺之间。詹成燕《宋代中越文化交流研究》(西南交通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指出,宋代中越两国佛教交流成果颇为丰富。徐国英《宋代中越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对中越之间的佛教交流亦有涉及。
此外,对郑和、法显、玄奘、杨仁山等人物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较多,但多注重其生平考证和贡献论述,很少专门从公共外交角度加以研究。
佛教公共外交现当代实践研究
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为了更好地推动佛教公共外交,除了对古代佛教文化交流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外,还加强了现当代佛教外交实践的研究,并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佛教协会在佛教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响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发挥佛教热爱和平和国际交往的黄金纽带作用,推动佛教界与各国佛教人士的交往,搭建各种平台,推动了佛教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如柯银斌《佛教国际交流与公共外交—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公共外交季刊》2011冬季号)一文中学诚法师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促进理解、增进友情、化解误解、消除隔阂,把中国佛教文化的智慧和真理介绍到其他国家,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认识、认同、理解、欣赏包括中国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呼应,充分展现了佛教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创造了两个重要品牌,即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和世界佛教论坛。
第一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于1995年在中国北京召开,其后每年一次,由中韩日三国轮流举办,掀开了中韩日佛教在新时代友好交流的新篇章。至2015年,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已成功举办了十八次,成为三国佛教界定期举行的重要国际性会议和亚洲佛教界和平友好的盛会,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于2006年4月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和舟山市举办,至2015年10月,已经成功举办4届。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陈冠桥在《世界佛教论坛:公共外交在宗教领域的成功尝试》(《公共外交季刊》2010秋季号)一文中认为世界佛教论坛作为中国公共外交战略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动契合公共外交发展要求而发展起来的。世界佛教论坛成功展现了我国政府的亲和形象,展示了我国公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状况,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有益尝试和成功探索。
学界积极呼吁和研究佛教公共外交
中国社科院黄夏年教授积极呼吁佛教民间外交,先后撰写了《法显大师是佛教民间外交的先驱》(《佛学研究》2011年)、《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发挥佛教的民间外交功能》(《法音》2012年第7期)、《佛教与民间外交》(《城市国学讲坛》2014年),认为佛教民间外交是中国佛教的传统之一,也是官方外交的拾遗补缺。应该抓住当前机遇,充分利用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其他如黄云静、谢明达、许淳熙、司聃等都曾撰文对佛教外交在东南亚及南海等问题上的积极作用进行探讨。
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察哈尔学会承办的《公共外交季刊》是中国首个专门研究和讨论公共外交问题的全新传媒,在佛教公共外交研究方面推出了许多重要文章,已经成为佛教公共外交研究的最重要阵地之一。除了上引部分文章外,《公共外交研究》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徐以骅与邹磊《“信仰中国”: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和两岸关系》(《公共外交季刊》2012春季号)、林影潭等《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公共外交季刊》2013春季号)、韩方明《宗教公共外交的和平使命》(《公共外交季刊》2014年冬季号)等。此外,察哈尔学会还通过举办论坛等形式推动公共外交研究,如2012年8月举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专门设立了“宗教文化的国际传播”专题论坛。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公共外交提供了新视角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2000年,并经由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岛等地区,搭建了一条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友好交往的桥梁。这些友好交往历史多数都是公共外交的范畴或与公共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虽然我们对中外友好交往包括佛教方面的交往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真正从公共外交角度加以研究的还不多。公共外交这个角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发现世界,从而促进不同民族、宗教、文化、地区、国家之间人民的交往和理解。
历史研究和对策研究之间需要平衡
我国佛教对外友好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对现当代的公共外交实践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事实描述的较多,而将实践总结升华成规律的较少,对当代佛教公共外交如何因应世界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提供操作实践指导的成果也较少。应该加强佛教公共外交智库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佛教公共外交实践研究,对其中的问题和经验加以探索提升,提出当前佛教公共外交的切实可操作的方案和对策。
中国各地佛教的公共外交活动的平衡
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大概可以分成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是世界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印度经由西域以及海上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地区。但当前的研究集中在汉传佛教公共外交方面,而对我国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公共外交活动研究不多,不少地方还存在空白。
佛教公共外交研究亟待加强
我们对中日之间佛教公共外交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对中印之间佛教公共外交研究的成果太少,已知仅有范名兴《佛教外交—印度对西藏政策的组成部分》(《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2期)等少数几篇文章。这种不平衡应该得到改善。近年来,由于南海问题的凸显,我们对东南亚地区佛教公共外交的成果已经有所进步,但还不够。
总之,公共外交为我们开展佛教对外交流研究,发挥佛教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倡议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和重要的视角,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果,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平衡,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
张 波:九江学院图书馆馆员,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兼职助理研究员。
刘佳佳:九江学院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