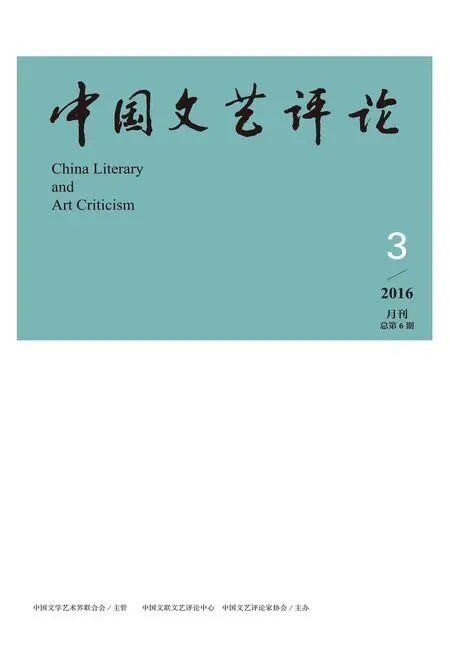“中国古典舞”名分的古今之辨
刘建
“中国古典舞”名分的古今之辨
刘建
一、“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
万事皆有名分,“中国古典舞”的问题首先也是名分。“中国”不用解释,既然“古”字当头,就应该确立它的历史时段。时段可以数量化,尽管数学是依靠人提出命题,但数字本身又具有客观性,“中国古典舞”如果不能确定历史时段的起点和终点,就无法对这一概念作出深入探讨。
然而,在叶宁、欧阳予倩提出“中国古典舞”概念之后,[1]1949年末,中国第一个专业舞蹈团——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正式成立。不久,人民文工团舞剧队与中央戏剧学院合并,当时的院长是欧阳予倩,在他的倡导下正式建立了舞蹈人才培训基地。1950年后,欧阳予倩与叶宁先后提出“中国古典舞”概念。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以后,欧阳予倩把其时的戏曲、舞蹈家们聚集在一起,从戏曲入手,实施中国古典舞最初的创建。这一概念始终未在时间学理上得到厘清,以至学者王克芬在近半个世纪后又提出了“新中国古典舞”概念,[2]王克芬著:《舞蹈续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9-260页。或者解释为“新中国的古典舞”,或者解释为“新的中国古典舞”,二者指的是一个对象。而在“新”字之中又藏匿着古今之辨,藏匿着历史向度中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显而易见,反趋古而崇尚今是王老师的本意,因为这种尚今的说法曾有不同的名目与解释,并逐渐汇成一种主流观点,略述如下。[3]下述资料转引自江东著:《古典舞新论》,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1.“中国新古典舞”说。20世纪80年代时,李正一在《中国古典舞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中国新古典舞已经形成。”此后,她与吕艺生共同撰文,写道:“我们名之为‘古典舞’,它并不是古代的舞蹈的再版,它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舞蹈美学基础上,适应现代人欣赏习惯的新古典舞。”此外,隆萌培和徐尔充在《舞蹈知识手册》中列出的“中国古典舞”条目标题就是“我国的新古典舞是怎样创造和发展的”。
2.“当代中国古典舞”说。在《对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剖析》中,唐满城直接采用了“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概念,认为“中国古典舞是指在某种特定传统风格(戏曲、武术)和民族审美心理基础上,吸收借鉴芭蕾训练中具有共性的因素,以当代人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要求加以发展的舞蹈形式。在此意义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可以叫作‘中国古典舞’。”[1]另外,罗斌在其名为《中国古典舞蹈的“和”品格》著作的第五章的标题也提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概念范畴”。
3.“现代的古典舞”说。孙颖将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来的古典舞形态,冠以“现代的古典舞”之名[2]孙颖:《中国古典舞评说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51页。(从实践操作结果看,孙颖先生所云应该是“现代人做的古代舞蹈”——作者注)。
4.“后古典舞”说。苏娅在其专著中使用了“后古典舞”的提法,指20世纪80年代古典舞“身韵教学”后出现的一些中国古典舞现象,并无学科或舞种界定。[3]详见苏娅:《求索新知》,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总而言之,“尚今”的主张强调“新”而非“旧”,申明“现代”和“当代”而非“古代”,提出“后”而非“前”。这种观念把中国古典舞先在的客观时间主观化了,并且将这主观时间转义为训练与创作、表演与接受的心理时间,因而在中国古典舞质的规定性上形成了历史时间的某种割裂和漂移,直接导致中国古典舞文化空间的某种错位而步入中国现当代舞范畴。
其实,有关“中国古典舞”定义的探讨实则关系“时间”概念的殊同,大可不必加上各种各样的定语。“古”所代表的时间是历史的客观时间——而客观时间是“时间”最基本的物质形态,没有谁能够改变它。亚里士多德的客观时间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真正开始了时间问题的系统论述,他认为时间不能独立于运动之外,是通过运动实现的。牛顿延续了这种时空观点的思路,他的绝对时空观将时间作为客观实体,外在于人的意识。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认为时间是物质所依的存在形式,是感性活动的持续基础,是人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历史时间。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舞的客观时间也物理地外在于我们的历史时间。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谁在什么时候去做古典舞,而是做什么时间的古典舞,并确立相应的历史时段。就世界范围的古典舞来看,我们的远亲“古典芭蕾”不会叫作“新古典芭蕾”或“后古典芭蕾”;我们的近邻且状况相同的“印度古典舞”和“高棉古典舞”也没有重建什么“印度新古典舞”和“后高棉古典舞”。
由客观时间走向主观时间的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他认为时间是主观的:“时间存在于我们心中”,不外于主观世界,是主体“思想的延展。”[4]奥古斯丁著:《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7、253页。康德从先天直观形式出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先天纯粹形式,空间是外在纯粹形式,由外感官所获的在空间形式中,时间是内在纯粹形式,具有先验的主体性。[5]杨祖陶、邓晓芒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0-85页。现代哲学家和美学家伯格森从生命体验和内在感受的角度出发,认为“流动的意识状态”的“绵延”(duration)是时间的原初和本质,心理体验存在于时间的流动中,同时,时间也在这流动中得以体现。他的“心理状态强度”演化为后来美学领域的伯格森“心理时间”(psychological time),这个概念中,艺术是时间的,而不是空间的存在,是“真正时间”的产物。该理论促使时间观念由古典走向现代[1]参见伯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与自由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87页。,如同古典芭蕾女版《天鹅湖》走向当代芭蕾男版《天鹅湖》。
“新中国古典舞”等概念的提出者即带着类似的“时间存在于我们心中”“时间是内在的纯粹形式”的“心理时间”痕迹。他们用当代人主观先验的经验对象取代客观时间划定中国古典舞的存在物;并且用自我主体思想延展出的“适应现代人欣赏习惯”“借鉴芭蕾训练中具有的共性因素”等,取代唯物主义所依的存在形式——历史习惯所形成的中国古典舞特征。
历史学是一门有关时间的学科,应该和人们的亲身经历或鲜活记忆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是从事科学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像《中国古典舞的回顾与展望》一类文字也是一种历史,但它们属于历史学中“短时段”或“中时段”的历史,更多地还属于一种记忆。[2]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传统中,历史和记忆向来泾渭分明。就中国古典舞而言,记忆可以成为记忆史,因为它也带着个人、团体和国家过去留下的痕迹,但这些记忆史还需要连接上此前记忆的时空场所,比如北京舞蹈学院练功房中古典舞的训练与中国古代乐府、教坊、梨园中的身体训练,它们之间至少有技术与风格上的相通,这其中有艺术,也有学术。
曾经有学者撰文评述“新中国古典舞”,感叹这一体系演员“高超的舞艺”。“中国舞蹈演员的基本功好,这是国际舞蹈界都普遍承认是事实。记得1995年9月韩国‘创舞国际艺术节’邀请我去参加学术会并观摩演出。广东现代舞团在开幕式上演出了3个节目,演员邢亮、桑吉加等高超的舞艺,使观众惊叹不已。9月27日,韩国中央大学艺术系舞蹈专业开车接现代舞团全团演员到该校区上一堂‘示范’课,其目的就是想了解用什么方法才能把演员们的基本功训练得如此之好。韩国学生在后排跟着练,舞蹈老师在一旁仔细观察。韩国学生的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但在完成高难度动作时十分困难。坐在我身边的广东现代舞团长杨美琦轻声对我说:‘我们的演员大都有十几年的古典舞基础,一堂课哪能学得会呀!’一语道破天机。这事给我的印象极深。”[3]王克芬:《读〈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创建史〉有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5月7日。
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技术的确值得感喟,但感喟的背后,却潜藏着“十几年的古典舞基础”乃至整个以训练为目标而建立的中国古典舞中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中国古典舞演员的基本功的技术属性是什么;二是这些基本功的服务目标是什么,即这一教学体系为何种表演体系服务。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在世界古典舞训练体系中,古典芭蕾“开绷直立”中脚的空中单腿划圆的基本功、高棉古典舞“三道弯”中手指搭腕(掌形)的基本功、印度婆罗多舞眼睛九种表情变化的基本功、韩国宫廷《黄郎刀舞》道具舞的基本功等,均有学术与艺术的指向,但中国古典舞基本功的要旨何在?芭蕾、基训、武术、体操、现代舞“博采众长”的混合技术无论让哪个国家的学生学习都有难度;除“身韵”之外,那些都不是中国古典舞的版权技术。通俗地讲,如果让韩国学生学习“身韵”,他们不会“十分困难”。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况且我们的混合技术既跳不了《堂吉诃德》变奏,也跳不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堂吉诃德》和《罗摩衍那》属于“长时段”历史中的古典学研究对象,中国古代舞蹈史中的《秦王破阵乐》《十六天魔舞》也在其中。就古典舞而言,古典学[1]古典学学科的倾向是中立的,所谓回归古典,是相信古代还留下许多值得现代人尊重的财富,并使他们利用这些财富介入当下生活。说到底,古典学也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与当代社会文化局面的流变密不可分。是研究那些古代经典舞蹈内核的学问,比如《堂吉诃德》的热情、《罗摩衍那》的善良、《秦王破阵乐》的勇敢和《十六天魔舞》的信仰,以及它们古代的和今天的价值。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故事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是因为它们正面对着当下的某些缺失。所以,回归古典并不是归回古代——况且在现代语境的前提下也无法回到古代。古典不是敬而远之的“古老”,而是可以唤醒反思的“新生”,其研究过程其实就是现代人展开情感与思想的训练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对古典的追寻、研读、对比和发微学到历史变革背后的基本规律和实践法则,学到“变”中的“不变”。中国古典舞的古今之辨所以应该趋古,也是这个意思。
这样就涉及到前面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今天中国古典舞这些基本功的服务目标是什么。在最优秀的中国古典舞演员中,转行跳古典芭蕾的、跳现代芭蕾的、跳国标的、跳现代舞的、跳音乐剧的已是普遍现象,他们的新目标几乎一律指向西方,因为他们的“新中国古典舞”训练体系中渗透了这些元素。在这里,我们没有资格看不起韩国学生,韩国传统舞蹈被记载的有367种,[2]参见朴永光:《韩国传统舞蹈的沿革与发展》,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44页。像《萨尔普里》《僧舞》《羌羌水月来》《刀舞》《太平舞》等剧目,它们都是经过1945年(比中国古典舞创建早5年)解放后的韩国舞蹈家的精心打造和身体传承并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即使我们的身体技术足以模仿它们那样跳出来,但那也是别人的古典舞文本。我们自己的教学体系承载了几何世界公认的中国古典舞文本?因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中国古典舞”之前都没有必要加一个“新”之类的定语。
二、沉浸于历史还是沉浸于体制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以为,“艺术科学课题的第一个形式是心理学的,第二个形式却是社会学的。”[1][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页。前者的时空多带主观,后者的时空多带客观;前者多凭直觉,后者则要面对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某种意义上讲,古今之辨中的“今”派优势的逐渐取得不完全是依靠学术和艺术,除了主观性的时空漂移外,客观性的体制性权力是隐形的力量。
中国古典舞创建之初,这种权力是以一维的方式出现:A拥有支配B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A能够使B去做某些事情。当年,中国古典舞的创建是在苏联化体制和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指令性行为,凡参与行为者要么按既定方针办,要么退出。坚持中国式“古舞新韵”的叶宁和吴晓邦最终成为退出者。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第二维的权力形式出台,它涉及政治学中议程控制的权力,也就是限制各种替代方案的权力。 这种情况有如孙颖先生在建立“汉唐古典舞”的过程中始终携带着一种庶出感;“敦煌古典舞”的发展也如此。台湾文化大学的国舞学者对大陆中国古典舞有过如此的评价:当初以一元方式建设的“身韵古典舞”,实际上是在限制了其他建设方式的基础上强大起来的。在多元发展的今天,这种权力还是以第三维的方式存在着,成为在各种现象的背后的“那些隐藏的和最不明显的权力形式”。[2][英]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82页和86页。这种权力形式不仅限制了中国古典舞的多元发展,而且滋生出一种权力维护大于学术与艺术探索的现象,致使一些本应有反思空间的问题成为了定论。
在《身份、模态与话语——当代中国民间舞反思》一书中,我们曾提到了当代中国(以1949年为时限)职业民间舞的成形、发展和壮大来自于“时势造英雄”,来自于一种新文化建设的体制性推动力。[3]详见刘建、赵铁春:《身份、模态与话语——当代中国民间舞反思》第一章.第一节.二“身份群体的形成及其关系”,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与职业化民间舞相比,中国古典舞的创建更是如此,因为前者的建设毕竟还有活体的垂直传承的乡土民间舞制约,所以还不易直言“新中国民间舞”“中国新民间舞”或“后民间舞”云云;而后者的创建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无所羁绊,更明显地带着现实体制性的“大干快上”风格,用以建成新文化中的一个主流舞种。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无形中依靠体制性权力推动的中国古典舞,很难安静地沉浸于历史之中;其持续性运转在今天被称之为“体制空转”。[4]所谓“体制空转”,是指文化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较大程度上存在着以“运行效率低”和“运行利益自满足”为特征的体制耗损结构。中国古典舞的“体制空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当代人的“自满足”,在国际上难以寻求接轨,在国内很难得到普遍认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了历史时间对中国古典舞的力量,忽略了两千多年“长时段”凝聚的丰厚的文化资源。这样,我们就很难在国际和国内的期待视野中输送有效对位的中国古典舞——像中国古典建筑、音乐、绘画、服饰、书法那样。
严格地讲,关于中国古典舞平地起高楼的“创建说”或“打造说”,本身就带着某种历史时间中断的意味,没有将其视为一种中国大传统舞蹈文化记忆的恢复、保持和继起,没有参透马克思所说的“推翻传统所有制”并不等于推翻传统文化(法国路易十五上了断头台,但古典芭蕾依旧跳到今天)。于是“时势造英雄”的当代体制性工程开始实施,从最初的训练体系到其后批量剧目的生产,直至泛滥的政绩工程。中国古典舞的创建是从教学体系(或曰训练体系)开始的,其体制性的构建方式延续至今——外部体制保护了内部体制。
其实,即便就古典舞内部的体制性而言,其刚性制度也应该向历史和文化靠拢。在历史和文化的视野中,“身体训练体系”“动作训练体系”和“舞蹈训练体系”是不同的概念,它们由宽而窄的依次关系是:人类历史阶段的身体训练〉人类文化差异的身体训练〉人类舞蹈文化差异的身体训练〉人类舞蹈文化差异中大、小传统差异的身体训练。这些不同时间和层级的训练是由生理学、体质人类学的公共性体系而指向艺术符号学的风格性训练体系:“所谓公共训练体系,我们知道,在某些领域中的确是存在的。比方说在体育领域中……所有这些领域所需要的人才需求及评价系统,是全球统一的,它们需要的是培养出相同的‘类’人来。而在艺术领域(当然包括舞蹈领域),情况却并非如此:不同舞种的动作体系,其在训练的方法方式及其价值评判上,是彼此完全不同的。因为,培养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彼此不同的。举个例子,日本雅乐舞者的训练,仅是为了培养表演雅乐的舞者而建立起来的。很难想象一个经历了日本雅乐训练体系的舞者,是为了去跳芭蕾舞的。反之亦然。”[1]江东:《古典舞新论》,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第146页。
这可以说是一个刚性原则。但是,当中国古典舞的创建撇开了“跳什么”而专注于“怎么跳”时,体质人类学的差异(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文化人类学的差异(基督教文化与儒释道文化)、社会学中阶级层级所带来的大、小传统文化差异(古典舞和民间舞)以及舞蹈学的舞种差异(汉唐古典舞和敦煌古典舞)等身体训练内容便全被混淆了,中国古典舞身体语言动力定型的训练就泛化成为了一种身体训练:“我们已经注意到,目前国内许多具有自主决断力的舞蹈团体或舞蹈教育机构,已经不再采用中国古典舞体系作为训练的基本教材和手段了,而是选用更能出人才、更健全的训练体系如芭蕾、艺术体操或其他的训练体系作为培养舞者的方式”。[2]江东:《古典舞新论》,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类”培养取代了“舞种”和“子舞种”的培养,中国古典舞训练的古今之辨当然也随之泛化了,泛化为初建时期随苏联体制而进入中国的芭蕾化。这种体制性的动力定型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而且以体制化的力量延续到今天。
事实上,无论是截止到近代还是现当代,无论冠以何种名称,中国古典舞虽然已经凋零,却死而不僵,依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于世界:存在在文物里,存在在文献里,存在在图像里,存在在古代舞谱里和乐谱里;存在在“礼失求诸野”的民间中,存在在“寺庙古典舞”中(它在某种意义上已属民间);甚至存在在韩国唐乐逞才中,存在在日本雅乐之唐乐中,等等。现存日本雅乐中的唐乐舞包括宫廷燕(宴)乐健舞类的《秦王破阵乐》《太平乐》等,包括软舞类的《春莺啭》《甘州》《苏合香》等;包括歌舞大曲类的《赤白桃李花》《采桑》等;包括歌舞戏类的《兰陵王》《胡饮酒》《拨头》等。《迦陵频伽》是从天竺经唐代传入日本的,敦煌壁画中屡屡出现。[1]迦陵频伽原是佛教传说中的美音鸟,人首鸟身、手执乐器、边奏乐边舞蹈。日本雅乐舞蹈中的《迦陵频伽》舞者着红袍,背饰鸟翅,头戴插有花枝的冠,双手各执一小钹,振翅欲飞,由瑞穗雅乐会表演[2]参见刘建:《拼贴的“舞蹈概论”》第四章・第一节・二“中国古典舞有无真身”、三“当我们面对活的古典舞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古香古色,为今人所高山仰止。尽管这些雅乐已经日本化了,但从历史和文化的刚性原则上讲,它们也比芭蕾舞更接近中国古典舞。
以此观之,“今”之中国古典舞与“古”之中国古典舞相遇,将如河伯面对北海若(海神名)时所言:“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而按照当代的古典文化建设者布尔克哈特的话来说,则是:“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3]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页。
刘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