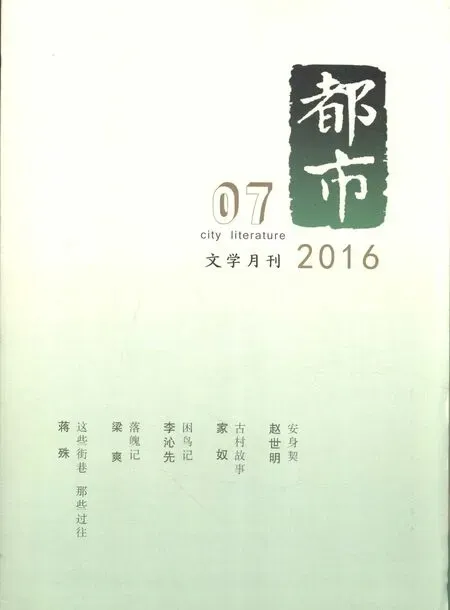龙城小人物五题
孙涛
龙城小人物五题
孙涛
坟前的黑蝴蝶
老Q从台湾回来,由县长陪着,到村子里来上坟,村子里能认识他的人已经不多了。虽然年过花甲,可老Q身板儿笔挺,只是那满头银发和一脸皱纹,将人生的沧桑折射出来。尽管县里早安排村里的干部们,要接待一下这位从台湾回来的老军人,但他执意不进村委会,要先去父母和妻子的坟头祭扫。
他的家曾是村子里的旺族。1946年,他从重庆的一所大学回到老家,还给父母领回一位漂亮的女同学。父母不得不遂了他的意,给儿子和儿子领回来的女同学办了婚礼。摆的是流水席,村里的老少爷们,无论上礼还是没上礼,全被请来喝了喜酒。婚礼罢,他和新婚的妻子到了县城中学,成了学校的教师。天下正乱哄哄的,县城里驻扎了国军,到学校来招兵。讲话的长官说的全是国家危难、精忠报国的话。他一腔热血往心口涌,当下就报了名,穿上了军装。长官喜欢他,要留他在身边做参谋。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部队就接到开拔令。他只好与妻子洒泪告别,离开了县城。
从那时起,一心精忠报国的他,随着那支国军,打一仗,跑一程,终于跑到台湾去了。他有文化,离开大陆后官儿越做越大,一直做到师级才退役,可他一直没有再娶别的女人。也有一位同居的女人在他身边,他却既不办婚礼,也不要孩子。从到了台湾的那一天开始,他每月都要给父母和妻子写一封信。信写好了,装进信封再贴上邮票,可那信无法寄往故乡。
他每月去一次邮政局,买一张精美的邮票,贴在那无法寄走的信封上。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他开始喜欢上了集邮。每个月装信的信封,就是他集邮的天地。信封的正面,写着无法投出的地址。信封的背面,则贴满了台湾最新版的邮票。有些成套的邮票,信封的正面贴下不,竟能贴满信封的整个背面。退役后他开始做生意,有了些积蓄,有朋友劝他,该和同居的那位女人补办个婚礼了,他却摇头。他依旧每月写一封信,给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写这种无法寄出的家书,成了他伤感也最快乐的一件事,而买下最新的邮票,欣赏贴满信封正面和背面的那些花花绿绿的方寸艺术,也成了他最伤感也最快乐的一件事。后来,两岸终于能通邮了。他给故乡的政府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当地政府表示,欢迎他回来走走,看看,要定居也行。关于他的父母、妻子,只有一句话:“他们已故去了。”
于是,他回来了。出现了我开头描写的那个场景。
他来到了被村委会重新整修过的坟前。一座属于他的父母,一座属于他的妻子。他看到了坟周围分明是刚刚栽上的小树。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都是死在“文革”时代。他们曾顽强地活着,活在他的阴影中,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跪在坟前,让积攒的眼泪尽情地流淌,落入膝下的黄土地。他打开了一直提在手中的皮箱,里面装满了一摞摞没有寄出的信。他将那些信点燃了。那些精美的信封、正面和背面贴着的邮票,还有那几乎是他用一生光阴写出的家书,全化成了无数黑色的蝴蝶,带着岁月的无情,飞向了天际。
县长事后对人说,这位从台湾回来的老军人,是一位少将呢!那一皮箱未寄出去的信封上,全是没有盖邮戳的邮票,那可是台湾近四十来年的邮票啊!可惜,让那老头子一封一封地全烧了。
我是在一位朋友家中见到这位台湾老军人的,时间是1988年的盛夏。我的这位朋友,是这位老军人的外甥,也是这位老军人在大陆故乡唯一的亲属。后来听这位朋友还告诉我,他舅舅回到台湾后,终于和同居的那位女人,补办了一个隆重的婚礼。舅舅邀他到台湾一游,他也是那场婚礼的重要嘉宾。
非洲的犀牛
老E退休了,参加了机关的老干部学习小组。每周两次,常来的,也就那么十来个人,全是住在机关宿舍区的,来回近便,念念报纸,扯扯闲话,以打发日月。老E成了学习小组新成员,大伙欢迎。不为别的,就为了老E肚子里货多,天上地下,国内国外,历史考据,时事新闻,无奇不知,无所不晓。也有与老E在某些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者,但辩不倒老E。比方说,某个字,查字典,不是老E说的那个意思。老E就笑着反驳,字典就全对?就不会出错?大家为此一乐,某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老头老太太的,一会儿也就忘了。
老E人好,自个儿买了个吸氧机,或者得了个什么养生偏方,都要告诉大家,好像是产品推销员似的。老伴做好芥辣丝,或腌好萝卜咸菜,特具地方风味,老E就给大家每人一小瓶。老E也很认真,读报时发现个错字,或者发现个标点错误,当下就会给报社总编办打电话。大家会说,这种错,除了老E,咱们可看不出来。老E听了高兴,他常在报纸上发表小文章,报社的总编和责编,几乎全认识。老E每天去小学门口接孙子,学校贴出开家长会的告示,竟被老E看出两个错别字来,他当即就去找校长严肃指出。
老E还做过许多好事,比如说,资助过一个穷孩子上学,直到大学毕业;比如说,在职时领导让他负责一项工程,包工头给他送来一个红包,让他当面骂出办公室;比如说,某夏夜,有小偷爬窗进入他家,正巧老E小解毕,如张飞般发一声怒吼,小偷落窗而逃,老E却不依,赤膊短裤地追下楼去,小偷竟将一包东西扔下后,拼命逃脱。最终,老E家分文未损,还为邻居们拣回一包被小偷偷去的物件。
老E也有糗事,那日众人又来学习,有人捎带给孙子改作文,孙子写的是动物园游记,那个犀牛的犀子,他左看右看不对劲,便问大伙:犀牛的犀字怎么写?老E脱口道:尸非牛!那人便说,看来我孙子没有写错。众人却纷纷搭话了,都说,不对不对,是尸水牛才对。那人就找来字典,一查,对老E说,这回你可说错了。老E呢,这回没说字典错,而是说,你们说的是中国犀牛,动物园当成水牛养在水池子里,我和他孙子,说的是非洲的犀牛,“尸水牛”和“尸非牛”,都是犀牛,都没错!大伙儿又哈哈大笑。
夭折的传记
老R五十来岁,很富态,很精干,可谓一表人才。老R是商界成功人士,是董事长、总经理,名片上还有一些能显示出社会地位的头衔。老R的生意做得很大,在他的商界伙伴中,口碑很好。老R的老家在山东沂蒙山,一口改不掉的山东腔,夹带着走南闯北学会的普通话,很有一股山东汉子的豪爽。老R的唯一缺点是文化低,连小学都没上完。要不然,老R也不会托朋友找到我。
老R在省城最好的大酒店定下包间,让我享尽口福。老R给我敬酒,说咱们的事就说定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对了,我最信奉你们山西的关老爷了,关老爷为啥不弄上一匹驷马骑,偏要骑吕布骑过的赤兔马呢?我本想给他说说驷马的含意,他却又热情地给作陪的朋友们敬酒去了。
老R说的“咱们的事”,便是由我来给他写一部传记。我不能脱俗,更不会讨厌人民币,老R开价不低,远比我创作一部别的什么作品报酬要高。再者,老R由山东沂蒙山里走出来,只带着一把瓦刀闯荡江湖,最后在山西落脚成家,又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顺势而为,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有传奇性,有时代性,有故事性,还有多年在商界拼搏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人物传记,我不愁写不好。
之后有一段日子,我陷在创作的冲动中。调查、采访、甚至跑到老R当年落脚的太行山里,去他成家的那个小山村体验生活。我在脑海中还原着历史,老R以前零星的一些口述,和我的调查采访渐渐地连缀起来。老R的父亲,一位曾经在解放战争中为刘邓大军推过小车,当过支前模范的老党员,却在“文革”中被夺了权的一派打成了反革命。父亲对儿子说,你跟爹学了一手泥瓦匠的好手艺,快走吧,走得远远的,留在村里,爹会拖累你一辈子的。老R于是离家走了,河北平川、河南沃野、淮河两岸、一路流浪。靠打短工糊口,还要过饭,被抓过“盲流”,又在收容所里逃走。流浪两年后,他钻进了八百里太行山,在一个小山村里,被村里的支部书记招了上门女婿。那位支部书记看小伙子人好,腿脚勤快,彻底收留了他。无须去虚构,这就是真实的故事。还有感情上更多的纠葛呢。改革开放后,经过十多年的奋斗,老R创业成功了。可妻子成不了他事业上的助手。妻子的文化比他还低。为了事业发展,他招聘各种员工,公司便有了一位办公室主任,是那种可以随他在各种社交场合应酬的女性。该女子成了他的心腹,最后也成了他的新夫人。旧的婚姻解体了,老R的事业继续做强做大,自然,少不了新夫人的支持和谋略。我不想用道德标准来判断老R的爱情和婚姻,更不想为老R的这两桩婚事断个是非。糟糠之妻不下堂固然是一种美德,古今中外名人们各种婚变的故事,也并没有影响了他们的声誉。婚姻,不也是人生和事业的一种需要吗?但我必须写出老R在情感纠结中的种种心路历程,这需要与他做更进一步的深聊。我明白,传记的真实性正在于此。
我终于完成了框架式的提纲。我必须听听老R的意见才能正式动笔。然而老R却通过所托的朋友,对我的提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要在传记中舍掉第一段婚姻,而且,这是不可再行商量的意见。我当即明白,“咱们的事”是无法进行下去了。因为,他要隐去的内容,正是我绝不割舍的章节。如果,老R自己会动笔,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写出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如果,他又找到了别的合作伙伴,我更不知道那位同仁,会不会遵照老R的意见去写。我不做“咱们的事”了,也与老R中断了联系。但愿老R能与别的执笔者合作愉快,日后有一部令他满意的传记问世。由此想来,眼下,书店里那些琳琅满目的当代各色人物的传记中,有多少传主的人生事件是杜撰的、删改的、隐去的,对读者而言,真是个谜。
大师的人生
老T如今成了大师,是坐在家中,便有人找上门来算命的大师。凡来算命运,问前程,或测祸福、定风水者,都不是穷人。老T口吐莲花,对方奉上银子,你情我愿,两厢满足。老T曾经在几个单位待过,那时拿的全是死工资,眼下的收入,比当年滋润了许多。
老T初出道时,还在“文革”期间。县里的剧团要排样板戏,要招些年轻人。老T当年长得帅气,“文革”前的初中生,写得一笔好字,除了会哼两句山西梆子,还会几样乐器。笛子、二胡、铜锣、小鼓,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也没有正经的师傅,他就是有这种文艺天赋。起小跟着村子里的梆子戏票友们混,没想到就攒下了被招进县剧团的一笔资本。那时的剧团是吃县财政,老T从欺负土坷垃挣工分的农民,成了端上铁饭碗月月领工资的演员。剧团演《红灯记》,老T饰鸠山。一次去一个村里演出,饰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和鸠山的演员,算是团里的角儿,有资格在村里的知青点上住单间。半夜里,这“鸠山”就摸进了“李铁梅”的房间。村里安排了知青巡逻,全是些青皮后生,发现有人窜进“李铁梅”的房间,便去“保卫”样板戏,生生地从“李铁梅”的床上揪住了老T。“李铁梅”顾脸面,两人做这事,原本不是一次两次了,被人捉住,她却当下大喊大叫,说是老T强奸她。第二天,“鸠山”强奸了“李铁梅”的笑话,就传遍了全村。团长找“李铁梅”问话,“李铁梅”还是那个说法,老T遂被剧团除名。
老T毕竟是有前程的人,不久,就托人进了城里的一家国营大工厂。老T的文艺天赋又成全了他,成了厂办一名写写画画的干事。改革开放了,老T一身西装革履,陪厂办主任去深圳,替厂里做一笔生意。结果很糟糕。主仆二人合谋,先用公款做了一笔倒手买卖,自个儿先赚一笔,再完成厂里的事。没料不久案发,对方被抓,供出了他们,老T在经济问题上栽了跟头,只好随厂办主任一道住进了大牢。没几年出来,老T又投奔到一位个体老板名下。老板娘还年轻,老T与她眉来眼去,让老板发现了,老T再次丢掉了饭碗。也就是从那时起,老T正式“下海”了。不做别的,在一处香火不错的庙院旁,租了个小门脸儿,做起了靠《易经》谋生的生意。老T其实根本看不懂《易经》,只是记住了《易经》上的一些名词,加上从书摊上买下几本打卦算命的盗版书,作为知识补充,凭着一张嘴忽悠人。老T是经过些世事的人了,看几眼上门来算命的主儿,与其闲聊几句,自会投其所好,说得天花乱坠,让对方跌进云里雾里,心甘情愿地给他掏出银子。特别是那些文化不高的富婆,更被老T说得心悦诚服。
我有位朋友研究《易经》,并在北京一家大出版社出版了厚厚的一本专著。他想通过《易经》所阐述的阴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尽力去寻找现实社会和具象事物的规律。此类专著,属于文化人对《易经》的研究。《易经》是一部反映古人哲学思想的经典。这位朋友的研究,走的是正路。只是稿酬寥寥,不够高档酒楼的一桌饭钱。而一本充满老祖宗智慧的《易经》,却成全了老T绝处逢生的活路。至于那些个坐在闹市街头行人道旁的卦摊主儿,比起老T来,就差劲了许多。或铺一张白纸,或铺一块红布,或铺一面黄缎,上面的“广告词”大同小异,虽不敢称“大师”,但“易经”二字,常常作为给人算命时的点缀。相同的是,他们如此落魄江湖,不知是否早算清了自个的命运?
还得说说老T,人虽渐老,经验却渐多,有了钱,保养的也好,可谓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了。我去看他,竟见其一身道袍,不知何时,大师变成了老子的弟子。
九指“的哥”
老J那天是一个人喝了闷酒后,重新回到家的。妻子还躺在床上,轻轻地抽泣着,两只原本总是闪出妩媚的大眼,成了两个难看的大肿泡,分明是老J睹气出门后,妻子就没有停止过哭泣。老J瞅一眼厨房,就明白,妻子一直没有做饭吃。老J想再次安慰妻子,可他不知从何开口。从澳门那家世界有名的赌场出来,老J就想好了,是该彻底和大大小小的赌场告别了。他下了飞机,回到家,向妻子坦陈,所有的钱,这回是全输光了。妻子问,真的?他再次坦陈,真的。妻子就是那时一下子哭起来,渐渐号啕、捶胸、跺脚,向他扑上来的。你给我滚!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呀!你给我滚!滚!老J只好先躲出了家门。
他于是就去喝闷酒。酒精在他的血管里燃烧,将悔恨、内疚、自责、一道燃烧,烧得他心痛。也就是不到半年的光景啊,三百万,三百万呐,一下子就没啦。妻子原本是不让他出这趟远门的。妻子说,赢过了,也输过了,这三百万,咱就留着做点本份的事吧。妻子又说,谁谁家把钱用来办公司了;谁谁家齐刷刷买进五辆大卡车,要搞运输了;谁谁家听说市里要办个养老院,正准备投资入股呢;你就不能不赌?就不能另外想个赚钱的路?可老J不听,他赢过,忘不了那种赢了钱的快感,那是一种让人成瘾的享受。他对妻子说,我就再赢一把,赢了,就把这三百万给你,你给存起来,咱再想法子做个生意赚钱。可他没有想到,这回竟会输了个精光。
老J的小日子,原本过得很滋润。妻子在城里一家超市打工,老J有出租车,自个只开半天,再外租半天,两口子挣不下大钱,但天天也是好日子。两口子结婚早,老J刚四十,妻子小他三岁,儿子就上了大一。老J在城里租着房,爹妈给他留下的院子可不小,又在新公路规划的地界上,只要城中村改造,风水宝地值个好价钱。但规划归规划,好多年了,市长换了一茬又一茬,就是没人管这事。猛一下发了财,是在多半年前。市里来了个新市长,雷厉风行要改造城中村,指哪拆哪。老J的村子,终于有了大动静。除置换了新房,这补助,那补贴,一下子到手三百万,还有个小零头。都知他发了财,几个老同学催他请客。老J是个性情中人,便在城里一家大酒店,设了个饭局。酒足饭饱,尽兴之后送别众客,正准备回家,被返回来的一位老同学拉住,说这楼里有一处好玩的地方呢,拉起他就钻进了电梯。那是他第一次进赌场。口袋里装着一万来块,请客花了三千五。老同学让他小赌一把,算是图个高兴。拗不过老同学,就上了手。几遭下来,一路顺风,口袋里的钱,几乎就快两万了。从此不能自拔,开始大赌,进而发展到去澳门豪赌。几番下来,赢过,输过,再赢,再输,在疯狂的快感中,在下一次将会大赢的期待中,终于将三百万输了个干干净净!
老J想给妻子掏出心窝子,说再不去赌了,说以后要好好跑出租,辛苦挣钱,珍惜这安安稳稳的小日子。妻子却不信,翻身坐起来吼他说,我不信,再不信你,你剁个指头我也不信你了……听着妻子的话,酒精在血管里燃烧着的悔恨、内疚、自责、突然拧在一起,由心底冲进大脑。老J吼起来,我让你不信,让你不信!他扑进厨房,摸过菜刀,将左手伸出食指,摆到案板上,右手挥刀猛地劈下,厨房里顿时血点飞溅。老J跌坐在地上,默默地瞪大眼,看着他的一截食指,还在案板上颤动、滴血。
老J重新开起了他的出租车。上午他开,下午租给别人。凡有客人坐车,看到他搭在方向盘上的左手缺一根食指,眼神总会有点异样。不用客人问,老J都会抬起手来,晃晃,对客人说,想听吗?这根指头,是被我自个儿剁掉的。
我便是这样听完了九指“的哥”的故事。我不知道该为他失去那三百万悲叹?还是该为他回到了生活的正路上点赞?老J却又开口了,说,钱算啥!家和万事兴,攒点钱,我还准备闹个公司发展呢。
(责任编辑高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