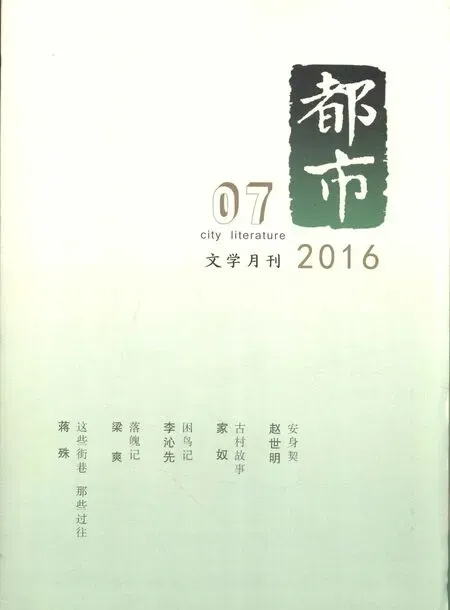这些街巷,那些过往
蒋殊
这些街巷,那些过往
蒋殊
择一个四月花开的日子,由南向北,穿过继北京长安街之外的国内第二条大街——迎泽大街,跨过五一东街,顺新城南街进入文庙辖区。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里弥漫着撩人的香火味。而围拢在庙宇周边的那些街巷,经历了云卷云舒,目睹了身边建筑的兴衰更替,从古远的旧时光里一路坚强,延伸到今天。一条窄窄的小道,用它无边的力量,携同两边不住变幻莫测的建筑物,连通起一个一个风格迥异的片区,最终撑起一座城市。
每一条巷子,都历经布鞋草鞋马靴到高跟鞋,一代又一代人踩出的,必然不是单纯叫脚印的东西。每一道街巷,既历经了深情的细雨中漫步,也承受过雷鸣电闪的疾风暴雨;每一条街巷,被爱过,也被伤过。
远远地,五一路拆迁工作紧锣密鼓,我甚至可以看到淡淡飞起的尘埃在空中飘移。一些人被拆走,一些人幸运留下来。欢喜与不开心,都在他们各自的心里。惟有这些经历过大风大雨的街巷,不惊不喜,静看身边新一轮变迁。
回望新满城
小五台小学,以65岁的年龄迎候在新城南街路东。
对一个建筑来说,65岁还很年轻。然而,小五台小学的脚下,却曾风起云涌。
小五台与五台山算不上亲戚,但确实是有一些关系。《太原志》说:“明代,此处有大士庵,建筑古雅,院中有奎星阁,为文人雅士联诗之地。明尚书王道行告老后,用朝廷嘉奖的3万两银子,在这里建成大花园,明末毁于兵祸,清初重修。后有僧人募捐建起文殊、观音二阁,因称该地为小五台,并名于世。民国年间为警士教练场、运动场。今古迹无存,故址在小五台小学校一带。”
小五台之名,究竟还是来源于文殊、观音二阁,这便也是它与五台山之间唯一谈得上的缘分。五台山路途遥远,崇拜观音的太原人,便把自己的心事,一桩一件说给小五台的观音听。从明到清,尽管风雨飘摇,观音却一直驻此,护佑当地居民。
可人类就是这样,用双手缔造了艺术,也要用双手把它们毁掉。明代大士庵、大花园,清代文殊阁、观音阁,虽历经毁损修复,最后终究彻底灰飞烟灭,连一片废墟都不肯留下。
今天,连曾经的小五台派出所也改为文庙派出所,留存在人们脑中的小五台记忆,也注定越来越遥远。
突然觉得,小五台小学肩上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因为只有它,才能隐约追寻到400多年前的历史,以及一段一段的岁月划痕。
并州名校小五台小学9800平方米的土地上,阵阵书声随风飘出,与对面盲校学生的训练声遥相呼应,掩盖了多少光阴多少陈年旧梦。今天的小五台小学,校舍一律青砖挂面,仿古的风格与周边建筑相比显得庄重严整。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是不是依旧要得到奎星的扶助,比别处多一些文运?懂得小五台的人们,会不会透过青砖,细细遥想几百年前那些崇拜观音的旧人,一声接一声的无边虔诚?
新城南街的风貌,依旧如几年前,窄,旧,繁华,散发出浓烈的老城味道。过了文庙派出所十字路口,便成了新城北街。早年,新城南街与新城北街本是一家,叫新满城街,也称新城街,与位于如今旧城街一带的旧满城遥相呼应。
清顺治五年八月,清政府已经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但太原汉民依然敌视清政权。于是第二年(公元1649年),在太原市旧城西南角的大南门街(现解放路)以西,修建了一座称为满城的城堡,专为八旗兵驻扎和旗人集中居住。满城西、南至城墙,东至大南门街,北面不到水西门街,东西约六百米,南北约四百米,面积约24公顷,东与北各设一门。
一座小小的满城,隔开了满汉间的缘分,让驻太原府的清军和旗民在其中安全生存。
满人们裹在城里,从顺治六年到光绪十二年,度过整整237年。然而没想到的是,公元1886年秋,一场汾河秋汛,冲决开城内东堤,汾河水顷刻间泛滥于整个太原城。旧满城所处的西南低凹处瞬间变成泽国,水积起一丈多深,以至于房倒屋塌。满城内的居民和城中旗兵,只能临时迁居府城贡院(今起凤街铁路宿舍),聊以栖身。直到第二年春天,也即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春,政府才以每亩16吊钱的低廉地价,购得西起文庙、崇善寺,东至山右巷南口泰山庙,东、南两面迄至城墙根的土地,重建满城。
这就是位于小五台的新满城。
一位老者“修油烟机”的吆喝响起在耳边,打断了我对130年那片古老城堡的还原。
从一些旧史籍记载看,新满城与旧满城的规模难以同日而语。新满城内有四条街、三个街名,分别是新满城街(今新城南街和新城北街)、新满城西街和新满城东后街。而这三条街的宽度,也分别只有9米、6米、5米。当时的房子,就建在今天新城南北街的马路东西两侧,东面共有排房29排,西面25排,分别属正蒙旗、镶蒙旗、正蓝旗、镶蓝旗满民居住。房前还设小旗校衙门4座。今天的新城街小学一带,设有方尉府衙门4座;现太原17中一带,设有城守衙门、关帝庙、万寿亭和传习所。
操练习武、农工实验、平凡日子,生活在新满城的644名旗兵与数千名满人居民,共同在太原府构筑起满城社会的别样繁华。
可历史就是这样,再怎么怒放过,也要凋谢。
清王朝的大厦,终于到了倾塌的一天。1911 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辛亥革命爆发。起义军总司令、山西河津人姚以价声情激越历数清兵入关、肆虐中华的各种暴行,以及清政府腐败无能,外患日深、国事日非的情势。他大声疾呼军人奋起救国,并下达了“攻占太原”的作战命令,第一道军令就是由督队官苗文华率领的第一营攻击满城。凌晨6点,满城外响起第一声枪响,起义新军顺着太原城墙一路向东,从城墙下向满城内射击。此时,城内300多名旗兵与千余名家属被枪声惊醒,拿起武器开始抵抗。几番僵持下,已经占领巡抚衙门的起义军将几门火炮从承恩门拉上城墙,拖到小五台城墙处,居高临下向满洲城轰击,之后都守尉孟长寿逃走,满洲城守尉增禧竖起白旗,缴械投降。
一夜的暴风骤雨,太原换了天地。
只历时短暂24年,新满城便在硝烟弥漫里人去城空。
新满城内的满民,成了一片片风雨飘摇的叶子,失掉了多年来由清政府下拨的粮银和生活费用。为了生计,大部分人重新走上了吃粮当兵的老路,参加了阎锡山部队;还有一部分人外出寻找营生,另谋出路。30年代初,阎氏兴办“西北实业公司”后,多数满族青年涌入“西北公司”下属各厂,学徒从工,成为太原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新满城中的满城营守尉署及农工传习所,也换了山西商业专门学校,从此传出新的声音。
新满城街,由南至北仅有310多米,到了民国中叶时,又从今天的文庙派出所十字路口一分为二,南段改称“新城南街”,北段定名“新城北街”,构建起新的格局,一直沿用至今。
从1887年创建,至1987年新城街小区全面改建,新满城从产生到消亡,历时整整一百年。
在这条刻满100年年轮的老街上,从南走到北。快到上马街时,一处旧院出现在眼前,黑木门,青砖面,满满散发着时间划过的破旧。小小的门上挂着两块牌,右上为蓝牌“新城北街19号”,左下黄色木牌为“新城北街四十号院”。主人正在锁门。我近前,问可否是他的家?他说是,房子是解放后所建。
尽管距当初的新满城有些遥远,但这古旧在当下繁华的高楼面前看上去异常古朴珍贵。
然而我知道,这个旧院,必将与曾经的新满城一样,要被时代的大潮冲刷得寻不到一丝踪迹。
山右巷的春天
多年不来,山右巷宽敞了很多。西面进山中学的侧墙也开放着,可以敞亮地看到里面的布局。才知道,近年是重新修过了。记得2000年初居住在这里的时候,最怕的便是开车出入,从山右巷到府东街,短短535米距离,却需一步步挪动。不小心,便会碰到身边的骑车人,行路人,卖菜卖饼子的小商贩。
时代带给人类总是如此矛盾,既有快捷的便利,又有寻不回旧时光的忧伤。
好在,一位年轻女子从窄窄的巷子里提着一只塑料水桶走出来,让我看到昔日时光还在继续。
可是,拐角处的情形,让我瞬间回到从前。与刚刚提桶出来的年轻女子一样,几位大娘在此接水。是年龄的原因吧,她们接水用的桶只是那种用完的油壶。或许是因为我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像路人一样匆匆而过。其中一位最年长的老人把目光敏锐地投向我:可是记者?
佩服她的犀利,我点着头。她于是打开话匣子。我知道了她今年82岁,在山右巷的平房里住了60年。突然之间升起一股乡愁的意味。60年,她是如何从一位花季小媳妇,成了今天白发苍苍的老者?尽管她看上去身体很好,然而毕竟是82岁的老人了。她把60年给了山右巷,而山右巷给她的依然是那个小房子,她依然需要天天出来提水,风雨无阻出来上路边的卫生间。
谈话中得知,她曾经做过多年的社区主任,也让我明白她会如此敏锐。她的前后左右都是林立的高楼,而她与她的邻居们还始终住在狭窄的平房里。她不停嘱咐我,你是记者你要给我们写一写、呼一呼。我知道,这话她不知说了多少年,也不知嘱托了多少人。然而我与之前的那些记者一样,替她传递出的信息能不能起到作用?一个82岁的老人,还有多少时光,可以消磨在漫长的拆迁、修建,与回迁上?
我更相信,待到山右巷小平房全面拆迁的一天,这位盼来光明的老人,必定是一边欢喜,一边在60多年的时光里泪流满面。
山右巷这个名字,常常被写作“山佑巷”,以至于身处其中的居民,也说不太清楚到底应该是哪个字才对。翻开1987年编撰出版的原“太原市南城区地名志”,看到记载:山右巷得名于民国时期杨泰嵘在该巷建立的山右大学。
遍寻,最终从网上看到一本《山西私立山右大学同学录》(1929年),除了有董事录、教授录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这本旧册子清楚地告诉今天的人们,当初山西私立山右大学的董事长为堪称学界耆宿的赵戴文,副董事长马铎,董事分别为赵效复、杨泰嵘、赵希复、张四教、李翰章、张思忠、傅敏中、张生明、马明鄂等人;前任校长赵希复,校长杨泰嵘。
山西私立山右大学自1922年创建,到1928年先后共计招收学生400余人;1929年,与私立兴贤大学合并组建了私立并州大学,在原山右大学校址内建设新校;1931年,私立并州大学改称太原私立并州学院。
1935年,私立并州学院停办,山右大学彻底消逝在人们视野。
有人说,山右巷后来误传为“山佑巷”,含有祈求神灵保佑之意。虽然1982年经市政府下文更正为山右巷,但许多不明此文的人依旧要习惯于称该巷为“山佑巷”。
由南向北一路走出去,才发现随着府东街的改造,通往府东街的路已另有其道,古老的山右巷,继续曲曲弯弯坚守在这座都市里。而巷中那些古旧的小院,混合着青砖,红砖,水泥,像一件打了多次补丁的衣服一样,向路人诉说着走过的历史。一些坚强的树,更是挣扎在这狭窄的砖石水泥夹缝中,顽强地寻找着它的生存空间,以至于枝干早已失去了该有的生长方向。
一棵树长成这样,蕴含了艰难,辛酸,变迁。更多的,还有树的精神,路的精神。
四月,正在太原最美的春天。这些树,正绽放着新绿,为这座城市添加着该有的春意。
上马街的故事
一听上马街这个名字,我脑中总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天空,大地,一匹马,一个官样男子,一跃而起,它帽子上的飘带,在微风里轻轻飞。
果然,在老辈太原人中间,流传着一句民谚,“太原有个上马街,北京有个下马街。”细问意思,说是李自成当年从这里上马,挥戈北上一直打到北京,在北京某街下马。于是,太原就此产生了“上马街”,北京也由此出现了个“下马街”。查史得知,上马街此名与李闯王没有丝毫关系,它得名于明初问世的皇庙。
位于上马街南面的皇庙,占地面积约11000平方米,是明、清两代帝王、皇族和文武官员祭祀先祖和庆典的场所。在现存皇庙建制里,仅存太原这一孤例。当时的官员参加祭典时,有一个规定下马、下轿或上马、上轿的地方。参加祭典时,官员们下马或下轿后,走皇庙西巷到皇庙;祭典结束后,再走皇庙东巷出来上马或上轿离开。
而官员们上马与下马的地方,便被称为上马街、下马街。
到了清代,废弃了明代的规矩,清除了皇庙中明代的皇家牌位与神彰。皇庙也改为万寿宫,成了道家做法的道场,皇庙巷也更名为万寿宫街。而凡去万寿宫祭祀者,均由万寿宫街直入,再无明代上马下马之赘举。于是下马街与上马街合并,统称上马街。
上马街与新城北街、山右巷形成丁字,西至五一路,全长709米,宽9米。
这是一条鲜活的太原古街巷,也可以说是一片小社会,窄窄的街巷里汇集了最典型的城市图景。这里紧邻太原最繁华的钟楼街、柳巷等商业街区,有进山中学、太原教育学院、太原七中等大中学校,还有崇善寺、皇庙、文庙这样的国家级保护圣地。
一直以为,走进上马街,就走进太原市。
最早知道上马街,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时候。一天,被好友带进上马街,她的父母家里。记忆中是一处院子,是小平房,然而那个时候,却觉得这就是城市。以至于多年以后暂住在这里,还常常去寻好友家那个小院。无奈人去楼空,早已没了踪迹。
那天在上马街一处街口,忽然发现路南两个旧院落。欢喜地跑过正欲推门而入时,街边那位卖熟玉米的陌生男子冲我们的后背几声喂喂。扭头,他笑:院里有狗。
透过院门,里面南北两排都是平房,以至于中间一条路最多只可容两人通过。几位老者在阳光里不知是下棋还是打扑克,吸引了一位提了一袋饼子的中年男子聚精会神驻足观看。突然记起,上马街上一家小饼子铺,曾天天排着长长的队。几年后再见,这个小饼子铺还在,打饼子的男人女人还在,铺面依旧那般狭小,只稍稍进行了装修。
上马街,是一处古老与现代交汇的片区。高楼林立间,平房里的人依然过着从前的日子。倒尿盆,提水,冬去春来,重复着自己。
2015年,由太原市实验晋剧院青年剧团5位国家一级演员倾力打造的红色晋剧《上马街》,在太原上演。《上马街》把太原解放前夕四合院里生活的一群勤劳善良的底层民众搬上舞台,他们在困境中自发组织,克服断粮断水、逼迫威胁的困难,与特警处斗智斗勇,最终将情报城防图送出,完成了一项事关太原解放大局的特殊使命……
老太原旧有的地名、人物、事件、语言,浓郁的民情、民俗、底层民众,纯朴、善良、勤劳、勇敢的美德,勾勒出《上马街》的精彩故事,升华了上马街的精神风貌。《上马街》的故事,或许就是上马街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也是太原市曾经发生的真实。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虽然平凡、渺小,但精神和觉悟却无比伟大。不知道有多少太原人看过这部剧,当你看到这些说着太原话、住在上马街、平凡而渺小的“小人物”,在历史的大变革中却彰显出非凡的勇气与觉悟时,是不是为身处太原而倍感荣幸?
说到上马街精神的,不得不提的还有其浓烈的书香味。
上马街最早飘出书香的地方,应该是崇修书院与汉山书院。崇修书院是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由太原府知府李崇蟠申请,山西巡抚英桂批准设置的,院址在崇善寺附近。1903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将太原崇修书院改为太原府中学堂,是山西省成立最早的中学之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岑春煊奏请农工局,在原汉山书院旧址上开设了农林学堂,也就是今天的进山中学校址。这是清末山西第一所实业学堂,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农林专门学校。1907年改名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开设高等农林本科,还设有农业试验场和苗圃。
与私立山右大学一样,进山中学同样创建于1922年,同样得到时任山西督军府秘书总监、参议总长赵戴文的大力支持,他还从《论语·子罕篇》内一句“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提出用“进山”二字作为校名,寓意为有“进”虽“一篑”但积“篑”成山,并有“前进登高”之义。
1931年5月,“山西省私立进山学校”改名为“山西省私立进山中学”;解放后又更名为“山西省立进山中学”;1953年全市进行学校调整时,又改名为“太原市第六中学校”。后来,为了继承和发扬学校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教育传统,1985年10月16日经太原市人民政府批准,山西省教育厅批准备案,由薄一波同志题写了校名,又恢复原校名——进山中学。
校名几经变迁,校址也是。初建时,在位于旧省政府东北隅的太原市弓步街“外国文言学校”;1931年迁入上兰村;1937年因“七七事变”爆发被迫停办;1941年秋,在晋西隰县复校,至1943的两年间先后在隰县南关、北门外后寺、大麦郊温泉村和汾西县窑上,办起四个分校;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太原,一院设立在新城西街前商业专科学校旧址(现为太原十七中),二院在上官巷一号(现市公安局职工宿舍);1962年,迁至今天的上马街,也即原山西农林学堂旧址。
风风雨雨,难阻进山在坎坷中登高向前。一代代教育者们恪尽职守,培养出诸如何雁秋、邓初民、池必卿、纪廷梓、程子华、裴丽生等大批共产党人、革命者以及王瑶、徐士瑚、张沛霖、李振麟、阎沁恒、朱葆晋等一批专家学者。在民主革命初期,乔亚、徐惠云等数十名师生更是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铸造了进山中学的光荣传统和英雄风范。
此刻再看进山中学,沧桑中竟含了苍凉的意味。
一代代标准的太原普通小市民,浸泡在这条街上的书香、庙宇里,鲜活了上马街,也丰满、厚重了自己。犹如,博古架上那些饱经风雨的宝贝。
两个外来孩子续写的传奇
清代,皇庙更名万寿宫,缘于废弃明代的规矩,清除明代的皇家牌位与神彰。
即便在今天,万寿宫的恢宏气势都在。黄琉璃瓦顶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耀眼夺目,显示出皇族祭祖建筑的不凡气势。
当年的周边,必然布满显赫。岁月更迭,战乱反复,再加上人们以发展及建设的名义,一点点将历史的过往揉碎在尘埃里。然而尽管伤痕累累,万寿宫的辉煌脉搏依旧高贵地延续。
明灭了,清逝了,皇庙不再,万寿宫清冷的只剩下华丽的躯壳。时间进入民国。两个外来的孩子,在这个恢宏之地再写传奇。
万寿宫南面,一处建筑以特别的长相静立在残破的环境里。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环境下,它不语,内里却透出无声的故事。
房子外面,是市政府于2009年9月3日悬挂的“太原市文物单位·万寿宫3号民居”。尽管十分破旧,但大门两边的两根罗马柱还是能看出典型的西式风味。
幸运的是,我很快联系到院子的主人之一,房子的第三代主人张云峰与他的爱人张慧茹。
这套院子建于1925年,为民国时山西邮政局局长张汉山的住宅。院子坐北朝南。正房五间(外加厨房两间),南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四合院现保存完整,院内有一棵桑树。西侧原建有花园,解放后拆除。
张汉山原名张天杰,大他两岁的哥哥叫张天俊。张天杰兄弟原为寿阳人,父母都为基督徒。1900年,在义和团与教会的大规模冲突中,张天杰的父母双双被杀。为了保命,张天杰兄弟俩由姑姑带着来到太原的基督教会,寻求帮助。
基督教传入太原时活动主要有英国的浸礼会、内地会、自立会和美国所属的公理会等。该教教会在太原兴办的社会慈善事业有赈济、慈幼、医疗、教育等。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浸礼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在山西赈灾时,在太原城内设立男女孤儿院各一所。同年,又在太原东夹巷办孤儿院。
东夹巷与万寿宫近在咫尺,兄弟俩之后把住地建在万寿宫,是否当初来太原就是被收养在东夹巷的孤儿院?
义和团很快失败,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这笔史称“庚子赔款”的费用中,有一部分就用作当时被杀中国教民孩子的教育。因此张天杰兄弟俩在太原的基督教会生活、上学,一直使用的这笔款项。两兄弟聪明智慧,长大后,张天俊考取了北大,张天杰考取了山西大学数学系。有趣的是,上学期间两兄弟因崇拜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将名字分别改为张汉中,张汉山。
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毕业时,受助款项却用完了。于是哥哥张汉中从北京回到山西,留在教会工作并直到生命最后;弟弟张汉山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山西省邮电局。
民国时期,邮电工人收入一般都比一般工厂工人高出不少。因此到1925年,主要靠在邮局工作的张汉山力量,修建了如今的万寿宫3号院。两兄弟一直和睦共处,张汉中育有一个男孩,五个女孩;张汉山育有六个男孩,两个女孩。14个孩子不分谁家,只以年龄大小进行排行。而孩子们也因张汉山的力量,中学时代就都到了北京读书。张慧茹说,她的公公那辈都是大学生,她的公公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兄弟还有西安美院、天津大学等,个个了得。
张汉山由于工作出色,很快做到山西省邮电局局长的位置。
更为神奇的是,张汉山兄弟俩娶的,竟然是一对亲姐妹,娘家就在太原宁化府。而且,张汉山的妻子,竟然与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是同学。
从孙辈张慧茹口里得知,张汉山与哥哥张汉中,并非同时娶了两姐妹,是因张汉山常随婚后的哥哥去嫂嫂家,这个优秀的弟弟才再一次被岳父母看中,甘心情愿把二女儿也嫁给他。
万寿宫这个3号院,越发神奇无比。
现在,院子里的第二代主人仅剩下老三、老四与老六,最大的已经88岁,小的也已超过80岁,都不在太原市生活。
在万寿宫3号院住在最后的,就是张汉中的孙子张长胜,以及张汉山的孙子张云峰。他们是2006年在附近买了楼房,离开老院的。
今天,他们虽然不在老院居住了,但张长胜几乎每天都要回去看看。张慧茹也说院子里的桑椹马上成熟了,得回去摘。
张汉山兄弟俩没有想到,当初普普通通一座院子,如今竟成了文物,成了太原市一道珍贵的风景。
离开,回望。大门楣上的四个字在“文革”时被铲除。问及张慧茹,她说原写着:主恩锡嘏。
希望上主给全家赐福,再无父母那样的苦难,或许是张汉山兄弟俩当初的最大心愿。
万寿宫上空的圣乐
一座极具西式风格的基督教堂,处在万寿宫3号西几十米,刚刚修缮一新。隔着紧锁的大门望进去,干净,整洁,沉静。
教堂与万寿宫张汉山的3号院属同时期建筑。张慧茹他们听爷爷讲过,当时是因为教会缺乏活动场所,在张汉中的倡导下,张汉山率先支持,教会所有的教友纷纷解囊,修建了这座基督堂。
基督堂也是一次次被毁得面目全非。2013年,古建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时,从地底挖出一块大约8厘米厚的石门头,上面刻着一个“真”字,以及“救主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字样。相关人员由此推断,该基督教堂建成于1923年,即民国12年。
到今天,已经整整93年了。
当时,就是因为挖出的一个“真”字,结合张汉中、张汉山给孩子们讲过的往事,推断出基督堂曾经的名字为“真耶稣教会”。现在的张家主人回忆,基督堂当时顶部有塔尖、十字架,还挂着一口用粗麻绳拴着的大钟。
随着麻绳摆动,悠长洪亮的钟声便会在万寿宫的上空响起。基督徒们捧着一颗虔诚的心,在他们敬仰的神面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面对着神圣的主,他们一个个许下心愿:按照主的旨意,爱人,如己。
这一片圣洁的场所,却未能让他们的心灵继续净化下去。突然一天,太阳照常升起,钟声却戛然而止。
基督堂,与别的建筑一样,任凭杂乱与战争肆意侵袭。
解放后,基督堂被派作它用。堂内上下两层均被分隔成若干个房间,分给没房子的人居住。张云峰说大概有6、7户,即便后来有些人搬出来,房间也很快被租出去。
做了住宅的基督堂,在住户心中也失了神的意味。他们每天进进出出,或许都懒得抬头看一眼这座建筑不同于普通住宅的高贵。于他们而言,每一间属于自己的只是一个勉强可以栖身的小格子。小格子成了自己生活的房子,他们对小格子也有了修改的权力。于是,东改一下,西造一点,基督堂的神性,一点点消磨在锅碗瓢盆的烟火里。张家后人叹息,不仅记忆中庄严静谧、美观大气的教堂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曾经基督堂内黄色的长板凳,虔诚的基督徒,悠扬的圣乐声,也都成了遥不可及的记忆。用张汉中的孙子张长胜的话说就是“该有的没了,不该有的却有了”。
居民们这一住,就跨了世纪。直到2012年,政府作出修缮基督堂的决定时,住户们才完全搬离。今天,古建筑施工队尽了最大的努力,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真耶稣教会”进行了精心修复,许多外墙砖依旧是当时建造教堂时所用的古砖。
曾经,基督堂内做礼拜及讲经布道的场所,已努力一一还原。然而失去了职能的基督堂,没有了教徒与神职人员的基督堂,也像一个寂寞且被冷落的孩子一样,只能无助地、不知所措地在喧嚣中静立。
祈愿,不久的将来,能听到圣洁而悠扬的乐声,在万寿宫上空再次响起。
“灯油将尽火更红”的侯家巷
元代的时候,侯家巷只是太原东面的一处郊区。这里生活着一群以种植瓜菜为生的农户,他们生活在城外,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这些瓜菜农中,以侯氏宗族人口最多、财力最大,居住也最集中,因此,便以侯氏之姓做了这个居住点的名称,叫做侯家巷子。
那时候的太原城,是一座伤痕累累的老城。太原宋城自创建后,饱经战乱。北宋末年,抗击女真人南侵的250天保卫战,几乎使太原城变为废墟。城陷落之时,已是城摧屋圮,满目疮痍。而金末元初的太原攻防战,再一次重创了这座古城。到了明洪武初,被逐出长城的元朝残余势力,时刻图谋南下。作为神京右臂的山西,必须加强军事防御力量,于是山西的中枢——太原府便被列为国家九边重镇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命令永平侯、晋王朱的岳父谢成扩建太原城。洪武九年(1376年),谢成在太原宋城的基础上,向北、南、东三面扩展,建成周长12公里,城高11米余,池深9米多,土砌砖包的新城,设八个城门,门楼12座,周围建小楼92座,敌台32座等防御设施。城周转又建了南关城、北关堡、新堡以拱卫,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起到相当大的防御作用。谢成扩建后的太原城被后人称为“明城”,被誉为“崇墉雉堞,壮丽甲天下”。明代大学者王世贞在《适晋纪行》中写下“,太原城壮丽甚,二十五睥睨作一楼,神京所不如也。”
就是这一次扩建,将太原东郊的侯家巷扩入城内。
而据传,谢成在太原时的居所遗址,也在侯家巷。只是早已经无了影踪。
明朝的时候,侯家巷内还有户部侍郎侯纶的宅第,也一度将巷名称为“侯侍郎巷”。太原人侯纶不仅勤奋好学,对《易经》有所研究,而且在做湖广副使期间,每督大项建筑,费用开支均能精打细算,不扰害百姓,口碑极好。到了清代,还是因侯家巷内居民以侯姓居多,再次改称“侯家巷”。
东西走向320米、南北14米的侯家巷,在明代却弥漫出浓烈的书香。而这些,离不开一代一代大力举办学院的那些人们。四川人陈讲在山西任按察副使时,就大力兴办学校,极大地振兴了山西的文风。明嘉靖九年,他在侯家巷西段的瓜菜地上辟建院舍,开办了“晋阳书院”,不久更名为“河汾书院”,让侯家巷随着书院的兴建而改为“书院街”。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万历帝朱翊钧登基后“诏毁天下书院”,侯家巷的“河汾书院”也未能幸免,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被废止停办。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山西巡抚魏元贞又接过重棒,托词以建“三立祠”为名,另建了实质上的“三立书院”,并迁址于右所街(今旧城街一带)。
到了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山西巡抚白如梅再次将三立书院从右所街迁回侯家巷的河汾书院旧址,并新建院舍70余间。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朝廷开始诏令各省设立书院,并拨银千两作经费。侯家巷的三立书院遂改为地方官办,一跃成为国家创办的晋省最高学府,复名“晋阳书院”。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书院进行了扩建;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又开辟空地新盖讲堂、书舍;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再建学舍及魁星楼、大照壁等,至此晋阳书院发展到鼎盛,侯家巷的书院街也成为太原市名震一时之地,大有“灯油将尽火更红”之势。
后来的山西大学堂,也得益于庚子赔款,以及一个人。
这个人是前面提过在上马街奏请设立山西农林学堂岑春煊(公元1861-1933年),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家。光绪24年,岑春煊被光绪破格提升为正两品的广东布政使,但不及三月,便因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仓惶西逃,各地官员惟求自保,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的,只有甘肃一个管文教的官员岑春煊。一天晚上,太后夜宿破庙,岑春煊提刀守护。半夜,慈禧梦见八国联军已追过黄河,要杀她的头,不禁惊叫起来。这时,岑在庙外朗声奏道:“太后毋惊,臣春煊在此护驾!”这声音就像镇静药,慈禧的心立刻安定了。一路之上,岑春煊竭诚扈从,直至到达安全之境。感慨岑春煊一路忠诚护驾,太后流着眼泪对他说:“回到北京,一定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慈禧同时向他咨询“如何雪此国耻”。岑春煊奏道,“欲雪此耻,要在自强;自强之道,首需培植人才。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广兴教育始。”
数日后,岑春煊即被任命为山西巡抚。1902 年5月8日,岑春煊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一起,利用清政府给英国的50万两庚子赔款中的部分开始创办山西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成立后的第二个现代高等教育学府。
山西大学堂是在侯家巷内的晋阳书院和令德书院基础上合并成立的,为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校舍暂时设在文瀛湖公园内;后经李提摩太多次协商,先创立的中西大学堂与山西大学堂合并办学,一部为中学专斋,一部为西学专斋。6月26日,西学专斋正式开课,至此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1903年,山西大学堂又在侯家巷购地皮200亩;1904年秋天,侯家巷新校舍落成,山西大学堂全部迁入。
山西大学堂一经创立,就具备了不凡的气势,一度被命名为国立第三大学,为中国最早设立的新型大学之一,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共同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1904年5月,山西新任巡抚张曾易选拔山西大学堂,及在太原师范学堂、太原武备学堂就读的50名优秀学生赴日本留学,吸收外界的营养与精华。
山西大学堂旧址规模宏大,布局整齐,建筑形制中西结合,是近代中西文化合璧的实物例证。然而一路走来,也历经变迁。1937年11月8日,随着太原沦陷,阎锡山下令解散大学堂。抗战期间又先后迁校晋南临汾、陕西三原、秋林虎啸沟、吉县克难坡四新沟、北平等地;1949年返回太原;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山西大学建制撤销,分别独立出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1958年,在山西大学堂旧址成立太原师专,“文革”时期废弃,后改为市委招待所,1978年恢复太原师专;1996山西省教育厅、太原市政府投资近600万元,对当时已成为危楼的大楼进行了抗震加固与全面维修,1998年竣工;2000年太原师范学院成立;2011年太原师范学院设立了山西大学堂管理委员会,负责山西大学堂旧址的文物申报与日常管理。
那天经过时,恰逢一群学子捧着书本出入。那青春的容颜与笑声,依稀晋阳书院当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欣慰的是,尽管历经种种磨难与变迁,山西大学堂继续坚守在侯家巷这条书院街上,延续着“灯油将尽火更红”之势。
注: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以及《迎泽区老街老巷老景观》
(责任编辑高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