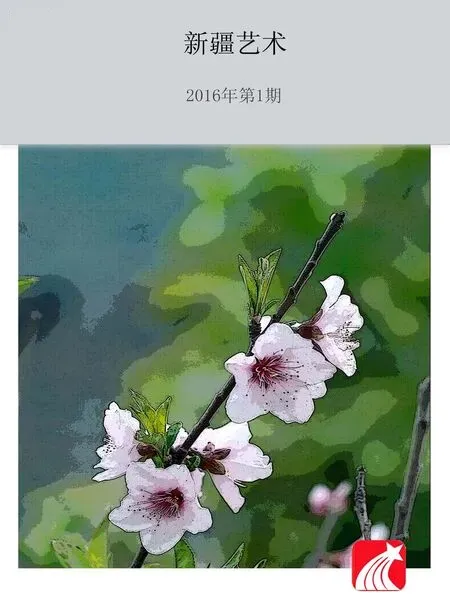留给时间的编创
——由王玫新疆班毕业演出引发的思考
□ 戴虎
很久以来,关于王玫一直想说些什么,可总是遥不能叙,用舞评家江东先生的话说:“相对于王玫艺术思想的光辉,文字是卑微的。”这肯定不是粉丝疯狂的褒奖,而是对中国舞蹈创作长久以来最为深刻的理性期待。

排练中的王玫新疆班
一
人类艺术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每一次艺术思潮、审美趋势、历史事件的发生,无不是以一些桀骜孤绝,不为当时社会所理解接受的另类艺术家的担当助推为标识。白居易、骆宾王、陶渊明是这样,贝多芬、梵高、蒙克、哥白尼是这样,就连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人类每一次的思想艺术高峰的到来,恰恰都伴随这样的“异例”,挑战着人们习以为常、习而不察、习而不觉的“规矩”,从而催生出崭新的反思性审美新知。
王玫的特立独行,是中国舞蹈圈内的共识,其传奇般的学舞经历、传说似的创作历程,也一直为舞蹈圈内人士不断言说。经历的磨砺、个性的倔强、行事的单纯、思想的自由,促合成王玫极为“偏执”“霸道”的舞蹈艺术直觉。
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总是能够把理性放置到自然感性漩涡的周围,在那里建立起艺术的时代精神,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创造历史而发现世界。王玫个人显然没有故意追求这分“孤独”,更没有想着带领来自新疆的这25个孩子去创造什么历史。用她的话说:“我没有想创造什么,更没有想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只是单纯地做件事,自己喜欢的事。”可恰恰是这分单纯,造就了王玫和她的2011新疆班在2014岁末为大家呈现的《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后简称为《现代编创》)这样一个极具文化表意、身体力量和情感张力的巨作。
一定意义上王玫在中国舞蹈界是“孤独”的,这种“孤独”的姿态不仅仅是其对舞蹈艺术创作的深入理解与表达,更是其舞蹈艺术旨趣所具有的文化浓度、意味深度以及因其无限表意动作、调度所传达出的思想深度。当然,现实中的王玫并没有因这分“孤独”而有高处不胜寒的体味,因为在她看来自己从来就没有在高处,她挂在嘴边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就是北京舞蹈学院里一个普通教员。”也正是这分普通的自觉,让王玫拥有了一个“躲进小楼”、“达济天下”而“悠然见南山”的自在。
中国传统文人中有一个“向内求道”的说法。四年前王玫亲自参与这个新疆班的招生,25个来自新疆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相整一训练水平的孩子应招被命名为“王玫的新疆班”。也就从那一时间开始,王玫面对这25个孩子心中有了十分清醒的艺术追求。四年后,王玫以几近“疯狂”、“变态”的训练和磨制,使这些青涩的孩子们脱胎换骨,呈现出《现代编创》中令人赞叹的舞台表现能力,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艺术锻造,这显然是王玫执意的用心锤炼,更是其内心对舞蹈艺术追求的外化,非“变态”的训练和坚持不能及也。也正是这种几近疯狂的偏执,王玫才以心之追求引领孩子们迈向舞蹈的自由王国。当然孩子们未必现在都领悟到了王玫这分有关舞蹈艺术理解的真谛,但显然这种“向内求道”的修炼,使得其“孤独”的姿态有了十分惊艳的生长态势,王玫也自然十分惬意而不觉然地在“孤独”中笑而不争春。
二
“传统——融合——现代——世界”,王玫以如此逻辑结构起新疆班四年学习汇报演出。这个看似些许牵强的四大板块更像是王玫新疆班四年一路走来的脚步。
四年前初见王玫这个新疆班的孩子时,这群尚未开窍的孩子们所承载的是模式化的舞蹈信息,对于舞蹈的体认与理解即是我们最一般意义上认识的教学组合和被“规训”的动作语汇,对为什么舞、舞什么、如何舞这样的艺术追问脑海中是空白的。随着王玫“变态”般的狂轰滥炸,孩子们原在的舞蹈体认与理解开始瓦解乃至支离破碎,很长一段时间这群孩子们彻底不知道该怎么跳舞,为此哭过和郁闷伤心是每一个学生的N次。而这恰恰是王玫所期待的,所谓“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当顽固的、潜在的对传统舞蹈的体认与理解崩塌瓦解,“重建”身体表达便自然成为了关键词,于是“融合”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主题便出现了。
王玫所谓的“融合”,其实是一种活在当下的身体语言创造。当孩子们在舞台上手持水盆踏着维吾尔族典型步伐、不断出现维吾尔族典型的手腕语汇,在现代配器下《青春小鸟》的节奏旋律中自在表演时,有关融合其实成为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指涉,在这极具意味的动作形式中,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对“现实存在”的身体思考和形式表达,是对人性本质的一种从动作而来的关怀与言说。用王玫学生的话讲:“王老师通过这样的意味形式就是要告诉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族别的人,人和人都要相爱。”这句话可看做王玫四年来对这个新疆班最为深刻的艺术修炼内核,而这一具有浓厚理想色彩和现实需求的艺术追求,在《现代编创》中化作孩子们专注无二的投入,融进孩子表演中始终张望、询问、期待的眼神中,与之共鸣的是,观众也始终思考着他们在张望什么、询问什么、又在期待什么?

新疆班学生排练片段
当普通的水盆划过舞台,当被水盆掩埋身体之后表演者突然爆发,以及因此而来的争执、对立甚至愤怒的对抗,我们不得不再次佩服王玫的深刻,极具叙事表意的动作、调度以及单、双、三、群舞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力量对比、情感张力的表现都不得不令人思考,这是因生活习惯不同的冲突?是文化身份之间的冲突?还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抑或这就是“融合”本身所必然出现的冲突?
无论是哪一种想法,我想肯定是这个有意味形式的使然,也是《现代编创》之“融合”的理性思考。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新疆而来的观者,面对这分“冲突”,我却感动地领悟到一种来自深层的“和谐”,一个有关对立统一的多样协和。
无论你在天山南北的何处、无论你在沙漠绿洲的哪端、无论你在河谷高原的何地,我们《共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冲突的必然是宁静眼神中对未来的期许。从这个角度我说王玫是现实而政治的,可王玫却笑道:“我是一个最不愿意涉及政治的人,可现在却做了一件那么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或许恰恰是这分现实,《现代编创》以“融合”命名,又以“冲突”走向“共饮一江水”的未来,有了更为踏实的现实反思和人文关怀。
三
重建之后的身体语言,必然要转向内心的表达,不仅仅是对传统还应该是面向现时、未来的世界表达。于是,三年级的孩子们开始不断发现自我身体语言,以“现代性”重新解构这些已被支离破碎的记忆,从而以新密码“密电码”自己的生活。于是“陌生化”成为这一板块的关键词,“陌生化”这个源自欧洲的文学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对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从而造成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而始终让观众在距离、新奇中保持思考。”
假如我们把前两个板块中的传统、融合视为编者对传统舞蹈的解构,那么在现代表意的第三板块中,就是编者以“现代”向“传统”的“陌生化”回归。只是王玫和他孩子们的这种“陌生化”回归,是以节奏破立、动作抽象、重力改变、方位调度、空间界定等解析手段实现的。纵观中国舞蹈艺术发展之脉络,每一个为时代所记录的经典作品大致都有两个基本维度,其一动作,其二动律。《孔雀舞》去了身后的大鹏、长了手部的表达,《摘葡萄》打破了手不过眉、目不能直视的旧俗,《酥油飘香》直起了藏家姑娘的腰板、在逆时针的大圆中高歌起舞。从这个层面来说,王玫所谓的“动作解析”和“抽象表意”恰恰是对“经典”奥妙的当下解读。
恐怕有人会说,我枚举的三个作品都是民间舞,而王玫做的是现代舞,对于这样的诘问,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轴线中,就会明白今人的民间舞岂非前人的现代舞?今人创造的现代舞难说不是明天的民间舞。当然有关民间舞创作的“魂、根”之说由来已久,而将其置于当下的现代文化语境中,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不需过分纠结之话题。民族文化的“根”与“魂”,是服饰的色彩、是建筑的曲线、是绘画的线条、是音乐的旋律、是舞蹈的动作……“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器有千变万化而大道唯一,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却常常让我们迷惑不解。
如此,我们再看《现代编创》之现代表意的板块,从维吾尔族舞蹈传统动作姿态因重力方向的不同,演化出令人全新的视觉动效,从对维吾尔族典型舞蹈语汇手腕表演空间的界定,而幻化出无限意象,打破维吾尔族脚下、膝部关节的节奏,却在呼吸中揉入熟悉的律动,在盘绕的手臂中表征旋律,“传统”与“现代”一个看似严肃的命题,在这里被完全消解。传统所谓的“根”与“魂”,在两个小姑娘一度空间始终缠绕的手臂中,在舞台后区四人横向的各种空间、方位的动作、时间对应中,被编者十分巧妙地以重力改变、延长、限定、变形、重复等诸种“陌生化”动作解析手段,抽象表意在这些极具叙事意味的动作隐喻中。
我们仿佛可以从这些动作隐喻里,获得潜在的对传统舞蹈的认识,但又清晰地觉然这已不是“那一类”民间舞,而是“这一个”我们“自己”的舞。这些刻意的隐喻,恰是《现代编创》“陌生化”回归“传统”的光标,在仿佛的认知中看到清晰的“传统自己”,又在熟悉的陌生中看到“现时世界”。
在节目单该板块的介绍里,编者写道:“抽象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舞蹈既能够表达维吾尔族的个性文化和传统文化,也能够表达人类的共性文化和当今文化。”一个有趣地例证是,现场我的一位法学专业背景的哥们,之前从未看过所谓的“现代舞”甚至连舞蹈的认识也基本上限于“大歌舞”,但在观看《现代编创》之后,对于两个小姑娘始终缠绕的手臂,感触良多,他问我:“是两条蛇、两根草、还是火焰”?我称赞他有舞蹈艺术的慧根,因为好奇恰恰是编者的期望,也因为这分好奇,编者的初衷——由“自己之舞”表达“普适意象”的艺术诉求得以最为恰当的彰显。
于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以“现代表意”为名的第三板块了,编者以打破传统节奏、化解传统动作为路径,通过空间界定、重力改变、时间落差等限制、变形、重复手段,抽象出一个个极具意味的具象形式,从而完成了对传统陌生化的回归和对“一己之舞”的意义超越。
四
四段“世界性表意的维吾尔族舞蹈”,在介绍中编者高频使用了“密电码”之词,试图深度解说该段的编创动因,然而其第一句话就一言蔽之:“以独特的舞蹈形式而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说的更彻底点,就是试图让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性的舞蹈具有世界性。早些年,有一句话说的很响亮:“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面对今天的世界,此话仅仅只说到了一个层面,是民族的同时是现代的,才可能是世界的。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如何现代化的讨论,是近些年涉及国家民生和发展大局的大事。而针对新疆文化现代化的讨论,更可谓深入而广阔,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不同族群的内部、外部,都越发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世界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社会和心灵问题,这远比经济现代化跨越发展要艰难复杂得多。王蒙先生曾说:“新疆人一定要乘上现代化这趟快车,不管现代化会带来什么陌生的东西,不管现代化使我们产生哪些不安,拒绝现代化我们就被世界边缘化了,被国家边缘化了,拒绝现代化我们就永远贫穷落后愚昧下去,就是自绝于地球、自绝于时代、自绝于未来。”(《新疆经济报》2014年9月12日,总第126期第一版)
就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新疆第四届舞蹈大赛,我写过这样一段评论:“过于沉浸在对所谓传统舞蹈题材的再现上,而对现实生活的疏离和对未来人心生活的漠视,造成了当下新疆舞蹈艺术品格不高和对现实社会人文启示的疲软。”从这个认识再来看《现代编创》之世界性表意,恰恰是最鲜活的个案。
我们暂不讨论《现代编创》之于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新疆有何具体意义与价值,也不去讨论其对新疆舞蹈艺术发展的可能意义。我们仅仅反思一下编创者有关“区域舞蹈世界性表意”的艺术诉求实现路径,便能获得实践价值的新知。
该板块中,道具椅子的使用耐人寻味,编创者王玫解释道:“为什么使用椅子,我也不知道,反正做出来了,把我吓一跳。”有关创作的解释,王玫的“不知道”,在林怀民、沈伟那里都有着相似的回答。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在中国大陆说现代舞必讲王玫,而讲王玫必提林怀民、沈伟,无论提及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动机,我想必是认为此三人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中国现代舞的世界面相。

新疆班学生排练片段
而究竟什么是中国现代舞的世界面相,什么是区域舞蹈的世界表意,答案定然不是唯一。在《现代编创》之中,所谓的世界性被王玫以20世纪初欧洲印象派音乐代表拉威尔的《波莱罗》作为听觉标识,以抽象化了的维吾尔族传统语言符号作为视觉载体,但如何将这样源自不同区域的听、视觉艺术密码表征世界意象,创作者充分调动起舞蹈身体语言的审美“普适性”,利用椅子将舞台的空间叠加、丰富,令舞者与椅子在舞台不断变化的空间、方位、时间中创作出一系列极具叙事意味的动作形式,从而实现“普适性”的审美意象。
舞台中区椅子之上舞者不断重复的维吾尔族典型动作手型,深刻表明着身体语言的文化属性,但舞者张望的眼神,不断站立、趴下的姿态,或高举、或垂下的双手,以及不断变化方位、空间调度的人与椅、人与人、人与空间的关系,让一个“前在的”“限定的”传统之舞,超越了族群、超越了地域,使一个已被模式化认定的区域风情舞蹈形式,具有了人文意义上的深邃。而更为深刻的是,这种超越和人文意义的深邃,又被创作者编织进以动作隐喻的历史传统中。所以,现代性究竟是以反抗传统而确立自身,还是以反抗传统而实现新的回归,实在是一个“鸡与蛋”的争论。就如有人认为林怀民、沈伟是“现代舞蹈的传统性创编”,而王玫是“传统舞蹈的现代性创编”。在我看来,这样两个不同思维向度的艺术创作,其最终表达的意象实质殊途同归,都是“这一个”眼中的“此在”。
五
因为《现代编创》与新疆的关系,我想作为一个新疆文化语境中的观舞者,来谈谈有关“传统舞蹈(维吾尔族舞蹈)”的现代性编创这个话题。其实我很不想提及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就不是问题。
这在本文的第二段落中已有涉及,但单独再陈述,一是编创者有这方面的思考;另一方面社会层面尤其是疆内圈内有这样的争论。就此我想以与舞蹈关系最为紧密的音乐为例来表达我的立场。(实质上舞蹈和音乐在新疆乃至在整个中国,传统意义上都是一体的)
新疆舞蹈尤其是维吾尔族舞蹈和维吾尔族音乐一样,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进入现代艺术教育的轨道和模式,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新疆维吾尔族舞蹈和音乐都曾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风靡全国乃至世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音乐界里就有《现代编创》涉及到的王洛宾,且不管个别别有用心之人怎么认为王洛宾,《现代编创》的编者们说得好:“我们了解和熟知新疆确实得益于王洛宾的歌曲。”及至今天,世界上对新疆音乐尤其是维吾尔族音乐的理解,王洛宾恐怕依旧是一个不能绕过的巨人。在王洛宾之后还有周吉、赵思恩、刘刚、奴斯来提·瓦吉丁,还有灰狼、艾斯卡尔、赛勒班努、刀郎,还有现在十分火爆的帕尔夏提等等。
结语
王玫和她的新疆班,之于新疆文化发展的意义,之于中国舞蹈事业发展的价值,尚在进行时态,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应该肯定,这是一件应该鼓励、关注、反思的事实,王玫和她的新疆班正从一个简单的舞蹈教育个案,转向社会文化事件。其因“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为核心的一系列的科学探索和艺术实践,其意义和价值恐怕早已超出王玫的预判。其“传统——融合——现代——世界”的舞蹈创作学术思考逻辑,还有继续深入和研发的可能,但其呈现出的有关“传统与现代争鸣”的协和,或可成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新疆文化发展的未来图示?
诗人沈苇曾有一段自白:“诗人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地域性写作既是地域的,更是人性的。地域性当然重要,因为人性的一半由地域性造就,但——人性要大于地域性。”将这其中的写作换做创作、诗人换做舞蹈编创者,大致就是我想对王玫和他的新疆班最想说的话。
我还想对那25个孩子说:“我们终将学会一个人独立地思考这个世界。”而王玫就是那一颗遥挂在东方天际的“孤独”的启明星。
(本文图片由戴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