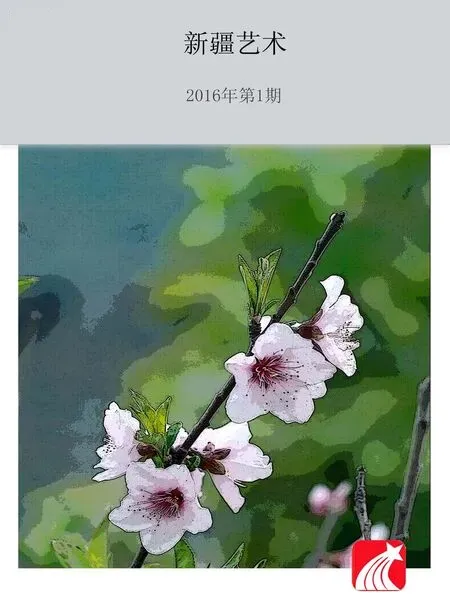纯粹的角色生存能否让我们过上好生活①
——对胡康华《粉墨》的政治生态解读
□ 户晓辉

胡康华的长篇小说《粉墨》写的是小地方小人物的小人生。作者既没有着力渲染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也没有以炫技手法描述他们后现代式的情感生活,甚至没有刻画出一个贯穿作品始终的灵魂性人物,但他以洗尽铅华的笔触呈现的那种集体沉迷于角色而又忘却人格的粉墨人生,却令我久久难以释怀,并且产生了驻足玩味的理论冲动。
作者开篇就说,“这部小说记录的是一群表演者。其实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又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②表演的舞台就在东盐池,而表演者除了知青以外主要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任意划定角色从而陆陆续续被打入另册的劳改犯和下放人员。作者叙述的各种表演,既在舞台上,也在生活中,恰恰是这种双重表演构成了小说人物的角色人生。
显然,东盐池的自然环境已足够险恶——躲在荒凉戈壁滩的地窝子里休“风假”是司空见惯;东盐池的物质生活也足够匮乏——“顿顿吃高粱米”③是家常便饭。可是,作者对自然的险恶和物质的匮乏却惜墨如金,因为外在条件再险恶也险不过人心,只有人自身才是人间恶行的真正根源,才可能使东盐池成为一座让作者“想起来就心悸的‘活狱’”。④不过,在《粉墨》中,胡康华保持了小说家应有的克制。按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⑤同样,胡康华在《粉墨》中始终站在“后台”,大有玄机地“等待着粉墨登场的人们卸妆”⑥。他作为小说家无需议论和表态,只须让人物自身出场说话,让小说中的情节或事件本身发言。这就可能使读者发现人物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意义和价值,也可能让小说发挥出超乎作家意料的认识功能。《粉墨》“不仅以原生态的写作手法写出了宁为玉等人物的命运,更把笔触深入到命运中人物的思想活动,深入开掘他们悲剧命运背后的深层心理和性格原因。”⑦只是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其实不仅在于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更在于小说呈现出来的政治生态。本文正是试图从政治生态的客观立场来进一步解读《粉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政治生态是人在特定政治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它不仅决定着人类公共生活的方式、规则和质量,而且决定着人是否过着真正属于人的生活,即人是否作为人来生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认为“人在本性上就是一种政治动物”⑧。在古希腊语中,politikòn zōon不仅意味着“过政治生活的动物”,也指“去做公民的动物、要过公共生活的动物”。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polis指的与其说是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城邦,不如说是一种应然的政治共同体或“理想国”。⑩我们过着怎样的政治生活或者具有怎样的政治生态,不仅决定着我们是怎样的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能否成“人”,能否过上好生活。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能力或政治潜能(politikē dynamis)就是人的至善⑪,这种政治能力或政治潜能是一种技能(希腊语politikē的本意就是城邦艺术或治理术),需要在城邦这种已经完备的政治共同体中加以训练和培养才能实现出来。正是从这样的视野来看,《粉墨》描述并呈现的政治生态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
一、底层小角色
《粉墨》中的“一群表演者”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本已被任意打入社会的最底层,共同被赋予了他们不得不接受的角色,他们本应相安无事、惺惺相惜。可惜这种应然只是一种可能,却没有变成现实。
小说一开始,曾任兵团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的“阶级异己分子”谢培良和儿子谢东就像被“一场疯狂咆哮的飓风”刮到了荒凉而偏僻的东盐池。他们被抛入东盐池的世界,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自己的幸福”⑫。大设计师陈从周的大弟子谢培良受到厂长金兆汉的重用,“自从他被打成右派以后,还没有人把他当人来看待,更不要说重用了”,所以除了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他“也觉得幸福突然降临”⑬;儿子谢东不仅“第一次看见有人让我爸爸喝酒,爸爸一个劲地点头,脸上的笑像是快哭了”⑭,而且“觉得自己像从地狱里出来进了天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⑮;“过去因为他长得黑,个子又矮,在师部中学老让人欺负。别人只要一笑话他黑,他就觉得低人三分”⑯,而东盐池的学生不仅不欺负他,还让他玩上了最喜欢的篮球。“东盐池似乎扫除了他内心的阴影,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惊恐”⑰。可是,谢东的幸福感是短暂的,因为东盐池“这个地方人的成分特别复杂”⑱,堪称纯粹的角色生存世界。尽管这里的人们多半都在接受劳动改造,但他们并不认为彼此拥有的角色是一样的,而是仍要分出三六九等,按照角色等级出演自己的人生,把生活变成一个高低有序、强弱分明的舞台。他们的眼里似乎只有角色,他们仅仅以角色来看人和待人。无论是否愿意接受这些角色,人们都被死死地固定在这些角色之中。角色构成人们唯一的身份。在这里,文工团的舞台与生活的舞台同形同构。不独东盐池的演员们在舞台上上演别人的人生,而且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生活当成一个粉墨登场的大舞台来上演自己的人生,都想在其中扮演有权有势的强者,谁也不想成为弱者,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自己必然会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因此,读者很快就和谢东一起发现,东盐池并非世外桃源,而是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共同组成并且共同造成的一个世界。由于被侮辱与被损害,他们被发配到东盐池,但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又在做着彼此侮辱与相互损害的事情。“演员们都化妆了,熟悉的人变个样,还真认不出来了”⑲,一心想靠舞台扮相在同学面前得意一番的彭兴国还是被昔日的老同学们认了出来,他们在台下使劲呼喊着彭兴国的外号“尿盆”,让他在台上终究难逃被羞辱和下不了台的难堪局面。在东盐池,连个人的生活习惯或生理特征(缺陷)都可能成为起污名的理由:谢东因为长得黑被同学们称为“卡翁达”或“老卡”,也有人叫他“非洲总统”,谢东的爸爸也因此被叫作“大老卡”;公社中学爱抽莫合烟的女校长被称为“大烟鬼”,学校的工宣队长被称为“秦塌鼻子”,炊事班的侯班长被叫作“猴子”,挖盐老职工田松林的外号是“田老鼠”。最典型和最悲惨的是和谢培良父子一起被遣送到东盐池的师文工团演员宁为玉。他的“女里女气”和“人来疯”不仅为他招来了“宁娘们!宁老婆子!”的外号,而且让他身心俱损、痛不欲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宁为玉受到诬陷,被民兵抓了起来。当时,“师部篮球队那个外号叫‘铁匠’的大个子两步就跨过来,当胸揪住他的衣服,一只手就把他提溜到了半空中,接着‘啪啪’两声闷响,他的整个脸就木了,舌头也像发面似的猛然膨胀起来,好像嘴里被人塞了一大团棉花”,“宁为玉像是‘铁匠’手中的篮球,被他抡起来从左手扔到右手上,像老鹰刚抓到的兔子,任凭他四肢乱蹬,几步就把他提出审讯室,扔到旁边的一间黑房子里。一个星期以后,就被遣送到东盐池来劳动改造了……”周围的人们不仅觉得好玩、解气甚至解恨,而且还由此得到了说不出的快意,谁也没有觉得“铁匠”的做法有什么异样和不妥。“到了东盐池,保卫科的人把他直接押送到新生队去了,让他和那些劳改释放犯人们在一起。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帐篷里,屋子里就像个牲口圈,出门上个厕所还有警卫端着枪跟着。”⑳好在队长看他是搞文艺的,身体单薄,就没让他打土坯,而是派他给工地拉水。“别看这是队上最轻松的活,但对他来说,简直能要他的命。别说装满水的重车了,光拉着空车从盐碱地里走到机井跟前,他简直全身都快散架了。每次拉上一车水,他要把身子伏下去,脑袋都快挨着地了,两条腿颤抖着拼命蹬,水车才能颤颤巍巍地动起来。到了下坡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松口气了,谁知道车一跑起来,他压不住车把,后面一沉下去,他整个人就被车把挑到半空中。工地上的人们看到他在半空中两腿乱蹬的样子,都只管哈哈大笑。”㉑而且,“到东盐池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是众人耍笑的对象”㉒。后来,当再次回到连队下工地时,“宁为玉的处境比过去更惨了,他成了这帮小青年任意取笑的对象。他们不能容忍他在人群里有说有笑,只要发现了,就有好几个人扑上来,伙同连队里爱开玩笑的老娘们,肆无忌惮地折腾宁为玉。做这种事,赵建勇从来不出头露面,而是指使李永强、黑旦几个不长脑子的年轻人对他进行摧残”,有一次,“把他的裤子扒下来还不罢休,有人还朝他的裆里倒凉水,撒盐粒……”㉓侮辱与损害弱者就这样变成了东盐池的“快意恩仇记”。人们似乎只有通过损人才能自保,才能显出自己的强悍,不逞强几乎就等于示弱。
在东盐池这样一个通过角色的任意分派来控制人身的社会,人们自然要向往权势。因为一个人只有接近权势才能获取人上人的角色(权势越大,就越能够任意地给别人分派角色而越少被别人分派角色),才能在一定范围内恃强凌弱和任性妄为并且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零成本或低成本),至少才可能不受别人欺负和凌辱,所以文弱的寇挥才会羡慕建勇,“我要有个哥哥就好了,啥时候都没有人敢欺负。”㉔北京知青杰子和华子虽然都被划归内部管制人员,但由于来自首都而且据说文武双全,讲哥们义气,还会唱戏,就受到东盐池年轻人的敬畏,惟独赵建勇颇为不忿地想,“那个叫杰子的北京流氓青年,居然成年青人眼中敢作敢为的英雄了”㉕。东盐池也有不少上海支边青年,但他们不敢打架,也不威风,当地青年就瞧不上他们。要想获取权势,除了凭体力,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通过特殊的门路和“关系”。因此,林志国在娶了金厂长的千金小姐金一鸿之后神气十足地说,“那没办法,他们干气,谁叫他们的爹不当官。我现在知道当官的有油水了,我要是不娶厂长的丫头当老婆,新解放能让我开,你门都没有。”㉖同样,为了进省城,漂亮的菊没有和自己喜欢的书呆子寇挥相好,而是以“调出艾丁湖那个鬼地方”为条件嫁给了并没有感情基础的师政委司机。在小说的结尾,这位已经和菊离婚多年的司机对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的寇挥说:“后来为什么你们没有发展下去,很简单,菊在骨子里是个很虚荣的女人,在那种时候,她是不会和你这样一个小盐工过日子的,我说的是实话。”㉗
在东盐池,一方面,人们向往有权有势的角色,另一方面,一旦有人得到了这样的角色,无论是否走了正道,往往都会引发人们不由自主的嫉恨情绪,甚至可能进一步引发疯狂的报复行为。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已经不大相信有正当的事情。即便是凭真本事获得的角色,也常常会招致无端的猜忌和恶意的报复。正因如此,本来要当演员的放羊女郭春玲只在宣传队呆了一个星期,就坚决要求调离。“她说宣传队的人特坏,合伙欺负她一个新来的弱小女子。还说刘组长和宁为玉去省城购买戏服,让大老王当了一个临时队长,他滥用职权,对她进行了大肆的污蔑攻击,而铁柱和几个男知青更是下流,刚开始想占她的便宜,后来知道她和大东恋爱了,嫉妒得不行,就散布了好多特别难听的流言。”㉘由于权势的得失和使用缺乏公平而又公开的规则,所以人们就只好想当然地迷信潜规则。人们一方面畏惧真正有权有势的人,另一方面又害怕弱者得势,所以在东盐池几乎人人自危却不一定能够自保。在这方面,越是人多的时候越想出风头的宁为玉是最大的受害者。“有些人嫉妒他的才华,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他”㉙;他受到陷害的主要原因就是别人的妒贤嫉能,“无论他怎么样上诉、申辩,根本没有人相信他。他没有想到,那些演员的心简直太狠了,平常大家还在一起说说笑笑,称兄道弟,可一来了运动,马上就有人揭发、造谣,明明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不但没有人出来替他说话,还都在专案组面前添油加醋。他这时候才明白,文工团那些人都在嫉妒他”㉚。在宣传队里,仅仅因为看不惯,大老王就仇视宁为玉,“只要有人一提‘宁导演’,大老王马上就变脸,不知道有什么仇。嘴里翻来覆去就两句话,一是‘把他个释放犯,狗日的咋没劳改’,二是‘那个女里女气的娘们样子,把人恶心死了’”,“一个扛搂耙拿大锹挖硝捞盐的工人,也想当导演。导演,那都是有级别的,最低都是副师级”㉛。宁为玉给女演员说戏,“大老王看得牙直痒痒,恨不得冲上去把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扔到大库房的窗外去”㉜;“宁为玉只要前脚出门,大老王就要在刘干事面前骂狗日的太骚情、太猖狂。宣传队啥都好,惟一不满意的,就是刘干事把姓宁的任命为演员组的组长,和他平起平坐。”㉝可见,在大老王的眼里,即便是舞台角色仍然要受制于生活角色的等级。这种几近疯狂的报复固然针对的是宁为玉,但又何尝不是针对那种畸形的政治生态呢?
在东盐池,似乎谁都可能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哪怕仅仅由于妒贤嫉能,就能够成为编造和散布流言蜚语、侮辱和损害别人的正当理由。侮辱和损害别人几乎变成唯一能够让人们兴奋起来甚至达到狂欢的一项娱乐活动。似乎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更没人觉得这是在做恶。
二、舞台角色与生活角色
本来,在纯粹的角色生存中被流行和被教导的是角色决定论,即恶是坏人的专利,好人与坏人的角色已经决定了人的好坏和命运的好坏。可是,在东盐池这个“从来都是搁牛鬼蛇神的地方”㉞,好像既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因为这里的多数人都是受害者,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人的加害者。比如,何艾香尽管由于父亲出身不好受到牵连,但她一直是学生干部,而且也被迫做过惩治“落后分子”的事情——有一次施校长逼她带领几个红卫兵骨干揭发一个爱说怪话的男同学,由此让他被学校开除了事。这表明,在权势的诱惑或逼迫之下,好人也可能干坏事。在某个场合下的好人,换一个场合可能又变成了不太好的人甚至成为坏人。即使弱者或受害者,心里往往也是对强者充满了畏惧和敌意,不仅同样向往权势,而且随时准备复仇,或者一旦自己处于强势也同样会欺负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这里的人们推崇和向往的勇敢“是野蛮、残忍和粗暴,是一种人对另一种人有恃无恐的欺凌和糟践”。㉟这样一来,人们都摇摆在得势便猖狂、失势便落魄的两极之间,犹如受宠若惊时的谢培良,“一会儿像个披毛散发的狮子在咆哮,一会儿又像是个可怜的小绵羊在打哆嗦。”㊱东盐池的人们以漫不经心、习以为常甚至理所当然的态度做着嘲讽他人、谩骂他人甚至加害他人的事情却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因为大家都这样,因为既用不着为此感到内疚,更不必付出多少代价。“无论他们活得多么委琐、下贱,但只要有一点能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机会,都会把歧视和不平等的病毒传播得无孔不入,并且成活率高得惊人。”㊲这些日常的举动好像够不上惩罚,也犯不着刑法,却成为人们在纯粹的角色生存中比狠斗勇的生存策略。

《粉墨》内文插图 作者 毕然
可以说,东盐池奉行的是暴力美学,除了舞台表演的短暂插曲之外,生活中经常充斥着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人与人之间的欺侮和歧视四处弥漫,甚至连道德都形同虚设,哪怕单纯的嫉妒都能演化为造谣生事和迫害他人的正当理由。老实本分的寇挥因为会拉二胡被选进了东盐池宣传队。可是,为了“不想让大家看他不顺眼”,他不愿早回宿舍,因为“自从他进了宣传队,一夜之间,就像是逃离革命队伍的叛徒,遭到了知青们一致的唾弃”,“他穿过一道道有些敌意的目光,走到屋角自己的床边坐下。”㊳“寇挥每天就是要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同学们全都睡死了,这才离开排练室,蹑手蹑脚地进屋、上床。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怎么现在连话都不说了。”㊴同样,长得漂亮、舞又跳得好的菊“觉得那帮同学看我的眼光怪怪的,我明白,班上那几个一直嫉妒我的学生干部,不知道在背后又说了我什么难听的坏话。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别看我们的中学不大,但班里面勾心斗角的破事并不少。加上我的舞蹈成功了,还不知道有人嫉恨成什么样了。”㊵由于缺乏公平而公正的明规则,所以一切规则无论正当与否都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为潜规则。人对人、对社会的游戏规则缺乏基本的信任。实际上,人们良莠不分地加以痛恨和报复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潜规则本身。
在东盐池,似乎只有角色“政治”畅通无阻——只要某人是弱者,就可能或者必然被人看不起,甚至可能或者必然受到强者堂而皇之的欺侮或理所当然的嘲笑,正如北京知青杰子“到了新疆以后,怕被人看不起,所以在各方面都争强好胜,在连队里干什么活都要争第一。可是,无论怎么表现,都没能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这一辈子是洗刷不清了”㊶;只要把某人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或“牛鬼蛇神”的角色,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以非人的眼光看待他,就可以仇视他,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手段折磨他、摧残他,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一旦有人自以为是地扮演了具有道德优势的角色,哪怕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也会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把他认为承担道德劣势角色的人踩在脚下。宁为玉的命运就是活典型。人们把荒诞剧演成人生正剧,却好像完全出于天经地义,很难有谁对此持有疑义或反思,更难有人为此做出良心的忏悔和拷问。《粉墨》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生态。
这里出现的是阿伦特所谓恶的庸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以及常人做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东盐池的人们基本上意识不到也不思考自己是否在做恶。东盐池的这些底层人物都算不上大恶人,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一些不以为意的小恶,而且“那些选择小恶的人很快就会忘记他们已选择了恶”。㊷人们随时随地可能感觉到恶,却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认真地想一想:这种恶来自哪里,谁才是真正的恶人。显然,胡康华没有像许多文革题材的作家那样把这些现象简单地归咎于特定时空、特定人群中少数人的恶,而是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反思人性恶的根源。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童年时受到的伤害……我并不想计较那些欺侮过我的童年伙伴,但我不能饶恕那种罪恶,那种把天真无邪的儿童们教导成凶手的罪恶。”㊸在《粉墨》中,胡康华只站在“后台”来描述常人和底层人物身上的恶的庸常性,却可以启发我们做深入的思考。
的确,《粉墨》中的人物既不是纯粹的恶人,也不是纯粹的善人。像北京知青华子和杰子,当年也曾是好学生,后来因为打架或以暴抗暴变成了“流氓青年”,被发配到东盐池。即便在这里,他们仍然有善良和仗义的一面。这说明,许多时候,善恶就在一念之间,而不在于角色的好坏。可惜,东盐池的人们太看重自己的角色,甚至在他们的眼里,角色联系几乎就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长此以往,人们就忘记了卸妆之后的自己,甚至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想一想:自己卸了妆以后会如何,卸妆之后还有没有自己。他们好面子甚至为了面子争强好胜,却分不清面子与人格有啥不同。正因如此,他们没有意识到:尽管他们经常为了面子而忘记人格尊严,但他们对别人面子的损害常常也损害着别人的人格尊严,他们隐隐约约地渴望拥有的恰恰是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不仅仅是面子。面子取决于外在的角色,人格尊严则取决于内在的意愿自由。人与人之间固然不得不拥有角色联系,却更需要建立人格关系。
尽管舞台角色受制于生活角色,但舞台上表演的毕竟是一种虚拟人生,也是一种可能的人生。这实际上意味着,舞台角色可以为人们摆脱生活角色提供暂时的、虚拟的可能,至少可以让人们暂时与生活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设想一种在角色联系之外获取人格关系的可能。宁为玉之所以那么喜欢演戏,恰恰因为舞台上的粉墨人生为他不堪忍受的生活角色暗示了人格关系的希望和可能。这种乌托邦式的希望和可能并非过去虚妄不实的“桃花源”,而是未来可能实现的“理想国”。
“妈的,演戏真好,平常唱歌受限制,说话要小心,穿啥样衣服,都看人眼色。只要是一上台子,想怎么唱怎么扭,真开心呵。”宁为玉感慨万千地想,不由得又拿起口红,朝嘴唇上重重地涂。㊹
也可以说,正是舞台上的这种自由生存状态为宁为玉暗示的希望和可能才几次把他从自杀的边缘上拉了回来。在生活角色中,宁为玉几乎没有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空间,连穿衣说话都受人管制。他在排戏、演戏时自己决定自己的状态,与他在生活角色中受人管制的状态形成鲜明反差。对生活角色来说,舞台角色只是一种希望和可能,但正是这种对生活角色的乌托邦式超越才给宁为玉活下去提供了勇气和理由。正因如此,他在寻死觅活的时刻才不知不觉地唱起了《白毛女》中喜儿的不屈誓言:“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我是淘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㊺
同样,东盐池的人们不仅在生活中表演,而且也观看甚至羡慕舞台上的表演。尽管这是一种双重表演,但舞台上的虚拟表演毕竟不同于生活里的实在表演,舞台角色也不同于生活角色。在这方面,胡康华已经给我们做了暗示:“无论人们怎么样装饰自己,或者扮演他人,他(或她)都无法改变与生俱来的本性。因为只有时间才是万能的真主,他早已按照你的遗传、秉赋决定了你终身的命运,他老人家才不在乎你目前是什么角色。你只可能是你自己,如果说你还有点出息的话,这一生就把自己演好。”㊻通过对舞台角色和生活角色的区分,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胡康华的真意在于表明:舞台角色实际上是对生活角色的虚化和扬弃。经过这样的虚化和扬弃,从舞台角色上卸了妆的演员可以回归生活角色,但从生活角色卸了妆的人们则不再是角色,而只能回归自己不扮演任何角色的独立人格。只有这种自己决定自己而不被外物或他人决定的独立人格才是每个人原本平等的原身份。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除了角色联系之外,还需要发生并建立人格关系。
三、法:善恶之彼岸
正因为人格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在意志上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因而也是自由的,所以它才能成为人们原身份平等关系的基础。法恰恰以这种原身份的平等关系为基础来约束每个人的任性并且保障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但是,纯粹的角色生存基本上只认角色甚至让角色决定一切,也就是让人完全受外物和他人的引导和决定,因此难以产生对独立人格的觉醒意识以及对法治的内在需求。当然,东盐池并非完全缺乏基本的善恶观念,但这里的罪与罚只是阶级斗争意义上的,而不是真正法治意义上的。谢东问黑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乱得很,不是还砸烂公、检、法吗,你知不知道啥叫公、检、法?”黑旦回答:“知道知道,砸烂公检法我知道,公安局都不管用了。”㊼东盐池早就没有法了,这里可谓无法无天,或者说长官意志就是“天”,“领导的话具有法律效 力(Führerworte haben Gesetzeskraft)”㊽,这也就意味着权力失去了有效约束和制度制衡就可能自己变成“天”。“当时的师长是延安时期的一个军械厂的厂长,有一句口头禅是‘修理修理’。看谁不顺眼了就说:‘让他到东盐池去,修理修理他。”㊾不仅如此,领导还可以任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谢东因为和连长顶嘴就被训斥道:“奶奶,你还敢犟嘴!要在部队上,我马上关你狗日的禁闭!”㊿,也许正因如此,谢东留的长头发又遭到连长的呵斥:“我命令你,马上回去把头推了,不三不四的,像个啥样子”[51];同样,“自从宁为玉被下放到东盐池来,他老婆就没有停止过为丈夫鸣冤。她成天挺着个大肚子,在文工团、师部、兵团到处上访,要求为他丈夫平反。她甚至还在师部农场找到了和她丈夫有‘奸情’的詹大胡子,让他写材料证明他们之间的清白。也许,她的苦心感动了老天,师政治部做了批示,宁为玉和詹大胡子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一来,宁为玉在东盐池的新生队劳动改造不到两个月,就调到老一连当盐工了”[52]。人的命运就这样维系于领导是否开恩或者领导道德水平是高是低这些原本靠不住的偶然性之上,真可谓命悬一线。
在砸烂公、检、法时代的东盐池,人们不仅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法,而且也普遍认为法没有什么用处。当年中国最著名的罗马法权威潘开墅沦落为东盐池中学的敲钟老头,就颇具象征意味。小说写道:
几杯酒下肚,一向沉默不语的老潘头突然滔滔不绝的说起话来:“……1926年,我潘开墅17岁,在‘中国公学’大学部读书,成绩是最好的。中国公学的校长是谁,你们知道吗?是胡适先生,胡适先生最赏识我,他亲自为我出具出国留学证明,让我到外国留学深造。1928年9月,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苦读6年,先后获得政治外交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震动了全校师生。当时,在比利时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不超过10个人呀,我为中国人的脸上争了光。1934年,我学成归国,先后在上海持志学院、东吴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当法学教授……”
“潘老师,你喝醉了,你在说胡话。”
“小于,小何,我没有喝醉,我没有说胡话。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罗马法?罗马法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被称为‘万法之源’,它是当今全部民法的鼻祖。当今世界有两大法系——在法国、德国以及中国等地实行的大陆法,以及在美国、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实行的英美法。罗马法对两法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连恩格斯都说过,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潘老师,说这些没有用,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没有用了。”

《粉墨》内文插图 作者 毕然
“不,有用,如果没有用,我就不会听周总理的话,3次拒绝蒋介石让我去台湾的邀请,我爱新中国,我想为国家出力。唔、唔……”[53]
正因为法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没有用了”,所以,在东盐池,人们不会意识到是否需要划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也缺乏个人权利和独立人格的观念。即使滥用权力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即使许多人都深受其害,大家也只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这样一来,不仅公权力可以随意“侵入私人生活领域,公共意识转化为个人意识,私人生活被刻上政治的烙印”[54],而且每个人似乎都可以随便干扰别人的生活并且随意侮辱别人的人格。确切地说,东盐池可能不乏某些社会标准,却没有真正的法律标准。但是,社会标准不同于法律标准,况且“如果法律追随社会偏见,那么社会就具有了暴政的性质。”[55]在东盐池,似乎强权就是真理,这里不顾情理,更不讲法理,所以才必然会出现政治生态上的暴政倾向。
不过,《粉墨》也暗示出东盐池人们法律观念的微妙变化。请看寇挥、华子和杰子三人在县城下馆子时的对话:
三人正吃喝着聊天,就听见窗外的大街上一阵吵闹,扭脸看出去,是两个赶毛驴车的农民在吵架,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一会儿,人群簇拥着朝马路对面涌去。杰子笑着说:“这是上哪儿说理去呢,难道还到法院里断官司不成?”
人群散开处,寇挥看见对面街道上的单位大门上,分别挂着县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的牌子。他随口问道:“这个检察院是干啥吃的。我光知道公安局是抓人的,法院是判刑的。”
杰子惊奇地看了他一眼,问道:“哎呀兄弟,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吗?”
寇挥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单位。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老听说砸烂公检法,原来就有检察院呀。它不能抓人,也不能判刑,要它有啥用?”
杰子说:“平日里我把你当成秀才,今天我可要给你讲一课了。你说的没错,公安局是抓人的,法院是判刑的。但是,公安局要掌握犯人的证据才能抓人。这个检察院要干的,就是调查案件,掌握了犯罪证据以后,发出拘捕票,公安局接到拘捕票以后,才能抓人。”
寇挥听得胡涂,说:“呜哟,还要这么麻烦,我们东盐池那么多劳改犯,没听说谁还要检察院来出什么证据,发什么拘捕票。”
杰子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东西确实都没有了。过去可复杂了,检察院收到审查案件的材料,要在3天以内,法院还要通知犯人,犯人还有权委托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呢。”
寇挥轻蔑地说:“哼,犯人犯法了,还让律师给他辩护,便宜坏家伙了。”说完他又问,“我在电影上也看到过律师为好人辩护,施洋大律师就是给工人辩护的。”
杰子和华子对视了一下,像是对他的无知无可奈何。杰子摇头笑了笑说:“过去的法律的确很复杂,给你一下说不清楚。”
寇挥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玩艺只有外国才会有。我们这儿哪里用得上这个。看谁不顺眼了,抓起来收拾,这有什么不好呢?”
杰子见他还不明白,又用筷子蘸着酒,在饭桌上写上公、检、法3个字,圈圈点点地重新讲它们之间的分工和律师制度,还打了不少比方。可寇挥越听越糊涂,一脸的茫然。华子劝道:“算了,别讲这些了,的确像小寇子说的,现在这些个玩艺早没用了,菜都凉了,咱们还是喝酒吧。”[56]
寇挥说出了东盐池人不约而同的看法,即法律只是用来惩治坏人的,普通老百姓只要不犯法,就与法律没有多少关系。在他们眼里,法律无非是刑法,舍此无他。因此,他们才会认为,一方面,犯人犯了法是不需要辩护的,要是“犯人还有权委托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岂不“便宜坏家伙了”;另一方面,“看谁不顺眼了,抓起来收拾,这有什么不好呢?”因为这在东盐池已经成了稀松平常和理所当然的事情,出证据和发拘捕票不仅闻所未闻,也没有必要“这么麻烦”。这里没人会想到,今天我们可以对“犯人”是否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不闻不问,明天万一自己沦为阶下囚又该当如何。这里更没人听说过,只有用程序权利(procedural right)才能确保实体权利(substantive right)的现代法治观念。但是,老潘头的角色由敲钟老头变成学校的英语老师,恰恰象征着法律在东盐池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当初,“在师部关押期间,宁为玉仍然不甘心就这么被人陷害,把专案组让他写交代材料的纸,全都写成上诉申辩材料。可那些材料交到专案组手里就如同石沉大海,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57]在小说临近结尾时,铁柱告诉寇挥:“华子在东盐池打官司的事,你知不知道?这都不知道,真是个书呆子。你走了以后快一年了,华子把林志国给告下了。地区在东盐池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审判法庭。杰子还帮华子请律师,你知道这个大律师的老师是谁,就是以前在学校敲钟的老潘头。原来这老家伙是美国留学的,平时窝窝囊囊话都说不清楚,一说法律滔滔不绝,一套一套的,谁也辨不过他。东盐池第一次审判人,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大家都觉得志国太冤枉了,又没把人打坏,判了8年徒刑。气得志国在法庭上大骂华子和老潘头,马上就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58]“大家”站在社会标准的立场上认为,杰子偷窥志国和金一鸿的家庭生活本来就不对,虽然志国用自制猎枪打了杰子,但志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且“又没把人打坏”却被“判了8年徒刑”,所以“大家都觉得志国太冤枉了”。可是,法律标准的确不同于大家普遍认可的社会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标准常常是人们依据角色联系做出的主观判断,具有很大的弹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它依据的主要是经验判断和情感“逻辑”,而法律标准恰恰是超越角色联系和社会标准的一种客观尺度,它依据的是可普遍化的理性思维和法律推论。法律标准以充分的说理性和程序正义为手段,以实质正义为目标,以减少社会不公。
四、角色生存
无论如何,东盐池开始有法了。有法就开始有“天”,有“天”的日子就有了盼头。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好社会不能只有道德而没有法治,也不能只有角色联系而没有超越角色联系的人格关系。换言之,好的政治生态不能只是按照角色的相对等级排序,还必须拥有依据平等人格和公平正义的普遍原则来运行的秩序。
东盐池的人们被抛在生活的舞台上,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不得不粉墨登场。于是,粉墨舞台好像顺理成章而又习惯成自然地变成了他们的粉墨人生。长此以往,他们就对这种纯粹的角色生存流连忘返,即便有时感到厌恶甚至恐惧,也常常忘记了自己还有卸妆之后的人格,他们在这种角色中沉沦,他们活着,却难以明白怎样活得更好;他们欣赏舞台角色,却很少意识到舞台角色实际上已经在暗示他们可以暂时摆脱并扬弃生活角色,从而设想另一种可能的自由生存。
显然,在对这种纯粹角色生存的看似不动声色的呈现和描述中,胡康华流露出一种质疑和否定的态度。因为角色联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更不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好方式。借用马丁·布伯的术语来说,我们固然不得不在生活中扮演角色,却不能只有角色联系,因为纯粹的角色生存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我与它”(Ich-Es)的联系,它往往会使人们成为彼此利用的工具,并且把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甚至物与物的联系。在一个好社会中,尽管人们不得不拥有角色联系,但除此之外还需要发生人格关系。换言之,人们要想保持真正属于人的关系就需要超越现实中的角色联系而进入精神上的人格关系,即由“我与它”(Ich-Es)的联系进入“我与你”(Ich-Du)的关系。因为我与你是一种伦理关系,我与它不仅不是伦理关系,而且实际上并不发生“关系”。从哲学原理上来看,“关系”不是发生在角色之间,而是发生在人格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人格之间才互相“有”关系,才互相“发生”关系,而角色之间则是对象(物)之间的联系,不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总是互相的和彼此的关系,当我说“你”时,我就把我的对方肯定为人格并由此与这个人格的你进入某种关系,我自己也由此作为人格转向了另一个人格。这种情况在我与它的联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其中没有交互性。这也就意味着,人格关系是发生出来的事件,而角色联系却不用发生也会自动出现。角色联系必然有等级分殊和利害差别,而人格关系则是一种超越角色联系的平等而自由的关系。[59]更确切地说,人的角色联系需要以人格关系为基础和前提。当然,这指的是一种应然的逻辑而不是实然的心理,因为生活在纯粹的角色生存中的人们恰恰在心理上难以意识到这样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虽然我们不得不拥有角色生存,但这种角色生存仍然有纯粹和不(非)纯粹两种类型。所谓纯粹的角色生存指的是人们在主观上缺乏人格意识而在客观上又完全受制于角色联系的那种生存方式。与此相对,不(非)纯粹的角色生存指的是人们尽管不得不拥有角色联系,却又同时发生人格关系。这也主要体现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在主观上,人们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联系需要以人格关系为基础和逻辑前提;在客观上,恰恰因为有了这种觉悟,人们会在角色联系之外主动而积极地追求以人格关系为基础的法治,有意识地克服长期以来对常人政治行为能力的高估以及对人治和德治的轻信与盲从。纯粹的角色生存与不(非)纯粹的角色生存主要是一种存在论层次上的理想类型划分。本来,人与人之间除了有(不平等的)角色联系之外还需要发生或建立(平等的)人格关系,但是,纯粹的角色生存只有前一种联系而缺乏后一种关系,因而它只具备经验上相对的角色等级而缺乏绝对的独立人格和平等权利的基础,所以也就难以产生保护平等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现代法治。换言之,本文所谓纯粹的角色生存只是理论分析的一种理想类型,而不是直接指《粉墨》呈现出来的全部生活,这就意味着,纯粹的角色生存更多地是对角色联系与人格联系做出的一种质的区分而不是量的判断。因为如果仅仅从量上来看,只要是人与人相处的社会,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人格关系。即使这种人格关系并非出自人们主观上的有意而为或者在客观上受到极端的压制,它可能暂时消失,却不可能在数量上永远消失为零。正因如此,尽管东盐池的人们在主观上过着纯粹角色生存的生活,但他们的角色联系在客观上仍然出现了一些“缝隙”,也就是必然会发生一些人格关系,《粉墨》恰恰为我们呈现了这些必然的因素。例如,宁为玉与老婆的同甘共苦和相依为命已经超越了角色联系;二连女知青冯克莉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仍被划为可以改造好的地富分子,可她偏偏不顾自己的前程和领导的反对,执意嫁给不三不四的“坏分子”杰子,她考虑的已经不仅是杰子的社会身份和生活角色;“下马崖的知青寇挥和东盐池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像认识了好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一见如故,“这个华子比他年长许多,一点都没有嫌弃他。这么热情,还把他看成哥们儿”[60],这表明,彼此不明身份的两个陌生人之间恰恰因为不了解对方的角色反而可能发生超越角色联系的关系;尽管在东盐池人们被告诫说“你不能见到谁对你好一点,你就把心里话都说出来,除了你的父母,明白吗”[61],但素昧平生又同样因为出身不好而挨整的何艾香和迟媛媛却互诉衷肠、结成了朋友:
迟媛媛一把抓住何艾香的手说:“何艾香,这么多年我们家一直受欺负,被人看不起,我从来没有和人说过心里话,没想到在东盐池有了你做朋友,我要是写信给我妈,还不知道她多高兴呢。”[62]
这同样是起初不了解彼此的角色后来却因为类似的处境而突破角色隔阂的例子。另外,东盐池宣传队去巴里坤草原慰问演出时与当地牧民联欢,“这一次,所有的人仿佛忘记了过去的无聊争吵,尽情地欢笑嬉戏”[63]。这些美好的自由瞬间是角色生存中必然会出现的亮光。尽管东盐池的人们主观上缺乏清醒的觉悟和足够的认识,但从客观上来看,假如没有这种我与你的关系以及我把别人当作你来对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就不再发生真正属于人的关系,社会也就不再是人的社会。人之所以是政治动物,就因为人必需生活在彼此以人相待的群体和社会之中,需要过一种公平正当的公共生活。人的生存就包含着彼此承认对方为人并且彼此把对方当人来对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人的存在不仅是一种伦理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法的存在。因为法是对人的伦理存在的客观保障。如果每个人的“我”都以非人的态度对待他人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也不会遭到任何约束和惩罚,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活在这样一个不知还能否称为社会的“社会”里,真会像宁为玉感叹的那样,“不知道这种可怕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64]:
宁为玉每天掐着指头算日子,每算一天,就像被刀子割下来一块肉。他觉得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像一头牲口,被那些刽子手们割成碎片。他的心里每天都在悲号、流血,连死掉拉倒的心都有了。要不是家里还有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还有那个和他同甘共苦的病老婆,宁为玉真想把家里灭小咬(小咬:戈壁滩上的一种小蚊虫)的那瓶“敌敌畏”全喝下去,不再受人间这么痛苦的折磨了。[65]
其实,角色联系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只要是角色,就难免有相对的高低强弱之分。如果缺乏法治的公平尺度和客观制衡,角色之间的权势差异往往就可能被人滥用和放大甚至由此导致种种恶行。尽管《粉墨》没有为我们描述人们卸妆之后的“身份”,但已经为我们暗示了希望和方向。所谓卸妆之后的“身份”就是每个人无法卸掉或脱去的人格。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可以拥有两种生存方式,而是说,我们不能忘记:人格关系是角色联系的基础和前提,粉墨人生远非人生的全部。换言之,我们固然不得不拥有角色联系,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发生人格关系。我们每个人在卸妆之后仍然可以作为平等的人格而彼此发生关系,这是一种自由生存的关系,而纯粹的角色生存恰恰由于只有或者只允许角色联系所以才是一种不自由的人生。法恰恰是以超越角色联系的人格关系为基础来设计和运转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反过来说,为了保障人在拥有角色联系的同时仍然可以建立自由而平等的人格关系,我们也需要法治做客观保障。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恰恰表明,现代法治是建立在人格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是为了给这种平等的人格关系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保障。
在德语中,Recht既是“法”,又是“权利”,“法意味着每个个人都被他人当作一个自由存在者加以尊重和对待……人在尊重他人时,就是在尊重自己。由此可以得出,侵犯某个个人的权利,所有人的权利就都受到了侵犯。”[66]在纯粹的角色生存中,人们缺乏独立人格的意识,因而也很难意识到:尊重他人的人格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就是尊重所有人的人格;侵犯了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等于侵犯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也就等于侵犯了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他们看来,自由无非就是为所欲为,但这种“自由”无非是得势便猖狂、失势便遭殃的单调轮回以及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式的恶性循环,与真正的自由精神恰好背道而驰。真正的自由非但不是为所欲为,而且恰恰同时意味着不损害、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责任。自由的真意在于每个人的自由都以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也就意味着,我的自由中包含着他人的自由,他人的自由中也包含着我的自由,这才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真正含义。因此,权利不等于权力:纯粹的角色生存中只讲通过不同角色获取的外在权力,由此也只能设想并产生具有差序格局的等级秩序。只有引入公平的社会游戏规则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秩序做基础,才能把纯粹的角色生存变成不(非)纯粹的角色生存,也就是通过法治秩序来维护每个人平等的内在权利和独立人格并且有效地限制公权力的使用。由此看来,只有根据法治的理念建立并运行起来的不(非)纯粹的角色生存才可能产生好社会,而纯粹的角色生存往往只能产生东盐池这样的坏社会或伪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往往只是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偶然因缘聚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动物”。
其实,法和自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它们都以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为基础。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形同虚设而且保护不了弱者的自由和权利,那么它也同样保护不了强者的自由和权利,因为强者一旦失去自己的角色也随时可能沦为弱者。假如没有法治对平等人格的保护而只有纯粹角色生存的分殊和不同,谁都可能在“扮演”弱者角色时遭到暴力和强权的不公平扼制。所以,我们才不仅需要法律而且需要真正的法治。法治不仅保护弱者,而且要限制有权有势的强者。如果没有规则至上同时又以良法为至上规则的法治,一个社会就很难具备良好的政治生态,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也就难以得到公平的保障,人们的生活就会失去根本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东盐池因为“无法”所以才“无天”(暗无天日),人们看不到希望,只能像浮萍一样听凭偶然的主宰,这里的人们“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航行者,从来就不曾意识到随波逐流有什么危险……”[67]。可是,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不能总是任凭偶然性的摆布和捉弄,而是应该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有保障和有尊严的好生活。因此,《粉墨》再次印证了我的一个看法,即小说是把我们从偶然性中拯救出来的一种精神手段。小说固然无法让我们过上好生活,但至少可以启发我们:怎样才能过上好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好生活不仅是老百姓所谓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不仅是活着或者生存,而是让每个人都活得有人格的尊严,活得有自由的保障。好生活是正当的生活,是有法治作制度保障的生活,是对坏的政治生态有所觉悟、有所抵制和有所反抗的生活。丛林法则、稀里糊涂、冷眼旁观或一味忍受不应该是人的生活,更不是人的好生活。
《粉墨》的作者试图站在“后台”,为我们暗示另一种生存的可能——即卸妆之后非角色生存的可能,所谓非角色生存也是一种超越角色联系而发生人格关系的自由生存。即使作者没有明确揭示但至少已经暗示了这样一种自由生存的可能。也就是说,《粉墨》把东盐池人们的生存状态当作诸多可能中的一种呈现出来。它要告诉读者,人们看到的和实际经历的生活只是一种可能,而且并非唯一的可能,因为在这种可能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再讲一遍:存在,就是在世界中。因此,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被作为可能来理解。”[68]胡康华从“后台”看,实际上就是从可能的自由立场来看。他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东盐池底层人物的粉墨人生,是因为他掌握着这种人生可能的底牌,就像他能洗出一张照片是因为他手中握有底片一样。如果说小说的客观描述是一种写作方式上的肯定,那么,胡康华站在“后台”的写作立场则是一种写作态度上的否定。胡康华呈现了人生的正片,是因为他完全了解人生的反片,并且用反片使正片变成不可能。也就是说,胡康华呈现了东盐池人们粉墨人生的不自由,恰恰是要让读者以超级魔幻的方式想像一种“后台”生活的自由。正因如此,宁为玉才会厌恶那种本不该属于他却被别人强加给他而且让他不堪重负甚至痛不欲生的生活角色,才会对舞台角色心驰神往:
宁为玉心里说:有鬼才好,闹吧,使劲地闹。把盐池子闹垮才好,把东盐池闹个房倒屋塌才好。这么活着还不如叫鬼给拿走,省得我自己寻死觅活的,老是下不了决心。说不定我重新投胎,还是个大富大贵的人哩;说不定我们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全家人还跳出苦海,过上幸福的日子哩。[69]
其实,即使重新投胎成为大富大贵的人,宁为玉也未必就能脱离苦海。“那个时代并没有伸出上帝之手来拯救他(也没有拯救我们),而是以更加卑劣的邪恶去摧残他”。[70]宁为玉之所以喜欢舞台角色,不仅因为舞台角色可以让他以乌托邦的方式暂时扬弃生活角色,而且因为他向往的实际上是角色联系之外的人格关系或自由生存。这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从精神上离开东盐池这个鬼地方并且过上幸福的日子,人们就必须扬弃这种纯粹的角色生存,在角色联系之外建立起人格关系,或者说,必须使人格关系成为角色联系的基础。
萨特曾说,“人们描绘世界是为了一些自由的人能在它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由。因此只有好的或坏的小说。坏的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旨在奉承阿谀,献媚取宠,而好小说是一项要求,一个表示信任的行为”。[71]我想补充的是,好小说还是让不自由的人们能在它面前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从而对自由有所觉悟、有所憧憬的小说。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只有两类小说:好小说是关于人的自由的小说,同时也是自由的写作;其余的都是坏小说。显然,《粉墨》在当代中国就是这样一部好小说。它不仅让我们体验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自由信任关系,更让我们通过小说中对那个特殊时期的小人物生活的描写领会到:纯粹的角色生存无法让我们过上好生活。单凭这一点,《粉墨》就超越了绝大多数同类题材的小说,达到了发人深省的思想深度。
①本文的删节版发表于《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这里发表的是未删节版。
②胡康华《粉墨》,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1页。
③胡康华《粉墨》,第50页。
④伊吾(胡康华笔名)《一种名叫打架的游戏》,见《上路的日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⑤参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152页。
⑥胡康华《粉墨》,“前言”,第2页。
⑦张江艳《追梦的书生与毁梦的时代——翟永明〈哀书生〉和胡康华〈粉墨〉的社会历史解读》,《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⑧Aristotle,Politics,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Rackh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8-9.
⑨亚里士多德这句话的德语译文就有这样的译法:Der Mensch von Natur das auf die Polis verwiesene Lebewesen ist(Joachim Ritter,Metaphysik und Politik.Studien zu Aristoteles und Hegel,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77,S.126),意思是:人本然地是趋向于(被引向)城邦(政治生活)的动物;吴寿彭提供的选择译法也是:“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人类自然地应该是趋向于城市生活的动物”(分别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页,第130页)。
⑩正因如此,欧根·罗尔费斯把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译为 der Mensch von Natur ein staatliches Wesen ist(人在本性上就是一种国家动物)或der Mensch ein von Natur auf die staatliche Gemeinschaft angelegtes Wesen ist(人是一种本性上就存心想要国家共同体的动物/人是一种本来目的就在于国家共同体的动物),分别参见Aristoteles,Politik, Übersetzt und mit erklärenden Anmerkungen versehen von Eugen Rolfes,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1981,S.4,S.88。
⑪参见Aristotle,Politics,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Rackh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230-231。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胡康华:《粉墨》,“引子”,第1—2页、第4页、第10页、第1页、第95页、第16页、第10页、第23页、第32-33页、第34页、第72页、第177页、第112页、第162页、第221页、第299页、第225页、第174页、第32页、第66-67页、第68页、第69页、第23页。
㉟伊吾(胡康华笔名)《一种名叫打架的游戏》,见《上路的日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㊱胡康华:《粉墨》,第8页。
㊲伊吾(胡康华笔名)《我们老百姓家的孩子》,见《上路的日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㊳㊴㊵㊶胡康华:《粉墨》,第 110 页、第 111 页、第126页、第249页。
㊷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㊸伊吾(胡康华笔名)《一种名叫打架的游戏》,见《上路的日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㊹㊺ ㊻㊼胡康华:《粉墨》,第119 页、第 179 页、第 2页、第96页。
㊽ 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Penguin Books,1994,p.148.
㊾㊿[51][52][53]胡康华:《粉墨》,第 13 页、第 160 页、第255页、第70-71页、第217页。
[54]朱承:《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55]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56][57][58]胡康华:《粉墨》,第246-247页、第 33页、第33页。
[59]参见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第160—161页。
[60][61][62][63][64][65]胡康华:《粉墨》,第 55 页、第 116 页、第61页、第240页、第34页、第173页。
[66]《黑格尔全集》第10卷,张东辉、户晓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7页。
[67]胡康华:《粉墨》,第281页。
[68]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42页。
[69]胡康华:《粉墨》,第251页。
[70] 伊吾(胡康华的笔名)《老师是上海人》,见《上路的日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71]《萨特文论选》,施康强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
(本文图片由蒋建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