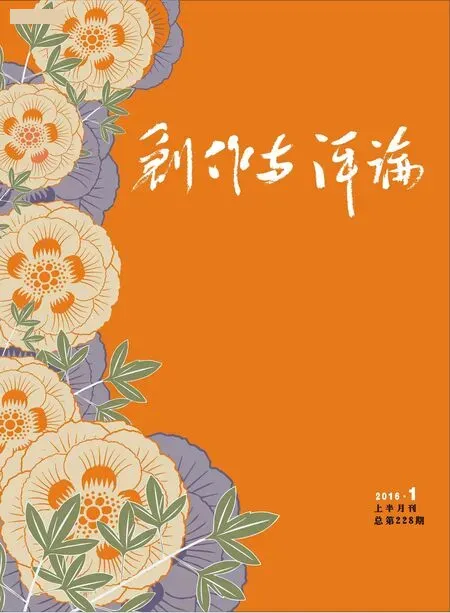在浓淡的乡愁中守望(创作谈)
○陈惠芳
在浓淡的乡愁中守望(创作谈)
○陈惠芳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与其说这是一种集体呼唤,不如说是一种集体记忆。
诗人是什么?诗人该写什么?诗人该留下什么?这样的追问,一直伴随着30余年。这样的追问,不但没有减弱,而且不断地加强。
从19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穿行到2010年代,一切都在改变,包括诗人们的审美与审丑、诗人的家园与根。在流离失所的茫然之中,诗人到底要坚守什么?
我是一个相当固执的诗人。回首诗歌创作之路,我有一个明晰的走向。从最初的“乡土”到“新乡土”,从最原始的“家园”到“新家园”,我对三湘四水始终不离不弃。我的诗歌本质孕育在这片山水之间。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创作方向不够先锋,这样的诗歌作品不够内心,但我执迷不悟。1980年代中期,我与江堤、彭国梁开启了“新乡土诗派”之门,被称为“三驾马车”。我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称谓。因为这是根植于民族与本土的诗歌流派。“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是几十年不渝的宗旨。我唯一要做的是身体力行。历时3年、至今还在创作的大型组诗《长沙诗歌地图》与已经写成的长诗《湘资沅澧组曲》就是一个证明。
坚守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荣耀。诗人的骨髓中流淌土著的血液,没有什么不好。当物欲与城市一道膨胀,乡愁慢慢地成为遥不可及的记忆时,当一个“土著级诗人”是多么珍贵。人家“黄袍加身”,我愿意披上蓑衣。
《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被认为是我早期的代表作。“在离开泥土和农夫的时候/我唯一的机会/就是顺着刀锋的一道寒光/回家去”。这样的吟哦,出现在1990年。那个时候,城市对家园的挤压、浮躁对乡愁的稀释,远远没有当下这么厉害,但我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感。作为诗人,环境与心境被迫改变。田园牧歌,将被重音乐所打击。其实,与《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一道诞生的还有《两栖人》。我更看重这首诗歌。因为“两栖人”一直是我的状态。“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我很可能腹背受敌/其要害正是/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的/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
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一直以杂音跳动到现在。诗歌的功能,诗歌责任,就是千方百计去减压、减负,以在城市这个变味、变异的“新家园”中尽可能维持纯净与天真。相当多的诗人太世故、太圆滑、太成熟了。
“三驾马车”走失了一匹。天堂里的江堤还在回味那首著名的《木瓜村阳光灿烂》。彭国梁与我是“老马识途”。诗书画中,我只有诗。“新乡土诗派”也快“三十而立”了,我还要一路同行。
振兴“新乡土诗派”的出路何在?唯有创新,唯有突破。当年,我曾提出“城市也是乡土,城市也是家园”的慨念,但实践得不多。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基于此,2012年11月,我开始了《长沙诗歌地图》的创作,默默无闻地寻访长沙的大街小巷,风雨无阻,不亚于一次“诗歌长征”。早出晚归,像一个农夫。从著名的岳麓山到无名的螃蟹岭,从棚户区到新楼盘,从河东到河西,靠脚步丈量城市的丰盈与缺失。与其说这是一次诗歌创作的寻根,不如说是一次对历史与文化的评估。300多个街巷,像300多双手拍击我的心灵。相当多的古老街巷,只剩下孤零零的名字,像稻草人。特别搞笑的是,一些本来韵味十足的古街,被改造成仿古街,而后连仿古街也一窝端。作为诗人,是失望的,甚至是绝望的。一个人,一群人还能“诗意地栖息在大地”吗?文夕大火,几乎断送了长沙的地面文明史。如今,开始“掘根”了。
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不可阻挡。但为什么城市疆域在扩张之时,精神却在萎缩呢?为什么生存空间在抬升之时,境界却在矮化呢?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但它的精气神不能变。没有历史与文化支撑,城市就是空壳。雷同等于死亡。
更多的时候,我在忧思中进行《长沙诗歌地图》的创作,力求为一座城市用诗歌立传,留下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痕迹。这样的痕迹,很多是伤痕。
当然,湖南不只有长沙。30余年,我几乎走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于是,有了对湘资沅澧的歌唱。4条河流,都是母亲河。4条河流,都是诗歌之河。4条河流,都流淌着酸甜苦辣。4条河流,都显示一往无前。《湘资沅澧组曲》将成为《湖南诗歌地图》的重要框架。
从青丝到白发,从奔跑到散步,诗歌创作的节奏在减缓。诗歌需要慢生活。急功近利,是诗歌创作之大忌。我的方向不会改变。我愿意做长沙,乃至湖南最后一名“诗歌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