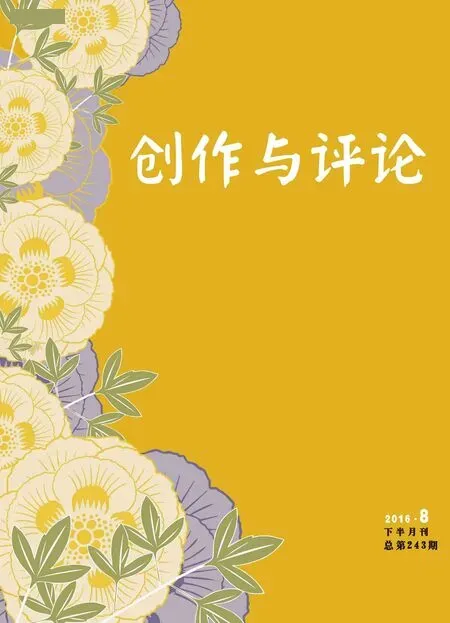『小女巫』的纯美歌唱
——论湘西诗人柴棚诗歌的抒情特质
○潘桂林 刘靖霞
『小女巫』的纯美歌唱
——论湘西诗人柴棚诗歌的抒情特质
○潘桂林刘靖霞
抒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的“根”。然而后现代解构思潮冲击甚至瓦解了诗歌的抒情性,在“个人化”转向的同时也将客观呈现推向了审美前沿。湘西女诗人柴棚却能在浪潮中专注自我,借助诗集《碎碎念》向读者呈递了独具个性的抒情诗行。她以俏皮诡秘的抒情主体、灵动活脱的抒情意象、随性跳跃的抒情结构,向读者活画了一个青春永驻的女诗人形象,并因此吸引了消费语境中浮躁而挑剔的读者。
一、俏皮诡秘的抒情主体
爱情是柴棚心仪的诗写主题。王跃文在诗集荐文中写道:“《碎碎念》是一部让人心动的爱情诗选,诗人在此倾诉爱情的私语。”①但她一反描写缠绵婉转的爱情常态,用清新跳脱的笔触表达了独特的体验和情致,令读者怦然心动。她笔下的小女巫“在你的眼皮底下上窜下跳/不断地问:漂亮还是不漂亮/你敢说不漂亮我就掐死你//我有时候躲进厨房里/用三分之二的时间研究香气/将我所有的好和一点点坏//统统捣碎/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味道/以此迷惑你/你离开半步也休想”。小女巫的动人情态跃然纸上,古灵精怪、胡搅蛮缠甚至有些狡黠霸气,有很多的“好”和一点点的“坏”,但正是这些反淑女的特质透出了骨缝里的真实和纯粹。
诗人宠爱世间万物,宠爱那用清香抚摸诗人眉梢的栀子花,宠着她的洁白、芳香和不愿收拢的裙摆,“不允许奔跑的狗嫉妒/不允许醒来的萤火虫/摘去她的洁白”(《栀子花》)。“嫉妒”和“醒来”两个词被人格化地用在了狗和萤火虫的身上,赋予了它们以人的思想,使得诗句灵动、俏皮,引发读者心灵的震颤,感召读者对自然生灵的爱心。但诗歌更加出彩的地方在于否定动词“不允许”的使用,这语气显出不可违逆的霸道,以此透出小公主的高贵和小女巫的邪气,却内在地表达了执拗到难以取代的专宠,这就是柴棚诗歌的独有情态和精神气质。她的诗语在描摹自然时显露出稚子的惊喜,在表达爱情时保留着少女的青葱,你甚至会误认为她是初恋中的少女。
然而这青葱的纯粹极富个性和力度。她博爱万物,却又情有独钟,深入骨髓。在她的《再见梅花时》一诗中,有这么一句“一株倔强的梅,只愿嫁给冬天”。这无疑是诗人柴棚(本名周玉梅)的精神表白。梅在诗中不仅有生命,还有倔强固执的脾性,只愿作冬天的新娘,严寒苦楚中的唯一,也不愿没入群芳之中博取一丝怜悯。《没有爱上你之前》这首诗中,将自己描述成“带刀的灌木丛”“有毒的蘑菇”,告诫对方“请不要爱我”,因为“我的每个毛孔/已被某人占据,没有多余的地方/供你自由呼吸”。诗歌通过表达对他人的拒绝,传递了坚贞热烈、不遗余力的专情。这种专情还体现在诗人越过流逝的光阴,恒久地守候内心,“时光就是一面镜子/只看到现在已是深秋/只照见你”;也体现在调动一切智慧经营和女巫般的霸道上,“我采集一百种有毒的花香/研制成一心一意汤,过往的恋人舔一舔/沾满草汁的红唇,永不背叛”(《女巫密码》)。她顺着女巫的传统意念走,采集“有毒的花香”,却突然反向落笔,“研制成一心一意汤”,用“永不背叛”为爱情放蛊。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伯曼语),即一切为传统肯定和坚守的爱、信仰、神性等价值观都被消解的时候,这样的女巫,这样的毒蘑菇才是世界的真人,是坚守爱情、纯粹、温暖的真人。
小女巫不仅是她诗中常用的字眼、形象,还是一种独有的语态、情境,不少诗歌渲染了一种顽皮、促狭、诡秘的情调氛围,可以说她的内心就深藏着一份女巫情结。她不仅写出了《小女巫》《女巫王国》等以女巫命名的短诗,还精心打造了《女巫密码》(组诗八首)。从小女巫的情态描述、王国设置,到编码解码,其实都在一层层铺开一个专注于爱、倾心于文字,因而具有强烈心灵关怀和灵魂追索取向的诗人的精神世界。女巫精神实则是一种温暖纯粹的爱,一种通神通灵通生命的诗性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在女巫身上得以展现,是因为俗世里有太多的戒备,人们都已经活成了文化和习惯的面具,唯有女巫,这离经叛道的存在保留着生命的质感、神秘和丰富,成为诗歌表达的独特符号。因此,以小女巫自况的柴棚,骨子里有着不可调和的叛逆。她反叛传统文化对女性情感表达须内敛克制的习见,自得地写出自己的毒性、率性,也反叛当下现实对爱情的消解和怀疑。在她洋溢着青草与栀子花香味的爱情表达里,我们能读出一个被时光遗忘的女子,一个永远的恋爱者,青涩而热烈,纯粹而痴迷。
二、唯美灵动的抒情意象
诗贵意象,以象传情。庞德认为,意象是“一种在刹那间表现出来的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既有感性体验,又有理性之光。李怡将之定位为“艺术家的生命转换为成型作品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②。总体说来,意象是构建诗歌文本、意蕴和审美风格的核心元素。李白偏爱壮丽山河,王维擅写禅趣林泉,而柴棚关注自然界中的小小“精灵”,一叶一花一小虫,在她笔下都情韵悠长。
荷花,因其亭亭净植的姿态被中国文化赋予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内涵,成为文人墨客抒怀的重要意象,产生了大量咏荷佳作。要在这传统的丛林里有所突破着实不易,柴棚却能转换思维,让抒情主体转化为青蛙,从物的角度看人看世界,将主体对象化、对象主体化,俏皮却深刻:“对于夏荷,我永远是池塘边/呆头呆脑的一只青蛙/不懂花语,不解风情/不是前世今生的你……”视角转换不仅写出了夏荷少女般的娇羞,也描摹了“我”的呆头呆脑,不解风情,进而抖出隐藏在根茎中珍爱的秘密,平静中的想念和对时光流逝的留恋。陌生的视角复活了读者熟悉的情韵和亘古的疼痛。柴棚钟爱自然万物,夏荷、栀子、桃花、紫藤、野菊、桂花、红梅等等具有梦幻色彩的花儿,以及果园、野草、秋叶和顽石等意象,都以独有的生命品性进入了诗歌,使得她的诗句灵动唯美,温暖馨香。
诗人擅借自然物来抒发自己明亮却真挚、淡然却悠长的情感,并且能够充分调动各种感官,全方位地感受事物的美好,融情入象,拓展意象的审美余韵。“落叶”是诗歌写作的常用意象,并被传统诗写定格为萧条、落寞和悲凉的象征符号,但诗人跳出窠臼,直接进入飘零的叶子,将自我生命体悟融入落叶与大地、与爱以及诗的关联。她在《我愿意这样落下来》中写道:
我愿意这样落下来/做大地薄衫上的一块补丁/走在暗下来的路途上/像一道响亮的闪电/尽管下雨时会疼,刮风时会痒//当我落下来,残缺不堪/我愿意化为泥土,躲在尘世的一角/尤其不让你看到我的狼狈/如果你能寻问到我的遗址/我已经用崭新的青草打开春天//我愿意这样落下来,留一瓣香/藏进书橱里/温婉而宁静/如果某一天,你翻阅到我所在的那个页码/我批准你流泪一次,心跳两次/我允许自己在文字的海洋里/波澜壮阔地爱你一次
这样的树叶,不论是哪一种状态,都自得自足,而这姿态源自蓬勃的生命和爱力。心甘情愿做大地的“补丁”,做照亮黑暗的“闪电”,即使只能躲在尘世一角,也无怨无悔。然而这伤痛是生命和灵魂的养分,会打开新的春天,在书页间等待与你相遇,进入一场波澜壮阔的爱。这样的树叶因自适而灵动,因隐忍却始终保留狂热的波澜而撼动人心。
对于桂花,诗人的态度是矛盾的,爱着却不敢轻易靠近,只能透过玻璃“窥视”,因为桂花“颤栗的花朵暗藏玄机”,我“害怕碰触她的香便会醉,醉成/一壶酒,浸透我内心的荒凉”。这玄机打通物我界限,桂花的寂寞和醉根植于“我内心的荒凉”。刘忠阳认为诗歌表现了人与花的交流,这是“灵魂的交流与对话”③,而我认为这是物我同构,花即“我”,“我”即花。在她的咏物诗中,诗人都化身入象,向读者展示精美画卷的同时,带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存在领悟,也是自身存在姿态的意象化书写。桂花、荷花或雪花,都因有了生命的血色灵魂的羽翼,在灵动中引发读者对生命价值、存在状态的思考。因此,灵动之美源自于内心对诗境的浸润,是灵动内心的唯美呈现。
三、随性跳跃的抒情结构
我们可以将一首诗看作一个以情感为主导、根底和命脉的生命体,由构架和肌理组成。如果说意象是肌理血肉,那么结构就是骨骼,是支撑诗歌之身的框架。结构有表层与深层之分,分别关涉意象的横向组合和意蕴的深层拓展。柴棚诗歌的灵动自然,除了视角别致之外,还体现在诗歌横向结构转换的随性跳跃上。譬如《没有爱上你之前》,开始就将自己描述为“带刀的灌木丛”,并出人意表地拈出“一只蚂蚁爬进去,半只蚂蚁/爬出来,还有半只在疗伤”,这样的转换在停顿处引发读者寻思另外半只蚂蚁的去向,惊奇和想象带来探知结局的动力,构成诗写的吸引力法则。整首诗歌从灌木丛的锋利,到蘑菇的毒性,再到面对一火车玫瑰的呆滞,推出最后的情感高潮——“每一个毛孔/已被某人占据”,情感逐步推高,直到爱得没有任何间隙。
爱情具有难以言说的魔力,恋爱者不断被甜蜜与苦涩、伤害和吸引消耗磨损。在《我的刺软下来》中,“我长出一根根的刺/保护自己、避免受伤”,果断的叙述、理性的表白都让读者坚信锋利的芒刺会跟随“我”,可顷刻之间话锋一转,远方吹来的光“照耀我,将我染得通绿通绿/我的刺软下来”,爱之光就这样毫不费力地将全副武装轻易卸下。柴棚擅于用情景突变策略来牵引读者的心。譬如《一朵虚伪的花》,开始写出了一朵花艳丽、卖弄、虚伪、逢迎,贬义词的使用为读者铺设了拒绝的心理定势,然而,“我低下头”,读者霎时愣住了,担心“我”被魅惑,而结果是,我“亲吻了旁边一颗含羞草”。这是一个相互捉迷藏的游戏,戏剧性突转带来了诗味。这转换带来了深层审美意蕴:由卖弄、虚伪、迎合转向与之产生明显对照色彩的含羞草,不仅于无声处反讽了社会人的不同生存状态,也表达了诗人的价值取向。短短八行诗歌竟然写出了一部情景剧的效果,跌宕起伏,意外频生,戛然而止却余味无穷。
意象是主体情感、意绪的具象化呈现。然而主体精神隐幽、微妙、复杂,从可感知的意识到隐秘情结,多层次多维度的心理能量必须借助隐喻性意象和弹性叙述方能显现。在《亲爱的石头》一诗中,诗人写到了白云、山神、温泉等意象,还想“再配上两只雄鹰的羽翼”,带着石头飞离尘世。白云的轻盈自在、山神的神秘诡异、温泉的和暖灵秀与雄鹰搏击苍穹的勇气,叠印在诗中,形成抒情主体“我”多维度的精神内涵。“我”可以被理解为深情的爱人、诗人自我甚至普泛意义上的诗人形象。当类似叠加或冲撞互补的意象进入一首诗,形成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体时,就构建了新的隐喻世界,带给诗歌更加开阔的解读空间。“石头”于是既指向冰冷的被爱者,也泛指麻木的俗世人。诗歌意欲使“石头”懂得眺望,爱上亲人,重拾柔软,乃至吸取光热,放出光芒,并获得爱的深度。这首诗,是物质化时代的灵魂唤醒之诗,真人重生之诗。而这些诗意根植于诗歌意象的跳跃组合产生了诗意延伸和增殖。诗集命名为《碎碎念》,是意识流动、心灵闪光的诗性传达,不少诗歌呈现出随性跳跃的结构特色。譬如,在《碎碎念》(四)中,“夜色”“碎语”“时光的花瓣”和“梅花”,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统摄在一个动词“饮”中,独自承担,独自面对,独自吞咽无言的一切,生命的寂寥和隐忍的忧伤渐渐浮现。当然,诗歌无论怎样跳跃都得遵循内在的审美逻辑,否则会令人费解。
诗歌结构除了横向勾连转换之外,还指向多层次的审美意蕴,从自身情感体验到社会生存境遇、历史承传、文化反思和禅趣哲理,等等。柴棚诗歌虽然主要以爱情为题材,但也将笔触指向家园、亲情、生命多样性领悟和时间意识、现实反思等维度。第四辑中的《窨子屋》《小镇醒了》等诗篇中植入了大量地方文化符号,也流淌着淡淡的历史沧桑。《小菊》则从一口井的深度写出一个人的命运,白菊花的纯净与节孝祠的冷酷引导读者反思文化对女性的囚禁。她的不少诗作也会触及灵魂的追问和存在偶然性的思考,《假想敌》则体现出某种意识流的特质:
我死后,看见你低下头/舔自己的悲伤,忏悔的白发和皱纹/也舔时间,空间和梦境/一夜之间刀耕火种,杂草丛生/你卸下斗志,停止浮光掠影/放下琉璃,拆开心的锁/与封闭的栅栏/释放灵魂和记忆/默默念叨我的好/你不再/唇舌相见/在鸡蛋里挑骨头/我用躲进另一个世界的缝隙/看你大笑,看夜色飞翔/泪珠带上面具,血滴弯下腰身/这辈子,你终于/在我死后输得很惨/输掉日,输掉月/输掉星光,输掉火
读者的第一感觉会锁定在冤家爱人的生死相离,这种爱情的主角往往一辈子互相对抗,只有死亡才能照见真实:对方就是自己人生的依托,甚至与之为敌就是自己活着的方式,对方的死会带走自己生存的意义。但诗意也可以由情感走向灵魂返观:灵魂不会因死而解脱,相反,会因死而看清存在的深意,看见那些荒废的时光、再也无法实现的梦、透明的隔离、锁闭的真心,以及一直压抑着的生命火焰。因此这是一首用灵魂去解剖人生并引发价值思考的诗,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苏汶指出:“一个人在梦里泄露潜意识,在诗歌里泄露隐秘的灵魂。”④《假想敌》就带有自我灵魂泄露和自我剖析的性质。
柴棚是最近几年冒出的诗歌新秀,俏皮的话语、写情的主题使其诗作被大多数人定位为小我情感书写。就境界的开阔和深邃而言,柴棚诗歌的确稍显不足,但是她具有较强的及物性写作倾向,关怀生命,也有某些篇目具有很强的哲理意味和存在追问姿态。在笔者看来,无论大诗还是小诗,都应该具有在场感和及物性,生命关怀和开阔胸襟。或许这种小角度、小角色、小趣味书写也不失为一种唤起读者共鸣的诗写方式。
注释:
①王跃文:《碎碎念》扉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版。
②李怡:《中国现代诗歌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③刘忠阳:《<碎碎念>情、诗、语的极致》,《文学界:文学风》2013年02月下旬刊。
④苏汶:《望舒草·序》,引自李怡《中国现代诗歌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系怀化学院沅水流域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南省“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怀化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佘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