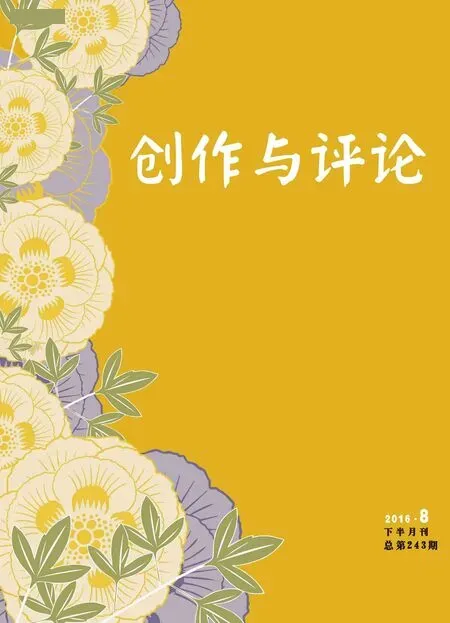贾平凹的“问题写作”
——读《极花》
○苏沙丽
贾平凹的“问题写作”
——读《极花》
○苏沙丽
贾平凹的小说往往有两副笔墨,一面是历史与现实的芜杂,人性恶、暴力纷争,杂乱破坏,一面则是传统文化的内蕴柔情,日常生活的琐细清欢,还有向上向善的人性人情美,这两副笔墨共同勾描作者对中国世相,乡土情状,人性人心的体察。《带灯》如此,《老生》如此,今年新出版的《极花》也是这样。《极花》看似故事寻常,情节简单,却在描述拐卖的境遇之下突显了诸种两难境地——主人公胡蝶被拐的经历是情、理、法的纠结冲撞,而拐卖事件的背后却隐藏着乡村更为悲凉的现实;我们看到,乡村只能以野蛮暴力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人性的丑陋自私无以言表,但是,乡土大地仍然潜藏着我们所浑然不知的文化深义与伦理情感,我们难以用好与坏、进步与落后这样的字眼做简单的评判。这些驳杂画面都让这部小说变得丰厚起来,也正因为这些驳杂,相较之此前体量庞大但旨意清晰的小说,贾平凹这一次以水墨山水画的轻逸与留白,写意的是乡土中国更为尴尬的艰难时局。
一
还记得新文学伊始,鲁迅是这样来定义乡土文学的:“骞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①他的理解不仅意在指出乡土文学是侨寓者文学,是客居异乡的人们因“乡愁”体验而回味的家乡的人事风景,而且也意味着一个普遍的视角——外来者,以外来者的身份还乡、探问。外来者代表着异域文明,不管他们是否有过置身乡村的经历经验,都受过城市文明的洗礼,彰显着异域的眼光。这也同样意味着乡村处于被看,被打量的叙事对象当中,更为具体地说,也就是处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对照观看之下,乡土书写中传统与现代的视阈由此衍生。与此同时,也生发出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像鲁迅及文学研究会那样,以启蒙批判与社会阶级分析的眼光来试图拯救与改造乡村及传统文化,尽管这其中也有启蒙者自身的彷徨犹疑,对故土的哀伤留恋。二是像沈从文这样,用边地筑梦的方式来对抗城市文明及其对人性的异化,尽管这样的梦在现实面前多有千窗百孔之感,但终归留下了最后一个乡土幻梦。这两种立场在百年乡土文学中一直存在,并相互映照,体现着不同向度的现代性的焦虑。
然而,无论何种立场,乡村一直是一个被建构,被叙事的客体,而不是可任由自我言说的主体,言说自我的欢乐与忧伤,表明自我的意志与想法,甚至是与城市平等对话,而非仰望城市或者总是处于被鄙薄抑压的位置——但很遗憾,至少从新文学发端开始,不管有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引,在城市的光照之下,大多数时候乡村就是这样一种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形象。
表面来看,《极花》也是外来者的叙述视角,胡蝶虽出身于农家,但天生有着对城市的向往,有着对美好事物的无限追求之心。她从城市被拐回乡村后,意识里最明显的对立也是乡村与城市,对于黑亮的村庄怀有着深深的来自城市的敌意与好奇。她自始自终都保持着对城市的念想,还有在城市所留下的标记印象,哪怕是她后来已经融入进了村庄的生活,比如她喜欢“高跟鞋”,“学会的东西很多很多了”②,但是,她的视角所掩藏的意识形态的意味毕竟是有限的。
因而,随着胡蝶自身思想、经历的转变,由最初的敌意、反抗,试图逃跑,鄙夷村子里的一切;再到被凌辱怀孕被迫融入;到最后的主动融入,或者说不由自主地融入,参与到家里的事务中来,叫黑亮爹,学会骑毛驴,做各种菜,为这个家精打细算地生活,用黑亮的话来说,就是学会了做圪梁村的媳妇……当她的叙事视角不断深入,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乡村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政治生态、风土人情像电影情节那样一幕幕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也正因为胡蝶城市经验的有限性,还有她本身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只是存留在简单的概念当中,在叙事这些乡村人事的时候,恰到好处地脱离了城乡巨大反差与对照的潜意识,脱离了被建构被涂抹色彩的可能性。从而,我们也有了再次认识乡土中国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看到维系村庄正常运转的,一面是乡村社会日积月累的各种禁忌风俗,比如,二月二炒五豆,谁家丢了人,或外出久久不归,就把他的鞋子吊在井里;还有像姥姥爷,黑亮爹充当了维序村庄秩序的角色,姥姥爷在胡蝶看来总有几分高深莫测,他会观星相,看古书,写一个个字数繁多的生僻字来表达原始而古朴的祝愿。他的经验里积累着太多乡风民俗,贯通天地古今。但是姥姥爷是一个沉默的角色,他不像《古炉》里的善人,给人看病时,用伦理道德来说病;也不像《老生》里的唱师,亲历时代嬗变,见过血雨腥风,他的唱词里记录着这些变或不变。黑亮爹是村里的手艺人,他会帮一家家做好女人石像立在家门口,寓意明显;村里的事务如分家之类,也仍需要他来主持。另一面,是以村长为代表的干部,这一伴随着现代基层政治出现的人物,无所谓用道德理想来树立自己的形象,也并没有实际的能力来操持村庄的发展。他能做的是帮助村里的光棍买媳妇,并作为自己的政绩之一;在种血葱时想要领头以分得更多的利润,以自己的身份权威来霸占乡村的资源,比如女人。
这其实是一个封闭,并没有自身能力也难以企望外在能力来帮助它运转跳腾的村庄,从村里的日常与经济生活就可知晓。土豆是日常主食,只不过是换着花样吃。村里少量的劳动力外出,大多数人会去挖极花卖钱,村里也有出现过一些其它经济形式,比如经营温泉,成立公司种植血葱,但都无法长久地进行下去。有限的见识,人性的自私与蛮横这些潜藏在意识里的东西也在阻止着村庄的发展。黑亮的杂货铺也是其中一种,但更像是一种自然经济状态下商品的简单交换。
这也是一个看不到出路的村庄,他们最大的焦虑来源于生理的需求,是如何延续血脉;而并非物质的穷困,对城市的向往而不得。他们居住的窑洞仍旧彰显着最为原始的隐喻,以远古文化的寓意来表达对生活丰足的愿望,其内在根基也仍然是匍匐于乡土大地,代表着农耕社会最为基本的欲求。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以“断裂”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何为断裂?“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③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组合成一个分裂的社会,如果说,以城市文明为标识的现代性是社会发展方向,那么可以说,胡蝶所在的村庄则是现代性所忽略的部分,是难以跟上社会发展节奏的部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与面对这一个更为真实,或者说也是代表着更多普遍现状的乡村现实?我想,这也是贾平凹在小说里所思索的问题。艾森斯坦特在《反思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到,现代性产生了不同的主题,但没有一个主题像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持续对抗这么重要,“一方面是现代性的文化,在特定的时空里作为霸权出现的启蒙运动的现代‘理性’模型,一方面是被阐释为折射着特定社会的更‘真实’的文化传统的其他模型。”④胡蝶被拐到的村庄其实就代表着更为真实与传统的其他模型,但在在现代性的辐射之下,尽管它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却越来越边缘化,只能苟延残存地活着。
因而,我们不能忽视与胡蝶对乡土中国的发现相辅相成的另一个视角,即黑亮的叙事。黑亮勤劳能干,有想法,敢作为,但贾平凹在他的身上规避了时代青年的特质,也从未写过他对城市的任何想象及念想——当然,他也有对现代生活及器物的向往,如电灯、电视,也想要赚更多的钱——相反,他是一个极其维护乡村的人,并为那些久远的文化蕴意真心感到自豪。他可以心存愧疚忍受胡蝶的各种反抗吵闹,惟一不能容忍的是胡蝶对村庄的诬蔑;他也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人,当他有媳妇孩子,他自以为的世界似乎很是美好,他的理想代表着乡村人最朴实也是最基本的愿望:“好男人一生最起码干三件事,一是娶媳妇生孩子,二是给老人送终,三就是箍几孔窑。”⑤他对身为乡下人的命运并没有胡蝶那么悲观,他以为在哪都是在中国,他理直气壮地将乡村的凋蔽归罪为城市的发展与掠夺——可以说,黑亮代表的是更多的如他所在的村庄向世界,向城市提出了质疑,这个质疑不仅在于将乡村的败落如何归罪,也在于乡村沿袭原古经验的发展是否有着自身的价值,他是一味地蛮荒蒙昧吗?现代性的惟一标准是否就只是参照现代城市文明?乡下人的命运转折是否就只是进城?黑亮的疑问与质疑,我想也是贾平凹的疑问与质疑。
在黑亮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乡村的自在自为,同时在现代性感召下的挣扎,无力,也看到那些走出乡村的人并没有带来好的消息,金锁进城之后,一开始杳无音讯,最后现身却被怀疑偷了自行车;立春两兄弟进城后回乡,带回的是一个在城里生活过的媳妇,但现代文明无法给予他们真正的思想冲击……这让我想起贾平凹以往的小说,除了像高子路、夏风这样的知识者能够在城里过得风生水起以外,农民在城里的生活往往并不如意。金狗如此,他最后还是回到了乡村。高兴虽然对城市充满着美好的幻想,但最后五富死了,高兴背着他的尸体还乡时,看到的是更多乡下人的结局……
城市,或者说,现代性是乡村最后的出路吗?
二
《极花》叙事到后半部分,也就是胡蝶怀孕以后,虽还有着逃跑的念头,不忘瞅准时机打听一下所在的地理位置,或者伺机打电话,想要把自己的信息传递出去,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候贾平凹更多叙述的是她如何关注与参与家里、村里的事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胡蝶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似乎没有那么地激烈,转向的是对命运的思索、诘问。比如,她在孩子面前的自言自语:“兔子,兔子。我在这村里无法说,你来投奔我,我又怎么说呀。这可能就是命运吗?咱们活该是这里的人吗?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呢?娘不是从村里到城市了吗,既然能从村到城,也就能来这里么,是吧兔子……娘是不是心太大了,才这么多痛苦?娘是个啥人呢,到了城里娘不是也穷吗?谁把娘当人了?娘现在是在圪梁村里,娘只知道这在中国。”⑥
小说是以胡蝶的梦境来结束,她梦见母亲和公安干警来解救她,如愿回到城市,却最终无法适应周遭的冷眼、误解,而又重新回到黑亮的村庄。胡蝶的悲剧里有着更为巨大的来源于中国现实的悲剧,或许她的确也能走出被拐卖的偏僻村庄,但是走不出被拐卖的事实,走不出中国的世情人情。
然而,胡蝶最深层的悲剧恐怕还是再次沦为乡下人,再无从改变命运的悲剧。她最开始或许也想着用知识来改变乡下人的命运,但是家贫,父亲早逝,只好将读书的机会留给弟弟。于是,在不用照顾弟弟的生活后,她跟随母亲在城里收废品。她是由衷地喜欢城市,喜欢用城里人的方式打扮自己,无法掩饰成为“城里人”的喜悦,尽管她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暂住者,尽管在城里她还是一个受人歧视的乡下人。但是,被拐卖一下子改变了她的人生际遇,从而彻底毁灭了她的城市梦。
她是想过自救,以各种方式抗争,逃脱,但是,她真正的出路在哪,救赎之路在哪,或者说,她以怎样的方式来达成与现实的和解,与命运来做和风细雨般的对话?现实的救赎之路当然是离开所在的村庄,逃脱被拐的命运,回到城市,可这条路被自己的梦境给否决了。最为关键的也许还是如何认识乡土及其生活。当胡蝶开始自主地融入黑亮家的生活,认识这个偏远落后的村庄,开始熟悉当地的人情风俗,人性人心,她的内心慢慢地变得平静下来,柔和起来,或许她也认识到这也是一种生活,而且是一种正当地生活,或许贫穷卑微,但也是应当存在,并有价值的。
我不愿对“蝴蝶”“极花”“血葱”的意象做过多阐释,但我常感觉,胡蝶一开始对命运的激烈抗争,像是无数乡下人想要摆脱自身身份标识与命运的努力;胡蝶对自身命运的追问,像无数乡村和乡下人对自身命运的叹问。在现代性急风电掣般的感召速度下,在中国依然严峻的城乡二元制度之下,乡村的救赎之路,也就是发展的前路又在哪里?借胡蝶的命运来探问乡村的未来,这或许才是贾平凹想要用心的地方。
小说里我们感觉到贾平凹在给乡村不断地“祛魅”,我们需要认识一个真切实在的乡土中国,正如同在胡蝶的梦境中,她回到城市里,那些城里人对乡村的认识是停留在野蛮蒙昧的想象中。正如胡蝶所一点点认识到的乡土生活的正当性——无论是那些维系乡村正常生活的禁忌礼俗,还是那些并不怎么崇高的生活愿望,那么,乡村这一社会结构及文化是否能在现代性的空间里赢得那么一席平等位置?——贾平凹是尝试着给胡蝶,给村庄提出那么一条路径。然而,现代性仍然是对乡村最大的危胁,这或许就是小说中贾平凹借黑亮之口一味地将乡村的现状归咎于城市的原因,也是作者在后记中所追问的:“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⑦
但是,贾平凹给予同样关注的,关系乡村存亡的恐怕还是来源于乡村自身的东西,或者人性本然的面目,这也是他的困惑所在,人性的恶,暴力,未曾驯服的蛮力是那么地寻常。当年沈从文同样将乡村的堕落归之于现代性的到来,同样看到的是现代性对乡村的掠夺吞噬,对人性的破坏腐蚀,那些令人不安的因素原来有着如此巨大的破坏能量,他在《长河·题记》里这样写道:“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⑧与沈从文不同的是,贾平凹并不认为人性人情美是乡村社会所独有保存的,将乡村视为惟一的净土,他更多看到是乡村的藏污纳垢,那些人性的丑恶并非来源于现代性的胁迫与影响。
近些年的作品,贾平凹都在有意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古炉》里作者将人性放置在动乱年代,看人性的自然裂变;《老生》里人性的恶与暴力也是随着情势的发展而显隐,但更多的时候人如同历史社会情境下被驯服的小动物一般,卑微地活着;《带灯》里村民的暴力也是普遍的,小小的纷争都可以让村民们揭竿而起,与此相应地,政府对村民也不过是暴力执法。《极花》里至少三处写到群氓的暴力,看客的蛮力:一是,黑亮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对胡蝶施暴;二是,黑亮与村长他们一起去买一个女孩,给园笼做媳妇;三是,訾米那来了几个女孩,却被几个村民看上,想要抢人把她们关起来做老婆。后两处虽然并没有正面地描写到暴力的现场,事情也并未按照村民事先想象的那样发生,但同样意味着一种潜在的暴力。与《古炉》《老生》里写到的人性恶一样,《极花》里一旦危及到自身的利益,昔日的温情不再,他们必也以一种残暴甚至是罪恶的方式进行对抗,或者加入到施暴的群体中来?黑亮爹在村民及儿子的眼里都是道德的模范,有不少仁义之举,对胡蝶以礼相待,疼爱有加,但是在黑亮凌辱胡蝶、胡蝶试图在挣脱自身命运的时候,他也不正是那个带着平庸恶的、施暴的看客吗?是否也可以说,暴力的背后,乡村正在以一种更为血腥残酷的方式,以一种扭曲人性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的烟火?
然而,倘若要说到救赎,要说村庄的出路,这些人性内在的丑恶与腌脏,极容易暴发出来的人性恶的救赎希望又在哪里呢?《极花》里并没有说教的善人,始终良善如一的蚕婆,也没有阅尽世事的唱师,只有迷糊古怪的麻子婶,明智内敛的姥姥爷,他们都不承担任何道德力量的指引与希望的点化,他们能够安抚浮躁的灵魂,但并不能阻止并消除那些恶的念头。倘若说乡村内部的传统资源无法给予他们向上向善的动力,无从产生一个自我更新的机能,那么又怎能指望现代文明带给他们什么呢?贾平凹对人性的追问,也如乡村的未来一样充满着迷蒙之色。我想,对于恶的关注,对乡村藏污纳垢的正视,也正是贾平凹无法再像沈从文,或者像他早期的“商州”系列那样,维系一个山清水秀充满灵气的乡土世界,将乡土视为精神的栖养之所。
三
乡土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局。于当下的乡土叙事,我想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来看待,其一是像莫言、刘震云、阎连科这样,以后现代的鬼火来点亮乡土世界,他们的文学乡土不复再有可以回味的风景风情,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乡土精神世界的神似,他们解构了乡土本身,也消解了现代文学传统上的乡土叙事。其二是像70、80后作家,乡土只是作为一种可以忽略,仅只是用来点染的背景而存在,或者只剩下一些依稀用来谈论的历史材料,他们亦不复在乡土之上建构什么,想要寻求什么。其三也就是像贾平凹这样,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路径,对乡村的日子做着扎扎实实的记录,为乡村的衰危做着真真切切的歌惋。
将视野放置在百年乡土文学中,可以说,贾平凹的乡土书写早已自成格局。他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作家,1980年代反应农村改革气象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古堡》《浮躁》,1990年代的《土门》《高老庄》,新世纪的《秦腔》《古炉》《带灯》,他的乡土书写不仅只是在聚焦乡土中国的常与变,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保持着对现状的敏锐观察,还有追问现实,对现实发问的权利——在他的探寻中,有一种乡土作家罕见的文化自觉,也就是去理解并在一个宽广的历史与社会视阈中来考察费孝通所说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尤其是在他1990年代写完《废都》之后,他整个的观察转向的是乡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式微情状及其困境,开启的是由“废都”向“废乡”的这一乡土书写模式,甚至像乡村基层政治、上访、拐卖这样的敏感话题都成为了他的写作内容,他不满足于只是描述和记录现状,回忆与书写历史,而是要去追问现象背后的陈因,是什么导致了今日的乡土裂变,是什么让人性如此狰狞?他不只一次在后记中提到过萦绕于内心的那些人和事,有着不得不说的冲动与责任,溃散的乡村,日渐消隐的历史往事。我想,在贾平凹的写作中是有着明显的为乡土作传,为乡土立言的意识,提出贾平凹的“问题写作”也就在此。
由“问题”而来的乡土写作其实并不陌生,乡土文学的肇始固然源于五四“问题小说”之后,当时的作家在给社会开据“爱与美”之类的药方时,毕竟还是觉知其中的抽象与不切实际,而只有面向更广阔的大地,熟知的乡村人事,才能真正看到社会的病症,这是一种更为深广的问题意识。再说到赵树理,他在谈到对写作主题的确认时,是这样说的:“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⑨现在我们再来面对他那个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能多有垢病,以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演绎,然而透过那层意识形态的怪圈,其实我们看到却是当时农村的真实现状。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兴起,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写乡土的实情,写作的冲动也正是因为虚构中的乡土无以再反映乡村的现实。而我们在贾平凹的作品中不仅还能找寻到“三画四彩”,还能真切地感知到这个时代乡村的遽变。
与贾平凹的“问题写作”相应地,我想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解析乡土中国现状的能力。一方面,是他出色的写实功底,而且是以虚实相间的方式进行:对风俗禁忌、面食做法等等细致描摹,对于胡蝶被关在窑洞里的感受、被黑亮凌辱时的身心疼痛、生孩子时的身体受难等,更多地则是以飞升的想象,在各样的比拟中寻找一种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他从未回避乡土中国的复杂性,不简化事实与生活,不固化人性人心的面目。由问题而来的写作,并非是像社会学家一样要给予一个清晰的答案,相反,他在呈现现象的多样性与模糊性的时候,出示的正是乡土中国的复杂性,既不回避伏贴于大地的艰辛卑微,也不无视精神世界的微末光芒;既不平面的速描一个人物形象,也不单一地呈现事件本身的面貌——我想这也是贾平凹并没有将胡蝶的经历单纯地写成一个拐卖事件的原因。从对胡蝶思想经历转变的叙述,到以她的梦境来结束,都可以看到贾平凹对中国现实及人性的深刻理解,他写出了胡蝶的反抗,也刻画了她的侧隐之心,比如,在黑亮与其他村民去做买卖女孩的交易时,尽管她内心纠结充满怨怒,但也不愿黑亮出车祸;到后来她融入黑亮的生活时,竟然也开始去察颜观色,不愿让他太难堪,灵活地调和一个家的气氛……
将《极花》放置在贾平凹个人的写作史中,我们也能看到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由《老生》开始,尽管他所要书写的历史逾越百年,但不像《秦腔》《古炉》《带灯》那样追求繁复的书写方式,体量庞大,人物众多,多条线索交织。我以为,写作《老生》时,贾平凹开始“做减法”,小说选择以四个故事对应四个时期四个村庄,来反应乡土中国近百年的变迁,其间还穿插着《山海经》的风物志,生活的气息、小人物的悲欣,扑面而来,在血腥与革命,焦虑与无望的交替中来勾勒现代性进程中乡土中国的特质。与此相仿,《极花》在简单的事件与人物中,不但不缺乏小说所具备的可感知的情节、可触摸的人物,而且小说所应看到的社会物质形貌也是如此的丰沛,更重要的是,借由胡蝶被拐卖的事件,贾平凹写出了沉重的乡土中国的世相;相较之他1990年代同样反应乡村境遇的作品,《高老庄》《土门》等等,《极花》的厚重与悲凉其实都已在字里行间。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问题与追问,我想,于当下的乡村社会,于当下的乡土文学,都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注释:
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②⑤⑥⑦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171页、第172页、第155页、第207页。
③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④[美]艾森斯坦特著,旷新年、王爱松译:《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0页。
⑧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⑨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125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